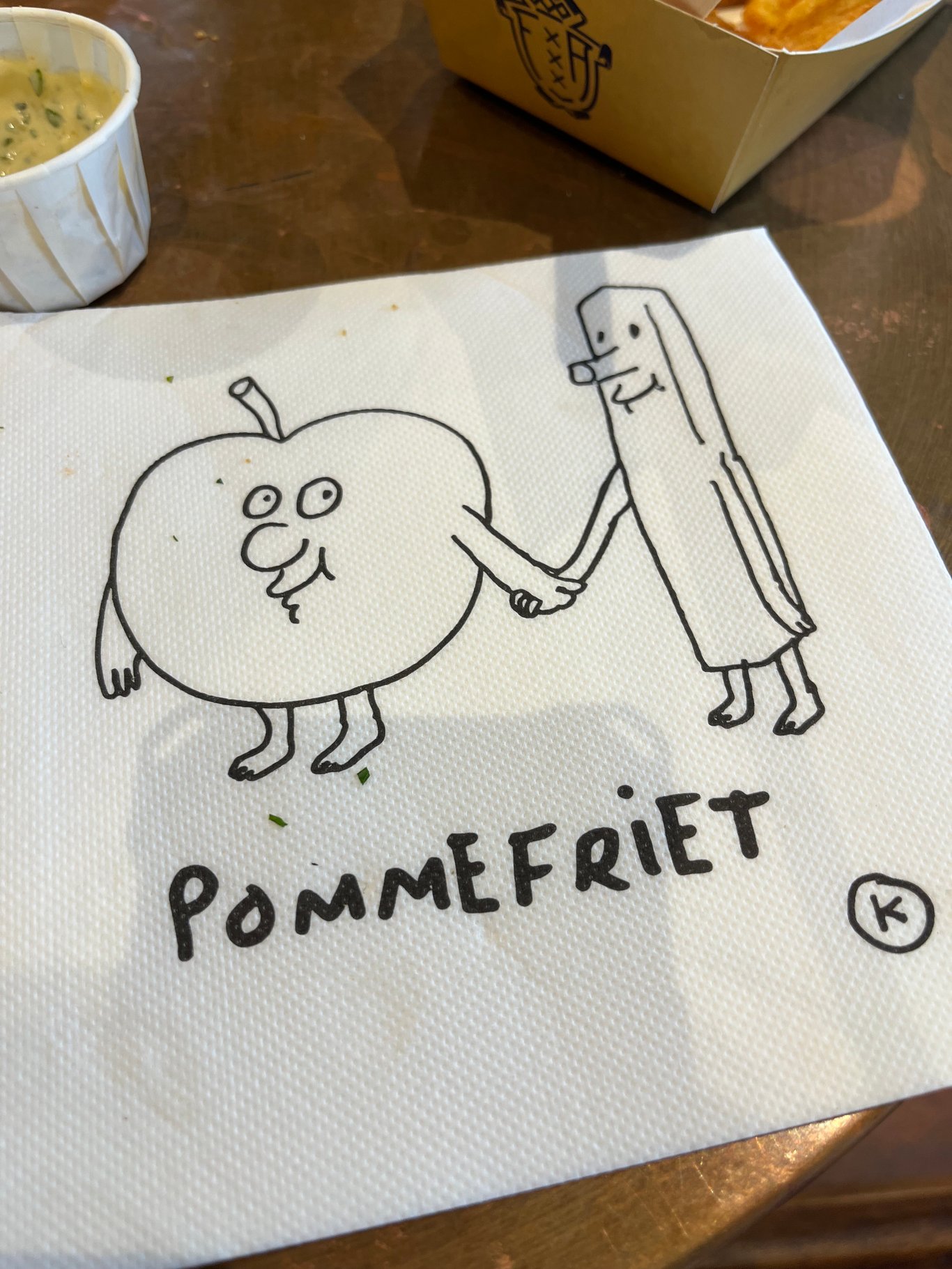七日书_2025.12|#1: 再没有哪场考试能决定我的人生
不知道是因为太幸运,没有真正被绑住手脚的感觉,还是因为太不幸,内化的牢笼太多,竟然无法回忆起任何一个在心中感到“能奔往自由”的时刻。站在25岁的下半页,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这句话写出来,我自己都怀疑是否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嫌疑。可仔细翻翻回忆里的那些分别,似乎都发生得太轻。
说到“自由”,脑海里首先记起的是2021年的春夏,大三留在校园里的最后半年。刚度过疫情的封锁,那时还不知道会有后来的事情。告别出入都需要通行证的日子,重新回到校园,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在行动上自然多了许多自由。但最自由的感觉,并不来自于物理的移动。那时通过了校际国际合作项目的选拔,大四就能出国读硕士。这个项目曾经是我疫情期间蒙在家中的那段彷徨日子里的一束光。
当时的我只知道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好工作,很多前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重回校园读了硕士,所以硕士是必须的。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做研究(虽然现在想来那是的目标也并不是要做研究),尽管绩点一直年级第一,但我写论文很慢,想出题目很慢,整理材料很慢,写出文章也很慢。我深深地怀疑,自己是被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机器,我所有的人生目标在于考出好成绩。明明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好学生”,但中考、高考,次次失利。以至于进入大学后,第一年的目标还是“能够改变人生”的插班生考试,一个上海特有的可以在大学入学后转学的机会。我说:我要去复旦。然而我大概的确没有什么考试运,文史哲三系一张考卷,最终成绩过了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分数线,可我报的志愿是中文系。再一次,我没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学生”,似乎平日的努力都是虚假。
我不甘心作那所高考分数为我选的学校的学生,于是我延续着第一年的惯性,拼命泡图书馆,哪怕通识课的绩点也不能低于3.9。于是我拿着学院第一的成绩,继续怀疑,我是个没有热爱,也不会思考的人。论文总是写得很慢,课后的自由提问时间对我来说也形同虚设,所有的问题总要课后重新梳理内容,阅读文献后才能产生,一切都呆滞的,慢慢的。闷在家中的时候,我每个安静下来的时刻都在想,活了20年,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强烈的热爱,兴趣大多浅尝辄止,不会为之废寝忘食。就像是语言,我从小感兴趣,可除了英语成绩比较好以外,并无其他建树,一直到读中文系之前,也未知晓还有“语言学”这一学科。
因此我妈常说:“你那是真的喜欢吗?”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读硕士,虽然成绩能够申请保研,可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想要出国读书,也不知道要如何申请。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如同小马过河,不熟练地翻找外网的信息,查找不同学校、学院的页面,然后止步于“宾大的语言学很厉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申请的第一步需要写出rp,然后联系意向导师。而这种无知带来的踟蹰,对爸妈来说,似乎是只要“相信自己”就能摆脱的事情。
某一天,在浏览学院网站的时候,偶然发现前一年下发的合作项目征选通知,有方向大体相合的专业,不需要自己联系导师,只要通过学院内部的选拔,最终和国内的学制相比还能提前两年毕业。我当即决定,就选它了。如果最终选择这个项目,要放弃排名第一的绩点,放弃保研资格。辅导员劝我想清楚,但我还是全身心投入了雅思的备考。通过校选后,我爸劝我:别放弃其他机会,再试试复旦、北师的夏令营吧,也许有更好的选择。但我不想选了。在那一刻,我这个上满优绩主义机油的考试机器,决定放弃那些考试可能带来的机会。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个好的研究者,但我要首先和应试的自己告别。
一整个春天和夏天,我还是呆在图书馆,不过手里拿的不再是教材,读的不再是论文。我第一次,没有查询借书系统,只是在感兴趣的楼层里流连,只读那些标题和封面吸引我的闲书。那个春夏,我读了自初中以来最多的书,也从中触摸到一缕细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