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媒體的女权之路──专访「新媒体女性」负责人李思磐
1990年代,中国政府难以负担对媒体的资助,媒体业在市场化背景下,纷纷启动市场化改革,追求经济收益之馀,媒体也开始出现专业主义的转型,不同于以往宣传角色的新兴媒体纷纷成立,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週报《南方周末》曾被美国《纽约时报》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藉由这些媒体,传达自由派思想,对于时政,也敢于批评。
2002年起,资深记者李思磐在南方报业工作十馀年,虽是在如此自由开放的环境,她仍深深感受到女权不被重视的挫折感。尔后受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启发,李思磐与一群女性媒体人成立女权传播平台「新媒体女性」(Women Awakening Network),她们倡议妇女议题,举办女记者培训工作坊、展览讲座,也投入性别议题的深度报导。
但随着2013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等事件接续发生,中国市场化媒体的舆论空间速迅萎缩,女权声音遭到严重打压,「新媒体女性」也面对压力,李思磐于2018年被迫离开这家NGO,到大学里教书;2021年5月21日,「新媒体女性」微博帐号也暂时停止更新,当时最后一篇贴文是关于朱军性骚扰案的转载内容。
身为女权运动者,同时也是调查记者的李思磐接受《田间》专访,谈中国自由派媒体的女权意识缺失,以及从2000年代以来,她对中国女权运动、女性报导的观察见解。

田间(以下简称田):过去中国媒体机构里大多是男性记者,您有曾经因此感到困扰吗?
李思磐(以下简称李):我是2007年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部门,当时部门只有两个女记者,一个在广州,另一位在别的记者站,这位广州女记者说她很开心(有新的女记者加入),说总跟一大群男人在一间充满烟雾的屋子里,觉得很难受。
我们不用坐班,那时候每週一吧,没有出差的人会一起晚餐,其实我们是很好的小集体,大家都是好朋友,从工作到生活交集很多。但作为女生还是会觉得有些边缘——在一起吃饭时,总之这是以男生为主的场子,(男生)会喝很多酒,拼酒拼到洋相百出。当然年轻一代可能都不这样了。男生与男生之间也有很多说话习惯让女生尴尬无语,比如美女、性感什麽乱七八糟的。
专业上也非常明显。在市场化报业时代,社会新闻、法治新闻是很重要的路线,比较容易给记者光环的。因为这类新闻常会接触到冤案冤狱等题目,符合中国传统对知识份子铁肩担道义、匡扶正义的想像,所以比较容易引起读者关注,做出成绩。
但是这一类题目呢,通常是男生比较容易做好。当时的舆论监督以异地监督为主,需要与地方上的干部打交道。经常有这个说法,男生(记者)跟他们喝酒,喝到彼此称兄道弟,一拍胸脯一拍肩膀或许就给出这个那个(新闻线索、关键文件材料)。我也会去跟官员周旋,但其实官场的酒局很多格调不高,性骚扰问题很多,黄段子、搂搂抱抱都有,这对女生多不方便啊,所以我宁愿事情做得没那麽好,也绝对不跟男的喝酒。
那时候的选题与今天的非常不一样,很大比例与农村有关,现在应该有9成选题都是有关城市里中产阶级。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深度部门的男记者里,有很多是非常传奇的人物,有人以前是卖水果,有人没正式读过大学,但他们很会突破、「拿料」,但是女生背景与男生就有些不同,我们周围女记者通常学历会好一些,他们本科比较多,女生研究生挺多。当初会进到《南方都市报》深度部门,就是因为深度部门负责人希望有人能做一些知识份子的、公民社会的,还有大中华区的内容,看上我港澳台新加坡都很熟,所以因此我还跑了一段时间的台湾。就像世界各地很多新闻研究观察到的,我作为女性记者,被派的题目,虽然我也做政治,但比起男性记者的硬题目,我的还是比较软一点。
田:为什麽会如此关注女性议题?
李: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大概在中学时,女权主义对我就很有吸引力,大学时,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时我有写信给他们组委会要资料,我自己的写作和学习也都(与女性)有些相关。但真的让我想做点行动,反而是这种以男性为主的新闻文化。
南方报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进步的报纸,我对它的好感来自于,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会称农民工为「外来盲流」,我觉得这是非常歧视的表达,但一到广州读到《南方都市报》,我感觉他们不把农民工当作特殊的、边缘的群体,报导里会详细描绘农民工个人,包括他是从哪里来、做什麽工作、在哪个工厂工作等等。
不过后来我发现,在性别方面的很多地方都让我不舒服,比如2005年,有一区进行性别教育,在课间操时,要求女生跳舞、男生打拳,广州几家不错的报纸都把这当成进步的东西在报导。还有北大小语种招生,有家长出来抗议,女学生录取分数要比男学生高几十分,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部门是非常进步的,天天讲政治改革,但出了一篇评论说这不是性别歧视。也是2005年的时候,《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法》修法,妇女组织花了好大力气,才在里头放进反对性骚法条,《南方都市报》评论说这是无厘头——周星驰电影里的那种无厘头。
我非常认同南方(报业)的理念,它提供记者很大的空间,我获得很多成长,也得到人生中重要的朋友。但在性别方面,真的是各种不行。其实《南方都市报》也有好几位编委是女的,可是新闻的文化是男性中心的,女性领导也对性别议题没有敏感,甚至跟很多主流机构的领导一样,女性领导虽然领导风格相对于男性更有同理心,但是专业理念上面,她们可能还要表现得跟男性无异,甚至要有意无意地撇清自己的女性身份。总之,大家觉得妇女权利不重要,认为男女平等是共产主义矫枉过正、没有成功的议程。
其实我比较喜欢当记者,但开始写评论就是因为北大小语种(招生事件)——不写出来我坐立难安——后来已经成为我写评论的时候的常态。我写了,但《南方都市报》不给我发,所以我拿到《东方早报》去发,《东方早报》编辑说我写得不错,但他也说(评论无法刊在《南方都市报》的原因):「你们那个不是自由主义,是反共。」
田:是在什麽契机下成立「新媒体女性」?
李:比较重要的关键是我和艾晓明老师认识。艾老师当时使劲想要改变(媒体的报导文化),她曾经为了《南方周末》的厌女广告,组织一个研讨会,邀请当时的总编辑任向熹来参与。但其实在报业内部,没有人会认同这套想(做)法。
后来,艾老师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邀请BBC的专家来做媒体与性别的培训,「新媒体女性」的成立是在这个培训背景下的结果。我不是唯一的发起人,我们是一个小组,由参加培训中的12位广州媒体人所组成。

其实,那次培训有一些问题,像是因为需要翻译,所以两天的工作坊没办法有太多内容。还有呢,BBC有伦理守则,在言论自由的地区,就法律层面和社会责任来说,伦理守则是必然要有的。
但如果只是伦理问题,在中国会很难推下去。中国记者特别讨厌新闻伦理,主要是因为中国是公共资讯很难公开化的地方,记者遭遇各种困难、风险,能把报导做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们(新媒体女性)在做性别主流化倡导时,不会把新闻伦理当成核心培训目标,我们用的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词,重点在于让记者有更多的性别专家和行动者作为讯息来源,帮助记者把报导写出来,而不是叫他不做这篇报导。培训他们如何用公共服务的新闻价值去做报导,如何揭示真相、促进改革,是以这样市场化媒体的逻辑来做培训。
中国的女权组织因为她们行动路径的问题,比较不熟悉市场化媒体。我意识到媒体对女权议题的疏离态度跟两边联繫太少有关系——相对于当时的人权律师和环保组织。我们也做了妇女研究和行动的通讯录,帮助研究者、行动者和记者之间互相联繫,我们把记者联繫方式做成通讯录提供给需要的机构,也把个方面的专家和机构的通讯录提供给记者。
田:「新媒体女性」组织的女权活动有什麽特别之处吗?
李:在2003年(艾晓明成立性别教育论坛)之前,广州是没有女权组织的。在世妇会之后,很多女权组织成立都是在北京,还有郑州、西安,因为这些地方的上一代女权主义者,在世妇会之前就在做相关工作,所以等国际资助进来之后,肯定先投资发展他们。
当时北方的前辈会说广州女权活动「搞得很活」,为什麽会这麽说,因为北京的女权组织,他们领导者的身份来自官方媒体、妇联干部和政府智库的学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不仅仅需要跟政府保持好关係,而且需要考虑到政府的行为逻辑,尽量不能添乱——也就是揭露社会问题,而是要帮忙,即透过政绩宣传来鼓励愿意支持女权项目的地方政府,来传达女权项目的相关理念。
但广州不一样,我们只有在汪洋主政广东时,做过一段时间的妇联专家,但我们的工作并不必然跟与体制内的妇联工作有关。广州是一个媒体的城市,所以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把媒体作为抓手。当时广州是每週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非常开明的议题,公共知识份子都很敢于表达,这是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公共场合很难听到的。
不过当时很少有女性的讲者,没有与妇女相关的讲座,更不要说女权主义的讲座。所以我们就先办讲座、办展览、办研讨会等等,邀请媒体记者参加。市场化媒体记者肯定不喜欢别人灌输观念,你要让他们生活的城市有女权的声音,让女权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
到2012年青年女权行动派出现的时候,广州媒体已经有一拨记者对女权议题有兴趣、对女权组织有基本了解,这是我们之前十年工作的结果。因此,广州媒体是对青年女权行动最为支持的媒体。当然,当时并不是女权一支独秀,当时广州公民社会都是朝气蓬勃,有很多年轻人在做各式各样的事,包括环保、预算公开、文化保育等,我们女权组织做的事也影响了一批年轻人。

田:「新媒体女性」也与网易、凤凰网等网路平台合作,刊出多篇深度报导,为什麽会选择与新媒体合作?
李:2014年的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事件,我们做了一个倡导,包括支持受害者,帮助她们进行法律维权和媒体发声;发表一系列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导和深度评论;组织全球华人大学教师学者翻译各国各校的反性骚扰制度文件,草拟给教育部和厦门大学的制度建议,并由全球学者联署致信教育部;编辑、发放给大学新生预防性骚扰册子,组织律师、社工和社会各界反学术性骚扰影片观影会等。
那时候,随着报业的广告市场不行了,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后吧,深度部门关门,资深媒体人离开,到处发生。很多有经验积累的媒体人已经不在传统媒体了,传统媒体也没有话份了,几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网络平台。当时的新闻客户端之战,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等平台都开始做客户端的新闻原创,用很高的待遇从传统媒体挖了很多人。
互联网公司钱很多,而且他们讲效率,讲究要用平台撬动更多资源。因此他们很开放很灵活。譬如我们民间妇女组织反家暴立法倡导工作组,要找媒体支持,所有的门户网站都给我们资源来曝光,譬如微直播、专家访谈。所以在厦门大学这件事,因为许多资深记者离开,传统媒体反而没有优势,犯了不少错误。网络公司更灵活,能够容纳外面的人,譬如NGO的人,一起来做报导性的内容。你要在《南方周末》刊一篇女权组织的稿子,可能不会被接受。
我们是跟网易真话频道合作推出关于厦大事件的报导,这有助于让更多人知情。
但我觉得传统新闻媒体相对于网络公司,仍然有更强的问责功能,因为它不是纯粹商业的单位,某种意义上,它是宣传系统的一部分。最后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这是第一个教育部的禁止性骚扰的文件;那时厦门大学还在拖延,还没处理吴春明,所以我们就让其中两位受害者,到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去讲述经验。播出第二天,厦门大学就发布通报,将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然而,主流媒体在衰落(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没多久,《东方直播室》就停播了。
应该这麽说,网路平台与传统媒体各有各的职责。但到了2015到2017年,传统媒体空间迅速缩小,同时社群媒体也被国家控制。像是我们2016年做了一个蛮好玩的活动「反三七过三八」,但到2017年就没法做了,因为我个人遭遇到挺严重的网暴,当然今天这种(网暴)模式发生在所有被针对的行动者、记者身上。后来也因为《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让NGO成为很有风险的一项工作,我被他们(政府单位)忠告,柔性劝导离开(新媒体女性)组织,才选择去教书。
田:在政府管控如此严格的现况下,要如何推动/传播女权主义相关议题、运动?
李:我自己关注的是女权和新闻这两块,我觉得疫情之后这两块都变得非常艰难。
疫情之初,还有很多记者在做报导,一部分不属于任何新闻单位的公民记者,但他们去到武汉,很多人被拘留被抓什麽的。当时我们还会觉得至少还有一些媒体的记者发出了那么多报导。但到了今天,当年发生在公民记者身上的事,不断发生在机构媒体的记者身上,大家都变得非常小心,记者面对暴力威胁已经非常普遍。
女权就更不要说了。女权运动其实从早在从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到现在,是一步一步被镇压下去,现在基本上已经註册的女权组织,倡导性的组织是不可能有了。「新媒体女性」坚持了很久,但也在2020到2022年间被要求註销。
他们会很重视控制女权的传播,他会要求一些个人和组织,「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但是不要在网上说」。
他们会控制有公共性的、女权相关的信息传播,什麽是公共性呢?往往跟公权力有关,但也可能跟传播范围扩大有关。如果你是去讨论家暴、彩礼、婚姻家事问题,引发较大争议,他们可能说你煽动性别对立,普通的博主遇到的事情——但是你仍然可以讨论。但是跟意识形态、国家机构有关的,就会严防死守,比如刘强东性骚扰案还可以谈,但是朱军案不能。
我曾经发过一篇长帖子,谈乌克兰在战争中有多少女性牺牲,然后就被警察打招呼,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乌克兰战争,但不是,他们的理由是涉及女性,因为那篇文章浏览几十万。在他们对于与女权主义相关的信息传播这麽警惕的情况下,要发起一个以前那样定义的女权主义倡导行动,已经非常难,比如说,铁链女事件的时候,一些女网友的个人行动,去探访那个村子;或者疫情封城时候的社区女性互助行动;白纸运动的时候,女性和性少数信任网络的动员能力。
不过其实以今天来讲,经过这些年的传播,女权主义变成一种常识,不再需要一个女权组织去推动才能发挥影响力,有点像一颗一颗水珠汇成一片大海,很多力量都在推动女权主义的传播。但我们既没有以前的行动的条件了,也不太可能会有主流媒体一起报导一个中心化的女权行动来作为支持。
2012年新浪微博就被盯上了,微博加速的公民行动,尤其是自由派的公民行动变成主要的靶子。当然,「淡化公知」在社交媒体上给女权运动带来了两三年的荣景;但是大家今天看到女权话语好像在社交媒体仍然很「主流」,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女权话语是女权运动被系统性清除出传播领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不能再依赖于一个很大程度受到审查、演算法控制的数字空间。
女权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粘合剂,对于建构另类文化空间、非主流群体来说,女权理论中的批判性是很有用的。
如果我们只去看这些被算法影响的平台,上面的女权思想是非常单一,用一个学术名词,可以说非常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徵,由于缺少面对面的连接,女权变成一个流行词彙,是相对来讲社会地位不太低的女性,用以合理化自我价值和优势地位,已经不是以公共参与、问责作为出发点。
演算法和商业意义或许不会去掉你的公共连结,比如我们做「反三七过三八」,平台竟然因此给我一个「微博大V奖」;但审查会,它会尽可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行动动员潜力都去掉。所以说,今天女权运动还想做些什麽,应该要离开社群平台,去寻找真正的人,像早期一样,举办小型的实体聚会,有人的面对面的接触。

田:就您的观察,如今的中国媒体环境与过去有哪些不同?
李:现在很明显做深度报导的女记者变多了,跟我的学生差不多大。但他们没有经历过硬核的新闻报导环境,舆论监督时代,所以也觉得(年轻记者做报导的方式)都变得不太一样了。
这与政治审查、商业模式等的影响都有关係,你也会发现农村题材减少,许多年轻记者成长过程中所读的深度报导以非虚构文体为主,写出来的深度报导也偏向非虚构风格,当然非虚构本身是对抗审查环境的一种做法。不过,比如说有人找我看稿,我会说以前做报纸时,这篇文章顶多5千字,你怎麽写到1万2啊?因为他们会偏重文学性的写作,也会放入很多过去我们做新闻觉得不重要的细节,但有些时候,新闻5要素里的5W1H,部分是缺失的,呈现时空悬置的状态。
有採编权的媒体,很多已经不做调查,也不做舆论监督了。没有採编权的媒体,倒还想方设法做一点,但没办法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比如说很难取得合法採编权的记者证。
我问过不少媒体号的营运者,基本上读者有70%是女性,连《纽约时报》都一样,有了付费牆之后,要更忠于你的目标读者。更何况,中国媒体要接触读者,都没有自己的平台,都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所以其实很能够理解为什麽(社群)媒体会走向女权。
但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一味乐观的。当年我担任顾问的项目曾经有一篇「爆款」,核心事件是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性,被她的丈夫打死了,还要按照老家习俗配阴婚。它能成为爆款的原因,是那些以城市年轻女性为主的读者,他们对农村并不了解。老实来说,我还是希望女性主义的传播,不要那麽汙名化穷人和农村,农村只是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一环。以前的记者非常关注底层的,但现在的传播环境之下,对农村的看法(态度)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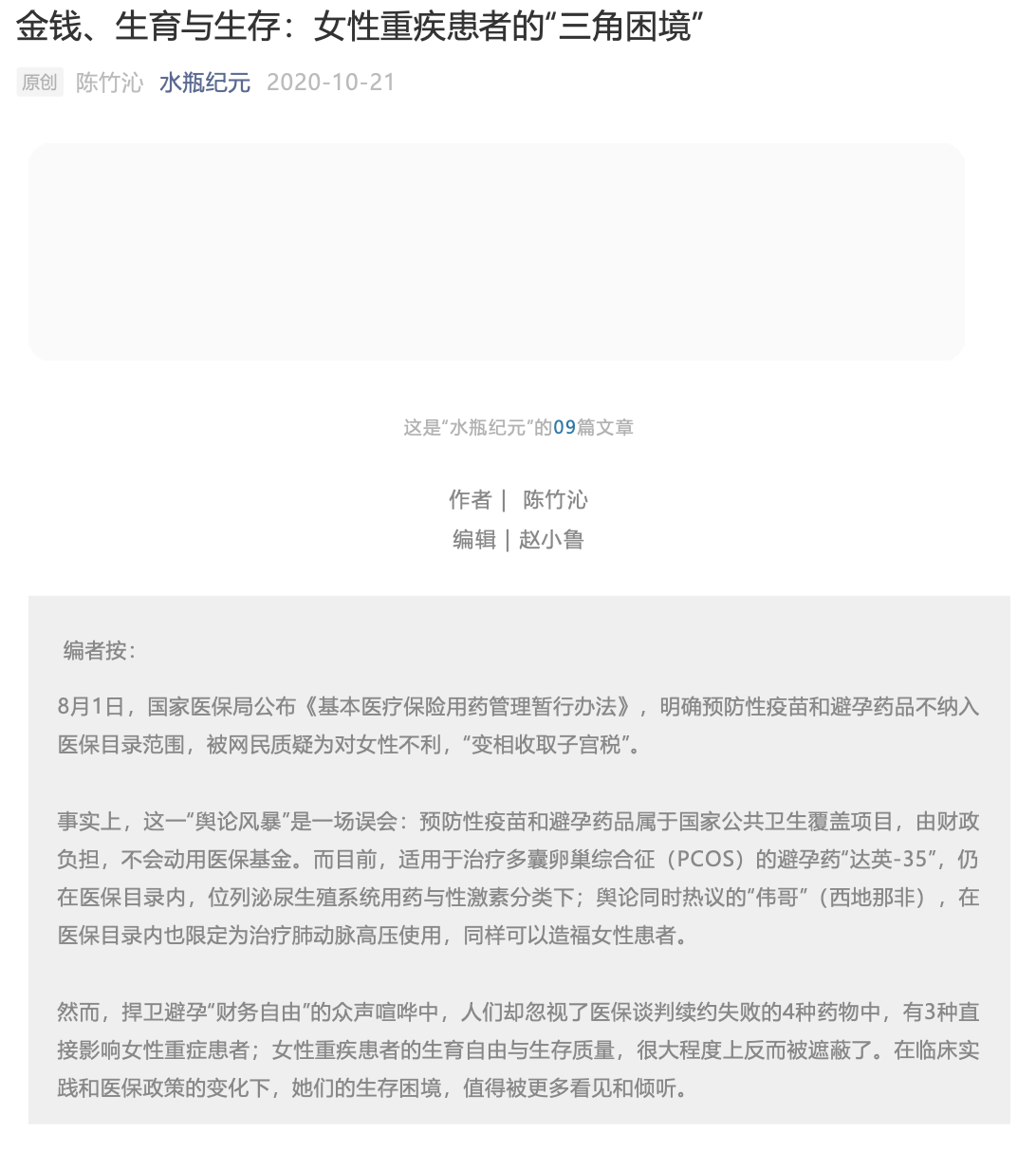
这是社群媒体上女权主义导致的问题,但没有办法,读者接触资讯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当你想要做跟政策有关的性别议题,这也很重要,但反而没有没那麽多人关心,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做过女性医疗政策的题目〈金钱、生育与生存:女性重疾患者的三角困境〉,它也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讨论的,但没有那麽多人关心。
社交媒体有很多女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它会进一步鼓励女性活跃在这样的公共话语环境,也会鼓励女性愿意去从事新闻工作,这两者是有关连的。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是正常的,但就是说,女权(话题、议题)有特别繁荣,性别议题能见度高,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新闻业有一点点像是of the women、by the women、for the women,让女性的贡献主流化。
可是在这不正常的言论环境里,也导致大家报导性别问题很专业,但报导城乡差距、贫困和劳工等议题,或者进行法治报导、对政府进行监督方面相对就比较弱,比如就算拿到料也不知道该怎麽解读,这与新闻业内出现代际传承缺失的问题也有关係。也因此女记者在行业里的主流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新闻本身的专业地位,越来越弱势。
田:您在文章〈News Media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China: A Brief History〉里有提到,女性记者有自己的社群,在珠海撞人事件时同业间彼此互相扶持。这是不是能弥补您所提到的代际传承等行业问题?
李:我觉得记者都是在同行的陪伴和竞争下成长的,其实合作多于竞争,所以女性记者有个网络是非常好的。以前可能是媒体报导出得多,大家的合作最后像天女散花一样,不同省份都有自己媒体刊出报导,但现在只有个别一些媒体可以刊出东西,但大家的合作还是一样的。(〈News Media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China: A Brief History〉结尾写道,这群年轻世代的女性记者,在现今维繫新闻韧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即使面对严厉的审查,也仍守护公众的知情权。)
田:2018年之后您投入教职,对于想做记者的学生们(或中国年轻人),您会给什麽建议?
李:我之前在国内教书是在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受创院院长陈婉莹的影响很大,所以是很强调新闻实务,重视老师的报业背景,但后来变成要跟其他新闻学院一样,老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我那个时候觉得这有问题。
另一方面,我的一些学生还在实习阶段就被警察找,因为各种原因,新闻变成一个风险超大的工作,他们所面对的风险和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那时候我们有机构的保护,现在的话,有了机构保护也不太可能做真正的新闻。有个笑话是,朋友的孩子选志愿,我们会先问是不是亲生,亲生的话就不要选新闻。
但实际上,我是新闻工作的鼓吹者,我会跟学生说,做记者培养的能力,是通过你自己去探索、理解这个世界,无论将来想做什麽,有记者经验都是一个幸运。对他们来说,在这麽不稳定的环境,最糟糕的时候,还愿意做记者,怀着理想主义、正义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坚持下来的话,之后一定可以做些事情。
【补充资讯】
艾晓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于2008年退休。2003年创办性别教育论坛,重要栏目包括「妇女维权行动」、「南方媒体观察」。同年她翻译、导演美国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该剧在广州首演,在上海、北京遭到禁演。她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製作多部知名作品包括《天堂花园》、《我们的娃娃》、《夹边沟祭事》等。
青年女权行动派:自2012年开始,出现一群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多数为大学生,她们利用行为艺术来表达诉求,所发起的「佔领男厕」、「染血的新娘」等活动都受到大量关注,但在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后,在中国也几乎失去街头倡议的空间。
吴春明性骚扰案:2014年6月,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一条〈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贴文,暗指有厦门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7月有受害博主指名道姓控诉教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2014年10月,厦门大学开除吴春明党籍、撤销教师资格。但事发隔年(2015年),吴春明被选上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显示他仍掌握学界资源,2018年更被揭露仍在厦门大学里任职。
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2016年4月28日,中国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要求境外NGO在公安部门註册,举办活动要提前报批,于2017年1月1日生效。
陈婉莹: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创院院长,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资深新闻工作者。她曾在纽约从事新闻工作20年,于1997年获国际新闻自由奖。
🍃《田间》关注全球华文媒体相关议题,串连关心华文媒体环境的人听见彼此心声,一起思考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法,促进茁壮、可持续发展的媒体圈。欢迎订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