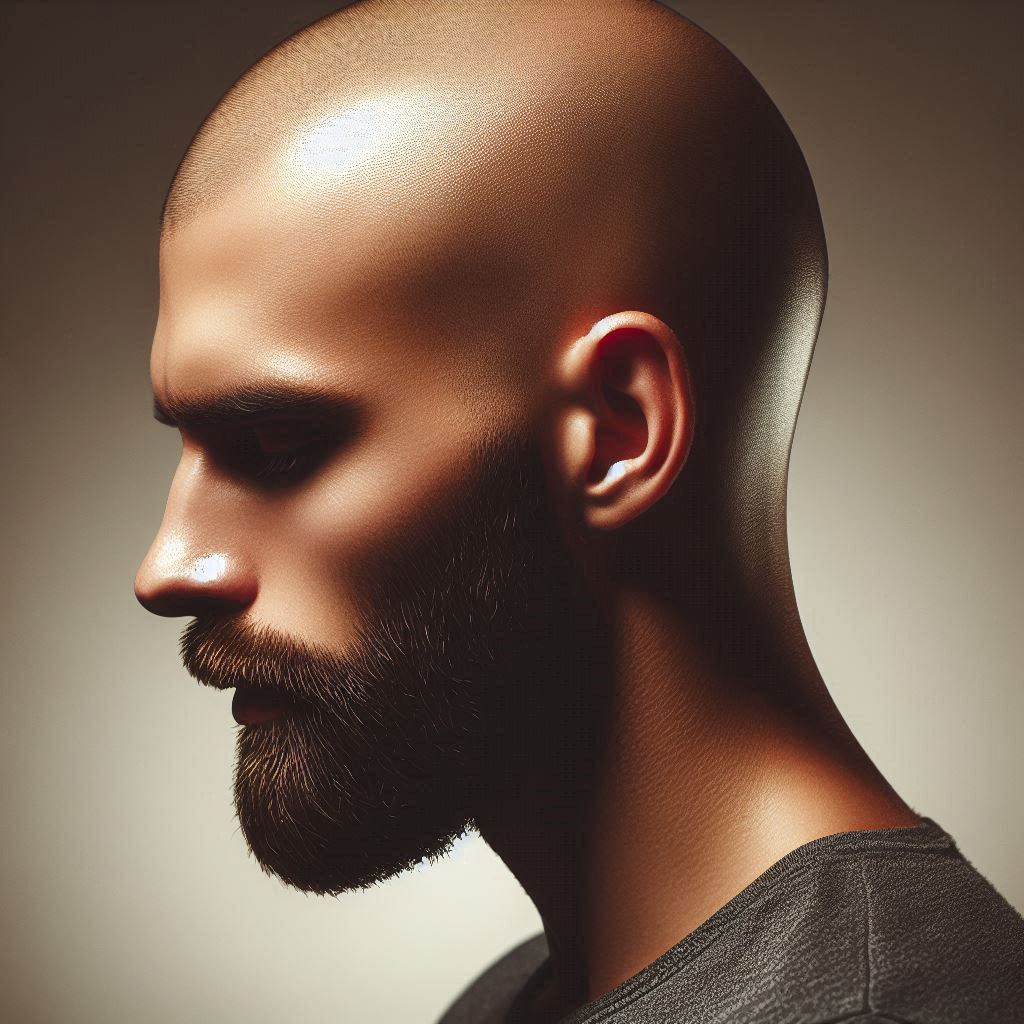《我們的健身房OurGym》 一枚五十元硬幣的夢想
105年,我做了一個夢。
不是計畫,也不是創業企劃書上的那種「品牌構想」,而是一場從身體裡長出來的夢。
那年我32歲,剛從看守所出來,處於假釋狀態。
身上沒有太多資源,也沒有完整的未來藍圖,只有一個,從21歲退伍那年就埋下的念頭:
我想開一間健身房。不是一般的健身房,而是一間能灌進我全部精神的所在,一間能把這些年我所學、所經歷的都傳承下去的地方。一間有溫度的健身房。
一間不只是讓人變壯,而是能讓人變成自己想成為的樣子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運動不是商品,健身也不只是肌肉的事。
它能改變一個人。
也許,有一天,也能改變這個世界。
說真的,當時也沒多想太遠,就是帶著一股熱情,還有一筆貸款,這樣開始了。
我原本的想法很簡單,找十個朋友,每人出個五萬,湊個五十萬當創業金,健身房的名字嘛,乾脆就叫「我們的健身房」。
因為沒讀什麼書,在Our Gym和 Ours Gym中陷入迷失。
還好學生之中有一個是英文老師,替我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那時我忘了一件事。
我剛從看守所出來,講白了,沒什麼人會信我。
我以為只要有夢就會有人跟,但誠信這東西,不是你說改就能改的。
人家看的是你過去那本帳,不是你嘴巴裡的新人生。
所以最後,我覺得還是去銀行借錢比較快。
快很多,雖然也硬很多。
但夢想這回事,好像也沒有一條是軟的路。
那個時候有一本書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夢想這條路踏上了, 跪著也要走完。」
光是找一個合適的場地,我就找了快半年。
那時每天不是在網路上翻租屋網,就是騎車晃,
看到一個「可能適合」的案子,就停下來記電話。
有些地方看起來不錯,價錢卻高得嚇人;有些地點合理,走進去卻像廢墟,連水管都要自己拉。
最後,我們選擇了六張犁站的崇德街,不太熱鬧,但有一種「可以開始」的感覺。
我簽下那張合約的時候,手心是熱的,腦袋是空的,只知道:可以動工了。
接下來,就是開始拆。
我帶著學生,一起拆裝潢、刷油漆,自己畫格局圖,自己量距離,就連LOGO和名片都是自己設計的。
一筆一筆地畫出空間,也畫出那種叫做「如果我們可以撐過這個月」的希望。
那年,105年7月1日,我們的健身房,正式開幕。
那天早上,我站在大家面前,講了一段話。
不是什麼熱血演講,也不是激勵名言,我說:「我手上已經沒現金了,真的一毛都沒有。你們的薪水,就在外面那些人身上。我不是你們老闆,我只是幫你們管理薪水的人。」
說完那句話,我記得所有人用不可置信加上無可奈何的眼神看著我,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營運之後,我們每天都像在跟時間搏命。
白天顧現場,晚上就留著開會、檢討、腦力激盪。
有時候坐在地板上吃鹹酥雞,聊到凌晨。
我們沒有資源,也沒有模板,但那時候腦子裡只有一件事,怎麼讓這間健身房活下去。
慢慢地,客人開始變多了。
不是那種一窩蜂的排隊,而是你會發現有人開始帶朋友來,那種感覺,就像熬夜看到天色變亮一樣。
我們也想了一個業界首創的模式:
讓私人教練可以用「單次租場地」的形式,自己帶學生來上課。
不用綁約,不用抽成,只要你想教,我們給你空間。
對於那些有教練夢、卻不想被體制綁住的人來說,那是一種自由的起點。
收費方式也不斷調整,從最早的「1分鐘1元」,到後來推出單次不限時,還附一包乳清。
就是這個想法,讓我們有機會跟戰神乳清合作,成為該品牌第一個和戰神乳清聯名的健身房。
有時候你以為競爭才是生存,但其實,合作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
我們當時沒這麼多理論,只是單純相信,能一起走的,就不要推開。
人開始變多了,也開始有人注意到我們。
最先來的不是祝賀,也不是媒體,是一封又一封的檢舉信。
有的來自同行,有的來自附近不具名人士,我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哪裡出錯,只知道,我們碰到了法規的牆。
那時我們經驗還淺,太多事情只靠直覺走,沒留意那些寫在黑字裡的規定。
政府來信了,限期改善,不然勒令停業。
我記得那陣子我們很安靜,不是因為沒話說,而是說什麼都沒有用。
只能一條條去對、一項項去改。
我們轉為低調經營,收起招牌、收起聲量,同時也找到民意代表,一起推動一件事:
讓我們這種「非傳統」的健身型態,有個合法的位置。
終於,在108年初,「運動訓練班」這個項目通過了。
那一刻,我不是為了自己鬆一口氣,而是替那些未來也想做這行的夥伴感到開心。
至少,他們不必再像我一樣,用錯誤開道。
那一年,是我健身的近20個年頭。
我看著整個健身產業慢慢長出枝節,一間又一間健身房冒出來,雖然競爭多了,壓力也重了,但我心裡是真的有點慶幸。
健身,終於在台灣開花了。
對了,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民國87年,我剛開始健身的那一年。
那時候,健身這件事,在台灣還算是冷門。
說得直接點,它是高消費娛樂,不是每個人都碰得起的生活方式。
記得那會兒,健身房一季的會費是四千塊。
是一季喔,不是年費。
但你知道當時的基本時薪多少嗎?64元。
也就是說,要一個月不吃不喝,才能換一身汗水。
但我還是去了。
不是因為有錢,那個時候我才剛從國中畢業而已,腦袋裡只剩下一句話:我要讓自己變得更強。
隔年,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
是我唯一的老師,陳能通老師,青年健身院的創辦人。
他突然說想找我聊聊。
說實話,那通電話我記得很清楚,語氣沒有特別起伏,但我隱隱覺得,老師是有話要說的。
其實從我開始帶選手以來,每次準備比賽,我都會把選手帶到陳老師面前,請老師幫忙調整動作、看姿勢、抓節奏。
所以他知道,我還在這條路上,還沒放棄,還在健美這條不歸路上,走得固執。
我的健身故事是從民國87年開始健身的。
第一間健身房,是葉瑞豐老師開的「葉瑞豐健身中心」,那是我第一回踏進健身世界的大門。
但真正讓我進入系統化訓練的,是隔年轉到的「青年健身院」。
從那時候開始,這裡就像一座不說話的學校,不教你說話,只教你怎麼咬牙撐住、怎麼不放棄。
那時候的我,說真的,根本不知道怕是什麼。
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句話大概就是為我寫的。
我站在老師的辦公桌前,跟他說一句我沒想過的話,我要參加健美比賽。
什麼準備?什麼底子?我哪管那麼多。
就像有人問你:「你確定嗎?」
你只回一句:「管他的,命一條,做就對了。」
現在回頭看,真的覺得——我那時候一定是瘋了。
可也還好,那時候真的夠瘋,夠傻,才敢開始,才撐得下來,才一步一步,把後來的「凹菌」走出來。
有些夢,是理智實現不了的,得靠一點不怕死的熱。
說回那次見面,陳老師開門見山,沒繞什麼彎。
他說:「你想不想增加你的事業版圖?」
那句話落下來的時候,我其實沒有太多猶豫。
沒有什麼條件交換,也沒有什麼精算思考。
我只是靜靜點了點頭,然後說:「好。」
因為我知道,這間健身房對他來說,不只是一間店。
青年健身院,是從民國67年就存在的地方,
是一代又一代健美選手的起點,是許多健身大佬的啟蒙地。
它不是豪華的,也不光鮮,但裡面每一塊鏡子、每一支槓片,都是記憶的標本。
那時我心裡想的是,老師信任我,這是我的福氣,即便最後得知的實情有很大的出入。
於是我決定,幫凹菌找個兄弟,一個有歷史、有靈魂的兄弟。
我們就這樣接手了青年,並肩走在那條,從汗水鋪出來的路上。
青年健身院OurGym。
兩頭跑的日子,其實也挺有趣的。
雖然說是「有趣」,但你要我講得真一點,那大概就是,心力交瘁的有趣。
白天在這頭調整課表,晚上在那頭修器材;一邊顧營運,一邊想辦法不讓自己倒下。
那時候連喝水都像在計時,腦子裡永遠在想下一步該怎麼撐。
半年這樣撐下來,我終於做了個決定:把六張犁的凹菌收起來,把全部的力氣,放在青年身上。
既然要留下,就要好好地留下。
我們開始更新器材,一件件替換掉老舊不合身的器具,挑那些更符合人體工學的角度、支撐點、握距,每一個細節都為了讓「鍛鍊」變成一種可以長久相處的事。
而就在這樣的整修與轉換裡,我們迎來了凹菌的第二個高光時刻。
一間健身房,從窗戶望出去,可以一邊騎飛輪,一邊看著台北101的尖頂。
不是炫耀,而是一種提醒:你流的每一滴汗,都在城市的光裡發亮。
我們的收費制度,後來也變了。
最早是「一分鐘一元」的計價方式,但在青年這裡,我決定不玩那套了。
我們改成單次50元。
是每次,不是每小時。
聽起來好像簡單,實際上對我來說,是一場資金流動的大考驗。
因為說白了,我的負債並沒有減少,甚至可能還在默默增加。
但我還是想繼續開下去。
不是因為我樂觀,也不是有什麼神秘贊助,而是家裡也有工作需要我幫忙,人手調度緊,資金也沒多到可以請人發呆。
與其每個月把資源砸在人事管理上,我乾脆讓規則簡單到底。
於是,「單次一律50元」就這樣定了下來。
不管你是誰、來幹嘛,來一次,就是一枚五十元硬幣的事。
說穿了,這制度也有風險,但我寧可冒這個險,也不想讓人因為錢,連走進來試一次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我們成為了全台灣少數用單次計費的健身房。
不是因我不怕賠,而是因為我知道,有些人,真的只差一個可以開始的機會。
同一年,我們成立了凹菌戰隊。
一群人,沒什麼資源,也沒有響亮的贊助名單,只有日復一日的訓練、簡單的器材,還有一種說不出口、但都懂的共識。
沒有最強,只有更強。
那幾年,我們拿下了不少獎,大大小小的比賽裡,凹菌的名字開始被聽見,量級冠軍、總冠軍,都慢慢寫上了我們的紀錄。
那時我才驚覺,原來有這麼多選手、這麼多健身網紅,曾經默默在凹菌訓練過。
有些人只來過幾次,有些人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們沒有特別說什麼,但心裡都知道,凹菌曾經在他們的健身歷程裡,寫過一小段篇幅。
就像一場旅程中,那個提供水壺和短暫休息的驛站,不搶舞台,也不留名,但願他們走得更遠的時候,會記得,有個地方,曾默默接住過他們。
我們那時,也在大安站開了第一間健身工作室,同時結合了運動按摩坊,是一個少數把「訓練」與「身體調校」放在一起的地方。
我們想的不只是「讓你變壯」,而是——怎麼讓你用得更久、走得更遠。
這樣的模式,慢慢被接受。
來的人多了,信任也多了。
收入,終於跟著穩定起來。
那段時間,我其實有點開心的。
不是那種大富大貴的開心,而是有一種:好像真的可以這樣走下去了。
然後,有一天,電視上的新聞成了重擊。
新冠肺炎。
從那一刻開始,健身產業進入了一段黑暗期。
不是關店這麼簡單,而是整個行業,被迫按下了暫停鍵,而我們,沒有人知道還能不能再按下「開始」。
我自己,也開始慢慢往下沉。
那不只是生意上的低潮,而是心理的。
我開始進入一場沒有敵人,只有自己的戰爭。
那是一段憂鬱症對我開戰,而我只剩呼吸的時候。
那接下來的一年多,真的是……負債直線上升,頭也不回的奔跑。
每個月的帳都像在演出一場高空特技,我看著那些數字,一路往上爬,心裡只剩下一句話:「沒關係,再撐一下就好了。」
我那時候真的相信,只要等警報解除,只要撐到可以正常營運,我一定能站起來。
所以我等。
每天都在等,邊倒邊等,邊撐邊等。
終於有一天,新聞說可以解禁了。
我記得我那天晚上走回家,步子是輕的,心裡想著:這下可以重新開始了。
然後,就在那不久之後,房東來說他把房子賣給建商了。
只給我53天。
53天內,我得把整間健身房搬走,找新的落腳處,重新安頓,從零開始。
我想著那句話,一時間連氣都忘了怎麼吸。
就像你花了三年修好一台老車,終於可以發動了,結果才剛上路,方向盤就被別人拆走了。
我看了幾個地方,每一間都像是命運在考我底線。
太貴的不敢想,太爛的不敢租,但時間在推,不能不決定。
我問上天,如果世界上需要凹菌,那請你給我一個地方讓我繼續。
最後,挑了一間,忠孝復興站附近的一棟廢墟。
地點還行,人流也不錯,但裡面什麼都沒有,然後房租有點貴,但是空間真的很大。
但我心裡想:「再不拼,就真的要結束了。」
跟銀行談增貸、轉貸,每一次開口都像在撕自己一層皮,但也只能咬著牙說:「再幫我撐一下,這次真的最後一次了。」
搬家必須在一週內完成。
從光復南路三樓到忠孝東路二樓,說近也不近,說遠也不是搬不動,只是時間太緊,錢太少,心太累。
我那時候對自己說:「應該有希望吧……好像也沒什麼選擇了,就這樣吧。」
一句話,像簽下一紙沒保證的賭注。
上天總是很會設計考題,尤其是在你已經筋疲力盡、以為該放過自己的時候。
搬進去之後我才發現這裡,沒有電,也沒有水。
我們沒得等,也沒錢請人修,只好先用白天的光——有光,就能運作;太陽下山,就休息。
前三個月,白天做事,晚上點露營燈,整個健身房像一座野地帳篷,只是器材比營地多得多。
有時一個人坐在器材中間,拿著小手電筒找東西,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在玩一場城市裡的生存遊戲。
但那段日子,真的很值得懷念。
沒有客人催,沒有聲音吵,只有我和學生們幾個人,一邊擦汗一邊笑,一邊做。
後來,電來了。
再後來,水也來了。
但還缺一樣——廁所。
是的,廁所要自己蓋。
不然,每次要上廁所,都得跑到捷運站。
我們自己鋪磚、裝門、接水管,一點一點,把「可以待的地方」,變成「真正可以留下的地方」。
直到那天,一切終於定位。
電穩了、水順了、燈也亮了,我站在那裡,沒說什麼,只是安靜地對自己點了一下頭,我們,真的做到了。
接下來,這裡變成了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
我們走的是無人化管理。
不是第一次,在青年就試過了。
但那裡的門比較重,進出也比較受限;這裡不一樣,沒有門,誰進誰出,幾乎無法追蹤。
唯一的機制,就剩那個保險箱。
每天開保險箱,都像拆驚喜包一樣,打開的那一瞬間,你不會知道今天收到的,是信任,還是失落。
有時候,人數和金額對不上;有時候,裡面出現來自世界各地的硬幣,有日幣、有馬幣、有美金,甚至有大魯閣幣。
還有更奇妙的是,有時結帳的尾數會是32、57、84……
我心想:「不是說好了50或100嗎?你是怎麼算的?」
但你知道嗎?這些我都忍了。
我告訴自己,可能是他們零錢不夠,或是算錯,
又或許……那多出來的7元,是他們的鼓勵金?
我寧可這樣想。
只是,有一天,我打開箱子,裡面放了一枚遊戲代幣。
我沉默了很久。
不是氣憤,而是一種說不上來的荒謬感。
好像整場社會實驗,忽然變成了一場大型惡作劇。
但最後,我還是合上保險箱,對自己說了一句:「沒關係啦,至少他有投。」
很多人都問過我:「你幹嘛要開一間50元吃到飽的健身房?」
有時他們是笑著問的,有時是帶著不解的語氣,也有人懷疑這是不是什麼行銷噱頭。
但其實答案很簡單,只是我從來沒好好說過。
因為我記得,當年我想健身的時候,得花很多錢。
會費貴、課程貴,連一瓶乳清都要想很久才敢買。
久了你會發現,健身這件事,好像默默變成了一種門檻。
不知不覺,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但我一直想:有沒有可能,讓健身變回一種平民運動?
不是高級品,也不是炫耀工具,就只是一個人,想要變好、變強、變自在的起點。
所以有一天我心一狠,「50元,就從口袋中掏出一枚硬幣即可。」
就像買一杯手搖飲那麼簡單,你不需要簽約,不需要擔保,你只需要一枚五十元硬幣,就可以走進來,流汗,喘氣,重新相信自己。
但便宜,不代表馬虎。
器材我照樣買最適合的,因為我知道,有人來這裡,不只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夢。
是健美選手的夢,是站上舞台的夢。
所以只要一有盈餘,我就買器材,更新、補強、調整,讓這裡成為真正能訓練出選手的空間。
久而久之,這也變成了凹菌的特色。
不是裝潢、不是價格,而是這裡願意為了每一種努力,持續變好。
或許,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什麼富二代,不然就是財富自由的那種人,才會開一間健身房,收50塊,還不設管制。
但,其實完全不是。
說得殘忍一點,開得越久,我的負債反而越高。
有時我也會在深夜想問自己:「你幹嘛不早點結束就好?撐什麼?」
沒人知道我已經動了不下一千次關店的念頭,可我總是會情勒自己。
我會在心裡編出一個聲音,「如果今天你關了,那一些人,要去哪裡找這麼便宜、這麼自由的健身房?」
「那些剛開始訓練的學生,那些不想被約綁住的教練,他們會不會就此放棄?」
我知道這裡面有些人是貪便宜,有些人根本沒投錢,甚至還有人笑我傻。
但我就是有一種莫名其妙、說不出口,甚至有點噁心的偉大志向。
不是那種要拯救世界的偉大,而是那種「我不做,誰來做」的執拗。
「你知道他有投錢嗎?」
這句話,大概是凹菌搬來廢墟之後,最常被問到的一題。
每次有人問,我都會笑一笑,然後說:「應該有吧!」
不是因為我真的確定,而是那是我唯一能說出口的答案。
我寧願相信,他們是多投了,把它當成一種小費,一種默默支持凹菌的小小回應。
我不想承認,也不願承認,的確有很多人,是沒投的,是逃票的,是把我們當笑話的。
但我能怎麼辦呢?
難道我要站在門口,一個一個盯著嗎?
還是要裝監視器、刷卡機、把信任換成制度?
如果那樣,我就不是我了,這裡,也不再是凹菌。
所以我選擇,相信那一些看不見的良善,即使它偶爾缺席,我還是想,留個座位給它。
到了112年,凹菌還在進化。
我們在健身區之外,開闢了一個拳擊區。
不是那種觀賞型的拳館,也不是職業選手訓練營,而是一個你可以真實揮拳、喘氣、重新認識自己的地方。
一開始只有一個沙包,後來越來越多,廠商送的、拳友贊助的、甚至有些是學員自己買來放的。
那時我們沒打什麼宣傳,只是默默維持了一年。
直到某天,有人說:「你們在格鬥圈小有名氣了耶。」
我笑了一下,沒有回什麼,因為我知道,我們不是紅,而是「被需要」。
我們做了一件,在傳統拳館很少能做到的事,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必須回到自己的名字。
不管你來自哪個拳館、練過幾年、帶著誰的技術與流派,只要踏進這裡,一切都放下。
在這裡,拳擊就是拳擊,你就是你。
不是教練的名片,也不是背後的徽章,不是你的紀錄,不是你的段數,只有你,和那顆正面迎向你的沙包。
我們讓拳擊,回到拳擊。
也讓每個人,有機會回到自己。
人數在那段時間裡,直線上升。
空間裡總是有人,沙包從來沒有閒著,飛輪轉個不停。
看起來好像是一切都越來越好了。
但其實,我心裡很清楚,熱鬧裡,也埋著隱憂。
越來越多的客訴開始出現,有來自會員的:說人太多、器材排不到、電風扇不夠;也有來自鄰居的:聲音太大、味道太重、人來人往太頻繁;還有最熟悉的,來自同行的檢舉。
我們盡可能地撐,調整流程、貼上告示牌、壓低音量。
該做的都做了。
能改的,也都改了。
但就在上個月,有一張檢舉單落到了我手上。
寫得不多,大意只有一句:目前的場所屬於市場用地,依法不得設置競技或運動產業。
一句話,沒有情緒,沒有解釋。
卻像一把悄無聲息的利刃,乾脆俐落地,把凹菌畫下了句號。
沒有緩衝期,沒有折衝空間,只是到這裡,剛好。
我盯著那張紙看了很久,什麼都沒說。
只是心裡有個聲音靜靜地浮起來:「也好,這樣……我自由了。」
如果你問我,這樣結束,我會不會難過?
當然會啊。
十年了。
十年心血,十年堆出來的地板痕跡、鏡子角落、沙包的磨痕,全都在一紙公文之後,歸零。
我也不知道,未來的我該去哪裡。
我只是知道,這次我真的沒辦法了。
最多人問的問題是:「那你要搬去哪裡?」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
我沒有資金再搬一次,也沒有足夠的周轉金,能再讓我撐過那一年的空窗期。
我不是不想,只是——我真的,累了。
真的,累了。
這不是一句情緒化的話,是我每次開保險箱、修器材、回私訊、處理糾紛之後,身體累了,心也跟著累了。
所以這一次,我選擇不再硬撐。
我只能讓凹菌,靜靜地、慢慢地,沉進每個人記憶的底層。
變成回憶裡,那間你曾經來過的健身房。
不管你是來流汗、來療傷、來重生,還是只是路過、逃票、短暫停留,我都記得你。
現在,我只希望你,也願意記得這裡。
哪怕,只記得那個50元的投幣聲,清脆落下的那一刻,曾經,是一場夢的聲音。
故事講到這裡,已然,全劇終了。
但在我第一次搬遷的時候,我就曾寫過這麼一段話,那時是寫給會員的,現在,我想再念一次,這次,是說給凹菌聽的:「我終於開了一間,改變這個產業生態的健身房,健身房也改變了我的人生。教學相長,我賦予凹菌生命,凹菌,則賦予了我新的自己。」
那時我以為我是在經營一間健身房,後來才知道,我是在築一座島,讓一群在體制之外、城市之間、人生邊角的人,有一個可以喘氣的地方。
而我,也在那座島上,慢慢學會了怎麼活下去。
OurGym 是什麼?
OurGym,從來就不是一間健身房。
也不只是某個地址、某塊空間。
它是一種精神——
一種對喜好、對身體、對自己不放棄的堅持。
你來過、流過汗、笑過、累過,
你曾在某一個時間走進來、
在一片器材與呼吸聲裡,找回自己一點點的輪廓——
那你,就是 OurGym 的一員。
而只要你心裡這麼認定,
不管你走到哪裡,哪裡,就是 OurGym。
我要感謝來過凹菌的每一個人,首先是在這期間的三任女友,感謝你們傾盡一切來協助我完成夢想。
再來是每一個我帶過的學生,我沒錢請櫃檯,然後又經常外出,是你們默默支持我,讓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往前衝。
最後感謝每一個自認是凹菌人的夥伴,是你們讓凹菌變得精彩,讓我的夢可以成真,希望在未來的旅程中,你們可以持續走在變好的道路上。
最後我要謝謝我自己,謝謝我勇敢追夢,雖然夢即將要醒了,但至少我曾經擁有過,就沒有遺憾。阿鋭之於凹菌,凹菌之於每一個人來過的人,謝謝你們豐富了我的人生,這會是我人生最美麗的一個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