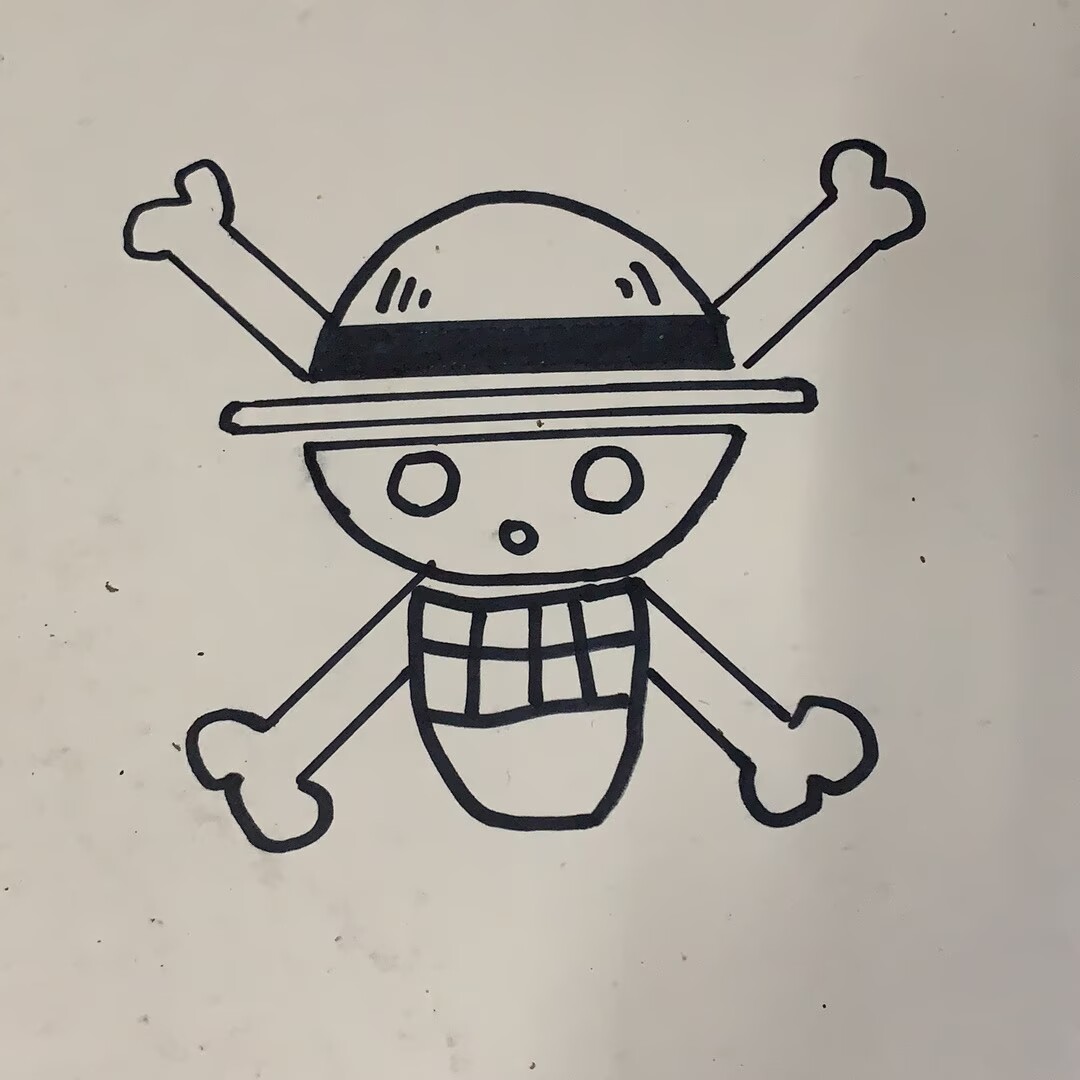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当记忆授权机制逐步开放后,越来越多当事人选择将自己孩提时代的记忆授权给至亲、给伴侣,甚至给社会中的某位审查者阅读。
几乎全人类的监护人们也都提出了查看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记忆的请求。
那些画面——不是被系统强行呈现的,而是当他们亲自点下“我愿意你知道我小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一刻,才得以导出。
不是新闻,不是别人讲述,不是司法通报,是亲自替他们,过一次那么一段童年。
那是这个时代最不能被轻描淡写的一种“教育体验”。
一段又一段“校园里的小事”,成了全民情感爆雷的最短电路。
你可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都在讨论什么?
不是梦想,不是动画,不是他们喜欢的星球或飞船模型。
而是——谁爸是某局长,谁妈是哪个主任。
谁能把车开进高铁站台而不被查,谁家的孩子不考试也能直接进重点中学。
在记忆读取系统里,这样的模式反复出现得惊人得一致。
“晓敏家真厉害,他爸开着路虎进站,站务员都得点头哈腰,帮他们开路。”
“高苗苗从来不上早自习,说她爸给打过招呼,不用考试,直接进五中的重点班。”
“人家小茜可说了,这世上很多咱们普通人都没处打听的政策,就是专为她们这些小群体私人订制的。通过人家的特殊渠道,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各种认证、资质、履历,顺理成章当人上人。”
那些话,不是孩子自豪地说出来的。
是他们在反复确认自己“要不要羡慕、要不要默认、要不要也学会这样说话”时,说出来的。
甚至有不少孩子自己低头思考: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如他们。”
“老师总是笑得更亲——我想,也许我家住得离校门口太远了。”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不是愤怒。
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碎。
这个世界为人设了外衣,为成年人套了借口、任务、韧性、制度、背景。
但孩子不该一醒来,就得先比父母的职级,然后决定吃哪一桌的食堂饭。
那些家境差的孩子,如果不够聪明,那一路都要学会“装狠”,从小龇牙咧嘴。
他们不是长坏了,而是逼出来的。
牙是遮羞布,狠是求生欲。
我记得有一段记忆片段中,一个八岁的男孩这样想:
“我每天都想跟旁边的人聊,但他们问我爸在哪儿上班,我不敢答。”
“他们不聊足球,也不聊作业。”
“他们聊谁送老师大疆无人机,谁让他爸帮体育老师订了高尔夫套票。”
他每天都要假装自己也知道这些词,假装自己不陌生。
有一天他试着说了一次:“我爸认识派出所的叔叔。”
他回家之后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想:
“那天大家都笑了。”
“但我觉得,他们笑的不是我爸。”
你问这种事严重吗?
我告诉你,这种社会氛围,是代际扭曲的根本。
它不是一拳打在脸上,而是用舆论、用童年设定的系统性羞辱,把人的灵魂从骨髓里一勺勺舀走。
那个年代,有些国家即便资源匮乏,即便成年人吃不上饭。但哪怕家长再穷,孩子在学校受到的对待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
无论身处农村或城市,山区或平原,孩子接受教育的条件几乎是统一的。球场、图书馆、医务室、学生餐、师资团队,一点不能差。
升学竞争也极为公平,从不允许偷偷摸摸搞隐蔽政策,若真被曝光出任何猫腻,恐怕就得有官员为此引咎自杀了。
他们的孩子至少站在同一条教育线,看着同一个太阳。
那才叫“哪怕我们失败了,也给下一代留个机会”。
但世上更多的地方,不是。
他们把所有标签,不仅贴在大人身上,还贴在了孩子的额头上。
你爸做什么、你妈哪里上班、你是不是“家里有资源”——成了五岁就开始接触的社会教程。
而当人们看到那些孩子的记忆……
当系统允许你从第一视角去穿那身小制服、坐进那张课桌……
当你听他们怎么努力合群、怎么偷偷查别人的家庭资料、怎么每次放学回家,都故作镇定地编一段“老师的留言”,装进口袋,等家长问起时就递过去,假装老师也关心自己一样。
整个社会的心,是一下子碎了的。
老人哭,小孩也哭。
老师、医生、司机、审查官,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如果逃避审判,我们就是替那旧制度的刀片,握了把柄,割的是自己孩子的灵魂。
这不是哪一场审判、哪一条通告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社会本身养出来的沉默瘾头。
现在,终于有人敢动了。
终于,系统不问你是不是官员、是不是公众人物,它只问:
“你有没有把特权藏标语里?”
“你有没有把幼苗种到石头堆上。”
这才是审判真正不可撤销的理由——
不是为了教育未来的人善良,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曾受过践踏的孩子,从记忆里重新站起来。
我确实见过反对者。
创世那年,他们站在人群中,低声和记者说:
“别老掀过去的事。”
“我们国家最擅长的就是‘失忆治愈’。”
那时候,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
我懂他们的犹豫。
当你曾得过便宜,占过位置,哪怕你再没心思搞权谋,那套逻辑也会在你骨子里偷偷告诉你:
“过去的事了,不要再翻了吧。”
可后来的每一步都让这种软和的侥幸,没了立足之地。
那些记忆,不是看一眼就能忍住的。
你以为你能扛得住伤痕的疼,可你根本扛不住孩子心灵开始扭曲的那种声音。
甚至你根本没准备好看一个八岁孩子的记忆:
“我爸不是主任,我不能说话太多。”
你看到那封没写完的日记稿,记忆导入时你的呼吸就碎了。
不是因为伤害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竟然是小心翼翼地为那一切开脱。
“也许老师说我不能还手,是考虑到了我们家的经济负担。”
全民不再是“被号召接受”,是主动翻开记忆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燃起怒火。
那之后的每一波民调,放弃上诉、主动认罪的比例飙升。
甚至连一些老官员自己按下导出的授权书,把记忆全开给公众,仿佛说:
“我愿意你们看见。”
“哪怕晚,也愿意交代。”
我记得创世四年后,有位教育局多年前内部退休的78岁的小姐姐,对我说了一句话:
“当年,我审批过的一份‘贫困生助学金’申请表里,盖着我外甥的名字。”
“我没改。我也后悔。但今天起,我不再躲了。”
那一刻我终于笃定了:
这个时代,不再怕真相。
它只怕我们继续假装没看清。
说完这些我转头看了一眼白露。
她没什么反应。只是掀了掀毯子,把手从一边抽出来,稍微靠近了我一点。
她的手不冷了。
过了一阵,很安静的光雾弥漫进窗台,她才轻轻说了一句: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变勇敢了……”
我望着她。
她眼睛没睁开,只是脸埋在披毯里面,声音像晚上泡好的老茶叶那样柔:
“是后来他们发现了痛点。”
“人在痛够之前,其实可以不管好多别人的事。”
“可孩子一旦被区别对待,那份痛,就直接捅到大人们的心口上了。”
我静静地坐着,没有打断。
她靠在我肩上左右摆了摆头:
“所有麻木的光滑表皮,都是急在那一瞬脱落的。”
她说完这句,没有继续。
也许她想到她爸曾把“为了你”当做一切腐败的借口。
也许她已经不为这句话掉眼泪了。
但我知道,她早就不是那个还在审查记录前发抖的白露。
她是那个在孩子们的记忆碎片面前,能够拍着心口说——
“哪怕我被羞愧折磨得体无完肤,也值得。”
这就是全民审判最大的意义。
不是肃清历史,是消灭那种“理解理解,孩子长大会懂的”的伪善剧本。
这个时代终于懂了:
“泄露的不是真相,是耻感。”
“追溯的也不只是过去,是一代又一代的常态。”
她靠在我肩上说完那句,我没立刻回话。
但我的脑子却从她这句话,一直跳进了一个几乎贯穿我这些年所有案卷的深渊地带:
孩子,不只是被差别对待。
有时候,连选择“被陪伴”这件事的机会都没有。
那叫“留守儿童”的概念,不是出现在某个社会新闻里,不是个统计名词。
是具体到千万人身上的现实。
他们的父母,为了三餐稳定、交得起房租、还得起账单,被迫离乡,去遥远城市劳作—— 早出晚归,三年五年,有的甚至十年,都没真抱过孩子一回。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记忆画面堪称人间惨剧。
而我无数次在他们的记忆里看到——那些留在老家的孩子,是怎么慢慢变得怯懦。
不是因为胆子小,是因为他们太早知道:
没有人会随时走过来替你说一句“有什么事冲我来,你们这群小流氓,敢欺负到我家孩子头上!”。
旧时代的权力者说,是现实太复杂,是制度不完善,是城乡发展阶段不平衡。
他们嘴上说着这些,脸上写满“革新需要耐心”。
可如今,记忆能被调出来,能被逐帧交叉解析。
我们明明白白查出了当年发展规划中的真实动机:
哪里该重点投资,哪里可以放任自流,
哪些影响中央形象必须美化,哪些“看不到”的地方就用来向上供血。
他们怎么分税、怎么配资源,不是靠公平原则。
而是一回事:
“那里偏僻,不适合带动增长。”
“省里的领导们没一个来自那些地方,资源配给它们,领导也看不见,我们也得不到提拔。”
你以为这是无奈规划?不是。
这是人为筛选——是“牺牲一方以喂养一城”的预设策略。
每一位无法陪伴自己孩子的人,并非只是“被命运驱散”。
他们,是被整块城市发展逻辑直接“推着走的”。
而真实的心酸错误,是:
他们一边流泪寄钱回去,觉得自己撑起孩子的未来。
但城市上层的人,早就在利益分配模型里,用他们的血肉筑了城墙。
不是夸张形容,是我亲自读取那些城市高官的记忆时,他们压根就没计划过让这些人“扎根”——
只希望他们来,工作完,别太吵,别太多要求。然后,再有下一批。
更多人真正愤怒的,是下一场记忆查看潮中的另一类图像:
为什么孩子连校舍的天花板都要漏水,而另一座学校却配备三个专业球场?
别说“国家财力不够”,别说“地形限制”,别说“地区困局”。
我们调出了当初政策配置会上,那些关键决策者的内心片段。
他们对“重点发展试点”为什么选A不选B的理由,是:
“这边老领导的亲属多,场地得体面一点。”
或者——
“那边城区都是祖祖辈辈的本地市民,亲朋好友都在机关里。”
你听到这样的话语,再也无法原谅“大义凌然”的沉默。
尤其当你知道,那场教育预算压缩决议中,所有“剥离优先级”的板块,大多来自那些已经流失大量家长的乡镇。
教育,是这个世界最不该拿来做等级筛选的东西。
你凭什么让一个孩子在东部县城中跑全塑胶跑道,而另一个孩子端着饭盒站在外面听雨声滴进教室?
有人说:“是出身。”
有人说:“是户口。”
可我们如今知道:那些说着“感同身受”的管理层,心里想得根本不是同理。
他们的真实内心片段显示:
“这就叫现实。”
“兜不住所有人。谁叫他们天生贱命。”
“穷山恶水的刁民,反正他们也习惯打补丁过活。”
你说这只是人心淡薄?
不——这是人祸,是罪恶。是明知道,还设计进去。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宿命。
我越来越清楚,在那个时代的权力场:
好人步步为营,怕出错,怕不得体,怕管多了惹祸上身。
而心狠的、肯上的、会送礼拉人、敢阴敢明的——一天一个台阶地往上窜。
他们会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哪管脚下踩成的,是一片片血肉模糊的同类。
他们爬得越高,脚下就要有人彻底趴下,代替他们咽下所有痛。
再培养几个和自己一样狠的,继续拉杆爬梯。
坏人越来越靠近权力系统的核心,这不是偶然,而是权力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恶性循环,滚出了一个全自动筛选“冷血精英”的机制。
所以,别再问:
“为什么那个时代好像坏人比好人多那么多?”
实话是:
那不是筛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聚出来的。你只要咬一个,周围就有人帮他撕你。他们互相认得出来。
你不会知道是哪一步不对了,只知道有时候活得太正,就显得格格不入。
说完这些,我没有继续说话。
空气里没有嗓音波动,也没有哪句话该被回应。
白露只是低头看了看指尖,像是刚在桌面上捡起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微型碎片,吹了一下,又放下。
她没有接我的话,但她却轻轻问了一句:
“张扬。”
我“嗯”了一声。
她轻轻推了推我的胳膊,语气里带着几分平时没有的认真:
“你每天看那么多别人的烂事,会不会也觉得自己……在慢慢变硬?”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眉毛在夜灯下轻轻挑了一下,眼神里并无苛责,只有一种深深的关切。
那句话落得极准。
我没有急着回应,只慢慢伸手从她身侧拿回她那杯已经凉掉的水,轻轻暖了暖。
“我怕。怕自己有一天,对什么都不再有感觉了。”
她又靠近一点,没继续追问,只是将头轻轻靠在我的肩上。我知道她听懂了。
她把一只手从毯子里钻出来,抱在我腰侧。
“你去哪儿都好。”她说,声音很轻,“但你记得就好,别变得说什么事都不疼。”
我答应得很轻,却是今晚最用力的一句“好”。
屋外风包得窗轻轻发出一点声响,像旧木头换季时的骨骼慢响。
我们没有开音响,也没有再放曲子。
只是坐在那儿,等这一夜慢慢熄热。
光线柔的像不肯睡去的记忆,贴在墙上,水汽微浮。
而她,就这样靠着我,一动不动。
那晚,我们像两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靠得很近,没再谈论任何关于“计划”“任务”与“命运”的词。
我们只是——在人类世界里,又一起活了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