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想像「澳門性」及其歸屬(宿)?讀《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
作者:遠東釣魚郎(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一本遲來的譯作?
最近,澳門研究其中一本可謂必讀著作—由美國學者雷凱思所撰的(Cathryn Clayton)Sovereignty at the Edge(中譯《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由香港大學出版發行其中文譯本。或許最初以英文出版的緣由,語言隔閡使得本書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只停留於學術界中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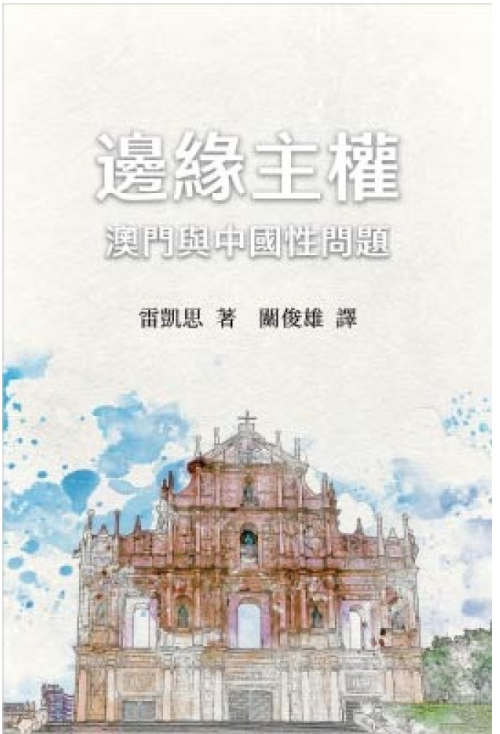
中文譯本的發行,無疑使得一般澳門讀者更易接觸有關本地的嚴謹學術著作,但原作到譯作間的時間差所揭示(英文原作於2010年出版),亦呼應作者於書中所討論的現象,便是澳門長久而來存在著數個「平行」的社群。雖然身處於同一城市,並在緊密的城市空間生活,但不同社群所經歷及認知的生活經驗,卻可謂相當不同,甚至很難被其他社群所理解。
「遲來」的譯作所揭示的,或許正是一種弔詭的現象:《邊緣主權》一書中所討論的,雖然與(上一代)澳門人息息相關,但下一代澳門人僅有在十多年以後,才能認識此一段造就現今澳門的歷史。
不論如何,中文譯本的出版,或許正是(重新)閱讀此本著作,透過作者二十多年前回歸前夕的田野調查,來對照現今澳門的契機。在本文中,我重新檢視本書的論題及核心概念,並反思在二十多年後,澳門社會的演變如何反映(或無法反映)作者當時的觀察。因此,本文可作為有興趣閱讀此書讀者的某種導讀,或許亦能視作二十多年前對澳門的第一身時代記錄。
「中葡匯聚」的反響
一些讀者也許與筆者一樣,對九十年代澳門的印象相當陌生。但透過本書作者的視角,我們或可嘗試想像這樣一個回歸前夕的澳門: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澳葡政府一改先前碌碌無為的作風,積極地在本地推進各種不同的文化項目。
在本書作者看來,各種看似「人畜無害」的博物館展覽、文藝表演、文化雜誌等項目,實際上有著深遠的政治意味。殖民政府正正透過建構圍繞不同文化工程的論述,來凸顯澳門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之所以出現,乃基於葡萄牙在澳門四個世紀以來的存續,使得澳門生成一種中葡混雜(或融合)的文化特質。由此,澳門一種與中國性同中有異的「本土性格」及住民認同,成為了回歸前夕澳葡政府的官方主旋律。

但相比起官方文化敘事的順理成章,葡萄牙人於澳門統治的政治基礎則存在著更多曖昧不清的灰色地帶。在長期無法於澳門建立壟斷性的殖民權力的情況下,葡萄牙人於是於二十世紀中期起,轉向另一種意識形態來正當化其殖民統治,亦即葡萄牙傾向以文化及種族融合(而非武力)的方式來建立統治,因而比起「傳統」的殖民模式更為優越。
「熱帶主義」與「非完整主權」,於是共同構成了作者所稱作澳門的「類主權」狀態(Sort-of Sovereignty)。在這種狀態下,殖民的政治形態並非(亦無法)以由上而下的獨斷性權力所施展,而存在著更多不確定性、模糊地帶、矛盾以及妥協。這些種種不同的性質,亦紛紛被當時不同的澳門居民所詮釋及經驗,從而形成了與官方論述對倒的政治與社會敘事。
那麼,到底九十年代的澳門居民如何回應官方的文化敘事,並建構他們對於殖民地主權的理解?作者在書中舉出了回歸前夕大大小小的事件,討論澳門如何被想像及建構。例如九十年代後期籠罩著澳門的議題「黑社會」,一直被視作澳葡政府管治失效的象徵。對當時的居民而言,管治失效正正意味著對澳葡政府「類主權」最為有力的回應。比起一直強調澳門的混雜地位,澳門的治安敗壞與混亂,代表澳葡政府缺乏「真正」主權單元維持秩序的政治能力。
因此,「回歸」並不僅基於愛國與民族主義,而是某種渴望「真正」主權於澳門落實的願景。葡式「混雜性」亦進一步在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上被推翻;中葡談判中土生葡人從中國及葡國國籍中二選一的方案(雖然最終並未落實),意味著不同公民身份互斥的特質,使得想像中多重的「本土」身份被斷然排除。

對於政治議程的反響,亦反饋於不同的社會事件中。本土歷史教育的缺席,相當程度上可歸因於「本地歷史」難以界定的性質:到底澳門是「中葡交匯」之地,還是遠東一個無甚生氣的「死水埠」。地方及街道的命名,對不懂葡文的本地居民而言,僅是再次證明葡萄牙管治與本地生活的疏離。澳門博物館中所平行並置的中國與葡國元素與宏大敘事,對居民而言亦僅是勾起過去生活的片段。最後,本地居民對澳門身份「無需表述」、「多重表述」、又或是平行且無關的表述、正好反映澳門集體身份的模糊性。
由此,「邊緣主權」事實上存在兩重意義,一方面,葡萄牙殖民澳門的不完整,使得澳門的政體性質處於「政治主權」的概念的邊緣—不是單一政治權力擁有在某一政治單元的壟斷性權力,而是主權被共享及挑戰。另一方面,澳門的地緣位置亦正好為這一邊緣性提供了結構性的誘因。在遠離葡萄牙本土及中國政治核心的情況下,兩種意義下的邊陲性,正好交織成澳門的邊緣性格。
那麼「澳門性」到底是甚麼?
讀畢本書以後一直纏擾著筆者的一個核心問題,便是「澳門性」相對於「中國性」的關係。雖然作者在書中並未有特別使用Macauness此一概念,但從字裡行間中,則能隱約看出「澳門性」被視作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以正當化殖民統治的手段;相較之下,澳門居民則祭出各種不同的想像來回應官方議程,造就出形形色色的「中國性」表述。
就此一關係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延伸本書作者的命題:如果正如作者所言,澳門於殖民時期模糊的主權歸屬地位,使得澳門居民在思考身份範疇及認同,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意義時,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宣稱,澳門在回歸後相對明確的主權地位,使得澳門居民在思考身份時相對清楚,甚至能夠想像一種或可稱作「澳門性」的身份?這進一步牽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中國性(或澳門性)如何成為澳門居民理解在地、國家或全球的基本範疇?
作者似乎並未完全回答此一問題(而把中國性視作一種給定、但充滿歧義的社會類別),但「中國性」在回歸前作為理解澳門的基本預設,或許正好預告回歸以來「澳門性」得以可能的條件。
註:筆者閱讀的版本是英文原文版,如部份概念翻譯與中譯本不同,敬請見諒。
#文章篇數:2️⃣5️⃣2️⃣
👉 成為免費爐友,郵件收取最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