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bh出發:那些移民故事
人類學有一個學說名「非洲出走」 (Out of Africa) , 其理論是以人類DNA進化,古人類進化,語言演化及考古證據去推斷20 萬年前現代人類(Homo sapiens)最初起源於非洲,然後由非洲遷徙到世界其他地區,逐步取代當時已經存在於其他地方的古人類,例如尼安德塔人,直立人等。此學說證實了人類不是定居物種,而是遷徙物種。
1892年1月1日,17歲的Annie Moore 帶著15歲及12歲的弟弟由愛爾蘭的Cobh 塔船去美國紐約,與比她早4年已到達美國的父母團聚。當她到達Ellis Island 時,入境處發她一枚$10金幣作為歡迎禮物。Annie Moore 的故事是當年大西洋遷徙(Great Atlantic Migration) 的其中一個故事。
一步出愛爾蘭Cobh 的郵輪碼頭,第一眼就看見Annie Moore 和其弟弟的銅像,Annie Moore眼神迷茫,心有牽掛, 其中一弟弟手指向遠方,那方就是美國。 此個銅像在美國Ellis Island 的碼頭也有一個,同是Annie Moore 和其弟弟,雕像則遙指另一方,那就他們的出生地-愛爾蘭。

愛爾蘭有一首經典名曲名”Isle of Hope, Isle of Tears” 把Annie Moore 的真實經歷以音樂譜出,故鄉的眼淚與未來的希望互相交織,是離散,哀愁然後重生。此曲感人之處就是以小人物見證著大歷史。當年的歐洲尤其愛爾蘭飽受戰亂,殖民年代的政治壓迫,及大饑荒的動蕩。很多愛爾蘭人及歐洲人為了生存,紛紛投奔美國,希望那個自由之地能帶來生存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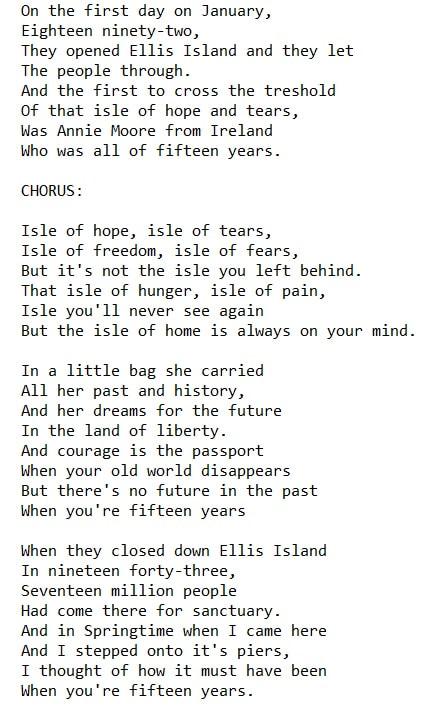
美國夢的原型由此而來,當年的美國就是以移民人口立國,第一代的艱苦成為移民二代及三代的福蔭。在美國生活的Annie Moore 一生不算順遂, 她在紐約市生活,嫁了德國裔的麵包師傅,育有11名子女,可惜很多也早夭。Annie Moore 一生貧困,大約50歲時病死,最後跟早夭的兒女合葬一起。
不是每一個移民故事也能福慧子孫,但差不多每個移民第一代的故事也跟Annie Moore 相差無幾,刻苦耐勞,掙扎於柴米油鹽醬醋茶。為了生存他們義無反顧在美國𡚒鬥,因為已經後無退路。 美國的生活難捺,但家鄉是絕路。
在Annie Moore 的雕像旁有一所Heritage Centre, 裡面記載了很多愛爾蘭移美的家庭故事,當然還有觸目驚心的鐵達尼號(Titanic) 悲劇。1912年4月11日, 鐵達尼號從英國南安普敦(Southampton)出發後,經法國瑟堡(Cherbourg),來到Cobh(當時稱為Queenstown)。此地方是鐵達尼號的最後一個港口,當天接載了123位乘客,主要是愛爾蘭移民去美國,最終卻不幸在北大西洋沉沒。
鐵達尼號沉沒的113年後,Cobh 此個愛爾蘭小鎭隨着愛爾蘭獨立後,經濟由早期封閉變成開放,政府引入外資,鼓勵貿易,加上成為歐盟成員國之一, 國家經濟突飛猛進,此個小鎭由貧窮變成富裕。今日的Cobh 與100年前相比,既改變巨大,又幾乎未變。城內依然保留着很多歷史建築物,例如山上的教堂,火車站,港口碼頭,鐵達尼號登船室, 當年營救鐵達尼號的Cunard郵輪辨公室等。 從街頭,雕像,博物館,當地居民的故事,每一角落都在訴說着那首船,那場離別,那些人,那些家庭。
在鐵達尼號博物館內,我買了個船長小熊作紀念。步出博物館,坐在海濱花園,正面迎向大西洋港灣,看到遊輪,目下的潮水,遠方燈塔和日落。


據說太陽是一顆壽命約 100 億年的恆星,100年前的太陽跟現在的太陽本質上沒有任何變化。它每天照樣為地球輸出能量,安然地升起與落下。同一顆太陽,照著同一顆地球。1912年4月10日傍晚,19歲的Jeremiah Burke 就是此處看夕陽,然後登上鐵達尼號。出身於愛爾蘭農村天主教家庭的他,是家中最年輕的男孩,他和數十萬名愛爾蘭年輕人一樣,因家境困難,社會又缺乏就業機會,前往美國尋找更好的生活,他的目的地是波士頓,投靠在美生活的姐姐。
上船前,他把母親給他的一瓶聖水倒走,放一張告別信在瓶中,從船上拋入大海。最後,他沒有到達美國,也沒有回愛爾蘭。反而那瓶中信在鐵達尼號沉沒後的數月漂流上岸,被一位漁民在愛爾蘭西部Kerry郡的海灘發現。信的內容是 “From Titanic, goodbye all, Burke of Glanmire, Cork.” Jeremiah Burke 的遺體從未尋獲,而他的家人用瓶中信作為他最後的「回家」。
夕陽見證了很多移民故事,移民故事又豈止Cobh,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移民家庭,在愛爾蘭,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在巴勒斯坦,在非洲,在香港,在中國等。大約在1950-1980年代,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家庭移居香港,他們都是逃避政冶動盪,貧困及追求自由。
本質相同的移民故事,為何Annie Moore 可以成為家傳戶曉的愛爾蘭經典,反而中國大陸移民香港的故事都是民間口述故事,缺乏一種共同認知性或代表性?
可能經典也需要一種話語權及政治正確性吧。Annie Moore 的故事不斷地被官方記錄,有媒體文化加持,例如雕像,音樂劇,文學等,因為她像徵一種向「新世界出發」的精神,而此精神又迎合着「美國夢」。然而港英政府當年視內地移民為一種邊界遷徙,加上移民人口帶來的冶安問題及人口壓力。逃難的原因又政治敏感,香港當時又是殖民地,沒有什麼國族建構的需求,就不需要以故事來凝聚社會。
“History is his story” 歷史是勝利者的故事,此話是真的。其實不止歷史,連民間故事也是,那些故事值得被記載,那些被遺忘,也包含很多時代的統治因素。
或許,每一段遷徙的腳步都值得被銘記。又或許從一粒沙至一個人,甚至一個世界,本體上皆是空性,亦即是無固定自性,沒有高下之分。所有未被記下的故事不是因為沒有價值,而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無論是皇帝還是乞丐,他們的故事終究皆過去,皆無常,皆歸於空。英女王逝世了,富豪李兆基逝世了,流落街頭的曾灶財逝世了,鄰居甲也逝世了。 無論故事有沒有被記下,都是終需一別,剩下的故事像大樹旁的一坨狗屎,成為人間的肥田料。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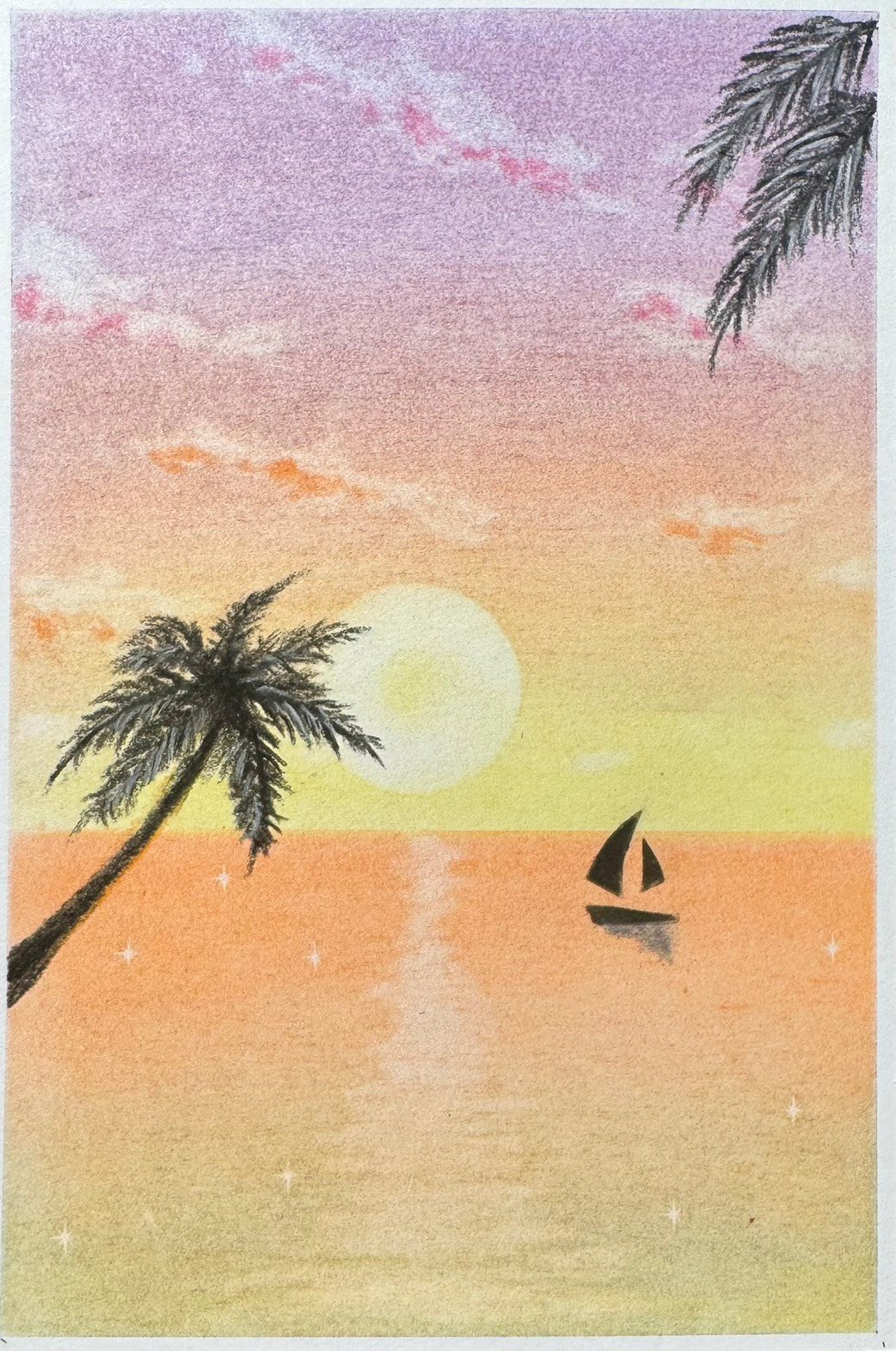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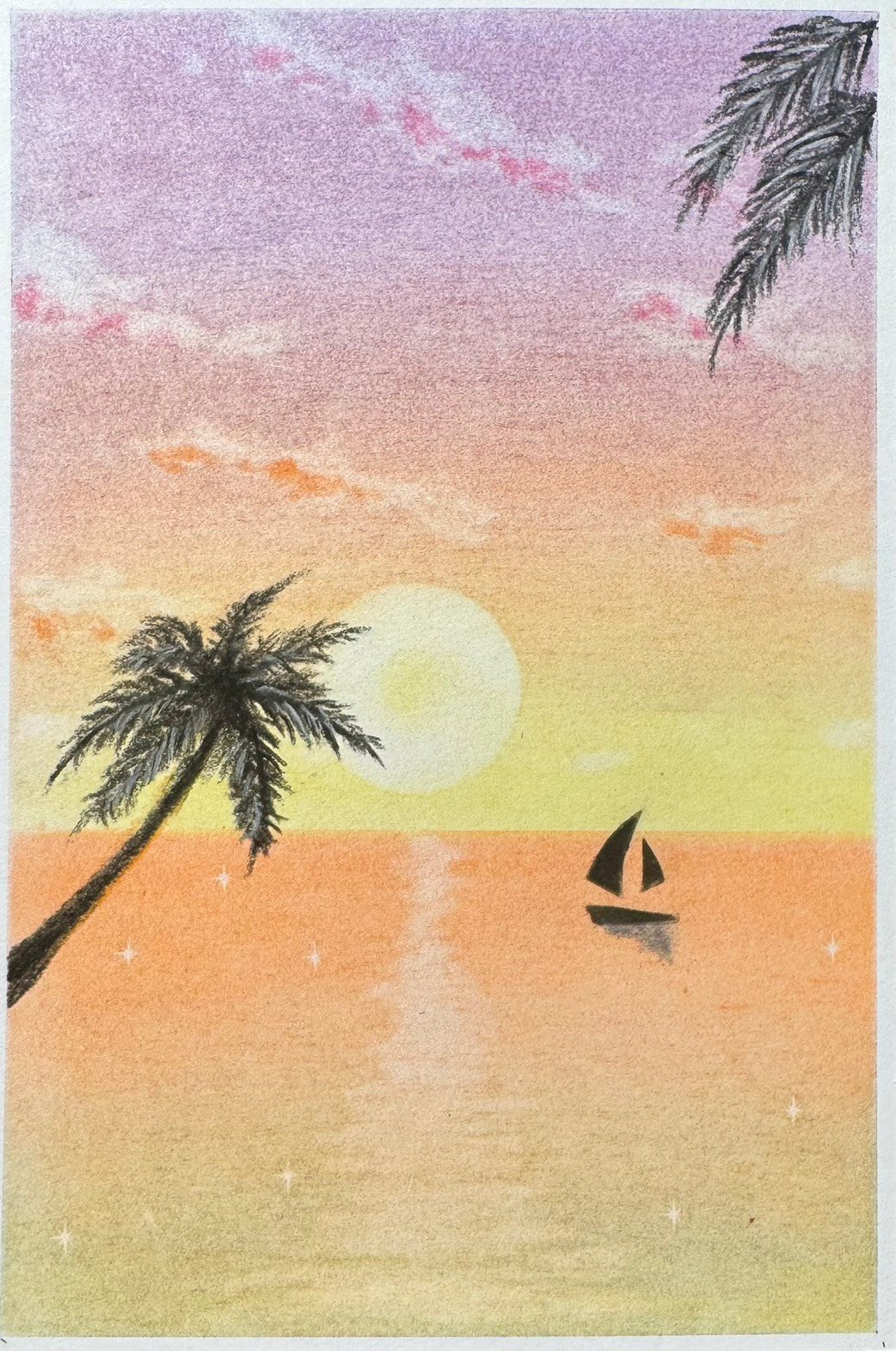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