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00: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2022年1月16日,天地圖書的前董事長陳松齡離世。想到天地圖書,這正是我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經歷與轉折。
1976年《七十年代》原租用文咸東街舊樓社址,面臨業主迫遷,經朋友介紹找到灣仔一個八千多呎的地庫。那是霍英東的物業。我因雜誌的成功,就雄心勃勃地想開一家中立的中英文大型書店,以讀書無禁區的態度,既賣大陸書也賣台灣署。那時正是文革後期,左派書店集中賣毛著,門可羅雀;右派書店以賣台灣書為主,規模較小。中共在港的工委,大概也看到極左路線在香港無出路,而我們又是外圍的華僑資本,於是同意我的想法。經新華社斡旋,霍以略低於市價的租金租給我們。我為書店起名「天地圖書」,是從古文「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聯想而來。並請中共駐港高層的潘公(潘靜安)為店名題字。他說他已經為不少左派機構題字了,不想被人認出,就從古代字帖中集了「天地圖書」四字給我做招牌。
我們雜誌是小本經營,要設立這麼大規模的書店,財政上要較大量投入。上海書局投入一些,潘公找富商以資助方式投入一些,三中商屬下的僑商置業投入一些,我再邀請願意支持《七十年代》的約十位海外和香港的知識人投資。因此,天地圖書的組成靠的就是支持《七十年代》的社會基礎。其中左派的僑商佔不超過一半的最大股份。董事長是出資辦《七十年代》的方志勇。背後的推手是三聯的負責人藍真。我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具體擔負所有的責任。
1976年9月25日天地圖書開張,9月9日毛澤東去世,左派在一片哀悼聲中,我們開張也低調處理。想不到頭一天就吸引大量讀者光顧,可見真是填補了當時讀書界的真空。但另一方面,毛去世,接著發生四人幫事件,在北京大變局中,我的編輯、寫評論變得非常傷神和忙碌。從三數人的雜誌編輯部一下子經營數十人的書店,管理、人事都忙不過來。除了編雜誌還要出版書籍,每晚都寫作、編輯到兩三點,第二天一早去書店處理業務。
那時我主要的思考和精神都專注於中國的變局和雜誌的出版,經營企業是我從來未做過的事,既不熟悉,心理上還有點排拒。兩年多後,藍真問我能否接受陳松齡當我副手。我想想,說可以。我與陳同年,1955年同期進入上海書局,他在發行部,我在編輯部,他不是寫作人,但為人敦厚、正派、誠實、勤懇。他在1979年進入天地圖書,曾經在《七十年代》寫過稿,但沒有擔任過雜誌的編輯工作。我把部分管理業務和出版圖書的業務交給他。我有一種感覺,是中共對他的忠誠信任度較對我的高。
1979年《七十年代》因連發三篇社論,對中共在開放後又突然禁止《七十年代》入境提出質疑,又發刊一篇《中共特權階層》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以致他以我們批評中共打擊民主牆為由,向新華社社長王匡「當面交代,『把他們撤底搞垮!』」(《許家屯回憶錄)。但長期在香港工作的副社長祁峰和秘書長楊奇都沒有執行。王匡邀我去新華社談,我據理力爭。在近年出版的《羅孚書信札》中有王匡給羅孚的信,其中提到請羅孚跟我談「七十」的事,「深以為念」。我想是勸我不要在雜誌中再針對中共。但羅孚實際上也沒有為此與我談過。
但搞垮「七十年代」的辦法終於有了,就是1980年天地接到霍英東辦公室的信,表示1981年租約到期後不再續租。這樣,辦得相當成功的天地圖書就找不到一個適合又還廉宜的地方繼續營運下去,投放在那裡的設施報廢不說,恐怕連銀行貸款都還不起。這時藍真就傳來信息,說如果《七十年代》結束,霍英東就會答應繼續租給天地。他認為天地是較大的事業,我不應該放棄。
但我午夜深思,一份擁有幾萬知識人讀者的雜誌,是否就應該這樣自動消失呢?我既然承諾過讀者也是作者、作者也是讀者,那麼雜誌的存廢就不應該由我決定,而應該交給讀者決定。
為此,我決定在雜誌發起眾籌資金的活動,使雜誌可以脫離天地圖書繼續辦下去。我把天地不再出版《七十年代》的決定通過新華社轉告霍英東。霍約我到他辦公室,親口問我這件事,我明白表示下個租約前,天地不再出版這本雜誌,他也很爽快地答應延續租約。
不少朋友勸我,不要放棄天地圖書總經理的職位,我不僅失去在左派出版界闖出的地位,而且可能連廉租的房子也被收回,家庭生計會困難。但我已經作出決定,就是保住天地,個人也離開天地,集中精力當雜誌總編輯,重新回到幾個人艱苦辦雜誌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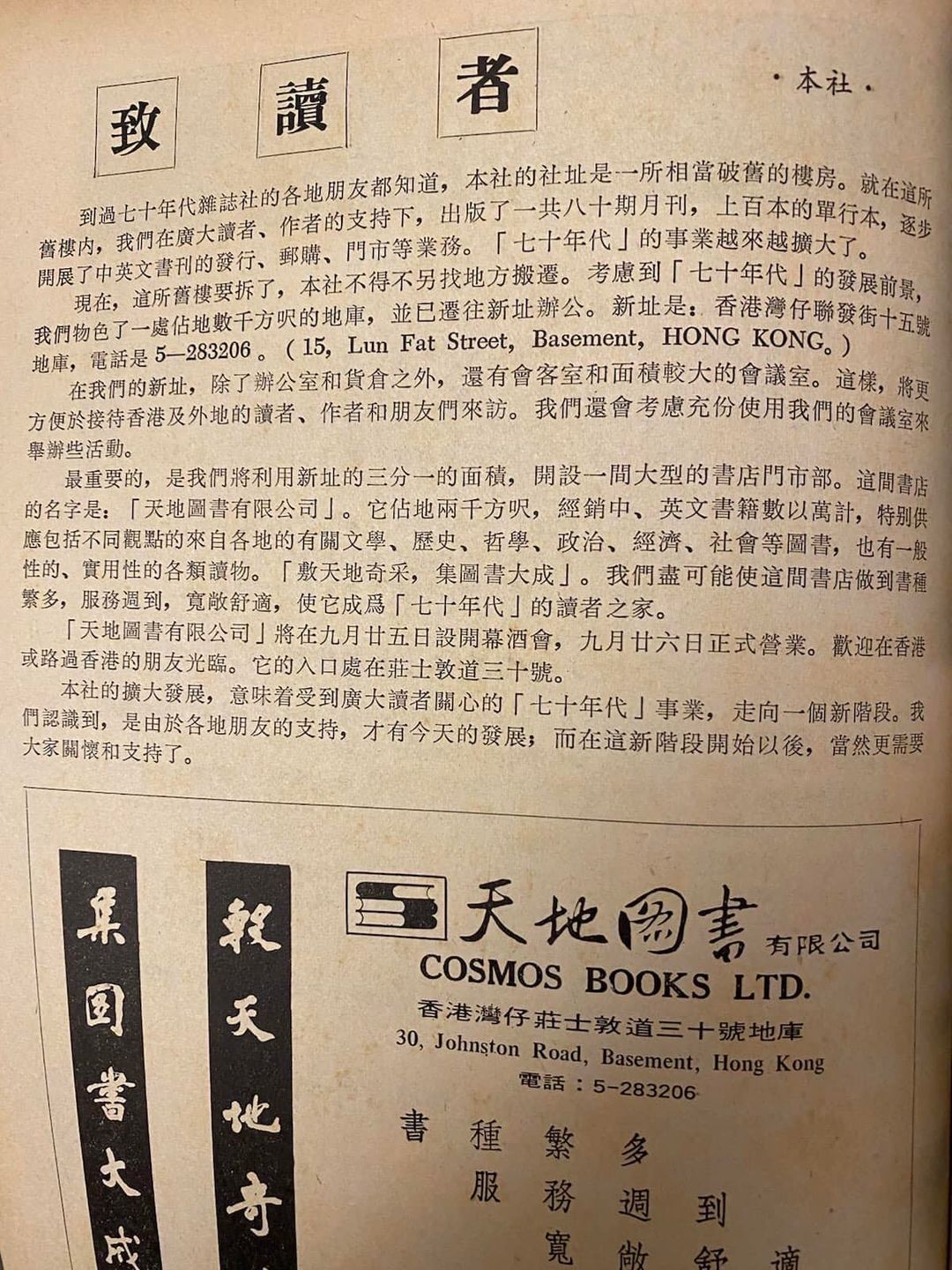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