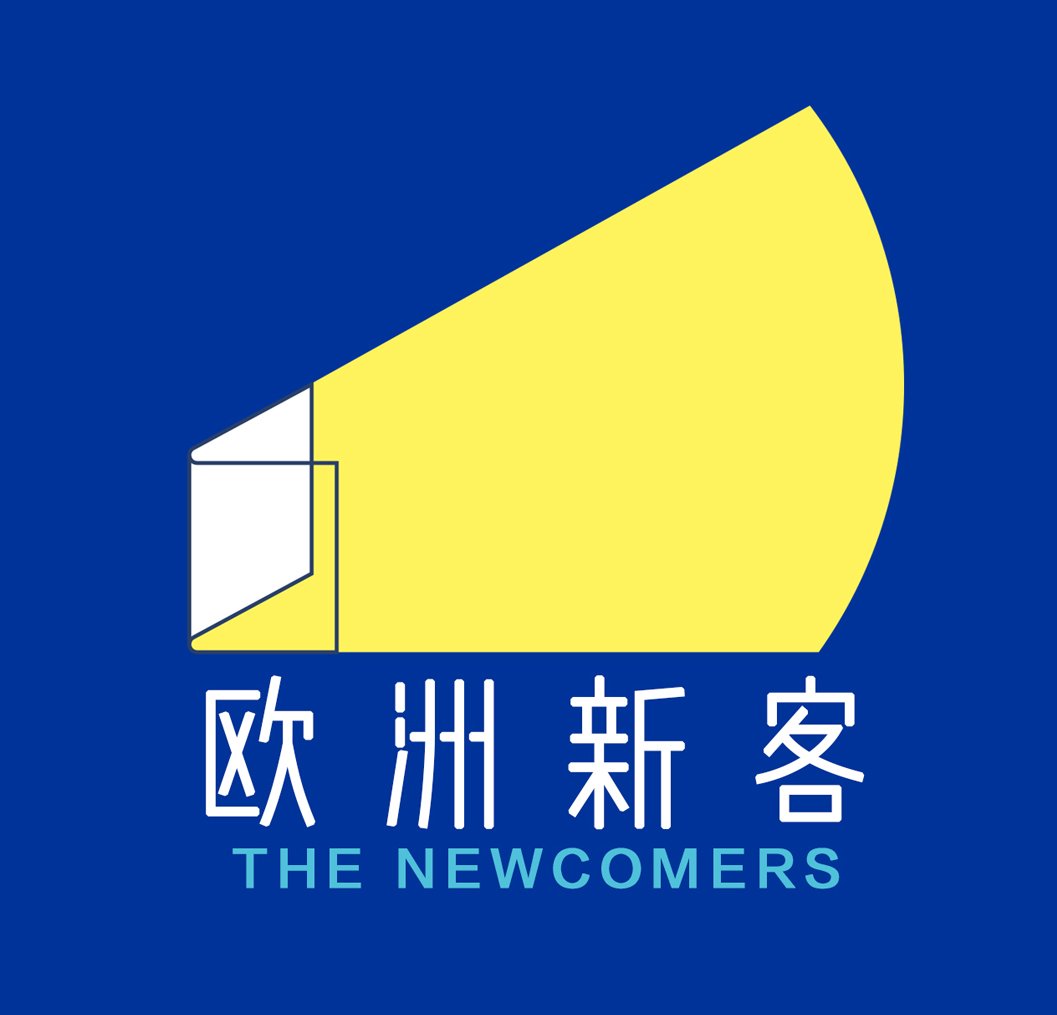谁缝制了奢侈?(一)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
导读
在意大利,华人移工主导的时尚生产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普拉托的纺织工厂到米兰周边的制衣车间,数万名中国移工在缝纫机前日夜劳作,为全球奢侈品牌生产着贴有"Made in Italy"标签的商品。这不是边缘案例,而是意大利时尚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组成部分。
2025年春天,在意大利米兰西北郊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内,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华人工人在讨薪时遭遇殴打,手部骨折,住院45天,工厂被查封。警方通过追查劳务关系,最终牵出了一条复杂的供应链:涉事工厂的供应商Evergreen Fashion Group,而Evergreen的签约方,正是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旗下的Loro Piana。
“奢侈品供应链中的影子工厂”再次成为了媒体的关注对象。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时尚界丑闻和品牌瑕疵,事件发生后,司法开始穿透外包结构,去追问这条外包链条上每一环节的责任。最终,Loro Piana被米兰法院判处为期一年的“司法托管”——品牌需要接受监管官的制度审计,整改其供应商体系。
针对奢侈品牌的又一次结构性问责尝试开始了。但这是一次制度性的转折,还是另一场合规幻觉?
我们希望以Loro Piana被司法接管这一事件为线索,开启一个深度的报道系列。本系列报道不止追问“谁做错了”,更想探讨:为何错误可以生生不息?
本系列由三篇文章组成,带你穿过缝纫机前的劳动现场,看见品牌合约中的空壳公司,最终抵达法院制度的问责边界。
在第一篇文章《谁缝制了奢侈?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中,我们将从几位在意大利服装厂工作的中国移工的真实生活出发,聆听他们讲述日复一日、十四小时起的缝纫日常,也听听他们解释合同、工资、和老板之间的故事。在“没有休息,也不想休息”的节奏中,我们追问:造成困境的是谁?在品牌下达订单之前,这条链条的下游还有议价空间吗?
第二篇文章《合规幻觉:Evergreen与“影子制造”的制度剧本》中,我们将聚焦于Evergreen,这家不缝衣服的“制造商”。它没有工人,没有设备,却能以一级供应商的身份签下Loro Piana的订单,再层层转包。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产业共识:在普拉托,纸面合规比真实生产更重要。通过剖析Evergreen的制度角色,也揭开品牌审计为何总是看不见剥削——它看不见的原因或许不是因为剥削本身隐蔽,而是整个制度的选择性无视。
在第三篇文章《品牌责任的极限:法院接管能否撬动全球供应链问责?》中,我们将深入整个意大利司法体系。在Loro Piana事件中,法院的介入是一次重大突破。但这一制度实验真的有效吗?我们将结合对Dior、Valentino等前例的整理,分析“司法托管”制度的成效、限度与落点,也讨论在多层转包、合同虚化、合规洗白的全球游戏规则下,制度到底能走多远?
我们并不是想否定奢侈,而是想追问透明。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寻找:在这条不透明的链条中,谁拥有权力,谁付出代价?
若您是普拉托或意大利服装代工体系的相关人士,愿意匿名分享您的经验、观察或资料,也欢迎联系作者。
本系列将于近期陆续上线。
谁缝制了奢侈?(一)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

一、说话的缝纫机与沉默的人
清晨七点,缝纫机开始响。钢针划过布料,发出脉搏一般有节奏的嗡嗡声,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渐次停歇。
23岁的小葵,来自江西。如今,她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五年前,她借钱通过温州中介来到意大利纺织名城普拉托(Prato),一落地就被送进了一家华人开的服装工厂,成为一名缝纫学徒。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如今能独立做“整件”,她花了两年时间。如今,她一人就能完成从打袖口到锁边,从上衣领到缝裤脚的所有工序。她现在是一名“计件工”,每月收入最高能拿到两千欧元,前提是“手快,不出错”。
如今,她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工厂包吃包住,宿舍里挤着四到六名女工。工人很多是中年夫妻,厂里提供两荤两素的饭菜,没有假期,只有在没有货的时候才被通知“休息几天”。
她说:“最累的不是在机器前,而是晚上回到宿舍洗衣服的时候。那时候才意识到整个人都快要瘫了。”
她不愿多说最初的事,只简单提到:“什么都不会,就跟着人学。哭过,返工过,没办法,还是得坚持。”那段时间她每月收入不到1000欧,衣服做错一件,就得拆线重做,一边掉眼泪一边缝。
她形容那段日子像从“机器运转的缝隙里挤时间活着”。

在米兰工作的35岁男工大郑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同样通过中介来到意大利,为此交了六万元,没有合同也没有书面保证。他自费买了机票,到厂房后发现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环境阴暗潮湿,宿舍与缝纫区间只隔一堵墙。“没有厨房,没有窗户,只有无休止的噪音。”
他说自己的工资有一部分是“黑的”,用现金发放,最久被拖欠了三个月,最终是靠“威胁报警”才拿回来。他回忆:“那时候真的是,想回国也没路,不干也没出路。”
他们都说自己是“自愿来的”,也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讲的。小葵现在在资助她的妹妹上大学,她最开心的时刻是收到工资给家人汇款的时候,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很能干。她希望妹妹不要再走她的路。她的愿望是以后开一家美甲店,像她一个朋友那样,搬去米兰,离开灰尘和机器。“现在还走不了,钱没攒够。”
大郑说他想存够四十万人民币,回国自己做点小生意。他知道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他也说:“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出来。只不过不会再给中介六万,太贵了。”
大郑说,有时候在梦里,都能听见缝纫机在说话,告诉他快一点,再快一点。缝纫机说话的方式不是言语,而是速度与精确。但坐在机器前的人,却越来越不想说话。
二、暴力的裂缝:一桩案件如何撕开层层外包
2025年春天,一名华人工人因追讨一笔约一万欧元的欠薪,被工厂人员殴打致伤,住院45天。警方介入后查封了涉事工厂,并开始追查其劳务关系。这条线很快指向 Evergreen Fashion Group,一家看似“合规”、实为中转商的供应商。而 Evergreen 的客户,正是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 旗下、以“手工、高端、意大利制造”闻名的品牌 Loro Piana。
据Financial Times和路透社报道,Loro Piana 虽未直接雇佣工人,但法院认定其在供应链管理上“未尽监督义务”。这起案件中,工厂与品牌之间隔着多层外包和中介,公司层层签约,生产地点却最终落在违规使用劳工、没有合规管理的小型作坊。工人的伤情,成了这套分包结构里一条“被记录”的失控。
2025年7月,意大利法院宣布对 Loro Piana 实施为期一年的司法托管(amministrazione giudiziaria),由指定监管人进驻品牌总部,监督其供应链合同体系与合规审核流程。这不是意大利首次对奢侈品牌采取此类措施——过去一年内,Dior、Valentino、Armani 等品牌也被短期接管过——但Loro Piana 的身份格外敏感。它不只是奢侈品的利润高地,也是意大利制造的道德象征。
Loro Piana 的吊牌仍然写着“Made in Italy”,不过意大利制造,也可以发生在法律看不见的角落里。

那一记打在工人身上的拳头,并非偶发的恶意,欠下的薪水,也不仅是老板的偶然失控。更准确地说,是这套体系维持沉默过程中,一个突然露出的裂缝。长期以来,奢侈品牌依赖层层转包、合规文件和形式审计,来将道德风险外包。只要合同签在“干净”的一级供应商手上,只要抽查样品合格、工厂位置不在黑名单上,品牌便能维持一个“不知情”的叙述。
但这次,警方、法院和媒体的多方介入,让这个系统的缝线崩开,短暂的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切口。“如果他没被打得那么重,没人会去查。”小葵说。“工时长是普遍现象,除非做得特别过分,一般不会出事。这本来就是自己选的路。”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Ardita Osmani 也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补充道,这种“信任”往往建立在表面合规的幻觉上:“合同看起来清晰、审计流程也存在,但很多工人与工厂之间早已达成一种非正式的共识。比如纸面上写的是兼职工时,实际却是超长劳动;工资表上一部分走银行,一部分给现金。只要这些安排看起来不‘太离谱’,大家就会默认接受。这种结构不仅让品牌撇清责任,也让工人与工厂学会了‘在规则缝隙中生存’。”
大郑认为:“如果那人不是被打得那么重,是不会查的,而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关注,就只是又一单烂账。”
Loro Piana 所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结构:上游有利润,下游靠人力。品牌不直接管理生产,但通过压价控制每一件衣服的成本。中介公司签合同,工厂去压时间、压人、压安全。每个人都有合约,唯一没有话语权的,是缝纫机前的人。在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系统中,暴力并非系统的失败,而是它压抑极限下的一次“自动校准”。一层层责任被移交、成本被转嫁、权力被抽象,直到有人试图反抗这一层积累已久的失衡——才爆发出肉身对抗结构的直接冲突。
一年的托管期,在法律意义上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监督通道。但对那些仍在缝纫车间日复一日踩着踏板的工人来说,系统响了一声,又迅速归于沉默,普拉托的缝纫机从未停过。
而裂缝,只在偶尔被照亮的一瞬才能被看见。
三、缝纫机下的制度灰区
如果说暴力是结构的裂缝,那么这条结构本身,从未真正遮掩过底层的混乱与灰色。
普拉托的代工体系与其说是一条明晰的线,不如说是一张不断拼接、移动、缝补的网:拼场、搭铺、伪合同、临时搬迁、亲属雇佣与身份依附,
“我们那时候厂小,和别的厂合着用一个车间。”小宣说。她是厂主的女儿,23岁,高中时和父母一起来到意大利。她的父母曾在普拉托开过一家小型缝纫厂,主接粗加工订单,工人住在工厂附近。她用“夹在中间”形容自己的角色,小宣有时候也和工人也一起干活,一起熬夜赶单。忙起来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还有他们的儿子都会一起上阵。
小宣成长的厂房中,并没有明确的上班打卡制度,工人的时间以出货量计算,吃饭和上厕所是唯一能离开座位的时机。“一天四顿饭,我们家自己煮——早饭八点、午饭十一点多、晚饭三四点、夜宵八点。”她回忆,“吃完继续干。”
这种生活节奏与制度安排,在华人移工主导的意大利制衣业中并非特例。根据多位受访工人描述,无论是普拉托的快时尚代工厂,还是米兰周边的高端制衣作坊,都采取着高度弹性的生产逻辑。工厂之间有时会共享设备、分包工序,工人按件计酬,工期紧张时加班通宵,淡季则"放假几周"——有时,是主动;有时,是应对检查的临时躲避。
“警察一查,我们就放假。”大郑这样说。他所在的米兰工厂曾被突击检查,“我们有后门,没证的就从那边跑。”
这种灰色状态不仅存在于居留合法性,也渗入了合同与薪资结构之中。为了协助工人申请或续签居留,许多工厂会“做高工资单”,即合同上写高薪、实际支付低薪,以此在移民局审查中“看起来合法”。“造假成分肯定是有的,”小葵说,“但我们也没办法。有工作、有居留,已经是运气了。”
因此,这种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默契":移民依附雇主拿身份,雇主依附订单生存。而无论是快时尚品牌还是奢侈品牌,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套灰色运作的外包体系——前者追求极致的成本控制,后者则需要在保持"Made in Italy"标签的同时压缩生产成本。
“来意大利是要办签证的。而合法签证需要雇主出具工作证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之间早就形成了’期待与被期待’‘给签证与要签证’的一种前设关系。”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范因坦指出。
更复杂的,是“搭铺”现象。小宣告诉我,一些熟练工不愿再为工厂打工,而是租下老板的机器和床位,自行接货、买线、翻衣服、找司机送货。“就是像‘半个小老板’那样。”她解释,“但其实也很累,要操心的更多。”
一套搭铺设备的成本约为八九百欧元,远低于厂主自营的支出。工人既获得了相对自由,也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赚得多,可能翻身;赔了,可能血本无归。“其实搭铺有时候赚得还不如打工,”小宣说,“但比较自由,因为没人管你。”
在这种制度下,工人与老板的身份边界并不清晰。有的人在打工,有的人在试着“上岸”,更多的人则在两者之间来回游走。而“意大利制造”的字面概念,早已与这套高度灵活、处处擦边的现实生态脱节。
一台缝纫机可以属于任何人,一条生产线可以被三家工厂轮流使用,一个工人可以在不同合同下不断切换身份——唯一确定的事情是:挂着品牌标签的那件衣服,必须按期交货。
四、谁负责这一切?分包链条上的品牌、合同与默契
Loro Piana 以极致工艺闻名——手工、山羊绒、意大利制造,是它长期以来向全球市场售卖的价值承诺。但在这场暴力事件之后,这些关键词突然显得模糊。
法院的判决说明了一点:尽管品牌与涉案工厂之间隔着两层合同与一个供应商,它依然有责任。
司法监管的判辞指出,Loro Piana 虽完成了形式上的合规程序,但“未对最终生产场所进行实地监督”,对下游外包企业缺乏实质性控制。这一“失察”,不仅让工人受伤,也使整个品牌形象与供应链诚信系统陷入危机。
品牌方最初的回应强调“并不知情”。这是分包体系最常见的防线——它靠的不是否认生产链存在问题,而是以合同层层隔离,制造“可不知情”的合理性。
“Loro Piana是高溢价的品牌,理论上有更多利润空间。但他们还是选择层层外包,把实际生产压价压到底。”社会学者范因坦向我们指出:“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没有同步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几乎是这个行业的共识,品牌可能知道下游工厂的实际状况,但它可以“选择不看”。Loro Piana 并不是唯一一个依赖这类结构的奢侈品牌,它只是刚好遇上了这样的事件。

“你说一个老板一件衣服只赚八十五欧,”范因坦说,“要扣掉水电、饭菜、机器磨损、员工计件,真的赚不了多少。但如果品牌愿意让他赚一百八十五欧,他对工人也许就能宽松一点。”
换句话说,品牌不是直接的打人者,但它设定了暴力发生的价格条件。
更微妙的是,法律虽然划出了责任边界,却无法改变定价逻辑。即使被监管一年,Loro Piana 仍然可以通过合规中介转包,仍然可以保持表面审计清洁,只要不再“出事”。
这种责任转嫁机制,是分包结构最核心的“技巧”。通过制造看似去中心化的生产网络,品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剥削的风险卸到最远的一端——而利润,却始终集中在最前端。
普拉托的缝纫工从未和品牌签过合同,也从未进过它的展厅。他们接触的是机器、订单、计件表和闹钟。他们不知道谁会穿上他们做的那件羊绒大衣,也没有机会向品牌表达任何不满。他们只是知道“做完,交货,拿钱。”
而当事情出了问题,品牌只需要一句“我不知情”,便可暂时免于声誉损伤。对某些大牌来说,这甚至只是一次“供应链危机公关”的演练机会。
工人没有议价权,中介没有代价,品牌没有现场责任——这正是“外包”作为现代工业道德机制的一部分所完成的功能。
在这条链条上,每个人都在规避责任,除了缝纫工。他们无法转交疲惫,只能继续工作。
五、沉默如何制造:从不抗议到“共谋机制”
在这场被打断的沉默中,人们开始追问: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为什么明知被压榨,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没有人说“不”?
但这些问题,对工人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
“这本来就是自己选的路。”小葵说。她用了“苦钱”这个词,“不是拿命换钱”,但确实苦。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觉得“出来了,就得干下去”。
不工作,就没有居留;不续签,就得回去;回去,就业形势这么差,也没有出路。
一样的,大郑也没有把“被剥削”挂在嘴上。他说自己愿意出来,是因为“在国内更赚不到钱”。他甚至说:“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来,只是不会再花六万给中介,太不值了,我会自己想办法出来。”
“我们会生气啊,当然生气,我们几个工友晚上出去喝酒发泄,但发完第二天还是照常上工。”大郑说。他承认想过逃离,但他说“走了钱不就白花了吗,回去了也就只能送外卖。”
小葵说:“我们一闹,老板不给我们出证明,不续合同,等居留过期就完蛋了”,她说这种制度就像一条链子,把工人与工厂系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有数,也说不出来。”
这种“心照不宣”也存在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小宣记得一些搭铺工自己接货、赶单,出了差错甚至不如打工稳当。这些人也是在搏未来。他们不是老板,依然出现在厂房里,自己做饭,和打工没区别。
大家共同维系着一种沉默。这种模式不仅是工人对制度的服从,更是一种现实判断的结果。社会学者范因坦也提到:“这些人出来之后,会发现刚开始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比如语言不通、不了解文化法规,连租房子都很难。所以他们只能依附在这些移民开的工厂、作坊里开始打工。如果他们能逐步积累经验和资源,就可能跳槽去别的厂,或者自己开工厂。这就是一种’复制的想象’。”这些工作虽然剥削,但给了这些人期盼未来的机会。
Ardita也指出,这种沉默并非源于个人的怯懦或文化隔阂,而是一种深植于制度结构之中的依附状态:“如果你住在工厂,一旦失去工作,就等于同时失去了住处和社群联系。你会被整个生态系统排除在外。”
她强调,工人沉默的背后并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根本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这种断裂的状态让移工长期处于无声之地:“他们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无法接触其他社群,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理解、沟通或争取自身权益。” 在她看来,这样的结构性孤立,正是压倒工人声音的沉默温床。
而结构性沉默的另一面,是结构性合法。
只要工人不举报,工厂不出事,合同不查穿,品牌就能继续维持它的“合规”。
有一次,小葵告诉我:“其实有活干是好事。你别看我每月两千欧元,好多人连厂都找不到。”她正在学意大利语、期待下月考驾照,想“以后能做点别的”。我问她别的是指什么,她犹豫了一下,说:“可以不一直坐在缝纫机前吧。”
她说这话时,我听见背景里传来一阵缝纫机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持续。
六、谁来扯断这条缝线?
那是一条精密的生产链。
从Loro Piana办公室里的合规合同,到Evergreen中介的供应订单,从华人工厂里不断交班的缝纫机,到移民工人钱包里的现金工钱,每一层都被处理得安静、有序、合法——直到一记拳头,将它击出了声音。一年后,司法监管会到期,品牌也许会换一家更干净的供应商,外包继续、合同更新,吊牌上仍写着“意大利制造”。
这条缝线是否会被真正扯断?
“对于资方来说,他们也有现实需求:在没有自动化技术替代之前,他们必须靠这些劳动力来维持生产。这是现状可能服装行业未来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被技术替代,但目前还没到那一步。” 范因坦提到:“普拉托是一座原本接近破产的城市,是华人把它撑起来的,形成类一种’移民与城市共生’的结构,执法单位可能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除非有系统性外力打断,例如工人罢工、能源危机、机器替代,不然这个结构很难自我转型。
但“系统性外力”意味着什么?是更严重的暴力、更广泛的曝光,还是更多被牺牲的身体?
在整个链条中,品牌追求利润最大化,中介维持表面合规,工厂主低价接单以求生存,工人用沉默换得合法身份与最低限度的稳定。他们之间并非彼此压迫,而是一种张力结构中互相容忍的状态。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方式,但也是目前“最不坏”的局面。
这就像一台持续开动的缝纫机,线路复杂,却没有人敢随意拔掉电源。
小葵也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大家都太怕声音带来的后果。”
那谁能打破这条缝线?
Ardita提出的疑问发人深省:“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 Loro Piana?”她认为,这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产业结构早已存在的公开秘密被偶然撕开了一角。
“当事情出错时,问题才会显现。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没人看。”
她对法院接管是否真的能撬动制度表达了保留态度:“除非这起事件真的能改变定价逻辑和问责方式,否则它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回应。”
她也提到,意大利司法制度流程冗长,程序复杂,“如果这场干预无法触及供应链的激励机制与治理逻辑,那它就只是一个时间点,不会成为转折点。”
这条缝线,会继续保持沉默,只是在某一天某个暴力发生的时刻,再次裂开,然后,又被更熟练的手,重新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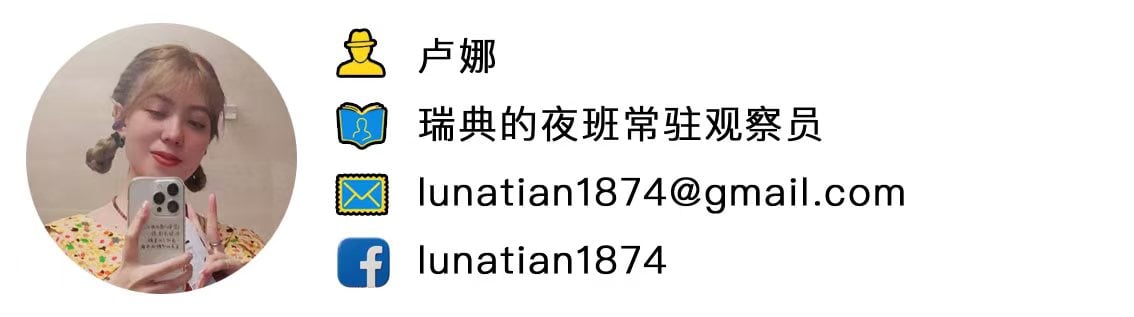
文章编辑:约小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