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好好吿個別吧
一、糖果色青春
我的童年是三線縣城裡中國小孩的童年,是電視機裡不停重播的動漫,是街角小賣部的香氣,玻璃絲手串和是連綿不斷的夏日午後。
我在華北的小鎮度過了最後的童年時光,那段時光,似乎成了我記憶中最不肯散場的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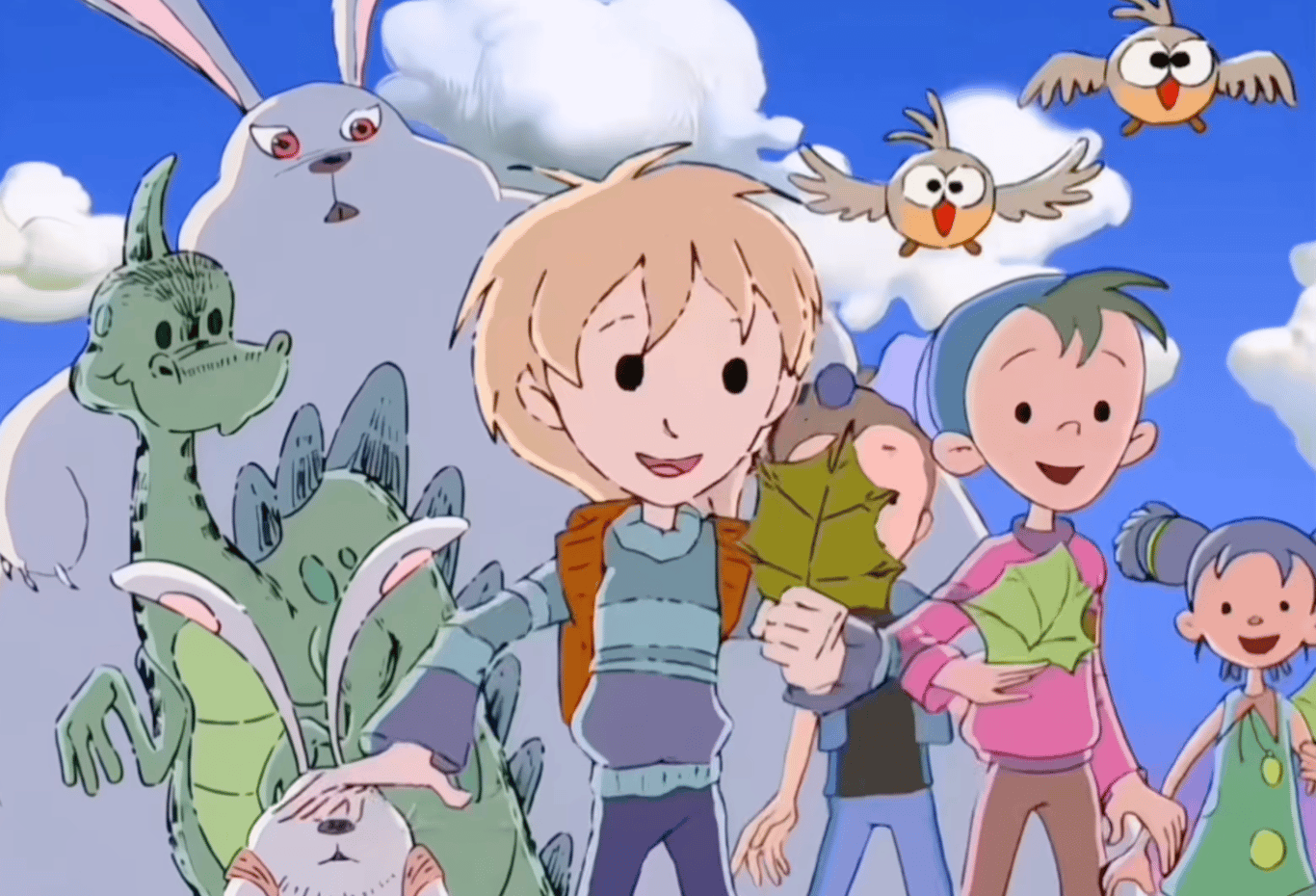
那時我最愛看的頻道是少兒頻道和卡酷動畫,最喜歡的節目是動畫城,我喜歡那個名為《快點告訴你》的主題曲,喜歡看《哪吒傳奇》,偶爾一邊看一邊哭,看《星貓》,還有中央八台的《快樂星球》——片尾曲的“再見了媽媽,今晚我就要遠航”,每次響起都讓我興奮。還有《精靈世紀》和《神廚小福貴》,那我的宇宙,和我的世界。
下午的最後兩節課往往是社團活動課,我們在教室裡唱合唱團的《郵遞馬車》:“馬車將要帶來快樂的氣息,馬蹄聲兒陣陣清脆嘹亮。”我們在操場上奔跑、追逐、跳皮筋,在教室裡講鬼故事,買五角錢一根的棒冰,夏天的所有涼意與快樂都融入進了放學後的夕陽裡。
稍微大一點,我們也開始追劇——《泡沫之夏》《浪漫滿屋》,那些印在香香的小本子上的圖片美的像夢一樣。週末我們會去書刊市場買一堆書,沉得抱不動,還是努力拎回家,晚上躲進被窩裡看《冒險小虎隊》《大宇神秘驚奇》,我還收穫了一本有點恐怖的《人類神秘失蹤案》,每次在宿舍裡給大家講這裡的故事都會把同學們嚇壞。
我成長的那個地方不怎麼重視教育,家長們都稟著小孩子只要不亂跑、身體健康就好的原則。我的小學也不是什麼名校,只是鎮裡面的普通小學,我幸運在剛好趕上了“素質教育”的風口。它是個素質教育實驗校,業餘活動搞的比正課還多。我的班是殘健融合班,在一樓,窗外的連廊爬滿綠油油的爬山虎。我和小夥伴曾經用輪椅飆車,在陽光下笑得東倒西歪。
我愛校門口小賣鋪裡的一切——一元錢能買一大包各色各樣的零食,有香氣的小風扇,一打開就會旋轉出氣味,我真想再買一個。門口角落大鍋裡煮著豆皮、海帶和辣串串,它們的美味也讓我難以忘懷。我是班上最能吃辣的那個,別人在邊吃邊喊辣的時候,我毫無感覺,像個擁有神力的小孩。

我在這裡認識了太多好朋友。這段記憶有一個明確的終點——那是一個夏天,7月2日,小學畢業會考的那天。我們考完所有的科目後,各自收上來一張張同學錄,再把它們裝訂成冊。每一頁上都是祝福和聯絡方式,像一本準備好的散場紀念冊。那天下午,下起了大雨。
暑假裡,我經常在街上的雜貨店、書攤裡消磨時間,喝奶茶、吃手握披薩、炸杏鮑菇(一定要灑上很多辣椒麵才夠味),最愛的是街角的動漫商店,店主總是送我各種小玩意兒。後來我告訴她,我要搬家了,要去別的城市,也許不會再回來了。
我真的沒再回去過。那座城市像一部完成了的劇集,沒有續集,沒有彩蛋。我再也沒有理由踏回去。我成了居無定所的流浪人,而居無定所的人,不會因為告別而過度難過——因為告別得太多次了。坐著綠皮火車一次次遷徙,後來在遷徙和關於遷徙的記憶裡,我度過了自己短短二十幾年的人生。
二、橙子和夏天
我會從小鎮搬去另一個城市,是因為那所中學願意招收外地戶口的學生。並且只要成績足夠好,就有資格獲得他們的獎學金。我靠著幾年來自學奧數的底子考了進去,選擇這所學校的原因很簡單——我的家裡不願意為我的教育負擔太多錢。
開學的那天我又驚又喜,我在開學典禮的現場認出來了我小學時候的同班同學橙子,我問她怎麼來這裡了,她說她家長說這個學校好,有前途,所以逼她過來讀書,她還說她其實沒通過免費生的考試,所以家裡給她繳了擇校費。
我問她,那很貴吧。她說對,一年要繳兩萬。我說,我的媽呀,那也太多了,換我媽肯定讓我繼續在鎮裡唸了。
橙子是我在小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對她的印象是一個成績優秀、安靜乖巧的女孩,她特別會寫文章,數學差一點,我語文特別差,小時候每次寫作文都得軟磨硬泡找她幫助,甚至給她塞汽水糖讓她幫我寫。每次做手抄報,內容基本都是她來找,但是我能畫漂亮的畫,我們一起完成的手抄報總能拿獎。
橙子的媽媽是一個小學教師。橙子特別喜歡初音未來,喜歡寫故事,她也在學畫畫,後來畫的就比我這個三腳貓好很多了。我們都喜歡週末的漫展。那時我住校,週六日懶得回家的時候,就會去她家。賴在她那張小小的單人床上,一起講八卦,聊夢想,她說她長大之後想成為一個化妝師,我說那很好啊。她說她媽媽可不滿意,她媽媽爸爸讓她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可是什麼是對社會有用的人呢,成為大教授還是大官,她說怎麼一從我嘴裡說出來就這麼奇怪。我說就是這麼奇怪啊。她問我想做什麼,我說大怪獸。她讓我好好講。我說,我想去開公交車。後來我大學的時候真的參加了公交司機培訓,那時候我就又想起來了我們的故事。她會拿出藏起來的可樂,我會拿出零食,我們就這樣把夜晚熬成閃閃發光的回憶。
但橙子的生活並不快樂。
她的爸爸媽媽是那種你一眼就知道的,控制慾太強的,管的太多的父母。她不能隨便出門,補習班一個接一個,還有琴棋書畫要學。學校會把考試成績貼在公告欄上,她一旦沒達到預期,就會被打、被罵,甚至被斷飯。她總是笑著跟我說:「我好羨慕你那種放養的生活。」我也總是回她:「我其實也有點羨慕你,至少有人給你準備三餐、削好水果,不過你這種生活我好像真的過不來,要是有人讓我這麼不自由,我現在就會死掉喔。」
她媽媽甚至會當著我的面在飯桌上說:「你看看人家Luna,學習那麼好,爸媽也不管,她還不是一樣考得比你強。」她低下頭,不說話。而我聽見這句話的時候,卻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我不過是自己在生活裡浮沉,從來沒覺得自己有多好,我熱愛玩耍,也熱愛學習,不過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學習就是一個隨緣的事情,喜歡就學,不喜歡就不學。我一直和別人講,我說我就是比較喜歡讀書,所以才一直讀到現在。
某個暑假,橙子給我打來電話。她說她快撐不住了,她在補習班表現不好,爸爸又打了她。她說:「我學不下去了,我想逃,逃幾天也好。」我告訴她,我現在在鎮上,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爸媽回廣州上班去了,問她要不要來我這裡躲一躲,我給她做拿手的菜。
她答應了。
我坐上巴士去接她,我們回到了靠海的那座小屋。那幾天,我們像過暑假的孩子一樣生活。我蒸生蠔,煮皮皮蝦,爆炒大八爪——小時候我很奇怪,我一點肉類都不吃,因為覺得肉類有味道,但我們都吃海鮮。她吃得很開心,我們坐在夕陽下,看天色從金橘變成深藍,再變成靜靜的夜。我記得她說過一句話:「這可能是我這輩子最輕鬆的幾天。」我和她說,我說你的一生還長著呢,怎麼就這輩子了。
可快樂很短。警察還是找上門來了。
她父母聯絡了幾個朋友,有人說漏了嘴。橙子就被他們弄走了,她媽媽當著她的面摔碎了她的手機,給了她幾個耳光,從此我們被徹底切斷了聯繫。
暑假的最後幾天,我接到了電話,來自我們共同朋友的。那一刻,我記得電話的響聲格外刺耳。小藍說,橙子跳樓了。
她從九樓一躍而下,沒有留下挽回的餘地。她和父母吵架後的那個夜晚,寫下了遺書,決定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
她的葬禮那天,下著雨。天空像是也明白這場告別不應該這麼早來到。我沒哭,一滴眼淚都沒有。甚至在之後的日子裡,每次想起她,我都沒哭過。我只是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場徹底的失去。我始終覺得,她很可惜,但是她解脫了。
遺書裡,她寫道:
「我從來不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人。請爸爸媽媽再生一個小孩,或者領養一個小孩,希望他不要經歷我經歷過的那些事。我愛你們,但我累了。我想結束。我有一個小箱子,請給Luna,那是我最好的朋友,裡面是我的日記和動漫收藏。」
我收到了那個小箱子。裡面有她最喜歡的初音徽章、手繪的小卡片、筆記本和記錄我們那幾天生活的日記。她在日記裡說,那是她人生最快樂的一個夏天——但她知道,快樂無法延續,她沒有辦法面對接下來的生活。
他們說她得了抑鬱症。她父母說:「應該讓她多跟正常的小孩玩一玩。」可我知道,她不是病了,她只是被這個世界困住了。
她葬禮那天,化了淡妝,穿得漂亮,甚至是微笑著離開的。我站在她的遺體前對她說:「你的痛苦結束了,可我會一直想你,那該怎麼辦呢?」
葬禮上放著《One by One》。那旋律像是為她寫的送別之歌。那天,雨下得很久。
此後的很多年裡,她常常出現在我的夢裡。我會夢見她穿著我們校服的樣子,走在漫展的走廊裡,拿著一袋買來的糖果對我笑。我偶爾會回到埋葬她的那片小小山坡,安靜地坐著。離開中國的前一個星期,我最後一次去看她。我告訴她:「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來見你了。但我會記得你,我會想你,我會好好活下去。你祝福過我,要我快樂,要我像鳥兒一樣飛翔,像鳴蟬一樣歌唱。」
那年的八月,蟬聲還在,而我,卻永遠失去了我的朋友。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這世界上會有這樣殘忍的父母。為什麼,有些孩子就永遠沒有被溫柔地對待過。
可世界並沒有因此變得更溫柔。
一四年,我在暑假和國慶假期期間去了香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現場」——我親眼看到街頭的燭光,看到學生用自己的身體築起拒絕沉默的防線。維園的燭光晚會、金鐘的雨傘遮蔽、街頭的白布橫幅與墨跡未乾的標語,那些畫面深深震撼了我。那一刻,「民主」「言論自由」這些抽象詞第一次有了溫度與重量。我只是個普通的中學生,但是我無法假裝這一切與我無關。
旅行回來後,我懷著激動的心情,把所見所感寫在QQ空間上,也貼了幾張現場的照片。我並沒有嘲笑誰,也沒有攻擊誰,我只是記錄和分享我知道的事情。之後,沒過幾天,我就被班主任叫去談話,又被教務主任約談,接著兩位派出所的警察出現在校門口。他們帶我去一間空教室,說是「批評教育」。我已記不清他們的每一句話,但那種壓迫感至今難忘。他們說我不能與「境外反動勢力」有來往,說我太天真,說我「好自為之」。最後,在老師的強烈要求下,我被迫寫下了一份保證書,保證不再談論、不再發表、不再參與。
其實事後,最讓我難過的,不是警察的警告,而是從我身邊一點一點退去的朋友。原本會和我聊天的同學開始疏遠我,有人甚至不再跟我打招呼。我也明顯感到老師對我「特別關注」,每次課堂發言、作文題目、社團活動,我都感到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在後面盯著。那年我十六歲,原本還算成績不錯,但從那次以後,我對學習徹底失去了熱情。不是我不努力了,而是我不知道努力換來的是什麼。是讚美還是警告,是自由還是更大的監視?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我開始逃課,開始躲避,不再參加校內活動,也不再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未來」的說法。
那時我常常想,如果橙子還在——那個願意把所有壓力都說給我聽的女孩,那個說我煮的皮皮蝦全世界最好吃的人——如果她還在,她會怎麼看我?她會不會和我一樣覺得,這個世界根本不允許孩子擁有真正的聲音?她會不會和我一起並肩而立,而不是躲起來一個人哭?
事隔多年之後,我收到了幾個中學時期朋友發來的道歉,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後來成為了抗爭者,也說契機來自於以前我做的事情,一直在關注我後面的經歷——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麼,但會想起當時的事情,我還是失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年蟬聲依舊,天還是藍的,而我卻比任何時候都孤獨,我好像有一點恨不允許他們再和我接觸的那些家長,可他們的孩子最後也離開了他們,甚至沒有告別,就離開這個國家,一去不回。這讓我覺得特別悲涼。
三、祝你前程似錦
在中國讀碩士的最後一年,有一種快樂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預感——我們都知道,這樣快樂的日子還會有幾個呢,很快我們就會散落在世界上的各個地點。
碩士開學一個月不到的時候,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們就給彼此取了花名,我們的四人組是山貓小隊,我們總是一起吃飯,三個男孩加一個女孩的小隊,我是隊長山貓,還有夜隼,鬣狗和禿鷲,每個人都有一個野生動物代號,我們在群裡聊天打鬧,研究今天吃什麼,在課堂上交換零食與眼神,在無數個雨天和晴天裡說過以後想做的事情。
其中有一個人,是我們的禿鷲彬。
他是那種體能與精神都異常堅定的人。在我們睡懶覺的日子裡,他每天早起健身,在食堂吃早餐。熱衷於野外冒險。他總是提議我們「拉練」,說得像軍校,其實就是約我們去爬山、看瀑布、穿越郊野公園。一去就是一天,回來的時候我們全身濕透、鞋子裡全是泥巴,但他總是精神奕奕,像完成了一場修行。他還加入了幾個徒步群,週末常一個人背包出發,朋友圈曬的是山路、雲海和帳篷。他笑著說:「留在城市太悶了,人一窩在教室裡,腦子都長霉了。」
他本來是學哲學的,喜歡談波普爾和庫恩,也偶爾和我們說起康德和維特根斯坦。但後來,他變得沉默了。他說自己學的東西沒有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有段時間他在科普中心實習,但不久後也不再出現了。課越來越少上,實習也漸漸不去,連論文開題都沒參加。我們找他,他總是說「太垃圾了,不想寫了」,可其實我們都覺得他寫得很好。他英文一流,讀原典不費力,也能寫出邏輯嚴謹又不失風格的分析,但他就是不肯相信自己。他說:「這套體系不是給我這種人留位置的。」
最後他決定放棄學位。沒申請延期,沒交論文,就這麼從我們的世界裡慢慢退場了。
我們找了他很久,終於有一天他回了微信。他說,他現在在流浪,說不上在哪個城市,說不清下一步去往哪裡。他說:「也許哪天我會重新開始,也許不會。」
後來,我們才從別人口中知道,他在一個野外徒步群裡已經成了一位廣受歡迎的嚮導。他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巧大力」。這個名字在群裡幾乎成了一個傳說——總有人說他帶隊穩、野外求生技能強,還特別會講故事。他像從城市的陰影裡逃了出去,重新用另一種方式與世界打交道。
他真的沒有回來,但他也沒有消失。雖然碩士典禮上沒有他的身影,畢業照上沒有他的臉。
我們一直記得他,就像記得一個沒說完的故事。他好像真的走到了我們沒能走去的地方。我總是想起他,總是羨慕他。
我意識到,每一次畢業都像是蜕了一層皮,真的離開了與你朝夕相處的人。像陽光灑在地板上,然後慢慢消散。
我畢業那年,內蒙古的學生們在操場裡唱著額爾古納樂隊的《畢業歌》。他們不唱流行的畢業歌《梔子花開》和《後來》。他們唱:「年輕的夢在這裡發芽」,唱:「明天又開始新的出發,請不要擔心害怕」,唱:「告別了青春的美麗童話,我們都一起長大」。
我記得那首歌,我記得告別前一夜,我們一起喝酒聊天,最後擁抱的時候,我親愛的同學們的眼睛裡閃著光,隱隱藏著濕氣。
畢業後的第三個月,我又開學了。我在新的城市裡認識了新的朋友,生活很順利,安定,平靜,沒有那種躲躲藏藏的不安了。我開始有機會在沒有審查的世界裡面繼續好好寫作了。但我也總是在夢裡見到過去的朋友們——夢見大家一遍遍問我什麼時候回去,夢見我們再見的時候,所有人都很好。
我在夢裡和他們說,等秋天吧。等下一個秋天來了,我就回去,我們再一起去山上坐坐,看太陽升起又落下,吹吹風,看天邊的雲漂來漂去。藍藍的天,白白的雲,我們無憂無慮,風吹過稻田,一片金燦燦。
有時我也夢見老朋友們過的不好,夢見他們說自己很迷茫,我想,也可能是我把自己的迷茫無意中投射到了夢裡。我夢見十年、二十年後的我們,還在思考夢想與無法選擇的路,還在困在身份與選擇、人與人之間的立場與衝突裡。
夢裡,有人去了堪薩斯——曾說過想去北歐的孩子去了那裡,夜空也有好多好多漂亮的星星。有我們說過的營地與篝火,有天文望遠鏡,哈蘇和銀河。遠遠的地方傳來劈啪聲,我們的聲音也在其中。
我有時候覺得,我好像什麼都擁有了,我在自己可愛的小屋子裡面,被喜歡的樂高包圍著,我能自由的寫作和大口大口的呼吸了,我終於不用擔心突然被抓走了。可是呢,我還是想和老朋友們一起出海。還記得嗎?我們曾經說過,總有一天,我們要一起出海,但我們一次也沒有一起出海過,我後來出海了,可是是我自己一個人。
我夢見他們深深地愛著我,我也夢見我深深地愛著他們。
我最好的朋友們。我記得我去祈禱的時候,我說此時此刻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我們都好,一切都好,身體健康,生活順利。
我好像真的想不明白,為什麼時間總讓我和我的朋友們分開,讓我們漂流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我可能沒辦法忘記,我們曾經在兩年三年中日日夜夜相見、相愛,到頭來也只能帶著行李箱與祝福各自離場,我仍然想念和我的好師妹一起喝奶茶,吃砂鍋米線的日子。我想,朋友是我在幾年裡的家人,那我大概這輩子都會為這場離別而哀傷。不到一年,我的思念就堆積如山。我無法想像未來還有多少個像這樣的日子,多少個如今天一樣漫長的夜晚,在夜裡,我將想念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還有我們不再在一起的日子。這是給深愛著朋友、並且擁有許多重要朋友的人,最深的懲罰。
我想念我們一起玩桌遊的日子,想念輸了要做俯臥撐的懲罰,想念開題那天坐在教室裡小聲說話的模樣。我想起畢業答辯後我們一起去吃拌飯、打麻將,然後我一個人回到宿舍樓下,哭得像個小孩子。我只是想——這樣的日子可不可以久一點,再久一點。
但我知道,我要走了。
離開家的那一天,我沒有回頭。也許對某些人來說,離開是結束煎熬的解脫;可對我來說,最難的日子才剛剛開始。明明是快樂的日子,卻那麼像懲罰。
我總是想回到過去。不過現在,我學會了一件事:再見,不是結束。
我允許我們再見,我也不怕我們告別。因為我知道一定還會有下次見面的機會,我知道,我們始終是朋友。我等著我們交換彼此那些知道與不知道的故事。
有了這份期待,告別也變得溫柔。寫別離,不再是寫失去,而是寫拿得起、放得下,寫沒關係,都沒關係。
我學會了怎麼離開一個地方,像付清賬單一樣,一筆勾銷所有的悲傷。也學會了:不消滅它們也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是滿族人,我在草原和大海之間生長,遊牧民族的悲傷是豁達的、廣遠的,一望無際。它絕對不是陰雨連綿,不是壓抑沉默,不是鈍刀割肉一樣的劇痛。
我們的別離,是鴻雁下斜陽,也是西出陽關無故人。我會認真地、大聲地告別,然後坦誠、驕傲、忠實地面對自己,包容地面對世界,迎接你的明天,我的明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