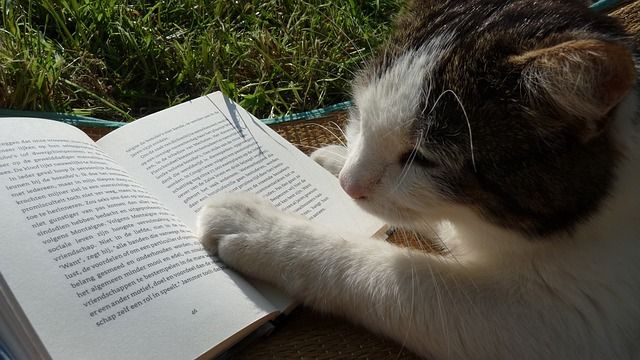《雪水消融的季節》:抵達所未知的一切

《雪水消融的季節》(2024)始於一起2017年佔據各大新聞版面的山難事件,新聞裡這樣描述的:「一對台灣『情侶』前往尼泊爾登山旅行,卻因大雪受困於深山岩洞中長達47天,男孩梁聖岳獲救,女孩劉宸君則於搜救隊發現的前三天離世。」
彼時,身為兩人「摯友」的羅苡珊,原預定於尼泊爾與他們會合,卻在印度旅行的途中疑似感染瘧疾而回台,這場約定好的旅程,就此成為一場永遠不可能抵達的遺憾。
事件之後,梁聖岳帶回洞穴裡的文字和話語,包括那封貫穿全片的、或許可以視為遺書的、劉宸君寫給羅苡珊的信,以及促使他們拿起相機的信念與渴望:「活下來的人要說出這個故事。」
作為活下來的人,該如何活下去?
影片前半部為羅苡珊與梁聖岳的日常對話、訪談、登山與看海的片段,兩人曾約好再次重返尼泊爾,回到多年前那座受困的岩洞,完成那趟年少時未能實踐的旅程。但隨著時間線的推進,可以看見梁聖岳從表面輕浮的避而不談,到明顯抗拒談論有關尼泊爾的事。
片中並未呈現太多關於梁聖岳如何看待山難事件與劉宸君的敘述,又或者說,梁聖岳想要透過鏡頭告訴公眾的內容,可能已然表述於身為陌生他者的媒體記者前;但是於親密朋友的羅苡珊前,梁聖岳反而展現出面對事件的的故作輕鬆、態度反覆。
這也許不只關乎公共與私人的倫理界線,而是本質性地指出創傷經驗的複雜性──倖存者不可能只有一種面貌,而對於特定情緒狀態的強調,只是反映出這個社會強加於倖存者的想像與期待。
創傷經驗的體現與外化,並不必然以哀悼、悲戚的形式呈顯,更可能是在無數次的攀爬、騎單車、按下錄影鍵的日常中學習度過。看似悠緩的生活記錄於是開展出一場辯證的關係,也讓羅苡珊開始明白,兩人所面對的創傷其實是不同的:梁聖岳的經驗來自面對好友離世的「在場」,自己則是面對好友離世的「缺席」。這個回到尼泊爾的約定始終是必須獨自一人前往的旅程。
從第一人稱的視角,羅苡珊告訴我們媒體視角以外的,自身所認識的劉宸君,及其對生命與世界的思考。無論是影片字幕中隱密的性別代稱,或是三人對於彼此關係模糊曖昧的表達,均傳達出一種屬於他們之間獨一無二的酷兒性。關於劉宸君的創作與思考,也集合成劉宸君離世後兩年出版的《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一書。追溯劉辰君遺留的生命痕跡,羅苡珊似乎隱然將自己活成了另一個劉辰君,正因為認知到無法代替任何人活下去,所以想去看見他所看見的世界。
影片後半段以接近民族誌紀錄片的方式,尋訪尼泊爾當地居民與搜救隊,重述他們對於台灣旅人與山難事件的記憶,也帶出自然的不可預測性,以及人的脆弱性。那是一種面對自然的謙卑,不同於鋪天蓋地、英雄主義式的台灣媒體報導,「山難」對於尼泊爾人而言,更像是一種人身處自然秩序中的必然性。山,本來就是一個充滿未知與神秘的存在,而非一個人類所要征服的對象。在山面前,一個生命的消亡是如此微不足道。
這或許也諭示了羅苡珊終於回到那座洞穴的經驗與感受,無論事前如何揣想好友生前所經歷的一切,多麼想要試圖理解好友、理解好友的死亡、理解好友如何面對與理解死亡,只有親身來到現場才能真正體驗自然並不慈悲。
也才終於理解,是理解到理解的不可能。沒有人可以代替生者存有於世永劫回歸的痛苦,正如同沒有人可以代替死者詮釋一段無人知曉的歷史。而我們所能做的,唯有不斷重複逼近真相的徒然嘗試,抵達所未知的一切,包括死亡。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發現這裡?但我還是決定每天跟你說話,一直說話到最後一刻,不管自己的文筆技巧了,那些都不是真的,到了這岩洞後,我想跟你說的才都是真心的吧。所以千萬別怪岩洞,如果沒進來,我是死的,我們還是一樣不快樂。
夜晚的時候我會很痛苦,因為我好想家,想把單純的自己給你們看,但如果肉體回不去了,我會把一部分單純的自己放在山上,一部分帶回家。
你不要擔心我了,我這輩子一直到現在才學會真正地放鬆,儘管真的很想活著,接下來交給山安排了,但即使食物不夠了,這樣一直寫一直寫我就覺得自己不會死了。
直到這時,我才覺得自己真的成了作家。」──劉宸君〈回家〉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