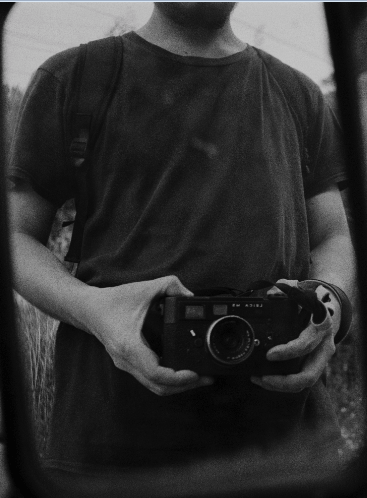北境織影 (The Fabric of Belonging,2025)展覽小記
Hjördis Haack(法羅群島)、Nina Maria Kleivan(挪威)與Bent Hedeby Sørensen(丹麥)三位藝術家的攝影項目《北境織影》(The Fabric of Belonging)將在本月27日於北歐當代藝術中心進行展出。此一三人協作的攝影項目言之簡單:三位藝術家身著各自映射著自我認同的傳統北歐服飾——法羅群島、挪威、丹麥各有分別——流轉於世界各地間的不同場景中,並以數字相機擷取圖像留存。較諸作品形式與內容上的單純,於時間卷軸上,此項目卻已敦實地持續了12個年頭,且目下仍在進行當中——布展期間,三位藝術家仍舊抽暇,特地帶著服裝到廈門島內拍攝。說起來,這樣一種以城市空間比作劇場,身著非日常化的「異裝」進行創作的方式於目下並不鮮見,反而是一個相當流行的當代攝影表達式。僅在國內來說,王寧德於廿世紀末開始持續創作了十年之久的《某一天》與區志航於差不多同一時間開啟的攝影項目《那一刻》,其實都算相似的表達。當然,在身著民族傳統服裝入鏡這一點上去看,更為相埒的莫過於繆曉春身著漢服兀立於城市中的一組攝影作品,譬如《渡》(2002)與《扶孤松而盤桓》(2002)。
然而,正如攝影評論家們注意到的那樣,繆曉春身著漢服的士大夫形象乃是一個幽魂——無論是刻意擬古的立軸、長卷之呈現,還是鏡中他自己與周遭路人那漠然的撲克臉,皆憂鬱地暗示著,這魂靈究竟是要歸返、並消失於來處不可。因此,其圖像之後便不由聯繫著一個徹頭徹尾的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崇高者的回魂與其無可避免的悲嘆。事實上,即便在今天,這一文人幽魂形象亦可相當真實映射出國人——尤其是智識青年們——的精神狀況:認同失效,身份模棱;精神空乏,無可如何。

由此比較,我們便大可看到《北境織影》的一個特別之處。對於亦在實踐一個長期攝影項目的筆者而言,直面這些圖像時最覺得有趣的部分便是其整體上完全不拘於電影劇照風格、從而相當貼近日常的隨意性——其語體層面的進行體(CONT and PROG)無疑也增益此一特性,圖像中既有極悲劇形式的拍攝——海天使雕像(Maritime Monument,Copenhagen)下構圖完美的哀默群像,亦有大量猶如徑直取自Instagram賬號上的日常留念式照片——以著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為背景的「遊客照」。我們當然深曉,即便是當代創作,在表達上也應盡量規避這樣的左右互搏式。但令人驚訝的是,當這些衝突的元素與圖像並燴一爐時,卻絲毫沒有減損作品的表達。除了三位老成藝術家的編集之功,我們當然還想繼續問上一句:怎會這樣?筆者以為,於此起作用的大約乃是一種因為足夠篤定自若、而能夠進行自我戲謔的力量。在這一意義上說,穿著傳統服飾的三人儼然「死亡之舞」壁畫裡那些敲鑼打鼓、四處拿生者取樂的「擬人化的死亡」——但絕非磷火般哀弱之幽魂——正於21世紀的大都市當中繼續著他們嘲弄的工作。其既用行動與鏡頭嬉笑詰問路人,也嬉笑詰問著自己:看吧,現在你我都給弄成了這樣了,奈何?!然而,正是這一主動將自身也一並平鋪的方法,使得那些攜帶著傳統的圖像徹底溶進了當代生活。一如游擊隊女孩故意管自己叫「女孩」以衝破沉舊結構,《北境織影》這般示以自我戲謔的面貌,亦奇特地現出一股強力,開啟對談,並藉此於虛無之世重新闢出一塊對傳統與認同的闡釋空間。與之相對,我們則能很清楚地看到,在繆曉春的「死亡之舞」中,那在城市的鐵筋泥灰裡格格不入的士大夫則成了被那「已死而不自知的都市人」所譏訕的對象,因而除出一聲哀嘆,並無一物留下。
當然,須得補充的一點是,上述這種憂鬱的無力與敗陣,想來只會發生於「視死若歸」的當代脈絡中——幾乎所有企圖在形式上擬古、在內容上繫聯歷史的當代創作都會遭遇同樣的尷尬:這卷軸端的不錯,因為它跟我的肥皂箱一樣好。我們究竟身處於一個「美讓位給陰影」的時代,顛倒反是常事。佈展閒暇與三位藝術家閒談,在提及攝影書的形式時,Hjördis與Nina表示12年的積累當然已成功編集出了攝影書,但這次我們並沒有為展覽把它們帶過來,因為那「太重了」。天然,作為專業的當代視覺藝術家,三位於此類由形式進入、進而探討攝影本質的思索恐怕並不甚在意,這並沒有甚麼奇怪。然而,隱藏其後的「展覽-感官」的興起與「印刷物-沈思」的逝去,仍將角力在嗣後一個個「不起眼」的瞬間,並持續引爆種種不容回避的議題:一種更普遍的身份認同是否真的可能?綿延的坐定對談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方法,而非流於一種裝飾性的躲避?隨勢消解,還是紮下根來?闇影時代,你我如何是好?
無論如何,這是當代的代價,也是當代的誘惑。
20250923@NAC, Hsiamen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