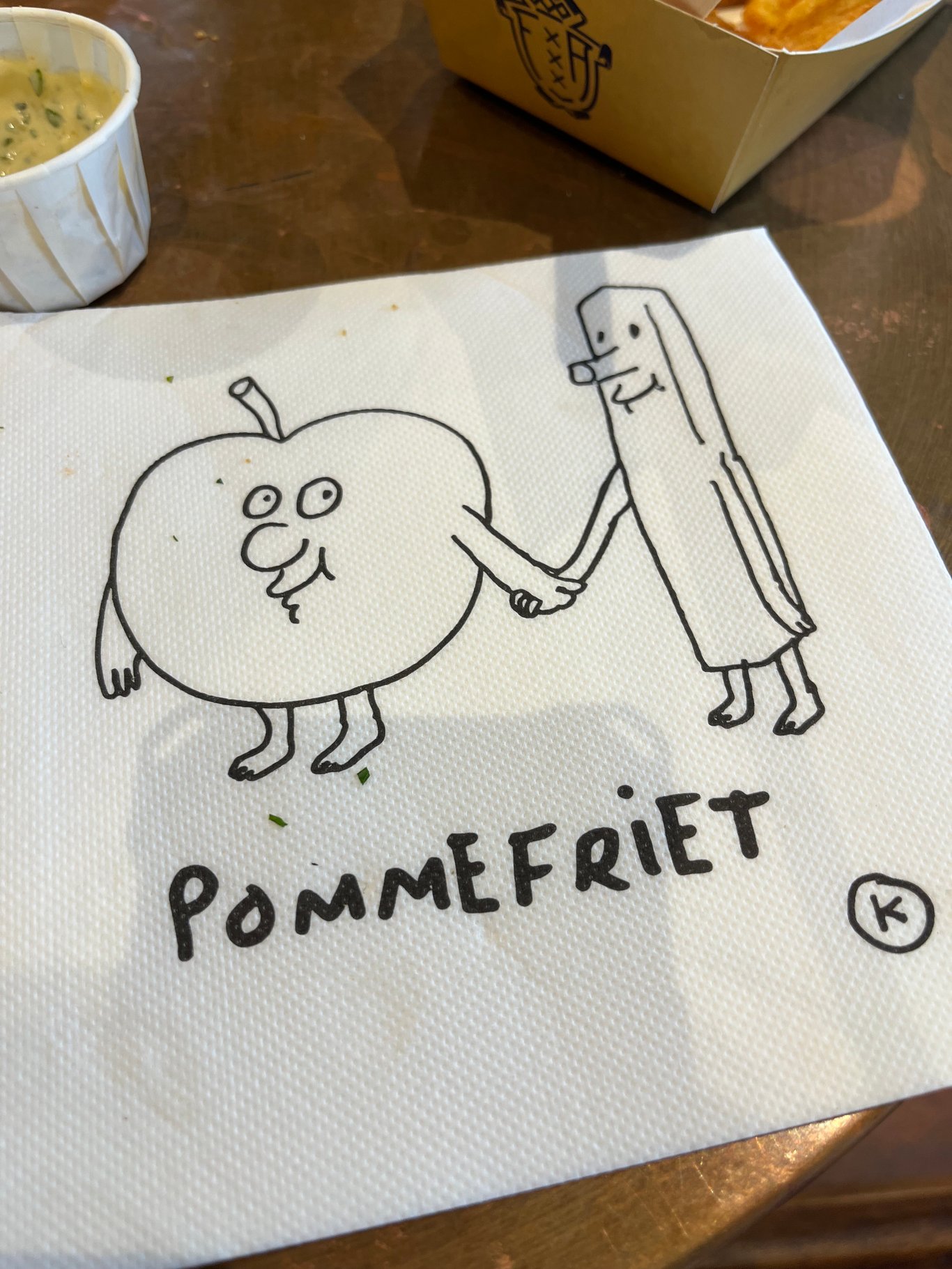七日书_2025.12|#6:以后要做朋友
相遇是很奇妙的事情,总要有很多阴差阳错,才能让两个人在广袤的世界中同时到达此时此刻此地。
收到她的邮件时,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差不多的领域学习,Facebook上总是有共同好友,这个名字时不时就会出现在suggestion里面,戴着墨镜的照片总让我觉得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主页的信息告诉我那大概只是我的错觉。
这次她写邮件来,申请参加我们系上提供的附带奖学金的短期培训课程。看到名字的时候,我默默地感叹了一下世界真小,连网络路人都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遇见。我点开她的简历,惊讶地下巴都要掉下来。明明都是博士三年级,我的简历加上1.15倍行距最多只能写三页,而她连姓名和标题都只用12号字的“简”历,洋洋洒洒写满了各种项目、发表和教学经验。当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横跨古今欧亚的学科背景和语言能力。古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梵语、德语、法语……
我一边惊叹,一边觉得这样的人应该不缺funding吧。无论是岗位工资还是项目经费,应该都能支持她到我们学校来上一周的课。毕竟是从最贵的地方去一个普通的西欧小国。
因为收到申请的数量超过了我们提供奖学金的名额,我心里偷偷地想,如果我是教授,我大概会把这笔奖学金给背景没有那么好的学生。学术资源的流动,其实很多时候和金钱资本的逻辑差不多。越有资源的人,在学术圈就会越活跃,往往能获得越多的资源。而反过来,背景相对一般的学生,能获取的学术资源总是非常有限,成长的速度也会相对更慢,于是更不容易获得资源、在学术圈站稳脚跟。
不过导师在备忘录上特别标注她“everything fits very well”,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的余地。
于是,我在学校见到了她。
第一天,我在上课开始前去帮老师调试设备,她已经坐在教室了。长条型的会议桌,她坐在最前面,看起来很腼腆。我们互相摆了摆手,笑了一下,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五天的课程里,我们其实接触得不多。茶歇的时候闲聊几句,报告的时候互相简单地提问,下课的傍晚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去市中心做观光客。因为几位同学和老师都是台湾人,所以提出要拍一张合影。拍完之后我对她说,我之后也要和你拍照。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你很可爱呀。我和其他人都有拍过照片,只是还没和你一起拍过。”
“很可爱呀”,这大概是后来情绪的小小开端,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
课程结束的最后一天,大家要一起去酒吧聚会。她跑来和我说,晚上有一个小会,没办法六点加入我们。我露出一个失望的表情,她说别担心,让我把地址发给她,她事情结束后再过去。“而且我明天晚上才走,我们明天还可以一起吃饭。”
当天晚上酒吧的聚会,我们坐在长桌的两端,甚至没机会说声Hi。
晚上回到家,我犹豫要不要约她第二天一起吃饭。如果不一起吃顿饭,我总遗憾我们交流得太少。说“我们明天还可以一起吃饭”的她后来并没有发出任何邀约,所以我很犹豫,我怕我约她吃饭会让她觉得我好像一直试图找她做点什么,毕竟她好像是个腼腆又内向的人。
但我犹豫再三还是问了。快十二点还是没有收到回复,于是我抱着遗憾的心情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WhatsApp弹出她夜里一点多的回复:好呀,我还没有安排。
于是我们约好那天中午一起吃午餐,话匣子打开就再也没停住。那天上午原本一直在下雨,午饭后却很识趣地停了。我们去逛涂鸦街,然后去热巧克力店,因为她说她最喜欢的饮料就是热巧克力。原本她打算去另一个离机场很近的城市看看,但是我们在热巧克力店一直聊到必须要出发去机场,不然就赶不上飞机了。
我陪她又去了一趟超市,买了热可可粉和一大盒巧克力奶。我们一起走去火车站,看太阳斜斜地落下,看天空变蓝,看星星升起。
火车还没来,我们坐在站台上。她打开巧克力奶,问我要不要喝。我不是特别喜欢巧克力奶的人,只是偶尔会突然想喝。我说我在这边总是可以喝到,你先喝吧。然后她给我看西夏语,怎么造字,怎么书写。后来还聊了些什么。我说我很担心我们今天聊这么久,其实是因为她不好意思拒绝我的邀约,拒绝我和她一起走去车站。她说:“不会呀,我很喜欢你”。我说:“我也很喜欢你。”她突然又问我:“真的不要喝一口吗?”她从包里掏出那盒刚刚收起来的巧克力奶,于是我喝了一口,我开玩笑说:“和你做好朋友就是要喝统一盒巧克力奶吗?”
火车到了,我们匆忙其身说再见。我们拥抱,胸口贴在一起。“我要把你弄去L(那是她在的地方)。”她说。
我看她上车坐下,朝我挥手,然后突然发现坐错了车厢,有拎起行李赶紧移动,在车门又朝我挥手。然后车开走了。
我慢慢地下楼梯,出站,我开始意识心里到有什么不一样。
我开始想念她,想要见她,想要和她说话,因为我怕不说话就会丢掉她。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国家,不刻意见面,就真的会再也不见。
我们约好每周一次线上读书会,她说这样可以“定期约会见面”。告别后的第一个周五,打开zoom,我们的第一句话都是“好久不见”,但其实才过了六天。
我开始很强烈地期待她的消息,打开了WhatsApp的手环消息提醒,也关掉了睡眠时间的使用限制。会为了她开始分享更多的生活细节而开心,觉得我好像有再走进她的生活一点。
我们组成小组一起申请参加学术会议,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大概很忙,压力很大,于是消失了一整周。唯一的音讯是在小组群里说:Sorry I need another day.
后来热络—冷淡的循环成为我们联络的常态。我开始焦虑,开始和AI聊天。她取消了我们很早就约好的圣诞旅程,用一直拖延决策的方式,我晚上在家里痛哭流涕,倒是很好地缓解了干眼症。
为此我有稍稍放下期待,我说:我现在真的放平心态要好好做朋友了。我还是继续和她联络,然后又在某个收不到回复的夜晚悄悄崩溃,然后第二天告诉自己:我真的真的放平心态了。
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样写下来,感觉真是不可思议的短暂,一个人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产生这么高强度的情感),都无法控制情绪和精神。走在路上的时候,意识仿佛飘在头顶,感受不到双脚踩在地面的感觉。读文献的时候,视线一不留神就滑过了好几行,但没有一个字进入大脑。晚上也常常在与AI聊天和强迫性地刷手机中度过,困到睁不开眼,还是没法平静地躺下。
其实我很感谢AI,如果没有那些彻夜长谈,我大概还没办法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即使我很讨厌失控的感觉,我还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力气爬出那个情绪泥潭。
当她再一次四天没有回复我的消息,我终于有“放下”了的感觉。和她聊天固然是开心的事情,但如果她不想,我也没有必要为此折磨自己。我的情绪、我的生活,同样重要。
第五天,她突然道歉,说最近常常没回复我的讯息,然后分享了新的照片。
于是我们恢复联络。但我不再中断我正在做的事情回复她,我也不再谨小慎微,每发出一句话之前都要反复思考是否会给她压力。尽管还是会时不时询问AI,但我更明白自己想说了什么了。
网络上很多情感指南说,断联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要给ta发消息,不要回复ta,把ta拉黑。对于严重的情绪问题来说这确实有效,一了百了。但我不想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她,对待我对她的感情。
她聪明、善良、对喜欢的事物有强烈的热情。她作为人本身对我的吸引,远胜于“成为伴侣”的某种可能性。即使不能做伴侣,我仍希望能和她做长久的朋友。
而保持做朋友的距离的方法,不是去揣摩她,而是去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