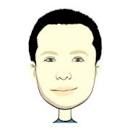清華十一偽簡《五紀》誤用『文后』一辭而露偽
清華十一偽簡《五紀》誤用『文后』一辭而露偽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十一輯只有《五紀》一篇,130支簡,約三千字。其內容,似在建立什麼“藉托「后」,論述五紀(日、月、星、辰、歲)與五算相參,建立常法;在此曆算基礎之上,將禮、義、愛、仁、忠五種德行,與星辰曆象、神祇司掌、人事行用等相配,從而構建了嚴整宏大的天人體系”(書中整理者言)。自從此清華簡十一於2021年公佈之後,不少媒體及學界也多有報導及研究,慘不忍視。到是有一位研究者,詳參內容,給出了一些評論,並認為:
『《五紀》篇內容較之於《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或者《管子》中的《幼官》都頗為不及。類似於《五紀》這樣的系統構築,隨便什麼人每天都可以編出無數個來,但無論編出多少,這些系統都自然屬於無功用。』(子居:清華簡十一《五紀》解析)
而且子居更敍其詳,今只舉其中二則,餘皆詳於其論文裡:
『《五紀》這種通過強行綁定建立起來的體系,雖然仍然屬於認知體系範疇,但只能說點錯了技能樹,文中雖稱“日、月、星、辰、歲,唯天五紀”,看起來好像“全篇以「五紀」為中心展開”,但卻沒有記述任何專業性的天文、曆法、物候知識,甚至值得考慮作者是不是根本沒有真正去觀察過外界客觀環境,只是在閉門造車式地拼接各種不同來源的資訊,例如簡039剛寫完“四惟同號曰天惟,行望四方,上甲有寅。”簡041就有“四維同號曰行星,有終,日某。”而按簡036、037的內容“凡此十神有八之日,上甲以爰辰,凡此群示之日,辰爰日。”則“四惟”與“四維”似有所不同,然而全篇再沒有任何地方顯示真的存在這樣的區別。』
『再比如簡028、029中“天曰施……亥曰惡”部分,不僅除了前三的天、地、時外其餘內容在全篇再沒有相關論述,而且“醜曰愛”與“申曰愛”的明顯重複也很難簡單以抄寫訛誤解釋,下面簡47“忠曰行,禮曰相,義曰方,仁曰相,愛曰藏。”及簡61“禮曰則,仁曰食,義曰式,愛曰服,四禮以恭,全忠曰福。”的羅列也看不出對全文的論述有什麼意義,且又出現了“禮曰相”、“仁曰相”這樣明顯有誤的情況,凡此當都說明了《五紀》是由若干不同來源的材料拼湊而成的,不僅來源冗雜,而且抄綴草率。』
按,子居雖能看出這些問題,但他是徹頭徹尾相信像是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這些偽簡全是先秦簡的,而只是詳加解析內容,及確定的偽簡裡的今人所造假古文字係何字及何義,與各內中文字屬於先秦春秋或戰國前中後期或未年之類,及這些文字與先秦諸子百家哪一家較接近,但完全無法從字裡行間去辨別出今人偽造的。但從能看出《五紀》裡的全無頭緒的亂拼湊之跡也是遠勝於仿間學界充數的一些學者專家及所謂的海外漢學家如美國人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人。但德國漢學家葉漢(Hans van Ess)例外,因他研究清華簡文章內因的結論,這批清華簡不是該置身先秦時代的典籍內該會出現的,而是一批偽簡。
其實這些如清華偽簡《五紀》這些今人偽寫的亂七八糟『閉門造車式地拼接各種不同來源』的先秦故辭的故作思想體系的偽文本,反而不太容易辨其偽的。因為,偽文裡的用辭都是先秦甲骨文金文及典籍裡的辭語裡拼接打轉,文義詰屈聱牙,而且下限在戰國時代,只要不犯了把後世的用的字辭或思想而誤用在此偽文本內,就不太容易辨其偽的。但,像《五紀》這篇偽文,因為誤用了『文后』一辭,先秦根本就沒有此辭語,而且也不合先秦組辭之義,故而根本拼不出“文+后”的組辭,即若寫出來先秦人也會看不懂,因而露其偽饀,其故安在?
因為《五紀》此偽文,拿遠古洪水做開頭,講到洪水亂了“天紀”,所以有個 “后帝”帶領四幹、四輔,敷天下以“五紀”,洪水乃平。接著把“后帝”又改稱了“后”,籍“后曰”之口講了一條條“后”的諭旨,而《五紀》講出了開頭第一段文字:
『后曰:日、月、星、辰、歲,唯天五紀。文后經德自此始。文后乃倫歷天紀,初載于日,曰䌛古之紀,自一始,一亦一,二亦二,三亦三,四亦四,五亦五。天下之數算,唯后之律。』
先是“后”說了,『日、月、星、辰、歲,唯天五紀』,接著改稱“后”為“文后”,其實“后”即是“文后”,因為,文末講“唯后之律”,即本段內容都是“后”的內容。
當然,偽文作者把”后”於後又改稱“文后”,是因為“后”講了“日、月、星、辰、歲,唯天五紀”之後,作者為了表示下面的“經德自此始。……乃倫歷天紀……”都是“后”的行為,又另起稱謂指其行為,但是為了尊崇“后”,所以用他以為的“文”是周朝謚法裡的崇美之稱,於是加在“后”字之前,但如此一來,正見一定是現代這個作偽文本的人寫的,因為,即使後世,也沒有這種用法。更不要談先秦了。
因為,先秦“文”這種讚頌字,是必擺在國君或貴族的親父或母或祖先之前的,形成“文考”“文妣”“文母”“文祖”之類,沒有用在天帝或帝王身上的,除非是他的親子。但是,依《五紀》所述,“后”相當於古代夏朝的君主,也許作偽者即是以夏后為範,因為夏朝的國君都是稱“后”的,而這個偽文的作者,也許他心中設定的即是禹,因為禹平洪水,而《五紀》開頭即講“后”敷了“五紀”平洪水。而心中以大禹為“后”(雖夏后始於禹子啓,禹並沒有當上“后”)。而假定這個《五紀》真是先秦戰國楚人的戲作,那他在造“后”的故事時,因為禹又不是他爸爸或他父祖,他不能用上“文考”或“文祖考”之類。如此,“后”之前根本就不能加“文”字,那是對於父王及父祖或貴族之父及祖的美稱。要用“文”字前綴,就後頭要明白的接上“考”(己逝之父)“祖考”之類,而能這樣講的只有繼位為王或貴族的身份。
而這個《五紀》裡的“文后”叫了出來,叫“后”是“文后”的這個後世的寫文本的人,“后”又不是他這個不是皇子或其後代的己死的先王或貴族先父,如何能用上“文”為前綴?況且,沒有“文”字可以加在稱呼帝王稱呼的泛稱的”后”或“帝”或“王”之上,而唯一的是周文王的“文王”並不是泛稱,而是實指的周文王,其謚號是“文”,所以“王”前綴“文”字。
所以,一分析其誤,即知此篇大而無當的胡謅偽文本,不是先秦的所謂清華簡內會當出現的文篇,正見乃今人偽造的偽簡。(劉有恒,202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