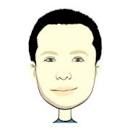偽青銅器〈保卣〉〈保尊〉辨偽
偽青銅器〈保卣〉〈保尊〉辨偽
〈保卣〉〈保尊〉於1948年在河南洛陽出土,銘文四十六字。但是奇怪的,就是其上的銘文,歷年學者間的解讀竟然多有不同,成為一件怪異疑案。本來,像金文這種十分格式化的銘文體,多有其陳規及演化之跡。但從商代到西周開國之初之間,這些演化之跡就十分模糊,甚至有學者認為,在商周之間,西周的銘文體尚未成熟。這種問題其原因可能是:
西周初年的真正出土文物太少。武王亡商之後,很快就死了。周公,而因餘子不服攝政,而成亂事,周初天下不靖,盛世之金文未能多有。即,本來,像是武王或成王時代的有銘青銅器就數量不多,而所謂後世的哪裡出土的所謂1948年以前的青銅器,號為武王或成王時器的有銘器的,偽器不少,像是偽〈保尊〉、偽〈保卣〉、偽〈禽簋〉及像是玉器類的偽〈太保玉戈〉,及 1949年以後出土吾人己辨其偽的〈利簋〉、偽〈何尊〉、偽〈荊子鼎〉等等。此因為有銘的青銅器可售高價,故即便出土西周初器,但現存的無銘的反而不如有銘為多,此因為出土後被人刻上偽銘文,而西周初年有銘的青銅器本少而不易得,不如刻上了銘文字,可售好價錢,故今世所傳的所謂西周初年有銘青銅器,偽器不少。銘文相同的〈保卣〉及〈保尊〉就是一例。
〈保卣〉及〈保尊〉的偽銘文如下: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彳止]兄六品,蔑曆於保,錫賓,用作文父癸宗寶遵彝。遘於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在二月既望。』
其偽跡如下:
(一)遘神是常見於甲骨文及金文的商周的祭祀活動,其所“遘”的是自已的先祖先妣,像《肆盤》『在十月,唯不廿祀哲日,遘於妣戊武乙奭』,其不少甲骨文例,如“在九月遘上甲祼,唯十祀”(合36482)。但是〈保卣〉及〈保尊〉卻言“遘於四方”,變成遘於四方神去了。
(二)“大祀”,此係抄西漢末年劉歆主持偽造《周禮‧春官‧肆師》裡的『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金文沒有“大祀”這種西周皇室之祀名。
(三)而且此一偽銘文寫手也是拿著《尚書‧召誥》及《尚書‧洛誥》在做文章。《尚書‧洛誥》:『四方民大和會……見士于周”,改成偽銘文的“遘於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
(四)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提到“殷制,月名通常在“遘於”之前,此則在後”,如殷商甲骨文作“遘於武乙彡日,唯王六祀彡日”(考古圖4.29),變成“遘於四方………在二月既望”格式。
(五)而偽作者頗通甲骨文,故其用辭多合甲骨文之用法,如陳夢家就舉了很多:
(1)東國的國字,從弋從回,和金文從巨不同,反而同於甲骨文的“回”字例。
(2)“兄”字形與蔔辭相同。
(3)“曆”字從甘從廠從埜,和晚殷卣文“蔑女曆”同形。
(4)稱其父廟為“宗”,與甲骨文同。
(5)遘於云云,同甲骨文。
(6)“彡+合”是說文古文的“會”字,同甲骨文例。
(7)西周望字作[左上臣右上月下壬],此省月,與甲骨文同。
(8)銘首為干支,銘末記月,同甲骨文。
(六)而“殷東國五侯”者,也是作偽銘文的寫手,整合後世的說法並兼自創,因為先秦,講到“五侯”者只見於《左傳》,《左傳•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但〈保卣〉及〈保尊〉裡把“五侯”設定為“殷東國”的“五侯”,這在先秦東周的任何竹帛金石所不書者,只有講到像是齊地原為“蒲姑氏”之地,在武王克殷後,把 “蒲姑、商、奄”做為周朝東土。又講到“徐奄”是叛周者:
——《左傳》昭九年:「及武王克殷,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述太公以前居齊國者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左傳》昭九年:「及武王克殷,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左傳》昭元年,趙盂數四代之叛國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邳,周有徐奄。」
而《孟子》內講周公“伐奄”,“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但也沒有講“五侯”,也沒講“五侯”是“殷東國”。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伐奄,三年討其君。」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趙注「飛廉,紂諛臣」
而周末《韓非子》《呂氏春秋》,也沒有講“五侯”,更沒有講到“五侯”是“殷東國”:
——《韓非子•說林》「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呂氏春秋•察微篇》「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
先秦沒有任何所謂『五侯』是誰的指謂。更沒有講這個『五侯』是指『殷東國五侯』。所以這個偽銘文的寫手,就是拿漢代之後的史料來自我想像寫出的,因為,依《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太公于齊,兼五侯地』來想像周公東征,把東方的殷方國或部族打敗,自己想像有太公兼“五侯”地的五侯就是殷在東方齊土地上原先的殷東國。至於哪五個殷東國的五侯,先秦史料未載,到西漢《史記》以後或西晉初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沒明寫,就廣參後自我聯想了吧:
——《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蒲姑」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太公于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蒲姑」
——《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作『誓』。」
——《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
——《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逸周書•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漢書•地理志》記載「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竹書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淮夷入於以叛」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遂伐奄滅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竹書紀年》「成王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等等。
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到了晉朝杜預釋“五侯”為「五等諸侯」,表示到晉朝都還在以為“五侯”為「五等諸侯」。
所以由以上的舉證,即知,所謂〈保卣〉〈保尊〉內的『殷東國五侯』就是今人偽造〈保卣〉〈保尊〉的直接證據了,更遑論以上其他的偽於後人的證據了。故〈保卣〉〈保尊〉可以確認必偽於今人,在1948年出土之前就已偽好埋入土中了。(劉有恒,202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