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靜居日記》讀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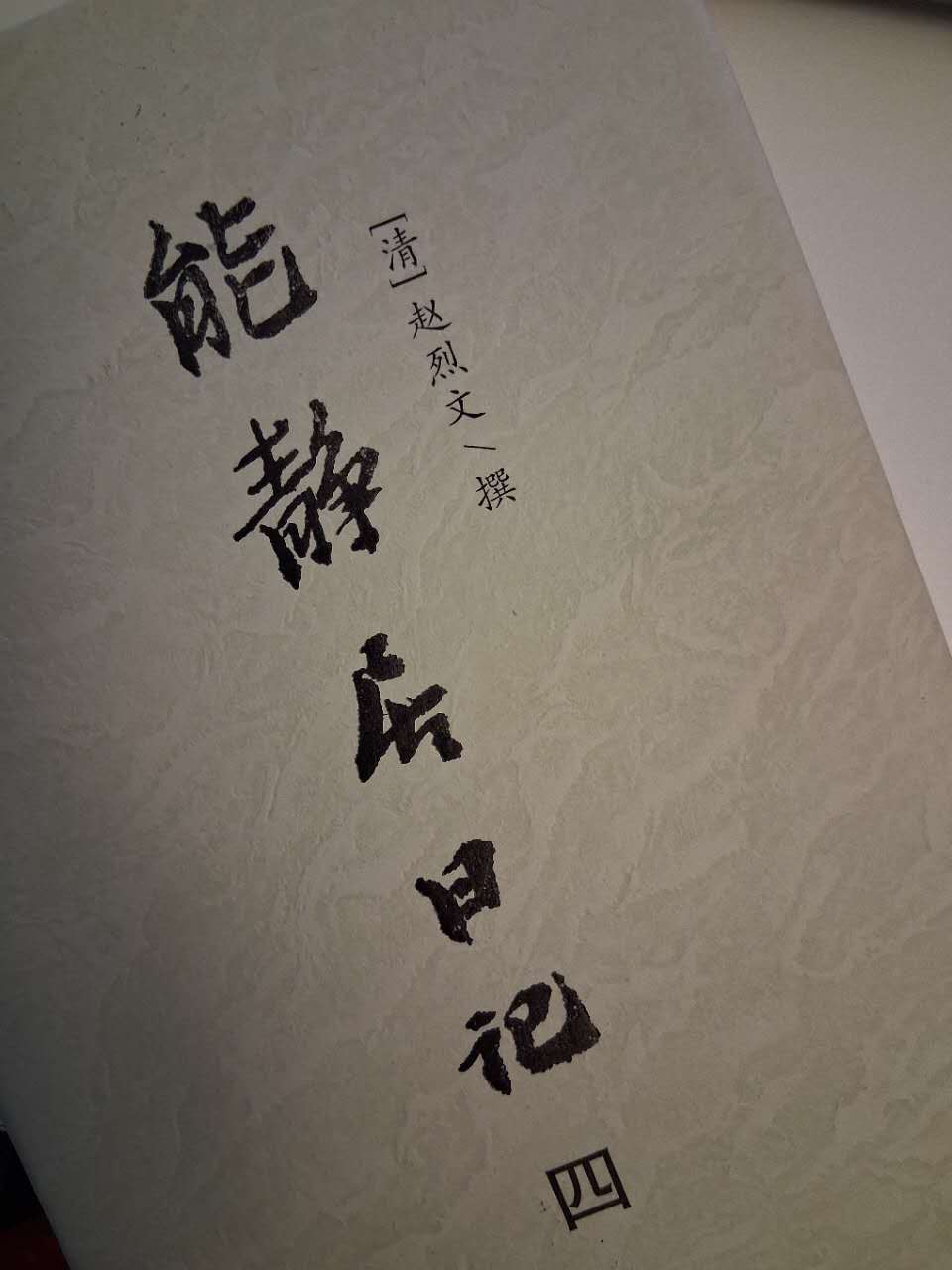
《能靜居日記》讀後感
四年前購得厚厚四大本《能靜居日記》,嶽麓書社出版,近兩年斷續閱畢。作者趙烈文乃晚清重臣曾國藩的幕僚,二人關係親密。曾在兩江總督任期,獨邀趙烈文長居官署後院,每徹夜長談,引趙為知己,對其家族子弟的生計亦不遺餘力。趙烈文在曾國荃攻打天京的戰鬥中臨時被曾國藩委派到其弟弟軍中,對天京陷落前後情形瞭若指掌。趙在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先後知磁州(今邯鄲磁縣)、易州(今易縣)。其仕宦生涯不僅與曾氏兄弟、李鴻章、沈葆楨等過從甚密,亦與當時江南的士大夫階層廣泛接觸,經緯百事,識見宏博。
趙烈文工詩、書、畫,隱退後居常熟虞山,在明朝萬曆禦史錢岱所築小輞川遺址起“趙園”,一時為當地名勝。
日記起于咸豐八年(1858),作者時年二十七;終於光緒十五年(1889)。歷時32載。趙因追隨曾國藩的特殊身份,歷經禮樂殺伐國之大事,也巨細靡遺地記錄了個人生活,可說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全景式地展現了晚清社會的畫卷。
所以想讀這套書,是因為讀了《鄭孝胥日記》,從時間上,《能靜居日記》恰好彌補鄭日記之前半個世紀的空缺,如此就可以對1850年代到1930年代這段將近100年的歷史變化有直觀感受。二者給人的印象的確不同:鄭的日記在前期充滿溫情,後期則更為公式化;趙的日記是前期滿是危機與公務,後期多限於私人生活。這大概很能做言行關係上的解釋。
農民起義帶來的社會波瀾固然是日記的重要表現章節,然其由無數細節堆積的歷史材料,也生動刻畫了當時的社會現象與紛紜人事。其中,趙對時局變化的預言、民生狀況的描繪、文物制度的記載、文化典籍的癡迷,均使讀者宛若置身晚清的社會土壤,切身感受當時的經濟民生、人們的心靈和道德狀況。
對我個人,日記帶來的感受主要有四。
首先,日記讓人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非理性。筆者在閱讀《能靜居日記》的同時在閱讀《資治通鑒》,從始至終不斷發生的戰爭,以及動輒斬首數萬、坑數萬的記載,不得不讓人想起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話:“歷史不過是人類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記錄。”在趙烈文日記的前半段,其所記載的慘絕人寰的社會現狀,亂離之人的無助與痛苦,仿佛杜甫在安史之亂後飄零蜀中在詩中所傾訴的彷徨、憤懣、悲哀和無奈穿越時空再現,令人讀來不免惶恐、淒切。
咸豐十年三月(1860年4月),趙烈文從朋友僕人(從杭州逃出)處得知,太平軍攻至杭州,”城中男女數十萬,晝夜露立雨中,冀城門或開得出。行走街上,足不能著地,踹踏死者,不可勝計。”城陷後,“淫殺之慘,更不可勝言,思之肉戰,言之涕零。”趙烈文在日記中發出“吾民生長太平,雖奢逸足以致禍,胡為酷至如此?”的天問。
當時趙行走道路,所見滿目瘡痍,十室九空的淒慘景狀比比皆是。由於兵匪橫行,險象環生,他一時“與二奴裹頭急裝,拔刀護車行。”一時“急解戎服匿之,易難民弊衣。”
戰爭帶來的屠殺和社會秩序的混亂,使得無論軍人還是民眾都變得殘忍和非理性。由於社會秩序蕩然無存,流民、逃兵、潰勇,但有機會即搶劫為生。不僅太平軍,湘軍也以攻城後的淫掠為習慣。民眾不得不團結自保。“時蘇州各鄉皆結鄉團,自初四廣勇焚掠之後,齊心見廣東人即殺。”
在此前後,趙烈文宗族所在常州、以及他當時定居的“木瀆”,不斷傳來厄運。由於太平軍攻打趙的家鄉常州遭到激烈抵抗,進城後“大肆屠戮,嬰孺不免,皆曳至北門外吊橋,受刃死者數萬,血凝橋面,厚幾尺。周城數十裡內,焚燹殆盡。”趙發出“吾鄉何罪,淪為鬼境,聞之氣結,無淚可揮。”的悲歎。其族人到上海,言“木瀆焚燹,十去其九,余者土匪日夜搜刮,屋材俱撤盡。”
湘軍圍攻安慶,城破,“男子髫齔以上皆死,各偽官眷屬婦女自盡者數十人,余婦女萬余,俱為兵掠出。”由於城內乏食,“人肉價至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兩。城破入賊居,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餘人手指,其慘至此。”到趙烈文隨曾國荃攻打天京,目睹了湘軍入城後大肆劫掠,“擔負相屬於道。”以至其在日記中大罵曾國荃“喪良昧理,一至於此,吾不知其死所。”
太平軍起事到滅亡,中華大地生靈塗炭,江南富庶地千瘡百孔。趙烈文家族“兩房亂前男丁百四十餘人,今存十七人而已。”士族大家尚且如此,升鬥小民的艱難可想而知。戰爭的殘酷和無情可見一斑。
其次,趙的日記記述了當時湘軍的組織與籌餉制度,即清廷在東南亂局面前無能為力時將軍政與財政大權下放至地方的做法,這在滿清時代應是絕無僅有之事。曾國藩曾數次指示趙烈文瞭解鹽務,其本意是讓他將來擔當籌餉重任。
其中一個有趣的記載,說明了太平天國的戰時物資分配方式。太平軍尚未到達,就在吳江出示公告,明確“下等人納口賦每日三十五文,中上漸加。又設立小票,每張二百五十文,有票許赴各處城市貿易,填明地方,不得逾越界限,票只得用十日,期滿再換。”閻錫山抗日戰爭時在吉縣頒佈購物券(糧票布票),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也曾廣泛使用購物許可券。這種在物資短缺時期,將市場化的物資供應體系嚴格管控和壟斷的措施,或許正起於太平軍,至少在太平天國曾大行其道。
曾國藩的幕僚體系十分龐大,幾乎是一個預備人才的實習營。趙烈文即經其姐夫介紹入幕。湘軍與淮軍的應運而生,不僅是地方武裝的崛起,也引發了從建立武裝、獨立稅務,到人才製備、地方管理的一整套地方自治式的權力運轉模式,為後來洋務運動的廣泛開展、延攬人才、經世致用的建設活動奠定了基礎。對比《鄭孝胥日記》,不難發現李鴻章的幕僚體系如出一轍,其中不同年齡的人組成一個人才梯隊,在事務中鍛煉,唯才是用,唯能力是用。幕府通過舉薦方式延攬各路人才,必經曾國藩親自接觸後,方委以職務。同時,不同職位上的人可穿插於幕府、公職之間,視時、事需要靈活使用。這套用人和做事的制度與腐朽敗壞的晚清朝廷形成了鮮明對照。同治中興被認為是儒家社會自我調節能力的迴光返照,事實上它得力于曾國藩在剿滅太平軍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這套行之有效的用才治事方法。然而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對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中華帝國臃腫的體格具有的慣性和尾大不掉的毛病,仍然毀掉了一代人的努力。曾國藩解散湘軍的舉動,李鴻章畏忌滿清貴族的行為,都是這種不得已的局面看似偶然或不重要、實質卻非常致命的表現。社會權力無法開放給才能卓越的人群,上下掣肘的行事風格導致低效率,這或是變革失敗的原因之一。
第三,日記給我一個意外的震撼是其無意間顯現的江南水運系統的高度發達。在趙第二次赴任湘軍前後,他主要活動在常州、無錫、上海、蘇州一代,出行一律乘船。船甚至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居所,隨動隨泊,無處不在。趙受曾國藩指示,在兵荒馬亂的蘇州乘船沿江而上,從鄱陽湖繞道南昌到長沙,再沿湘江入長江,順流而下至武漢,最終抵達安慶,無一步走陸路。這意味著江南水系的連接範圍可以涵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乃至浙江的廣大區域,這在中國,甚至在世界史上,算得上內河運輸系統的奇跡。這種出門乘船的習慣,甚至在趙烈文應召去直隸省任職時還在延續。他乘火輪船從上海北上天津,再從天津乘船到保定。可惜,這條水路在白洋澱上斷斷續續,迫使他經常在陸地乘車。在磁州期間,趙烈文甚至動過打通北方水路網的嘗試。當然,在相對缺水乾旱的北方,這根本行不通。然而此事也從側面印證了江南發達的水系對人的思維模式的影響。江南文化的細緻、典雅、寧靜的美學風格,與水以及人的行為方式有著密切的關聯。今天,中國的運輸系統已經被高鐵覆蓋,然而歷經千年疏浚的江南水系,絕不應該被歷史遺忘。
第四就是文化的希望。《能靜居日記》洋洋幾千頁,作者對書的癡迷,購書、藏書、讀書,朋友之間相互借書,寫讀書筆記的習慣貫穿始終。書是讀書人的命。咸豐十年(1860)八月,趙烈文在戰亂危亡之際,不忘在轉移全家時,“下行李、書櫥二十余藏一舟。”當時只有西方租界盤踞的上海相對安全,他輾轉將家人和書籍運至上海,再到崇明島找民居安頓。在日記中,趙暗自慶倖:“理家中藏書竟,共裝十二廚。此書自常至木瀆,自瀆至崇明,舟車七八易,殘少不及十種,殆有呵護之者,尚能免於兵燹邪。”到太平軍滅,同治五年(1866)七月,趙遣僕人從崇明島取回書籍,“撿書粗竟,亡失無幾,為之大慰。”
趙隨軍常備書籍在身,無論何時何地,翻閱不斷。不誇張地說,趙不僅對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諳熟於心,有著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並且遍閱當時能夠買到的有關西洋文化的書籍,甚至對佛教、道教,尤其是傳統醫學也有極深的涉獵。有人常譏諷古代科舉是皇帝延攬人才、治國齊民的手段,並非對文化建設有所主張。但是不能否認,科舉制度在漫長的歷史中塑造了中國士族階層的讀書基因。智識階層始終如饑似渴地讀書,擴展認知範圍,彼此相互影響。讀書的習慣一旦深入骨髓,人就不可能僅僅圍繞應試而自我局限,必然自發地延展和擴充。從趙烈文的閱讀筆記即可得知,中國人讀書向來無禁區。這些人不僅閱讀正統典籍,對歷史、地理、民族、飲食、經濟、科學相關的各類書籍兼收並蓄,也對稗官野史、地方雜誌、風俗家訓等概觀博覽。沉浸於如此廣博的知識系統中,必然會有一部分人于紛亂雜陳中尋找知識之間,以及觀念、實體與人類行為之間的有機聯繫,而引發“求真“的思想意識。正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說:“文化可以使精神具有各式各樣的觀點,使它即使想起這些觀點,使它擁有一大批考察一個物件時所運用的範疇。”中國雖然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但是中國讀書人對詞彙和概念的敏感,對文化的醉心,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況。這也是中國人一旦獲得適宜的土壤,就能在教育和個體發展上表現優異的原因。這種傳統中仍可撿起的民族特性,意味著文化的希望,但希望轉變為現實卻面臨著更蕪雜、更艱深的障礙。
把日記內容作為一種“原始歷史”的材料,則它在近一個半世紀後仍可作為“反省”的對象。從這些個體經歷的特殊現象,可以抽象出當時社會的普遍情形,即社會的紛雜與精神的猶疑。人們無法回到過去,也沒有明確的前途。社會面臨外力迫使的轉型任務,而當時的制度與人們的心靈狀況並沒有為這種變化做好準備。葛蘭西在其《獄中劄記》中說:“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尚未誕生:現在是怪物橫行的時候。”十分形象地描繪了趙烈文所處的晚清在社會轉型期的混亂與危險。
儒家建立的寧靜而相互適應的社會協調狀況,君臣父子的倫理體系面臨瓦解。這不僅僅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反動所致,國家本身就醞釀著內在的動亂危機,對於趙烈文這樣心懷天下的士大夫的努力是深可悼惜而無可奈何的。1878年,他的長女身懷六甲,得知夫婿方恮在保定因病遽然辭世後,誓死殉夫,雖經家人反復勸解看護,仍在誕下一女後,趁人不備用頭巾自縊身亡,時年二十六。這種對破碎的生活面貌無法容忍的堅貞情緒,象徵著具有理想情懷的人在混論的社會時期的迷惘與絕望,既是對過去的信仰與懷念,也含有對未來的拒絕和無奈。時至今日,這種情緒真的離開了我們了嗎?
高嶺 2025年,6月23日——6月25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