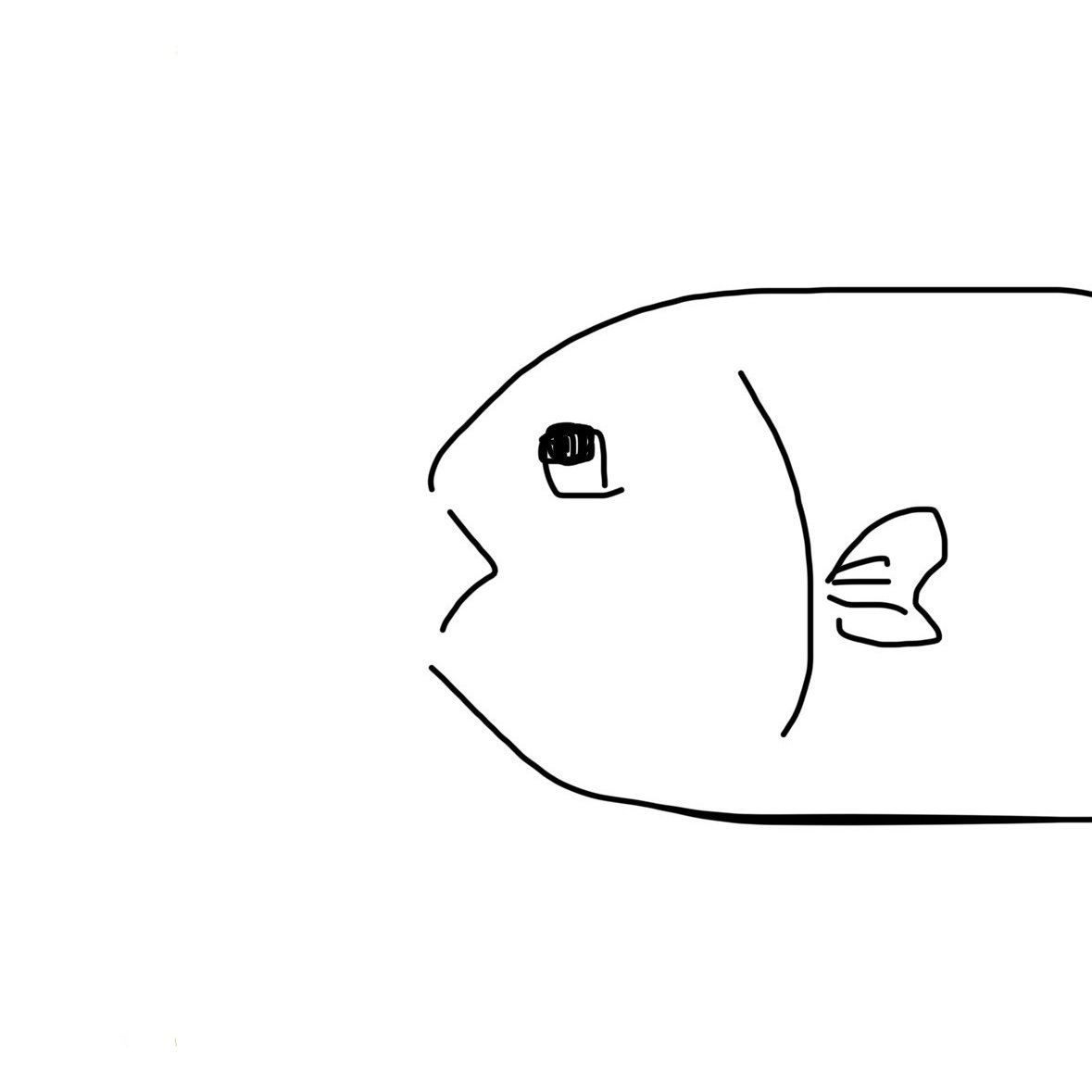清苦
知道的人自然会知道我在写的是谁,但不必点出,我连那个小孩的性别都不想点明。
世事莫测无常,世人蝇营狗苟,我总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正直应当胜利,好人该有好报,奇迹是会发生的。只是现实不是小说,事与愿违,好人落难,期待破碎才是常态。
但她和ta都总算走到了一个结局。
早该写给你们的。抱歉。我没有更多能做的。
两年前的盛夏,我受人所托,去东京的一个边角,探望拜访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突发重病导致陷入昏迷,植物人状态卧床多年的小孩所租的房间,ta的妈妈从中国飞来日本照护ta。
一个小小的,狭长的,标准一人居房间。弥漫着中药清苦的味道。拥挤,家具簇拥出一条狭窄的走道。ta躺的护理床很大,占了绝大部分的空间,照顾ta的妈妈的“床”是挤在角落里的小沙发,几乎要被埋在杂物里看不见。房间里还有两个大柜子,一个放满了那个小孩病发之前的个人物品,另一个分门别类地塞满了那个妈妈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偏方用材。还有一个小小的冰箱,里面的食物都是简朴的,胡乱对付一下的东西。阳台小小的,用杂七杂八各种容器种了很多葱姜蒜之类的植物。
她对床上的小孩说话,说有人来看你啦。又说,你听到了吧。又要我去捏一捏小孩的手,唤ta的名字。我不知为何升起一种惧意,不敢碰ta,因为ta躺在那里的样子太悲惨无望,又太脆弱易碎,我怕我多呼吸一下都会弄坏ta。
我提起其他话题转移她的注意力,问她平常生活还算方便吗。她淡淡笑,说幸好楼下就是超市,买东西不会超过半小时,要不然把小孩放在家里太久,不放心。上门介护的护工一周来两三次,这个时候她才有机会去附近散散步吹吹风,附近的河岸很好看,让她想起家乡。但她也不敢走远,怕小孩突发什么状况,护工应对不来。她来东京照顾小孩好些年了,基本没离开过这附近。“希望小孩快点醒来,我想带ta回家。当初就不该让ta一个人来东京。变成这副样子。”她说。声音逐渐小下去,最后一句话近乎嗫嗫絮语。
我不知该回什么比较好。太沉重。那天的阳光妩媚得不合时宜,光线照进室内,有亮晶晶的灰尘在舞蹈,但那轨迹却像在失速下坠。
她靠在阳台门框上,见我顺着阳光往外看,她脸上生出几分神气的色彩,喊我看阳台:“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有了这些就不用买超市的了,做饭时随便扯一点就好,日本的东西,好贵,省点钱,多给ta买点药才是。”阳台太小,她站过去之后,我就没办法上阳台了,只能探出半个身子,看她在郁郁葱葱的小东西里笑得和阳光一样灿烂,灼得我快掉泪。我把眼泪憋回去,这太不合适。她都没掉泪,我掉什么泪。
我缩回身体回到室内,她喊我坐那个沙发上。沙发上凌乱地堆着她的衣服,她费劲给我清出一块,我看到那个沙发已经凹陷下去一块,坐着就像脚脖子上绑了重石一般几乎要沉进水底,这感觉让我不舒服,但我还是说“这沙发好软啊真舒服。”她笑眯眯地:“对吧对吧,我每天都睡这上面,既方便处理紧急情况,也方便起夜照顾小孩,每晚都需要起来给ta吸痰呢。”
她看了看时间,说到了给小孩按摩肌肉的时间。小孩整洁的睡衣袖子挽起,她仔细地按摩那个细弱的胳膊,还帮ta活动关节。我陪她聊了一会儿她喜欢的话题,就告辞了。近乎落荒而逃。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所有能想到的应对和话题都显得过于天真轻浮。
她留我吃饭,说冰箱里有她自己包的饺子,冻好了,她一周做一两次,冻起来随时可以吃,方便、便宜且快。我慌忙找了个借口,说一会儿还有事,真得走了。她仍然是笑眯眯地,像一个普通平凡的大娘:“下次再来找我家xx玩呀!我做的饺子很好吃的。”
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沙发小小的,在大量的衣物覆盖下显得不堪重负,中间清出来的空位睡得陷下去一个小小的窝,但她有那么小只吗,她怕是蜷缩着睡的,夜夜如此。
我没办法去想。她困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24小时被吸痰、按摩、洗身切割成碎片,“照护小孩”将她的空间和时间都挤压得所剩无几。大部分时候,她都站着或坐在小孩床边。看ta不变的虚弱。看ta手腕上的血管在苍白之下呈现近乎透明的青色。看ta的面容歪斜得失去了原本的模样。看呼吸罩和氧气管维持着。只是维持着。日复一日。她站在失速坠落的发光尘埃里会想什么,她期待过多少次小孩突然醒转。
我来访的时候,她在我面前聊的每一个话题都和小孩有关又或是最终和小孩有关,那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会和小孩说话吗,会说什么话呢。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个清苦的房间却是物什件件不离ta,ta像一个纯白的黑洞,ta是引力ta是重量ta是意义ta是希望,她则像脱了线的毛衣,线头牵在ta身上,扯啊扯,她逐渐萎缩,她是自己的路是自己的标,她沿着“她”向ta坠落向ta回溯。
我没办法去想。
甚至没办法去写。
我最终并没有吃到她说她做得很好吃的饺子。
几个月后,消息传来,小孩病危。隔天,小孩去世。火化和葬礼都匆忙。又过了几天,我陪同其他帮忙处理后事的人再次造访这个房间。
清苦的中药味没有变,不堪重负的小沙发没有变,分门别类的偏方食材柜没有变,阳台上郁郁葱葱的小东西也没有变。但护理床没有了,塞满小孩生前物品的柜子也空了。
房间突然变得很空。属于那个小孩的痕迹都已经被她整理好带走。留下来的都是她自己的。这个时候才更直观地看到“她”在这里有多小,挤压成了什么形状,像枯树轰然倒塌后掉在一旁的爬藤,细细的,扭曲的。我们在惨白的灯光下帮她整理她自己的东西,讨论那些违法入境的偏方用材该怎么处理。她已经无心或许也已经无力带走“她”,她只带着自己的小孩,终于回了家乡。她不必再在日本的河川边眺望。她不必再在拥挤的房间里磨损。她不必再和清苦的中药一起煎熬。倒塌的枯树尘埃落定。跌落的藤蔓落叶归根。
好萧瑟。一定是因为该死的灯光太白。好冷。一定是因为入夜了。
东西不多,我们很快就整理完毕,井然有序地理进了纸箱里。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像在分尸,这是一个案发现场。
和她最为亲近的那个人开口,声音干涩:“至少她总算是解脱了。”
我点头。
我没有问,他说的解脱了的人是谁,是她,还是ta。是那个妈妈,还是那个小孩。
也许都是。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