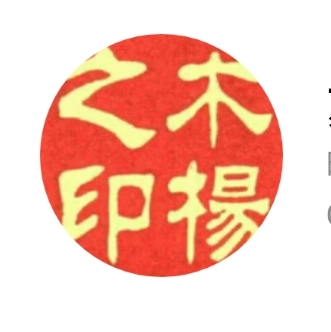長篇小說《通榆河》第十章(下)
各位文友早上好!
本部小說記錄的是1958-2010年間蘇北農村往事,甚是有些趣味,供大家有空閒讀!🤝
依仗書記威,橫行無所忌。
哥倆難進屋,求助年長侄。
導讀:校園霸凌什麼時候都有,梁家莊的這個小學堂裡也有,這不,惡霸來了……
長篇小說《通榆河》第十章(下)
承闊一看今天肯定要挨打了,嚇得眼淚都要流出來,承廣不怕,無奈打不過只有挨打的份。
“你們兩個兔崽子,敢用紙飛機射我,你們誰射的?” 卞長明來勢凶凶。
“是梁承廣,我看見的。” 卞長明是書記的弟弟,這馬屁一定要拍的,旁邊有人立即回道。
“啪啪。”卞長明沖上來就給承廣兩個耳光,心中這個解氣呀,上次放學帶人打梁承山都沒有這麼解氣,畢竟在這麼多人面前不一樣,帶人打梁承山那是偷偷摸摸的。
“我不是故意的。” 承廣眼中噴著怒火,拳頭握得老緊,恨不得上去跟他拼命。
“你這個小兔崽子,敢跟我鬥,幹嗎握著拳頭,有本事來打我呀,梁承山不是凶嗎?還不是一樣躺在家裡連學都不能上了嗎?”
“這麼說我三哥是你打傷的?”
“是的又怎麼了?你來打我呀,哈哈。”
“卞長明,老師來了,快回到座位上去。”有放風的人叫了起來,大家一聽,知道這回不是放蒼蠅,趕緊回到座位上。
承闊承廣也趕緊坐了下來,兩人知道,這事不能告訴老師,告訴了反而會讓大家瞧不起,這仇啊,只能請人出面了。
中午放學,承闊承廣沒有回家,而是坐在莊子口等源平。
初中離莊子有四五裡地遠,源平放中學回家,在莊子口發現承闊承廣坐在路邊上,好像在等人。
“你們坐在路邊上幹嗎,回家吃過飯了嗎?”
“沒有,等你呢。”
“什麼事?”
“那個狗肏的卞長明今天打我了。”
“這狗肏的,走了嗎?我去找他。”
“早走了,這會估計已經到家了,廟口到這裡也不過三四裡地。”
“便宜了這王八蛋了,總要找個機會把這傢伙修一頓的。”
“源平,今天卞長明說三哥也是他打傷的。”
“啊!?是這麼回事呀,我都奇怪,承山身體那麼好,怎麼突然生病的?”
“ 那天三哥說出去還燭臺和香爐,我就看見有幾個大小孩來找卞長明的,第二天,三哥就生病了。”
“好了,我曉得了,你們先回去吧,等兩天,我把這傢伙修一頓。”
“好的。”
一連幾天,承闊承廣也沒有看到源平,初中離家遠,放學還比小學晚,這小學放學了人都到家了,源平還沒有放學呢。兩人上學也不敢早去,在離教室老遠的地方待著,遠遠地看見山羊鬍子來了,才敢進教室,搞得大家都知道只要他倆一進教室,老師隨後准到。
幾天後是冬至,農村風俗這天要祭祖,按傳統老師會晚來或上午不會過來,承闊承廣在外面待了一個上午,也沒有看到老師過來,到了放學的時間,兩人沒精打采地往家走,在莊子口又遇到了放中學的源平。
“二娃,承闊,你們怎麼還沒有回家?”
“源平,上午老師沒有來,我們在外面一個上午,沒有進教室。”
“這狗肏的,這麼囂張啊,你們回去吧,今天下午我和老師請個假,早點回來,收拾一下這個傢伙。”
“真的?我們等著。”
下午山羊鬍子終於來了,承闊承廣也是在老師快到學校時的前一刻,沖進了教室,大家哄笑一陣後趕緊坐正,等著山羊鬍子。
承闊承廣心不在焉地聽著課,頭腦裡老想著源平什麼時候來。
好不容易等到放學,這回承闊承廣沒有像逃命似的向外跑,而是站在門口東張西望,卞長明一看,喲!這兩小子今天膽大了,好的,正好跟他倆玩玩,也在門口磨蹭到山羊鬍子走遠了。
“梁承廣、梁承闊,今天膽大了,今天燒紙祭祖,你們家祖宗給你們膽子了?”卞長明晃著膀子笑嘻嘻的,幾個死黨跟在後面一樣搖頭晃腦走了過來。
承闊承廣還在東張西望,心中那個急呀,源平啊你在哪呢?
教室門口就剩下這幾個人了,卞長明心說弄兩下子就走,正準備動手,發現教室後面有個人右手上拿著一個短木棒,不斷地敲著自己的左手,“啪啪”地走了過來,大家仔細一看,是梁源平。
幾個死黨一看是梁源平,嚇壞了,他不是去上初中了嗎?怎麼會在這裡,冤有頭債有主,自己和梁承廣他們沒有過節,不值得在這邊挨打,還是先跑再說,也不管卞長明瞭,撒開腿就跑了。
就在卞長明一愣神的工夫,源平拿著那根木棍站到了他的面前,看著逃走的死黨,再看看好長時間沒有見到的梁源平,心中早嚇慌了,這裡不是廟口,沒有人買他的帳。
“卞長明,還認得我嗎?”
“梁源平,你想幹什麼?我跟你無仇無怨的。”
“是嗎,把我三叔承山打躺下幾個月了,你還說跟我無仇我怨的?”
“不是我打的。”
“不是你打的,那誰打的?好漢做了不要賴皮。”
“你有什麼證據?”
“源平,不要跟這個傢伙囉嗦,前幾天他還打了我兩巴掌,他自己說承山是他打的。”承廣狠不得立刻就甩開膀子給卞長明上耳光。
“梁源平,我警告你,我哥可是大隊書記。”
“什麼?你還抬出書記的帽子壓我,這周圍哪個不曉得你哥是怎樣當上書記的?呸!”不說書記倒也罷了,一抬出來壓源平,源平火立刻大了,“啪啪”上來給卞長明兩個耳光,揪住耳朵拖到了教室的後面,這地方隱蔽,沒有人看得見。
卞長明像殺豬般地嚎叫起來,無奈這地方沒有人過來,就是有人過來,也沒有人管這閒事,幹部家沒有人餓肚子的,老百姓恨不得多揍兩下子。
“說,你怎麼把承山打傷的?”
“不曉得。”
“還說不曉得,打你個狗肏的——承廣,他不是打過你嗎,現在輪到你打他了,給我狠狠地打。”
承廣上來就甩著膀子掄開了,個子矮,夠不著,源平從後面抓住卞長明頭髮,一腳把他踹跪在地上。
承廣一邊甩著膀子打,一邊說:“叫你小子不承認,把我三哥打躺下這麼長時間,家裡花了那麼多的錢,你說還是不說?”
承廣打得自己手都疼,卞長明剛才挨了源平兩個巴掌,源平也是鉚足了勁打的,一下子就讓卞長明嘴角在流血,承廣這小手在他臉上打,實在沒有什麼分量。
源平看到承廣與其說是在打卞長明的耳刮子,倒不如說是在替他按摩,對承廣說道:“二娃,你力氣小,你這是替他揉嘴巴子呢,把這個木棒拿著,給我狠狠的抽。”
卞長明一看梁源平把剛才在手上敲來敲去的短木棒遞給了梁承廣,頓時臉色就變了,傻瓜都知道,梁承廣力氣再小,這玩意在抽下來,臉上就得開花,好漢不吃眼前虧,急忙求饒: “別打了,別打了,我說,我說。”
“承廣,停停,讓他說。”
“那天放晚學,我看見梁承山送東西到莊子外,他走得很快,我們沒有趕上……”
“放屁,沒趕上,我三哥怎麼受傷了?”
“承廣,讓他說。”
“我們就在路上等他回頭,結果我們就打上了,他真凶,我們幾個都沒有打得過他,後來有個人,用一根路邊上的木棒趁他不注意打了一下他的頭,把他打倒下來,他爬起來後,發瘋似的追著我們打,大家都嚇壞了,就往家跑,他追了老遠才停下來,後來我就不曉得了。”
“是不是你用那個木棒打的?”承廣問著又掄了兩巴掌。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是誰?”
“一個姓夏的傢伙,不上學的,也是廟口的。”
“真的假的?”
“是真的,如果我說謊,就叫我全家死光光。”
“好的,卞長明,別以為不是你打的就與你沒有關係,這事還沒有結束呢,今天就到這裡,等承山病好了,自然會找你算帳。看樣子,你是上得起初中的,只要上初中,你就得從梁家莊經過,要不你就天天從北邊漆家莊兜圈子吧,那裡還要趟水過河,遇上大水,再把你沖回廟口。記住了,你要是再在這裡倡狂,不要怪我們以後在這裡天天等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我再也不敢了。”
“還有,你還欺負他們倆嗎?”
“不敢,不敢,真的不敢。”
“那好,發個誓吧。”
“好的,如果我以後再欺負梁承闊梁承廣,就叫我不得好死,全家死光光。”
“好,卞長明,我相信你,你今天發的誓,你不要忘了,別以為我上了初中就管不了你了。”
“不會的,不會的,我一定記住。”
“滾。”
卞長明像剛被釋放一樣沒命似的跑了,承廣看著卞長明的背影說道:“源平,我們應該把這傢伙送到承山家裡去,讓三伯他們也曉得一下。”
“不行的,承廣,他哥是書記,真要是理論起來,咱爭不過他的,打他兩下子解解氣就行了。”
“那三哥的事就這樣算了?”
“還能咋的?我爺爺跟我說了,三叔爺家是造房子犯了什麼子午線,又說他家房子下面原來埋過死人的,就是卞長明不打傷承山,承山也要倒楣的。”
“憑啥是三哥倒楣呀?”
“我爺爺說,三叔爺家裡承山最小,什麼陽氣是最弱的。”
“那三哥家是不是不能去了?”
“不是的,現在沒有事了,我爺爺說風水先生用了什麼塔的磚把承山家的妖魔鬼怪都趕跑了,現在比誰家都安全呢。”
“啊!?是這樣的呀。”
星期天三個人都去看承山,大家發現承山還是在床上躺著,人瘦了好多,三人都不敢認識了。梁德凱也在屋裡坐著,承闊承廣看到就害怕,用爆竹籽炸尿的事件他倆還記得呢,倒是梁德凱好像忘了,看到他倆也不提。
“三奶奶,三叔好些了嗎?”
“比前些日子好多了,現在不大喊大叫了,就是頭還暈,老是要睡覺。”
“現在還吃藥嗎?”
“大隊醫生給抓的藥,天天熬著喝。”
“看來這風水是大事啊,以後要跟小輩們說清楚了,承海你不要笑,這事馬虎不得的,你們幾個也要聽著。”梁德凱腆著大肚子,目光把每個人都掃了一遍。
“曉得了,二伯。”
“好的,二叔爺。”
到了第二年快要立夏的時候,承山才能偶爾下床走走。
承闊承廣提了4個雞蛋去看承山,兩人看到承山斜坐在床上,挺瘦,精神也不是很足,給人的感覺虛得很。
“三哥,現在感覺怎樣了,能下來走路嗎?”
“不大能,走幾步可以的,時間長了吃不消,哪來的雞蛋?”
“那兩隻喜鵲幫助孵出來的小雞開始下蛋了。”
“噢!我想起來了,那兩隻雞也往樹上飛嗎?”
“不飛的,從來沒有看見它倆和喜鵲一塊過。”
“我以為那雞和喜鵲會認親的,我媽說我躺了快半年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啊?三哥,你連這個都忘了?”
“想不起來了。”
“那你記得去年中秋那天我們到二伯家用爆竹籽炸尿的事嗎?”
“記得,晚上被我爹打了一頓,第二天我穿我哥的衣服上學,和卞長明打了一架,把他的牙給打掉了。”
“這個狗肏的,三哥你記得你家抬屋子嗎?”
“記得,這是記得的,連老師說的原子彈也記得。”
“原子彈你也記得呀,你不說我們倒忘了,那二哥訂親你記得嗎?”
“我哥訂親……我哥訂過親了?”
“是的呀,你忘了?”
“一點印象也沒有……真的,沒有一點印象。”
“哎!這真奇怪呀,那送香爐你記得嗎?”
“香爐,什麼香爐?”
“那天放晚學了,你說二哥訂親借人家的香爐,三伯叫你還給人家的。”
“沒有一點印象。”
“這犯紫霧線這麼厲害呀,連讓人做過的事都能忘掉?”
“什麼紫霧線,怎麼聽不懂?”
“三哥,你記得風水先生到你家改作嗎?”
“什麼時候?不曉得。”
“那過年前吳大宏又生了個丫頭,你曉得嗎?”
“啊!又生了個丫頭?那二伯沒被氣死呀,這都四個丫頭了。”
“我奶奶也是這樣說的,還說老生孩子,可苦了咱大姐招娣。”
“唉!也是呀。”
“那今年過年你記得嗎?”
“都過年啦?”
“那你記得什麼時候的事?”
“只記得前段時間祭祖燒紙,我爹扶我起來磕頭的。”
“那是清明燒紙,這才幾天,不過才一個月呀,三哥,從二哥訂親到清明燒紙之間的事,你都不記得了?”
承山斜躺在床上,頭腦裡轉了一圈,有點吃力地搖了搖頭,說一點印象也沒有,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
“那,三哥,送香爐回來的路上你和卞長明他們打架你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把他牙打掉的,後來我又和他們打過架?”
“這是卞長明跟我們說的。”
“卞長明說的,怎麼回事?說給我聽聽。”
“你生病後,這狗肏的老是欺負我倆,有一次我射紙飛機碰到他了,這狗肏的打了我兩個嘴巴,還說連三哥你是被他打躺下的。”
“這狗肏的這麼狂呀,後來呢?”
“後來這狗肏的就一直找我們的茬,害得老師沒來我們都不敢進教室,最後我們叫源平把他打了一頓,才曉得你是那天送香爐回來後和他們打過架的,裡面有個廟口姓夏的傢伙用木棒把你打倒了。”
“把我打倒了,打我哪了?”
“卞長明說是頭上。”
承山摸了摸頭,說道:“我頭上沒有傷呀,你們見過我頭上有過傷嗎?”
承闊承廣對看了一看,搖了搖頭,兩人也沒有見到承山頭上受過傷。
“可是,三哥,從那天打架回來,三伯母說你那天夜裡就喊頭疼了。”
“這麼說是木棒打我頭,我才躺了這麼久的?”
“也許是吧,但三伯母說那天晚上你還好好的,還吃了夜飯的,夜裡才頭疼的。”
“我爹曉得我那天晚上和卞長明那狗肏的打架嗎?”
“我們不曉得三伯曉不曉得,你又記不得那天晚上的事。”
“你們剛才說風水先生是怎麼回事?”
“你生病了,老看不好,二伯怕造房子犯了什麼東西,叫三伯請風水先生的。”
“風水先生怎麼說的?”
“風水先生說這房子犯了什麼紫霧線,幫助改作的,你們家屋樑上還貼上了一張紙,就是風水先生叫二哥貼上去的。”承闊承廣對看了一眼,房子下面原來埋過死人的,兩人沒敢說。
“這紫霧線是什麼東西,能把我弄躺下這麼長時間?”
“不曉得呢,看二伯那臉色,肯定很厲害。”
“那狗肏的卞長明還欺負你們嗎?”
“自從被源平打了之後就不敢了,這傢伙發了誓的,說不欺負我們的。”
“這還差不多,要不等我好了,饒不了這狗肏的。”
“這麼說三哥你不找那狗肏的算帳了?”
“怎麼算呀?我又記不得,打他也要理由呀,那風水先生不是說犯了什麼紫霧線我才生病嗎?”
“三哥,你什麼時候去上學呀,這學期就剩下兩個月了。”
“不曉得呀,現在肯定不能去,你看我走路都不大行的,要是和卞長明打架,我打得過嗎?只有挨揍的份了。”
“這倒也是啊,不過下學期開學,三哥你就要留級了?”
“留什麼級呀,大不了不上了唄,這勞什子學我早就不想上了,我爹說早點進兒童班,還能掙點工分。”
“是呀,不上學多好,我媽和奶奶老說上學要做什麼讀書人的,真難受,早曉得這樣,開始我就不和我哥去上學了,最後被老師留下來,這不想不上都不行了。”承廣一臉悔意,像上了什麼大當似的。
三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梁承山躺了半年多,因為沒有明顯的外傷,家裡的人都認為是造房子犯了子午線,因為德勝不相信西醫,又不知道承山頭部被木棒打過,所以都信了風水先生的話,舊時中國農民的愚昧與迷信從這就可以看出來。
梁承山記不得頭部被打的那幾天的事,現代醫學上對這種因頭部受外傷而導致記憶部分喪失的現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逆行性遺忘。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