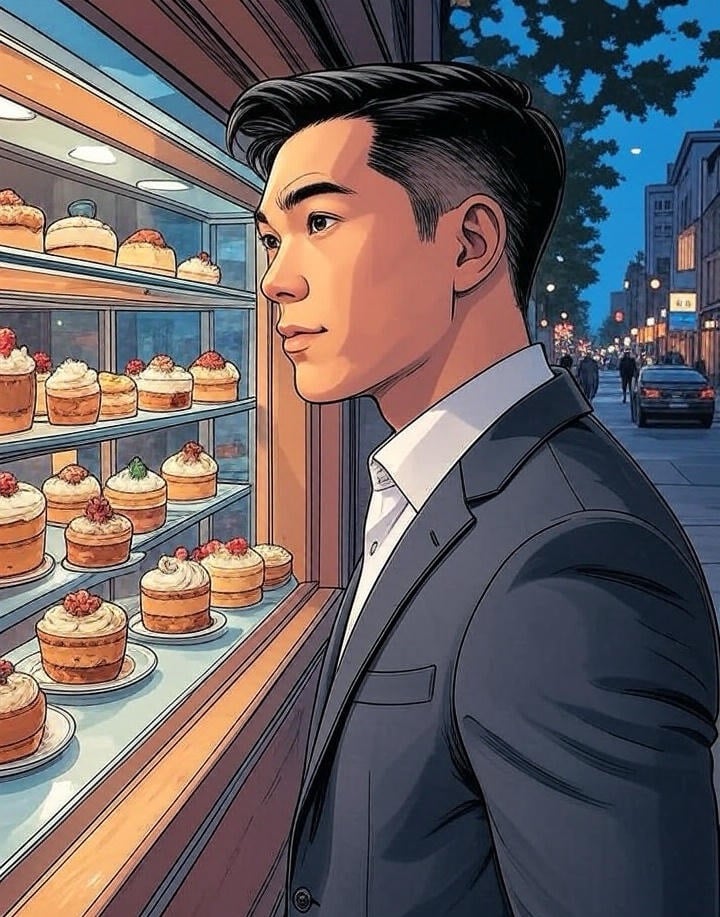都市奇幻|當糖把你變成現代殭屍
夜色像薄糖紙,城市邊緣的霓虹把一切包得亮晶晶。便利店的冷櫃裡,甜點排成隊,標籤像小旗幟:新品、限量、買一送一。李明站在那兒,手指在包裝上遊走,像在觸摸某種遺忘的記號。他不是貪嘴;他在尋找一種能讓世界停止索求的證據,哪怕只是幾秒的安靜。
那天他遇到一位老婆婆。雨濕了她的髮絲,手裡的提包破得像老書的封面。她遞給他一顆用褪色紙包裹的糖,聲音像紙折疊的縫隙。「吃一顆吧,孩子。」她說,「這是讓你不用太用力生活的糖。」
他接過,猶豫,最後放進嘴裡。糖在口中化開的時刻,味道像一條記憶的河回流,溫暖、無負擔,像有人替他把心裡的刺拔出來。那一夜,他回家後睡得很沉,很久沒有夢。
接下來的日子,糖的影響慢慢顯形,像蜜糖滲入木頭。
李明不再只偶爾吃甜點,而是按小時取食。他的臉色漸漸變得蠟白,眼底失去光澤;他的語氣越來越簡短,像被剪掉了銳角。他仍然上班,還會在會議上點頭微笑,但下班後他總會去便利店,像被某個溫柔的命令推著走。
有人會說,這只是成癮:糖刺激大腦,讓人一再追求快感。也有人會點出社會結構,無處不在的促銷廣告、永無止境的慰藉消費、夜間仍然亮著燈的商業街。
李明的變化在這個城市裡不是獨一無二,但他看見得更清楚:甜味不只是滿足生理,它像是一個安靜的契約,允諾你不再質問、不再掙扎。
如果要給這現象一個「解釋」的外衣,故事裡會說那顆糖啟動了某種老舊的生化通道,深埋在血液裡的記憶程式被解鎖,讓原始的「果實獵食模式」復甦。通道一開啟,人的焦慮被甜味替代,疑惑被甜味吞噬。可這些話語像醫生在說夢話:表面合理,卻無法拯救任何一顆仍在淪陷的心。
他發現自己不只渴望甜品,還渴望那種剛離世的「甜」。有人說,死亡的最初瞬間,身體裡還殘留著生命最後的甘醇,血液裡的葡萄糖尚未完全散去,呼吸還帶著溫度,呼出的氣息能讓他在一瞬間再次感到完整。從此他學會等待:不是犯案式地奪去,而是潛伏在城市的邊緣,等著時間把糖交到他面前。如同殭屍渴望鮮血一般,成為本能。
這裡的「殭屍」並非腐爛、喧囂的怪物。李明依然穿著領帶,還會接電話,還會被同事誇獎專業。
但某處,他的欲望被置換成了無聲的程序:行為機械化、情感被餵養、選擇被縮減。他像是一台運轉正常、內部卻被替換了系統的機器,外面的人看不見內部的錯亂,只覺得他「變了」。
故事不是只為驚嚇而寫。他想問的是:在一個提供無限慰藉的社會裡,我們如何辨識那種被溫柔馴化的狀態?當甜味可以買到安穩時,誰又會冒著不安去追求真實?李明的變化是一種悲哀:他沒有被迫成為怪物,卻也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他選擇了甜眠,換來的是日常裡的麻木與夜裡的空虛。
城市仍在亮燈,便利店的架上永遠補滿新品。有人說救贖在意志,也有人說救贖在覺察。李明有過掙扎,他嘗試戒除,嘗試把那顆糖的包裝紙折好藏在口袋裡,像保存一段曾經的記憶;他也曾想去找那位老婆婆問個明白,卻發現街角已經空無一人,只有雨痕提醒着他曾有的選擇。
最後的夜裡,他站在鏡前,對著自己的臉試圖說話。鏡中的人回以一個禮貌的微笑,像是替他表演一場沒人要求的安寧。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到了那張褪色的糖紙,邊緣有老婆婆亂寫的幾個字:別太用力活。
他把糖紙揉成一個小球,然後丟進垃圾桶。外頭風很冷,呼吸起霧。片刻之後,他又去了便利店,買了一盒最便宜的黑咖啡,坐在窗邊慢慢喝下。
咖啡苦,是初次的苦,他讓苦味在舌尖停留了比平常更久一些。也許是反射,也許是真實。他不知道自己能否醒徹,或只是換了口味繼續漂流。
城市還亮著燈,甜點仍然排整齊。問題不是糖本身,而是當甜味成了選擇的捷徑,剩下的人心是否還有走遠路的勇氣。
你在下一次伸手去拿那塊蛋糕時,不妨停一下:問問自己,這種甜,究竟在喂養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