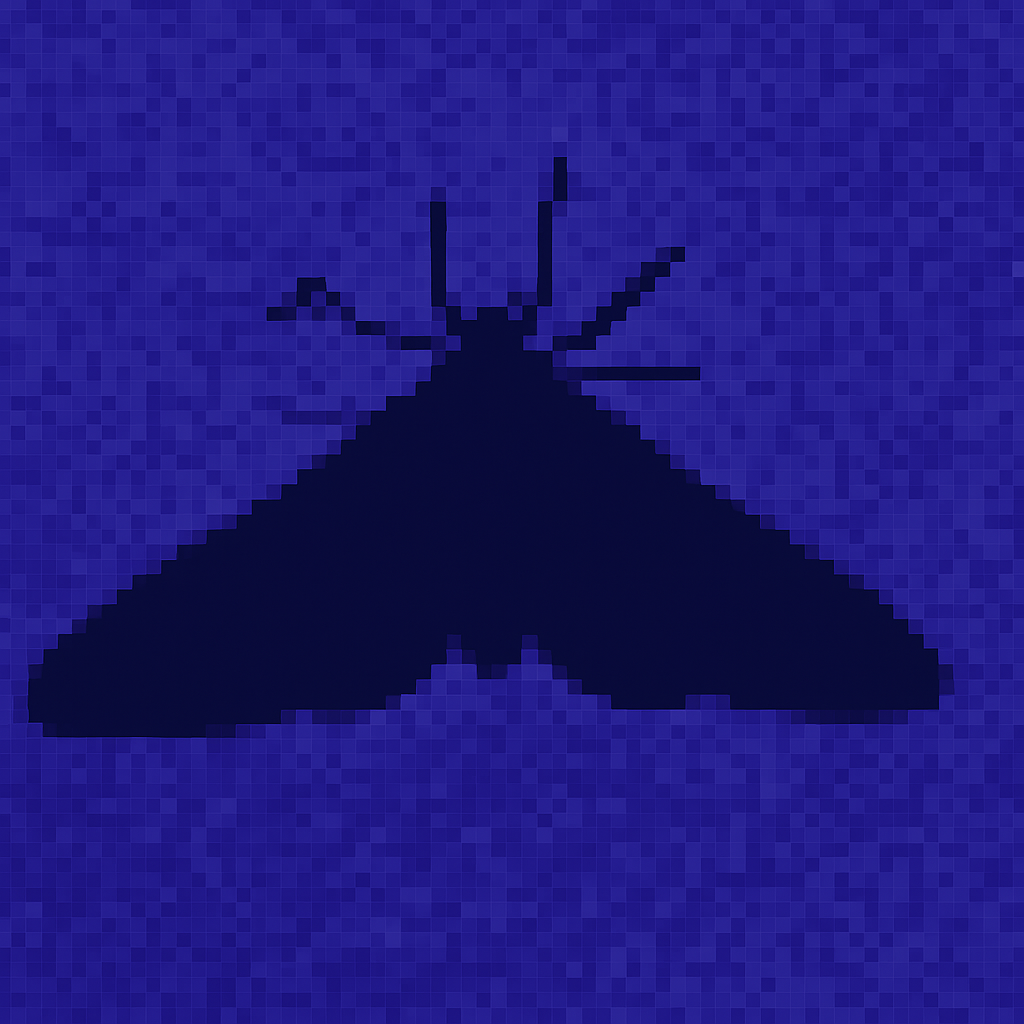對《上下游》〈89歲阿嬤停電夜葬身火海〉的一些想法
7月6日晚間近12點,逾百年後,再有颱風丹娜斯從嘉義布袋登陸。這場颱風季揭幕以來對台灣造成重創的首個颱風,對北台灣的實際影響有限,災損多集中在中南部地區,不過,在丹娜絲過境後,災區一片狼籍之際,在台灣的網路世界上,也引發一場場關於「光電」的械鬥。
其中,先不談光電場遭到颱風襲擊的面積與實際影響幅度實在有限,但在媒體的部分取景下,顯得宛如災後浩劫般,這類作為政治操作素材的打擊攻勢,在台灣的政治地景早已不陌生。
這篇想談的是,網路獨立媒體《上下游》在7月15日發布的〈89歲阿嬤停電夜葬身火海,災後安置混亂,制度失靈成悲劇〉報導。這篇報導的主角,是一名高齡長者,因颱風侵襲後地區斷電而屋內無法照明,其兒為老母親點燃12根蠟燭,卻不幸因為風勢吹襲,導致蠟燭傾倒後點燃火勢,最終導致老母親遭燒死在屋內的悲劇。
這起事件非常不幸。一個可能接近脆弱的家庭,因為風災後的斷電與一連串的意外,導致如此無法挽回的遺憾。這家人住在台南七股,一個位處地方偏細的村落。七股實際上作為光電場的一個重要案場,也多次成為媒體報導討論的地區。
不過,《上下游》該文也在臉書發文後引發一連串的爭議。簡單來說,《上下游》臉書轉貼報導的初始文字,將林立的光電場與消防找不到路加以連結,這也導致間接讓部分意見不滿,這樣的宣文是有意/無意地將悲劇的結論推向「光電」殺人的指涉。
事後,《上下游》多次編寫該則貼文的文字內容,不過依然可以在編輯紀錄中看見初始的貼文文字。
回到該篇報導,先旨聲明,我是很敬佩當南部發生風災後,記者直接趕抵現場的意志力與那份「我不寫就不會被知道」的使命感,但就稿件內容觀之,我想還是有許多需要商榷的部分。
在該文刊頭,記者便寫道事發地點是一個「需經過2.5公里長的光電場才能抵達」,並在後文的註記表明,車輛行駛其中,「若無當地人帶路,外地車輛不易分辨分位」。
誠然,該起火災悲劇,在這樣的開場寫作技法下,實際上形塑的框架效果便定義了光電場在這場悲劇中有其要角。至少,套一個我們這行自我表述的用詞來說,就是一個重要的環境背景。作為一種非虛構的技法,環境的鋪陳與描寫,的確能勾勒與立體化事發地點的環境以及地景。
然而,問題在於,光電場與該起火災,以及火災與此名長者的死亡是否有因果關係?
依據內文指稱,這場火是在於丹娜絲颱風過境後,暴風吹襲導致電線桿倒伏,進而導致大區域的斷電。而起火原因,正在於連日停電,長者的兒子為其點燃12根蠟燭「助其照明」,卻因風勢強勁致使蠟燭傾倒,進而點燃易燃物引發火勢。
作為一個事發原因的釐清,蠟燭始為這場悲劇的起點。在《上下游》的表述底下,撰文記者更認為這是系統性的結構性失靈,包含:長時間的電力中斷、無法即時應變的救援與失靈的社會安全網。在這樣的「結構」式書寫下,事實上,個人的風險意識以及災害管理,在其中被移除,或是被擱置。
我對這樣的悲劇,第一時間最感到無力的,並不是該文意圖連結的「光電導致消防隊找不到事發地點」。而是,在這年的台灣社會,城鄉差距以及資訊落差,讓人們不僅無法在颱風來臨前做上基礎的防災準備,甚或是作為緊急避難計畫。這些對位處偏鄉、但又是極其脆弱的居民來說,「防災準備」並不是一個日常的語彙,更不是一個能落入生活視野的事件。
你會看到,人們依然使用蠟燭作為緊急照明之用,而非包含從政府到民間都在極力宣導的「手電筒」、「乾電池」等作為斷電時期的有效工具。這一點非常令人難受。也讓人必須重新檢視,現有的防災宣導,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如果行禮如儀地繼續以我們慣常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現實中,就是有居民接收不到這層訊息。
這樣的資訊落差,從此案例中,即以一樁不幸的罹難事件收場。
再者,以讀者的角度來看,這篇報導中仍有許多我不明白的部分——那些的不明白,更像是對寫作者的框架如何拿捏,以及對於報導與私領域間的模糊情感,該如何取捨與自制?
舉例來說,該文提及一名里長怒斥區公所的行政文化。該事件起因在於,風災後,區公所通知災民前往指定地點填寫房屋修繕補助申請表,但因為繕寫不符表格格式要求而遭退件,此舉讓該里長大為光火。
但作為記者,對這樣的場景需要照單全收,或是更擴展事件的樣貌,去釐清是什麼樣的繕寫錯誤、表格需求是什麼,為什麼需要到退件的程度?對我而言,這是行政部門掌握效率與流程的規格化工具,倘若因為繕寫錯誤,無法符合規格要求,導致後續的修繕補助因而作業瑕疵、甚至引發法律官司,責任又該由誰負?
特別這是關乎政府預算發放的行政管控程序。難不成即便填寫錯誤、或是潦草以對,行政作業依舊給予放行嗎?這樣的「給一個方便」,是否更導致後續的作業混亂,以及各種行政系統的無法對焦?
而作為一名記者,里長的怒言是基於情緒性的發話,或是背後折射出行政部門的官僚與效率延宕問題。在這樣的段落處理中,讀者無法見得更多的爭執細節,只得出一個「敢言」的里長,以及一個怠慢的官僚機構。如果這樣的潦草以對是所謂的「監督」的話。(內文中僅以社會課表示會再去了解表格問題帶過,但一個不具體的模糊控訴,得不到另一造的有效回應,業內的形式平衡,說白了就是求一個「並陳」的外觀。)
此外,該篇報導中另採訪多名里長的視角。有里長指出,「直到他主動打電話給區長,才知道安置中心在哪」,該里長並主張「事前都沒通知,是臨時才知道地點。」
這段細節很有意思。該資訊細節實際上透露出,區長是知道安置地點的,但沒跟里長說到;除此,在颱風來襲前的災前整備作業中,里長實際上也未主動了解安置中心的處所。
困境之所在,在於依據台灣的《災害防救法》設計,里長並非防救災的法定人員。但里長作為村里層級——也就是行政區的最基層——的一線人員,其角色經常被外界定位在災情預警與居民通知,災中災情回報與居民協助撤離,以及災後協助統計損害、發送物資、協調救援的要角。
除此,依據內政部訂定的《村里辦公處業務手冊》與各縣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性防救災計畫,里長也通常被視為里內災情的回報者,並協助安置中心動員與災民轉送,以及是里內弱勢人口的名冊提供者。但在災防法中,里長就是一個並未明確授予災害防救法定定位的角色。
當然,倘若公所有提供安置中心的地點,依據《地方災害防救計畫》,若公所提供資訊,里長需負責轉知里民。但在風災斷電斷訊的情況下,該如何轉知、鄰里廣播是否得效,在在都是問題。
也有一名後壁區的里長說,颱風夜段話斷訊、聯絡不上人,並指責整個系統毫無變通。他也批評上級機關沒有公告安置地點跟聯絡窗口。不過,該段落並未採訪上級機關。災防法實際上並未規定政府在颱風來臨前必須強制公告安置中心地點, 依法需確保「適當安置」。不過,實務上,大多地方政府會在颱風來襲前預告安置處所。
這篇報導中,一些段落的寫作方式也讓人不解。
例如,死者家因為風災後屋頂還在,並未被通知安置。這篇報導以一個「後照鏡」式的寫法,事後回看如果該時安置的話,就不會發生這場災害。然而,以該地區受到的慘烈災情,在難以預見因為蠟燭引發火勢的情況下,該屋作為「相對安全」的環境,在資源有限下,我不確定公所該如何回應,才能令人信服?
另外,報導中,記者提問到「沒有電話、無法對外求救的民眾該怎麼辦?」我反覆閱讀這段文字,在一個斷訊的狀態下,難以掌握人員、人數、以及受災與待援情況下。一個沒有被回答的問題,並非政府的冷漠,而是在本是災害管理中屬於自救的部分。一個凡事都需要政府介入、管理及援救的社會,我不認為對於整體社會的防災意識與災害教育有所助益。
作為讀者,這篇稿件在框架設定上,拉入的光電作為環境背景,由此展開一樁不幸的悲劇。在《上下游》一系列對光電的批判中,這篇稿件無非是作為制度殺人的一篇總結性觀點。我並不是覺得光電毫無問題,也並非要對《上下游》進行攻訐與潑污水,而是在該文的敘述中,個人的責任被稀釋,當人人指向結構性因素又沒「接住」任何人時,與其質問「發電的土地沒能留住一盞燈光」,毋寧提問「防災意識進不了偏鄉」的原因何在。
光電自然有其在台灣發展的侷限與爭議。但將所有的問題都指向光電,只是模糊淡化了其他責任分配的討論。我不否認這是一場系統系的悲劇。但我更希望能肯認到,防災教育的缺失,也是系統中的一環。
其實回看多次這篇報導,你很難對這戶不幸的家庭苛責什麼。但也由於這樣的不幸,我們得以看見該家庭的默默且努力生活過的痕跡。也許他們從未想到,這一家的聲名大噪,即使兒子承認是一場意外後,這起悲劇卻在他人筆下成為光電害人的敘事版本。
他人的不幸,執筆的人更應謹慎。而非寫自己想寫的,讓他人成為你筆下作為推動敘事情節的角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