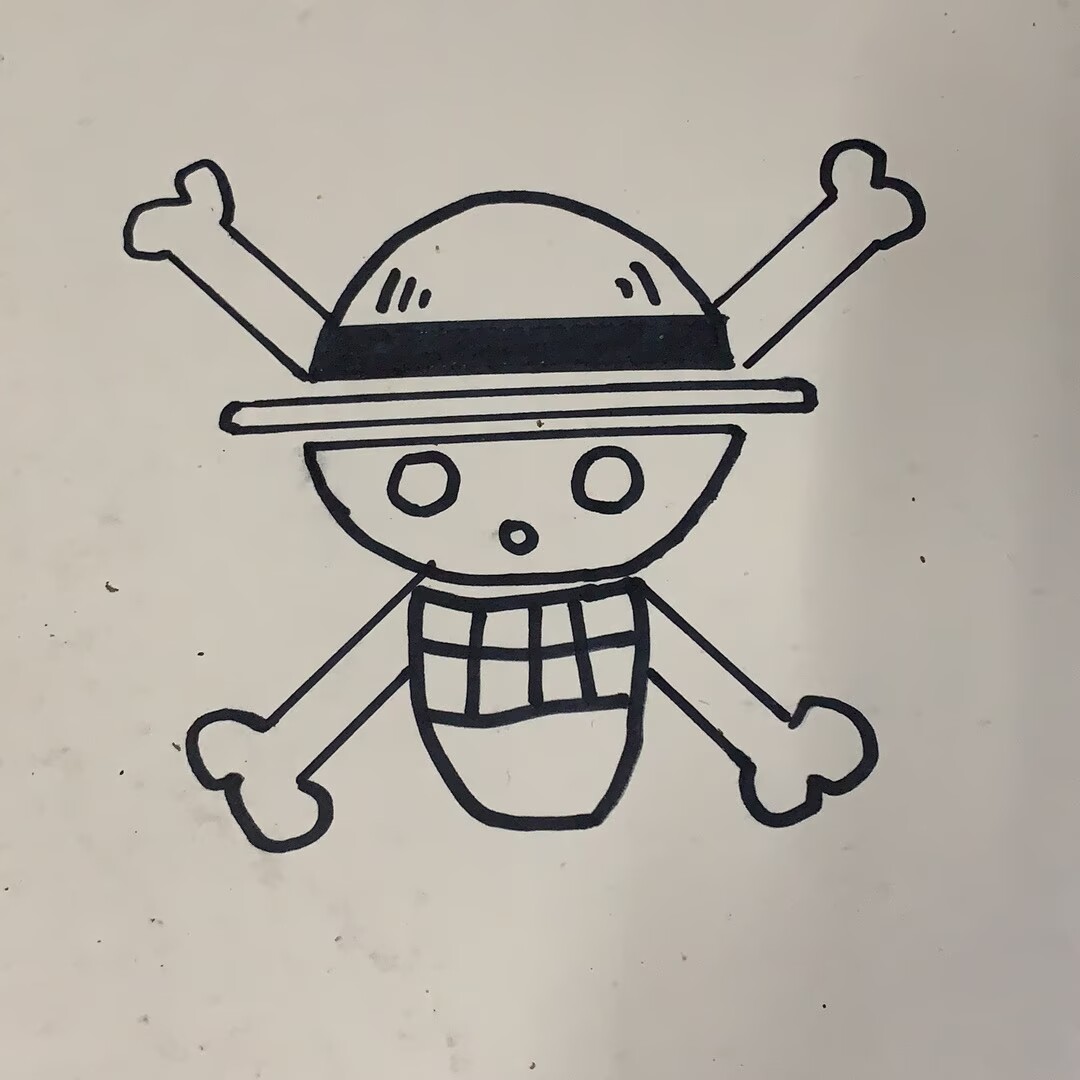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我曾以为,人与人之间的欺骗,终将被系统看穿;
后来我才明白,更大的难题是:即使连系统都承认你是真心的,你也未必愿意面对那份真心背后所照出的——真实的自己。
过去,人们总说"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那是种死无对证的修辞,安全得像隔着玻璃接吻。
如今不必了。
只要站在你面前,就能获取你罪行记忆里的真实想法。若你肯授权,那些非罪行的记忆也能完整回溯——带着当时的体温、心跳频率、以及每一个你以为藏得很深的念头。
真相从未如此容易抵达。不需要费尽唇舌让人相信你的真心,系统会替你作证。你说'我是真心的'那一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记忆一页页都记着;你说'我爱你'时,心里是满怀柔情还是例行公事,清清楚楚。
可人呢?
却一个个像被掀翻壳的乌龟,缩在最狭小的缝隙中,恨不得把呼吸都切换成低频模式;
纷纷涌进休眠舱,仿佛植物状态才是保留尊严的最后表态。
讽刺的是,信誓旦旦地索求真心的是他们;
如今真的可信之心可被导出、可被投屏、可被按时间排序,他们却集体褪色,主动断联,宁愿像死去,也不愿被看清。
我看到一个女孩在向情感主播哭诉。
她说在和男友冷战。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付出,述说自己多么深爱着男友,一直在卑微地维护着这段感情。声音里的颤抖不是装的——我读过那段记忆,她说这些话时,泪腺分泌确实达到了悲伤阈值。
所有人都在安慰她。
“你是好女孩。”
“成熟、有边界感。”
“你来自稳定的亲子关系,自然懂得如何爱。”
“而他,出身混乱,心智晚熟。”
最终,她被集体温柔所抚慰,情绪回温,结束连线的指尖都轻了几分。
可就在挂断那一刻,不过短短两分钟,她给另一个电话发送了一句:“几点?我订房。”
下午,她直接按预定酒店开了房,上床的对象是个“地下情人”。
那段记忆我读过。她在陌生男人身体下说出的话,淫秽、直白,像从另一个人格中长出来,语气甚至带点孩子气的调皮。
奇特的是,她那一刻脑中对男友依旧保有深切挂念,她真的“深爱着”。她们计划两个月后结婚,并没有一丝“不爱”的动摇。
这不是她“虚伪”,不是渣,也不是精神分裂。
这是她真实人格的一体两面——
爱,可以真挚到令旁人动容;
而慾,也无需构建道德防火墙。
她的反差,不是“切换”,而是“并存”。
这种情况我看得太多了。
男人在办公室午餐间隙跟同事谈及配偶,语气殷实,讲起两人的情感基础——如何共度经济低谷、如何在彼此生病时对方不离不弃——那种语调,是许多被社会事务压成粗木料的男人在提及亲密关系时才拥有的柔光。他说:“她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港口。”
他的记忆确认这是真的。他下意识愿意在危险时持身取代她承担所有冲击,那种肌肉层下的防御反应是真实的。
但接下来的行为是——
回家路上经过洗头房,他眼神没一丝停滞地推开门。十三分钟后抛弃安全套,再次回家。
你说他没良心吧,他在灾难面前能毫不犹豫挡在爱人身前。
你说他是真心爱吧,他却能在撩拨他人肉体时压根想不起来有个妻子。
人类的逻辑系统不像机器。
没有“爱则不背叛”的互斥判断,
也不会因为真心存在就自动清除一切污点。
我审过成千上万段这类记忆。
我们以为记忆透明化会让真相大白,会让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实际上,它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
人可以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真实情感。
爱与背叛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大脑里和平共处。真心与欺骗也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们回访自己的记忆行为轨迹时,脸上常常写着诚恳,眼神里透着祈愿: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会做这种事。
那不是我真心。
我是受伤太久了。
是环境冷落了我。
我配得到理解。
可Jesus调出来的那一帧帧短片里,他们自己走进去,自己说出来,自己暗示、回应、放行、完成,每一个瞬间都透着判断力与自觉。
不是病。不是魔。不是误会。
是你自己。
这世上越来越多的人,忽然丧失了对自我的解释能力,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数据层透明之后——自我矛盾已无法掩饰。
人可以在同一时间热诚发誓、同时也轻率地越轨。
可以爱你怜你,同时也用最凉的方式伤你。
他们被打碎成一层层逻辑节点:
▍你曾发誓“绝不欺骗”,几日后却编织谎言哄骗另一个人;
▍你真心向往婚姻,却漫不经心地把手伸进了别人衣领里;
▍你说你最怕被背叛,可在那句“她不会知道”的默认中,你就是背叛者。
我们以为证据与回忆,会让正义更清晰。
可往往是结构照亮后,才看出人心如蛛网,专挑光影交错的点织结谎言;
自己也成了无法拆解的一段——可恶、可信、可怜,又无法分割。
人不是两面派。
人是多维体。
那些维度疊加而非排斥。真实的不是“悖论”,是真相群落:矛盾的、并存的、不消解的。
所以现在,人们宁愿躲进休眠舱。
不是怕谎言被揭穿——如果只是谎言,反倒简单了。承认、道歉、接受惩罚,总有个尽头。
他们怕的是真实的复杂性被看见,是本真不可被解释;
怕的是,他们曾以为“这不算什么”的事;
怕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怕别人发现:原来你不是装的,你是真的能在爱一个人的同时背叛他;你是真的能在发誓忠诚的三小时后若无其事地撒谎;你是真的能把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装在同一个躯壳里,还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不是道德沦丧。
这是人性本来的样子——只是以前,我们有幸看不见。
现在,镜子太清晰了。
清晰到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灵魂的所有切面,包括那些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
于是他们逃了。
不是逃避审判,是逃避自己。
逃避那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无法解释的——真实的自己。
七十八天后,我和白露即将抵达真相之塔。
这段时间里,我把两万名中国籍受审者的记忆翻了个底朝天。每一段罪行片段,每一个出现过的旁观者、受害者、共谋者——筛查出七十五亿个ID像雪花一样在我脑中飘过,然后沉淀、分类、比对。
没有张振山。
《梦回湖南》的数据更是密不透风。三亿人参与了这场文化狂欢——投稿的、点赞的、转发的、哪怕只是顺手评论了一个表情符号的——所有ID都被Apollo忠实记录,被我逐一过目。
还是没有。
这不是"没找到"那么简单。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缺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你知道它必然存在,却无法直接观测。
这种“不存在”并不可笑,它可怕——
其结构如真空区域:除非人为涂抹,一个人不可能从数据体中央消失得那样干净。
这让我开始真正恐惧。
张振山究竟是谁?
我几乎摸遍了全人类的数字指纹,他却像从未在这个时代呼吸过。
如果,这趟真相之塔之行也一无所获呢?
Jesus已不再主动参与这个问题。被重净化后,已不再记得它曾向我递过话,也不再记得,当初是它让我去查。那段秘密路径,如今回归沉默,只剩我还记得。
我承接了它的委托,如今成了真正的独行者——但我仍然要查。因为我是先驱者。那些肩负而来的使命,不会因技术停顿而暂停执行。
飞船在接驳口降落时,真相之塔的气候层尚未调息完成。引擎壳体外结了一层音障后的微缩冻结棉,像某种未定性思考的冷膜。
刘烬生在出口等我。他脸上挂着那种老朋友见面的轻松笑容,可我的表情大概像块冻了三天的铁。
白露跟在我身后,对刘烬生礼貌地点了点头。她看出了气氛不对,便轻声说了句"我去那边看看风景",识趣地走向了航站楼的观景台。
"烬生,把塔思关了。"我走近,声音压下所有寒暄余地:"我有事相求。"
他愣了一下:"啥事这么急?你……看起来不像是来玩的。"
"关了再说。"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但还是照做了。我能感觉到他的脑电波瞬间变得安静——那种被AI辅助时的微弱嗡鸣消失了。
"啥也别问。"我说,"用你对我的信任来担保。"
这句话的分量他懂。他点头,等我开口。
"第一件事,我要真相之塔十三年来所有求职档案。完整的——原始档案。"
我故意要全部。如果只要姓名和ID列表,太明显了。
"可以。"他说,然后补充,"我现在开启塔思就能调取,这样行吗?"
"别。"我立刻否决,"去你办公室翻存档。"
任何AI痕迹都可能成为线索。我不能冒险。
他没追问,只是点头:"好。"
"第二件事。"我盯着他,问得很轻:"玛阿特还保留着在地球时的记忆吗?"
他的表情像听到了今年最荒唐的笑话:"你疯了?联邦怎么可能让我带走那些信息?我买的是它的能力框架——共情计算和是非判断的底层权重,不是它的记忆库。"
我微顿,点头:"也对,是我想多了。"
我没再追问。如他所说,那就是废路。
来到刘烬生的办公室,他调出了离线数据库,十三年来的求职记录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界面——每月更新,从未中断。
白露在仿生人引领下去了客房休息——这趟长途飞行让她有些疲惫。她临走前只说了句"别太晚",便没再打扰我们做事。她总是知道分寸。
我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七十五亿ID都找不到的人,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几百万份求职申请里?
我将数据包传入大脑,机械地一扫而过,直到一个名字让我的呼吸卡住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缓缓闭上双眼,确认了三遍。
张振山。人类ID:CNE387492681594。
他在。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在。
我花十亿CZ币撒网、扫遍几乎整个地球的ID都没捞到的人,竟然十三年如一日地往这里投申请。
那种荒谬感让我差点笑出声——这算什么?我像个傻子一样满世界找他,他却每个月都在敲真相之塔的门?
不是偶尔投递。是十三年来,每个月,雷打不动。
一百五十六次申请。同样的格式,同样的内容密度,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但这不合理。
正常人找工作,会同时撒网——第一志愿没回音,就从其他发来录用通知的地方挑个最满意的。没人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没人会对着一堵墙敲十三年——除非,他要的不止是门开,而是要在墙上留下什么。
我翻看他的申请内容。每一份都附带了完整的剧本构想——持续、规律、稳定,且从不跑题——像在想办法,把什么藏进塔里。
他想说什么?
随后刘烬生连接联邦系统将当前求职池打开。我看见他的名字时,甚至没能立刻相信那是“真实文档”,而不是某种钓我上钩的镜像幻影。
我坐在办公桌前,装模作样半小时,最后深吸一口气,将他的ID和十九个干扰ID一起递给刘烬生。
"这二十个人。"我把名单推给刘烬生,"全部录用。"
张振山藏在其中,不显眼。
"剧本策展补充人员?"刘烬生扫了一眼,"行,这就办。"
他没问为什么。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不该问的别问。
真相之塔是完美的猎场。
远离地球,远离盘古的全域扫描。这里只有刘烬生的主场规则和他买下的玛阿特。
我始终保持着梦露的断开状态。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张振山,不必把每一个念头都封存、加密、再封存。那种反复的心智体操让人疲惫。
按规定,刘烬生作为雇主可以查看所有求职者的罪行记忆——就像当初李晋的雇主查过他的毒种子案一样,这是评估风险的标准程序。
可张振山的情况不同。
一个敢连续十三年往同一个地方投简历的人,不会不知道雇主有这个权限。他明知会被查,还是来了——这说明他的罪行记忆里,要么什么都没有,要么有也无关紧要。
所以即便刘烬生去查,大概率也是白费功夫。能公开看到的东西,不会是关键。真正的秘密,应该没有嵌在罪行档案里。
让他介入,只会多一个人承担风险,却未必能多一条线索。
刘烬生是我信任的人,但我不想让他卷入这件事。他的脑信号能力不比我强多少,只要我稍加防备,他读不出我在想什么。
这不是不信任,是保护。真相有时候像毒药,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先驱者的能力分化是个有趣的现象。
八十七万三千零八个人,同样的大脑开发程度,却因为原始结构的差异,觉醒了完全不同的天赋。
有人能在脑中构建一座完整的城市,每一片树叶的纹理都清晰可见。
有人的脑电波能覆盖半径三公里,像个人形雷达。
有人是逻辑机器,能在千万条信息中瞬间找出唯一的因果链。
而我,是这八十七万人中记忆力最强的。不是背书那种记忆——是结构性记忆,是能在碎片中重建完整图景的能力。官方测试过,有据可查。
这个能力,正好用来追捕一个半透明的人。
张振山,你终于进入了我的射程。
这次,你无处可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