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重複的部分
2047年:如果香港成為新加坡————後中共時代的香港未來想像
【一】倒塌的不是香港,是高牆

2047年7月1日,香港——曾被稱為「東方明珠」,後來被稱為「紅色警戒之城」——迎來了它歷史上的第三次誕生。
第一次,是1842年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殖民政權建立;
第二次,是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進入「一國兩制」時代;
第三次,發生在2044年4月12日凌晨2點17分,北京發出緊急聲明:
「為維護社會穩定及重建國家體制,自即日起中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運作,由中國國防委員會直接接管。」
但那道命令,沒有送達。
因為在幾個小時之前,中國政權已經陷入全境通訊癱瘓與武裝叛亂。
無數省級軍區各自為政、外交部與國家廣電總局陷入沉默,央視畫面黑屏。
北京失聯了。
而香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必須自己決定未來。
當時的行政長官早已被北京在一年多前換成臨時軍管專員。立法會解散、政務司長叛逃至新加坡。港島一夜之間,成為無主之地。警方停止勤務,港鐵暫停營運。
但市民沒有慌亂。
反而比以往任何一次「緊急狀態」更加冷靜。
中環出現自發義工維持交通,深水埗街坊組織自衛巡邏隊。大埔的社區中心用來收留老人,柴灣的年輕人開始用開源軟件建立臨時訊息網。
這不是革命,不是暴動,也不是殖民復辟。
那是——一個倖存城市的自我重建。
有人把那天稱為「香港新日」。
但更多人說,那只是我們終於被遺忘、於是得以活下來的一天。
【二】臨時政府成立與國際承認

臨時市政會議是在港島中環的一間律師樓誕生的。
那間律所原本在 2030 年國安法擴權後被迫關門,卻保留了香港最後一批願意承擔風險的法律人:
早年「反送中」時期的義務律師
流亡歸港的年輕法律系教授
曾在旺角被捕、服刑三年後決定留下來的前線抗爭者
他們不是政客,甚至不想掌權。
但他們知道:這座城市不能沒有制度。
他們草擬了《臨時市政憲章》,恢復區議會選舉制度、建立臨時議會。
六個月內選出 60 席代表,承諾兩年內完成憲政改組、舉行全民市政公投。
這是這座城市久違的政治承諾。
沒有金紫荊廣場,沒有五星紅旗,沒有政協代表坐鎮。
只有布條寫成的選舉通告、手工張貼的民意問卷、在人行天橋上臨時架起的市政論壇。
這不是體制的復興,而是制度的重生。
🌍 國際社會的反應
第一個發聲的是 台灣外交部,表示:
「高度關切香港局勢,並尊重港人自我治理選擇。」
接著是 加拿大:歡迎因政治鎮壓而流亡的港人歸國,並支持聯合國派出觀察團進駐。
再來是歐盟、美國、日本、新加坡、澳洲……
最沉默的是北京——它已經無力發聲。
臨時政府沒有宣布獨立,這是極其重要的政治選擇。
臨時市政會議主席對媒體說的一句話,後來被寫入中學公民課本:
「我們不是要脫離中國,而是要在歷史崩潰的瞬間,保存一點文明的尊嚴。」
這不是港獨,也不是革命。
這只是城市保衛戰——不為疆界,而為制度、記憶與選擇的空間。
【三】我們不是獨立國,我們是倖存者

2045年秋天,香港與中國新成立的「華夏聯邦臨時議會」簽訂了一份歷史性的協議。
協議條文被公開張貼在金鐘前政府總部的大樓門口,題為:
《關於香港特別城市體政治地位的共同聲明》
這份聲明中,中央政府首度正式承認:
香港未來三十年內,不受北京派遣任何行政人員干預本地事務;
所有立法、司法、外交、教育、媒體、文化、海關、財政與貨幣政策,由香港市政議會全權負責;
外交及國防由中央代為處理,駐港設有非武裝聯絡機構,不得干預市政。
其中最具爭議的一句條文是:
「香港為中華聯邦體系下具國際法人格的城市實體,享有與一主權地區相等的功能與權限。」
這讓香港正式踏入了**「非國家國家」**的邊界地帶。
有外媒形容香港成為「東方版的梵蒂岡」或「亞洲的科索沃」。
但港人自己怎麼看?
在油麻地的社區報《火堆日報》上,一位年輕寫作者這樣寫道:
「我們不是國,也不是殖民地;不是中國,也不是中國以外。
我們不是一種制度成功的產物,而是一個歷史事故後遺留下來的倫理殘片。
我們是被歷史壓過,卻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倖存者。」
這篇文章被無數中學生引用在公民科報告裡,亦被許多移民港人掛在客廳牆上。
🏛 臨時政府制度化:香港自治議會的建立
2046年,臨時市政會議轉型為正式的:
「香港自治議會」
並設立了以下核心制度:
機構名稱職能說明香港總理辦公室(Office of Chief Minister)由市民直選產生的行政領袖,任期三年,最多連任一次市政議會(Civic Assembly)100席,按比例代表制選出,涵蓋港島、九龍、新界、離島等選區憲政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負責憲章解釋與基本法監督,具備最終終審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專責調查、重審過去政治暴力與冤獄案件社區自治中心每區設立地區公投制度、社福審議平台、與自組民兵備援系統
這不是烏托邦,制度並不完美。
選舉中亦出現黑金、資訊戰與投訴舞弊。
但比起過去的沉默、無權與封閉,這已是翻天覆地的轉變。
一位曾被褫奪律師資格的老人,在重建法院開庭當天坐在旁聽席,悄悄說了一句:
「這裡,不再審思想了。」
【四】記憶不再犯法
2047年6月3日晚上,維多利亞公園。
沒有封鎖線,沒有警車,沒有高牆。
十萬人手持電子蠟燭,靜靜地站在草地上,仰望著重新豎立的——國殤之柱。
坐在前排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坐著輪椅。
她曾在三十年前多次因悼念六四被控「非法集會」,如今成為了香港記憶協會的名譽顧問。
她抬頭望向那座雕像,眼中噙著淚。
✴️ 重現的記憶:新國殤之柱
那天,矗立在草地中央的並非原件,而是由數百位本地藝術家與歷史學者共同打造的複製版本。
原柱早在2021年被港大移除,據說其後被切割、部分運至海外,部分被秘密運出中國大陸,至今下落不明。
新的國殤之柱底座,刻著一句話:
「六四不是歷史,是我們活過的部分。
記憶,不再犯法。」

悼念會無人高呼口號,也沒有任何政黨旗幟。
現場只有一片靜默。
一位年輕的詩人登上臨時搭建的小台,朗讀一首他為這座城市所寫的詩:
他們說記憶是可以刪除的
他們說歷史是可以選擇的
他們說,你可以忘了名字,忘了時間,
忘了那晚火光中斷掉的聲音
但我們還在這裡——
手裡握著光
眼裡握著淚
心裡握著那年沒有握到的手
掌聲在那一刻響起,又很快沉沒在人群中。
一位中學教師在草地上,對著身邊的學生輕聲說道:
「現在可以拍照,但不要自拍,這不是展覽,是告別。」
不是對六四的告別,
而是對那個我們無法為自己作主的年代的告別。
📘 背後的修復行動
2046年起,臨時政府設立「記憶重建小組」,由公共歷史學者、倖存證人、社區檔案義工共同協作。
修復資料館中遭刪改的1989年紀錄;
從流亡者與海外檔案機構中追回新聞片段;
建立「政治記憶資料庫」,將個人故事、法庭記錄、訪談逐步數碼化。
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審判誰,
而是要讓這座城市,再也不必活在選擇性遺忘的陰影下。
這是一章沒有勝利者的歷史。
但正因如此,
當我們終於能點燃一支燭光,並不再為此付出自由或代價,
我們才終於擁有了「文明」最根本的東西——記得的權利。
【五】我們成為了什麼?
2047年,這是一座活著的城市。
不是重獲自由的勝利者,而是從死亡邊緣走回來的倖存者。
這一年,《香港自治憲章》正式通過,寫進首條文字是:
「本市因歷史所致,成為世界唯一一個曾歷經殖民、極權、流亡、自治,並最終由人民集體選擇命運的城市體。其主權未必獨立,但其意志為自主。」

👤 歸來的人
2047年6月,在深水埗一間獨立書店的開幕儀式上,一位滿頭白髮的老者緩緩走入門口,人群立刻靜了下來。
那是黎智英。
被囚近20年後,他於2042年獲釋,身體消瘦、聲音依舊洪亮。他沒有重新創辦報社,只在每週固定寫一封《致後生的信》,刊登於《自由地》週刊。
戴耀廷成為新憲章起草團的顧問。他曾因「47人案」被判監十年,出獄後長年居於偏遠地區,2040年代初受邀加入臨時法律重建團隊。他說:
「這不是復仇,也不是『我們對了』,而是讓制度再次可以被信任。」
何俊仁沒有參選任何職位,成為「民間法律診所」的義務顧問。
何桂藍於2024年被判囚七年,其後在歐洲展開人權倡議工作。2046年,她與周庭一同返港,成立「城市婦女協會」,協助政治犯家屬就業、心理支援與紀錄重建。
周庭於2023年9月流亡加拿大,在海外長期參與港人倡議,並於2046年歸港。她說:
「這座城市,給過我們恐懼,也給過我們名字。如今,讓我們給它一個未來。」
🌍 留守與流亡的人
鄭文傑長年定居英國,在2044年香港政局逆轉後回港。他拒絕出席所有公開場合,只在一次封閉式圓桌會議上低聲說: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沒死而已。能回來,已經夠了。」
羅冠聰在倫敦成家立業,成為知名學者。他於2044年後重返香港,2046年應邀出任「香港未來發展論壇」主席。他不登記戶籍、不定居,只每年在中環主持一次「未來之夜」,召集青年與國際學者對話。
每年開場白都一樣:
「我們的城市,還在寫故事。」
黃之鋒原定於2027年1月出獄,2025年6月在獄中再次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持續多年,最終於2040年代初釋放。他之後選擇回歸教育界,不參政、不接受媒體訪問,只在屯門開設「城市記憶寫作坊」。據說每年考進港大文學院的學生,有一半來自那裡。
✊ 還在的聲音
鄒幸彤於2025年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纏訟多年。2045年出獄後,被推選為第一屆憲政法庭常任法官。那一年,她拒絕著法袍,穿黑衣出庭。她在憲章生效典禮上說:
「不再有國安法,不再有因思想入罪。不是因為權力赦免,而是因為制度重建。從今天起,這城市唯一的法,是由人民寫下的。」
梁天琦早於2016年被判監,理大圍城時仍在獄中。他出獄後保持低調,沒有重返政治,只在2040年代初公開發表文章〈後抗爭時代,我們何以為家〉,其中寫道:
「我不曾在理大,但我知道那裡的每一道煙、每一聲哭喊,都是我們共同走過的路。香港不會死。」
許智峯在重新投入立法工作後,成為「環境與都市更新委員會」召集人,推動多項綠能政策與城市規劃改革。他說:
「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做過錯事。但還願意留下來改的,才值得被記得。」
🕯️ 我們成為了什麼?
在2047年夏天,一場題為「我們是誰」的城市論壇,在遮打花園舉行。沒有人設置舞台,只有草地上互相傾聽、書寫與回憶的群體。
沒有一個人能代表這座城市。
但每一個人,都在這城市裡留下痕跡。
這是一場歷史的逆流。
不是高唱凱歌的勝利宣言,而是歷經壓抑、牢獄與流亡後,仍選擇站出來說:「我們還在這裡。」
我們成為了什麼?
我們成為了:
仍相信可以討論未來的人;
願意把受過的傷,化作他人庇護所的人;
在歷史的廢墟上重建制度、語言與彼此的城市人。
不是國,也不是族。
但是一種仍然能相認的共同體。
2047年,香港還在。
它不是變成了新加坡,而是成為了香港。
【六】無名者
不是所有的名字都會被記住,
但這些人,構成了我們得以存活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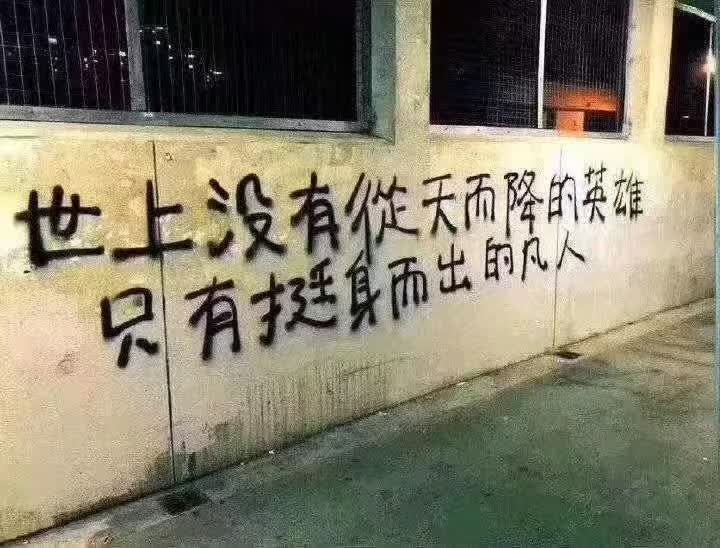
是那個在反送中時為前線遞水的中年婦人,撐著傘站在後巷,只說了一句:
「小心啲。」
是那個在地鐵站口派發護目鏡、自己卻被警棍打到手指骨折的義工。他的名字沒有上新聞,但手上的傷疤陪了他一輩子。
是那位在中學教室裡偷偷教學生「議會民主是什麼」的老師,後來被家長舉報、教育局調查,最後選擇辭職,遠走他鄉。
是2044年政權崩塌那夜,無人指揮卻自發維持交通的計程車司機:
「條路要有人管。」
是市政論壇裡默默做義工的老人。他年輕時參與過六七暴動,晚年卻說:
「我唔再信槍,依家我信票。」
是那位在2020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年輕記者,只因記錄了警察圍捕時的一段片段,而那段影像最終成為真相的一部分。
是那個自2020年起,每年都向監獄寄信給政治犯的中學生:
「我唔識佢哋,但我唔想佢哋覺得自己無人記得。」
是我自己。
也是我們這些曾在運動中被捕、被控、被囚、被邊控的人。
我們不是英雄,
我們只是活著,並記得。
我們曾經是新聞裡的片段,
是社交媒體的標籤,
是政府報告中的統計數字,
是監獄名單上的編號。
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曾走過街頭、曾喊過口號、曾在黑暗中相信:
這座城市,值得。
2047年的今天,那些資料檔案被解密、那段歷史重新整理時,一批由青年組成的「記憶整理團隊」在金鐘地鐵站口架起帳篷,逐一記錄每一位曾經參與過抗爭的人。
他們不是為了寫歷史課本,而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那天,你做過什麼嗎?」
不是所有人願意開口,
太多年了,太多苦了,
也太多背叛與遺忘了。
但每一個開口說出自己故事的人,
都成為了這座城市的延續。
有人在法庭門外排隊送便當,
有人把陌生人藏進家中避捕,
有人默默剪下那天的報紙,藏入抽屜三十年。
有人曾被朋友出賣、被警察侮辱、在看守所裡嘔吐出膽汁,
但現在,他們還站在這裡,說:
「我還在。」
歷史從未記下他們的名字,
但我們知道:
沒有他們,就不會有 2047 年還能存在的香港。
他們,就是那道裂縫中的光,
是廢墟之下,最柔韌的根。
他們讓這座城市不只是制度與建築的集合,
而是——記憶與情感的總和。
「歷史寫下誰的名字,不由我們決定;
但誰在歷史裡活過,是我們自己知道的事。」
—— 臨時市政憲章 序文(虛構)
他們沒有進入議會,也沒有站上講台,更沒有登上報紙的頭版。但正是他們,讓我們活下來,讓這座城市有機會說出2047年的今天。
✊ 無聲的前線
2019年的一個夏夜,旺角街頭,一位穿著黑衣的年輕人在人群散去後獨自留在路口。他彎腰撿起被水炮打濕的紙張,把仍完好的便利貼重新貼上牆。他從不曾在鏡頭前出現,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一名中年婦人,在831太子站事件後的幾天,帶著自家煲的湯去前線醫療站,放下便走。有人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些,她只說:「佢哋都係人。」
還有那個在理大圍城前夕,在Telegram群組中負責坐鎮轉發資訊的人,每一條撤退路線、每一則破門信息、每一次「已收」的訊息背後,是他不眠不休的堅守。如今,他已失聯多年,沒有人知道他是否安好,是否還在香港。
📷 他們的名字從未出現在新聞中:
一位送水工,在夜裡默默為被催淚彈薰到的抗爭者遞水、沖眼;
一位司機,免費接載示威者離開封鎖區;
一位街坊,在連儂牆重建時提供牆面、文具、甚至窗紙和膠紙;
一位退役教師,在課後私下向學生講述1989年的歷史與「六四」的意義;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我,也曾是其中之一。
我曾在清晨五點被押送看守所,曾在審訊室裡一言不發,曾在社工紙筆下寫下「情緒穩定」。但我知道,在那段歲月裡,我與千百個陌生人,曾經並肩存在。
🧭 他們讓這城市沒有走向遺忘
他們沒有身份證明,也不需要歷史證明。他們只是默默地存在於城市的縫隙之中。
有人說,歷史會遺忘小人物。但我說,是這些小人物撐起了歷史。
當香港在2044年再度成為無主之地,當政權崩潰、秩序瓦解,正是這些人所構築的信任與連結,使得城市沒有崩潰。
—
他們撿起散落的記憶,用雙手把城市拼貼回來。
他們沒喊過口號,卻走得比誰都遠。
他們的名字,或許不會被記住;但他們的身影,早已刻進我們共同走過的路上。
【七】最後的香港
香港沒有變成新加坡。
也沒有變成任何人曾經幻想的樣子。
它沒有軍隊,沒有國旗,也沒有國歌。
但它有直選的總理、有能訴諸憲政的市民、有公開悼念的廣場。
這不是一場勝利,而是一場倖存。
這不是一次終點,而是一次重新學習如何走路的開始。
2047年,是我們從歷史的廢墟中爬起來的年份。
🏛 一座記憶中的城市
沒有誰能否定這座城市曾經失落過。但也沒有人能否定,這裡的人民選擇了站起來。
在堅尼地城的海邊,現在有一面公共記憶牆,上面不是什麼烈士銅像,也不是什麼官方碑文,而是一句句匿名留言——
-「我在831那晚跑過地鐵站,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氣味。」
-「我怕,但還是選擇不離開。」
-「我不是英雄,只是想見證這裡會變好。」
-「我曾經沉默,現在學會說出來。」
記憶牆不斷更新,也不斷被重寫。這就是歷史。
🌏 香港還在——我們還在
我們曾以為,制度可以賦予我們一切;後來才明白,是人撐起制度。
我們曾以為,遺忘是前進的代價;但原來,記得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香港沒有變成新加坡。
它變成了那個曾經從未存在、卻由無數香港人用愛、痛、沉默與堅持,一點一滴刻畫出來的——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