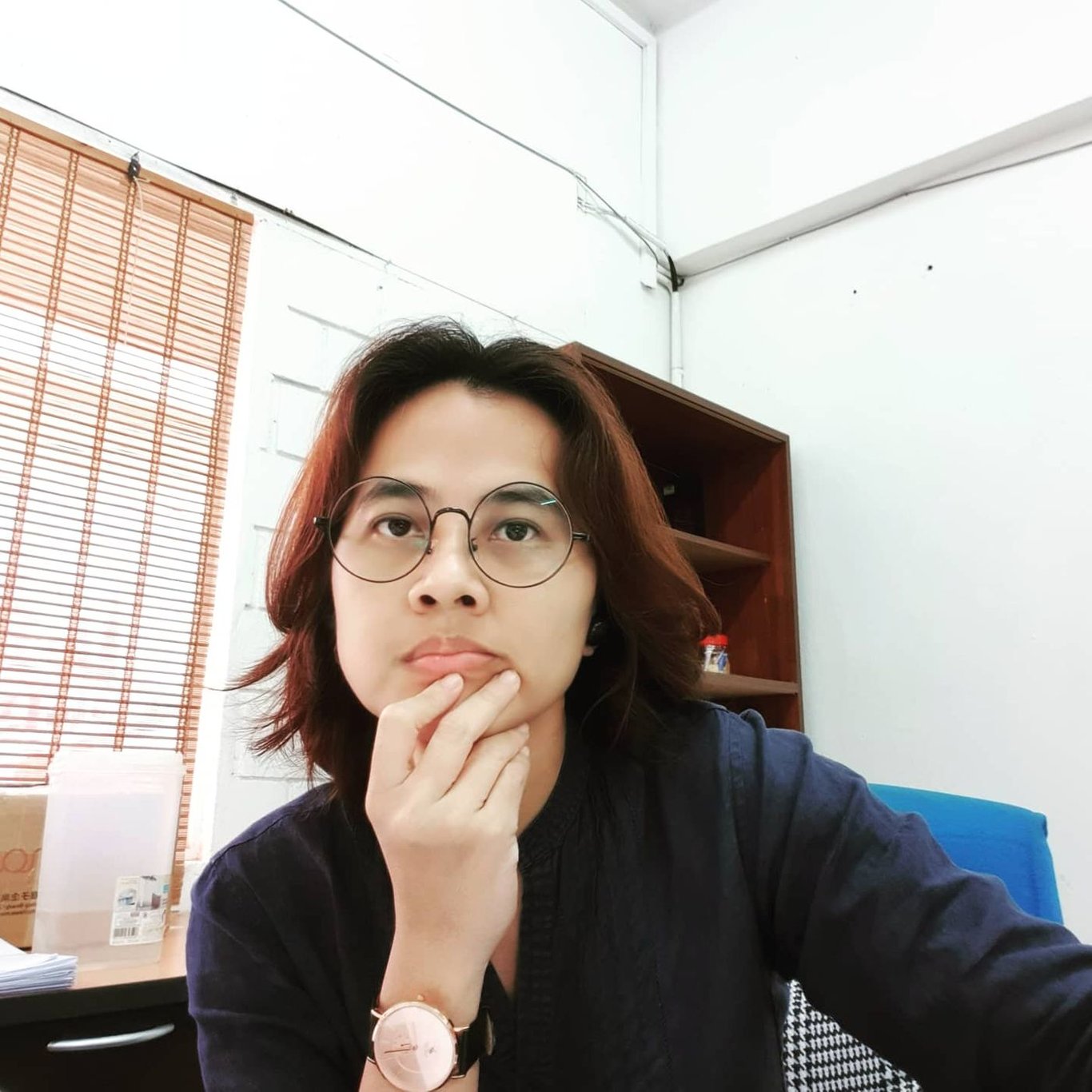像看油漆乾掉的過程
塔爾科夫斯基(安德烈·阿爾謝尼耶維奇·塔爾科夫斯基Andrey Arsen'yevich Tarkovskiy、俄國電影導演、1932年4月4日—1986年12月29日)最早以「詩性電影」(poetic film) 風格聞名,看塔可夫斯基,會給我們一種精神性的東西,一種詩意。他曾言:「電影和詩的表現特質極為相似,而生活更多是詩意的、不連貫的,而非直線式發展的戲劇敘事邏輯。」
塔爾科夫斯基生於解體前的蘇聯,畢生只拍了七部電影及一些短片,已足以讓他躋身電影大師之列。他的七部電影 ──《伊凡的童年》、《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1966)、《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 1972)、《鏡子》(The Mirror, 1974)、《潛行者》(Stalker, 1979)、《懷鄉》(Nostalgia, 1983)和《犧牲》(The Sacrifice, 1986),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世界。
緩慢與深刻,是塔爾科夫斯基電影中最本質的時間哲學。對他而言,電影並非剪接片段的連續,而是時間本身的雕刻——「電影是用時間的流動來創作」。這種「緩慢」不是遲滯,而是一種讓觀眾重新學會「看」與「感受」的節奏。當鏡頭長時間停留在滴水的牆面、搖曳的樹影或角色無言的凝視中,觀眾被迫放下思緒的速度,進入一種近乎冥想的狀態。緩慢使時間變得具體,使我們從被生活驅趕的節奏中,重新體驗存在的重量。
深刻則來自這份時間的延展。塔爾科夫斯基拒絕以劇情推動情感,他相信情感必須「滲透」而非「爆發」。他以詩的節奏讓影像發酵,讓人有機會沉入畫面與聲音之間的縫隙,思索存在與記憶、信仰與孤獨。緩慢讓觀眾經歷時間,深刻則讓觀眾進入自我。兩者相互依存,如水滲入石縫,日久方見形。
「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有生之年,提升我們的精神世界。這意味著藝術必須服務于這個目的。有人希望,藝術像其他智力活動一樣,要有教育的意義,但是我不相信藝術有教育的可能性。知識讓我們遠離知識,我們學的越多,我們知道的越少。我們太投入了以至於,丟掉了關於生命與世界,更廣大的視野。藝術的目的是,幫助人類提升精神世界。以自由意志,超越自身。」塔爾科夫斯基
在當代快節奏的文化裡,緩慢被視為浪費,深刻被誤以為晦澀。然而塔爾科夫斯基提醒我們,唯有在緩慢中,我們才可能抵達真實;唯有在深刻中,我們才理解生命的不可言說。這樣的節奏,是對浮躁世界的抗議,也是對靈魂的一次召喚。緩慢使我們聽見沉默的聲音,深刻讓我們看見時間的靈魂。
時間是生命,生命是時間,當生命停止時間也就停止了。弔詭的是,正是對速度及效率的嚮往,導致我們即傷害了效率也丟失了時間。看緩慢電影重整生命,學習從速度文化中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