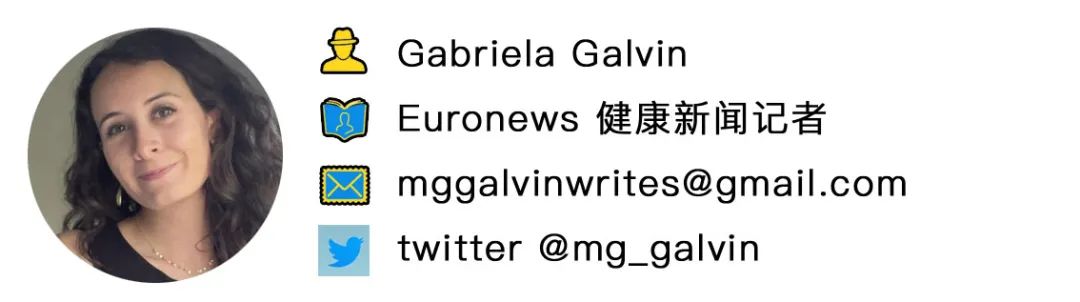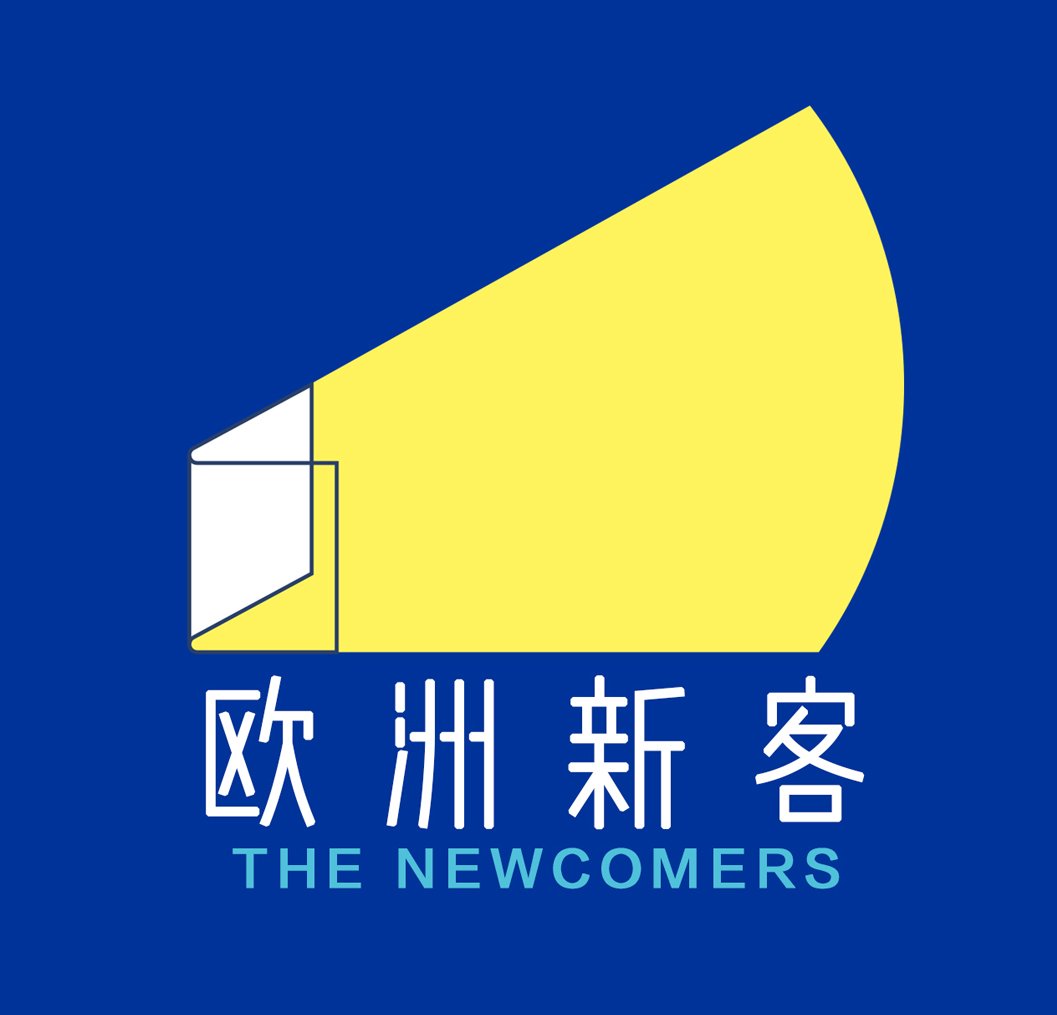在保姆式国家丹麦成长:一个非西方人的体验
当法蒂玛·阿卜杜勒-哈米德(Fatema Abdol-Hamid)的儿子 11 个月大时,当地政府通知她,必须在孩子一岁前将他送进日托中心。由于儿子是早产儿,身材比同龄孩子矮小,她希望让孩子在家多待一段时间,直到学会走路再考虑入托。她担心儿子在日托中心够不到玩具,无法独立行走,这让她感到焦虑。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丈夫经营一家叙利亚餐厅,她自己正在攻读学士学位,觉得没有必要匆忙送孩子入托。
然而,丹麦政府并不认同她的想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丹麦出生,她的巴勒斯坦父母在她出生前就移民到这里,一家人住在沃尔斯莫斯(Vollsmose)——这是丹麦最大的"族裔聚居区 (ghetto)"*,政府对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的官方称呼。作为沃尔斯莫斯的居民,政府认为她的儿子丹麦语不够流利,学习能力也存在问题。自2019年以来,所有居住在所谓"族裔聚居区"的家庭都必须在孩子满一岁时将他们送进日托中心,否则面临失去公共福利的风险。这项政策旨在督促他们学习"丹麦所倡导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译者注 丹麦于 2018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将满足特定社会经济指标且超过一半居民为非西方血统的社区定义为"族裔聚居区"。)
丹麦政府还认为,这些地区的孩子如果跳过日托,很可能在入学时语言技能落后,导致未来教育和就业前景堪忧。在该法律生效前,1-2 岁幼儿中,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家庭有 69% 会将孩子送入日托,而丹麦本土家庭的比例高达 93%。在"脆弱社区"——即丹麦本土居民、移民及其后代混合居住的社区——这一比例为 75%。
回到位于丹麦第三大城市欧登塞沃尔斯莫斯,当阿卜杜勒-哈米德申请日托豁免时,一位市政社工前来家访,她才了解到儿子需要在日托中心学习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具体是什么。这位社工显得很有同情心,拿着一份清单逐一询问并打钩,问题包括"阿卜杜勒-哈米德将如何确保孩子们的性别平等"(当时她只有一个孩子),"她将如何让孩子理解民主",以及"如何向儿子介绍圣诞节"——这些问题对身为穆斯林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实在难以回答。
"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可怕,但给人的感觉就像在说'你以为你是谁?就因为我住在沃尔斯莫斯,你就跑到我家来教我怎么带孩子?'"现年 26 岁、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说道,"我觉得太荒谬了。但我当时想,必须结束这场对话,同时还要达成我的目标。"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儿子暂时不用上日托,同时保住家庭的现金福利。
社工对她丈夫的丹麦语水平表示了担忧 —— 他大约八年前作为政治难民从叙利亚来到丹麦。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丈夫的丹麦语很好,但他还没有参加强制性的语言考试。最终,他们儿子的日托豁免获得批准,但他们无法像居住在非族裔聚居区的家庭那样申请额外的居家照护补贴。六个月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儿子学会走路后开始上日托;如今他快五岁了,丹麦语比阿拉伯语说得更流利。
日托政策是丹麦备受争议的族裔聚居区法律之一,该法律于 2018 年在主流政党的广泛支持下通过。
丹麦政府每年都会对居民超过 1000 人的社区进行综合评估。是否被定义为"脆弱社区",只需在教育水平、失业率、收入和犯罪率四项标准中达到两项即可。但如果一个地区既满足"脆弱社区"标准,又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是非西方血统,那么就会被划为"族裔聚居区",也被称为"平行社会"——这是左翼政府在 2021 年对这部法律的重新表述。
被贴上"族裔聚居区"标签可能预示着一个社区的终结。
族裔聚居区面临一系列旨在打散族裔聚居的政策——包括房屋拆迁重建、强制搬迁以及对该地区犯罪行为的加重处罚。正如阿卜杜勒-哈米德所经历的,家长也必须将孩子送进日托中心。然而,日托中心对生源构成有严格规定,来自族裔聚居区的孩子比例上限为 30%。这意味着,如果最近的日托中心已有 30% 的儿童来自族裔聚居区,新入园的家长就必须将孩子送到更远的、尚未达到配额的日托中心。
政府已拨款 145 亿美元用于实施该法律直至 2026 年,目标是到 2030 年改变族裔聚居区的种族和经济构成。
丹麦政府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和融合问题",即人们担心非西方移民尽管享受了丹麦慷慨的社会福利,却无法融入丹麦文化或熟练使用丹麦语。反对这些法律的人认为,它们破坏了移民社区和第二代移民的社会结构,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18 年所说,这相当于"强制性同化"。
"尽管欧洲各地都有类似趋势,但在我们看来,这是种族歧视最明显和恶劣的例子之一。"开放社会司法倡议组织高级诉讼主管苏希拉·马思(Susheela Math)说道。她支持对目前提交给欧盟法院的一揽子计划提出法律挑战。
最新的族裔聚居区名单发布于 2023 年 12 月,由于社会经济数据改善、人口迁出或非西方居民比例降至 50% 以下,被列为"平行社区"的社区数量从 2018 年的 29 个减少到 12 个。如今,这些社区约有 28,600 人居住,非西方居民比例从 53.1% 上升到 77.4%,而丹麦全国的非西方居民比例为 10.1%。大多数居民来自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或伊朗,以及自 2022 年起的乌克兰,但乌克兰人不受族裔聚居区政策约束。
非西方标签涵盖了所有人,从新移民到丹麦护照持有者,只要他们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来自非西方国家。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的共同语言是丹麦语。"住在哥本哈根 Mjølnerparken 族裔聚居区的教师玛伊肯·费勒(Majken Felle)说道,她是土生土长的丹麦人。"社区的孩子们玩耍时,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说丹麦语。"
族裔聚居区的特殊住房政策经常遭到抗议——曾有 5.2 万人签署请愿书,诉讼也持续不断。但相比之下,日托规定却较少为人所知。根据新线新闻社收集的市政数据,自 2019 年以来,至少有 241 名儿童参加了这项免费的强制性项目,有 53 个家庭因违反规定而被取消公共福利。这些数据还不包括那些为了避免法律威胁而主动报名参加日托的家庭。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研究族裔聚居区法律影响的博士后研究员阿玛尼·哈萨尼(Amani Hassani)认为,这项政策造成了"流离失所压力"(displacement pressure),意味着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以搬离以逃避规定,而弱势居民被留下,失去了原本邻居提供的社区支持。
保守党议员于 2018 年提出这项日托提案,依据的是一项初步研究,显示非西方背景的双语儿童在 3 岁时的语言测试中得分较低。虽然这些孩子在 6 岁时的语言水平通常会有所提高,但他们的总体表现仍不如单语家庭的孩子。这项研究涵盖了数百名儿童,他们的父母分别来自丹麦、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研究基于标准化的语言评估,研究人员承认这种评估可能存在缺陷,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双语儿童或社会弱势儿童学习语言的独特方式。
其他研究人员表示,政策制定者不应使用这类语言测试来为强制日托制度辩护,因为报告无法全面反映孩子们的各种沟通方式。
他们还认为,幼儿学习丹麦语的速度因人而异,并不需要以完全相同的速度进步才能掌握这门语言。该计划的政治反对声浪来自幼儿教育工作者联盟等专业团体以及左翼政党,他们希望通过其他方式鼓励日托制度的普及,例如让市政卫生工作者在与新家长见面时讨论日托问题。但这项立法最终以78%的支持率在丹麦议会获得通过。
"我不太担心强制性条款,"中左翼社会民主党成员安妮·哈尔斯博-约根森(Ane Halsboe-Jørgensen)在 2018 年该法案的辩论中表示。自 2019 年执政以来,该党进一步扩大了族裔聚居区立法的范围。"如果这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我将始终选择支持。"
事实上,高质量的早期儿童项目确实能够对儿童的认知、社交和行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对低收入和双语儿童而言。从长远来看,它们与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就业参与度密切相关。
丹麦人将日托视为在儿童发展关键时期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工具,国家自2004年以来一直保障全民儿童保育——这项社会投资被认为促进了这个拥有近 600 万人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等。
"自从日托制度在丹麦建立以来,它就一直是构建福利国家的政治工具,特别是专业性工具,"奥胡斯大学教育社会学副教授克里斯蒂安·桑德比耶尔·汉森(Christian Sandbjerg Hansen)表示,他反对族裔聚居区法律。"一岁儿童以某种方式上日托,这是基于经验的做法。"
托儿所工作人员、家长和研究人员认为,日托政策的问题在于其强制性。他们表示,如果政府真想提高日托入园率,就应该专注于为特定困难家庭提供宣传和激励措施,而不是威胁对主要为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实施经济处罚。
"人生的前三年至关重要,"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族裔聚居区的儿童保育员丽莎·布鲁恩(Lisa Bruun)说道。为了帮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家长更放心地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她会在孩子入园前进行家访,并邀请父母到日托中心参观,让他们有足够时间感受日托的氛围。
关于日托中心的 30% 配额规定,不考虑日托中心的容量,也不考虑某个多子女家庭是否已经有一个孩子在园,单纯规定新入园儿童来自弱势居住区的比例不得超过 30%。这项规定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港口城市埃斯比约(Esbjerg)的一个族裔聚居区,日托中心 Bydelens Børnehus 目前仍有一半空置,尽管附近有很多孩子在等待入园,该中心经理迈克尔·弗雷德里克森(Michael Frederiksen)表示。
由于法规强制家长必须将一岁的孩子送到日托中心,等候名单上的家长不得不长途跋涉穿过城镇,将孩子送到其他中心,弗雷德里克森说道。这些中心通常距离他们的社区 1 到 3 英里,甚至有一个中心的距离超过 8 英里。然而,来自非族裔聚居区的家庭无需面临这样的学生分流规则,而且由于他们通常将孩子送到自己社区的日托中心,因此 Bydelens Børnehus 中心的总体入园率仍然很低。弗雷德里克森说,这意味着附近族裔聚居区儿童的名额非常有限。
"我们都接受过指导和培训,要真正了解孩子们的基础水平,并从孩子们真正需要培养的地方开始培养他们,"弗雷德里克森说道。接受采访时他正站在 Bydelens Børnehus 中心空空如也的操场上,"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额外的培训,但根本没有孩子来玩秋千,因为我们只能以一半的容量运营。"
去年玛鲁亚(Marua)刚生完孩子,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女儿加入 Bydelens Børnehus 中心的候补名单。她姐姐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拥有土耳其和巴勒斯坦血统的玛鲁亚很喜欢那里多元文化、包容的氛围。但到了报名时,30% 的名额已满,意味着她不得不去其他地方报名,直到几个月后 Bydelens Børnehus 有空位为止。她觉得这很不公平。
"我想让我的女儿明白,每个人都足够优秀,长大后不必再为肤色烦恼,"22 岁的教育系学生玛鲁亚说道,她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
"教给她一套价值观很难,但这些价值观却在整个社会都得不到认同。"
族裔聚居区规则反映了一项长期战略,即利用国家强制规定的日托服务来促进丹麦文化的同化。自 2011 年起,3 岁及以上的双语幼儿如果丹麦语水平被认为不合格,就必须送去日托,这项规定在 2016 年被降至 2 岁。但英语和德语儿童不受此限制,因此汉森将"双语家庭"一词描述为"穆斯林移民的委婉说法"。
换句话说,日托规则首次提醒了非白人家长,尤其是穆斯林家长,他们的孩子在丹麦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社会"他者化"。哈萨尼说:"这些法律暗示着,在这个住宅区内正在形成的社区是不够好的。平行社会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的。"
族裔聚居区法律的出台也与丹麦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移民政策右倾化同步。2016 年,丹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寻求庇护者上交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以资助他们在丹麦的居留费用;2018 年,丹麦又通过了一项禁止穿戴面纱的禁令;2019 年,丹麦政府认为叙利亚部分地区可以安全返回,并开始撤销难民的居留许可;2022 年,丹麦宣布计划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2023 年,丹麦首相、社会民主党人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表示,她希望削减那些非西方女性的公共福利。
2020 年,曾任移民与融合部长、现任儿童与教育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马蒂亚斯·特斯法耶(Mattias Tesfaye)在接受哥本哈根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一些国家的移民"能够毫无问题地融入丹麦社会,而另一些国家的移民则要落后好几代人。因此,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少来自融合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的移民数量。"
特斯法耶通过发言人拒绝了采访请求。社会民主党、反对族裔聚居区法的左翼政党红绿联盟以及几位当地政客要么拒绝了采访请求,要么没有回应。
虽然丹麦人对移民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但强硬的政治言论已逐渐渗透到公众视野。根据哥本哈根 2010 年的一项研究,如果非西方学生的比例超过 35%,拥有丹麦血统的家庭更可能选择退出当地公立学校。最近,丹麦人权研究所发现,如果所在学区有族裔聚居区,白人和富裕家庭更可能选择退出当地公立学校。
丹麦媒体报道这些地区时,总是聚焦暴力、毒品、帮派活动和警察行动,并将那里的孩子称为"族裔聚居区儿童"。汉森表示,除了族裔聚居区政策本身,媒体报道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丹麦的所有社会问题都集中在这些街区。
居民们对他们的社区有不同的看法。57 岁的易卜拉欣·埃尔-哈提卜(Ibrahim El-Khatib)于 1990 年从黎巴嫩移居丹麦后,在霍耶-措斯楚普(Høje-Taastrup)的一个族裔聚居区里抚养了三个女儿。这位 IT 项目经理表示,他所在的社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封闭的平行社会,这并不符合他的感受。去年他被迫离开该社区,因为他所在的街区将作为住房开发计划的一部分被拆除。
"对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来说,那里非常安全——他们在那里玩耍,没有任何危险,"埃尔-哈提卜说,"我称那里为丹麦最友好的族裔聚居区……离开那里,我和我的家人都很难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会将成长过程中听到的污名化信息内化。根据经合组织 2015 年的一份报告,父母来自伊拉克或索马里的儿童,只有 63% 在丹麦学校有归属感,而同类儿童在丹麦的邻国芬兰,有归属感的比例达到 83%。
奥胡斯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娜·巴克尔·西蒙森(Kristina Bakkær Simonsen)表示:"通常情况下,当孩子们长大到足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毫无保留地将他们视为丹麦人时,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受伤和沮丧。"
法丽达(Farida)出生于叙利亚,如今在她从小长大的哥本哈根族裔聚居区抚养三个孩子,她已经在为这些对话做准备了。当她 9 岁的女儿想尝试戴几天头巾时,法丽达试图劝阻她,担心一旦离开这个社区,她会面临质疑。在这个社区,大约四分之三的居民是非西方人。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经历这种事,"37 岁的助产士法丽达说道,她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当谈到社区的污名化时,"我会让他们自己判断这是否基于种族主义或其他原因,但我认为孩子们很聪明。他们会弄清楚的。"
一些族裔聚居区居民——无论白人还是非西方人——已提起诉讼,挑战这些法律。在最受瞩目的案件中,欧盟法院将裁定"非西方"标签是否根据族裔将人们区别对待。如果是这样,丹麦针对"族裔聚居区"的开发计划可能构成欧盟法律规定的种族歧视。丹麦政府辩称,"非西方"指的是国籍或原籍国,而非种族或族裔。
开放社会司法倡议组织的马思表示,欧盟法院将于 7 月审理此案,最早可能在明年做出裁决。如果这些居民获得法律胜利,将向其他欧盟国家发出一个信号——欧盟的反歧视法将得到维护。"你不能用种族或族裔出身的替代措辞来规避这些法律,也不能以种族融合之类的名义将种族群体视为二等公民,"马思说。
诉讼原告之一、居住在 Mjølnerparken 社区的费勒表示,许多家庭已经接受了永久安置,因为他们厌倦了各种诉讼和住房流离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2023 年 12 月,最新一轮的族裔聚居区名单公布时,Mjølnerparken 社区首次被排除在外。它的教育、收入、就业和犯罪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变化,但它已经不再符合统计资格——人口已降至 966 人(少于 1000 人),离开的人已经足够多了。
"很多人在 Mjølnerparken 社区住了大约二三十年,邻里关系亲密,他们已经成为来自异乡的家人,"费勒说,"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原本牢固的支持网络真的被连根拔起了。"
在诉讼进行期间,丹麦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今,房屋拆迁和驱逐仍在继续,有能力的家庭被迫搬离族裔聚居区,父母必须向政府申请才能将孩子留在家中,丹麦幼儿则被送往日托中心学习如何成为丹麦人。对于非西方背景的丹麦父母来说,族裔聚居区政策的政治考量反映出丹麦不愿接受多元文化社会。
如今,这种冲突正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孩子。
"我无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阿卜杜勒-哈米德说。"我用丹麦语做梦,用丹麦语思考,用丹麦语说话。但与此同时,我身份的一部分,也确实是巴勒斯坦人。"
本文为 2025 年 European Press Prize 的 Migration Journalism Award 获奖文章,首发于 New Lines Magazine,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