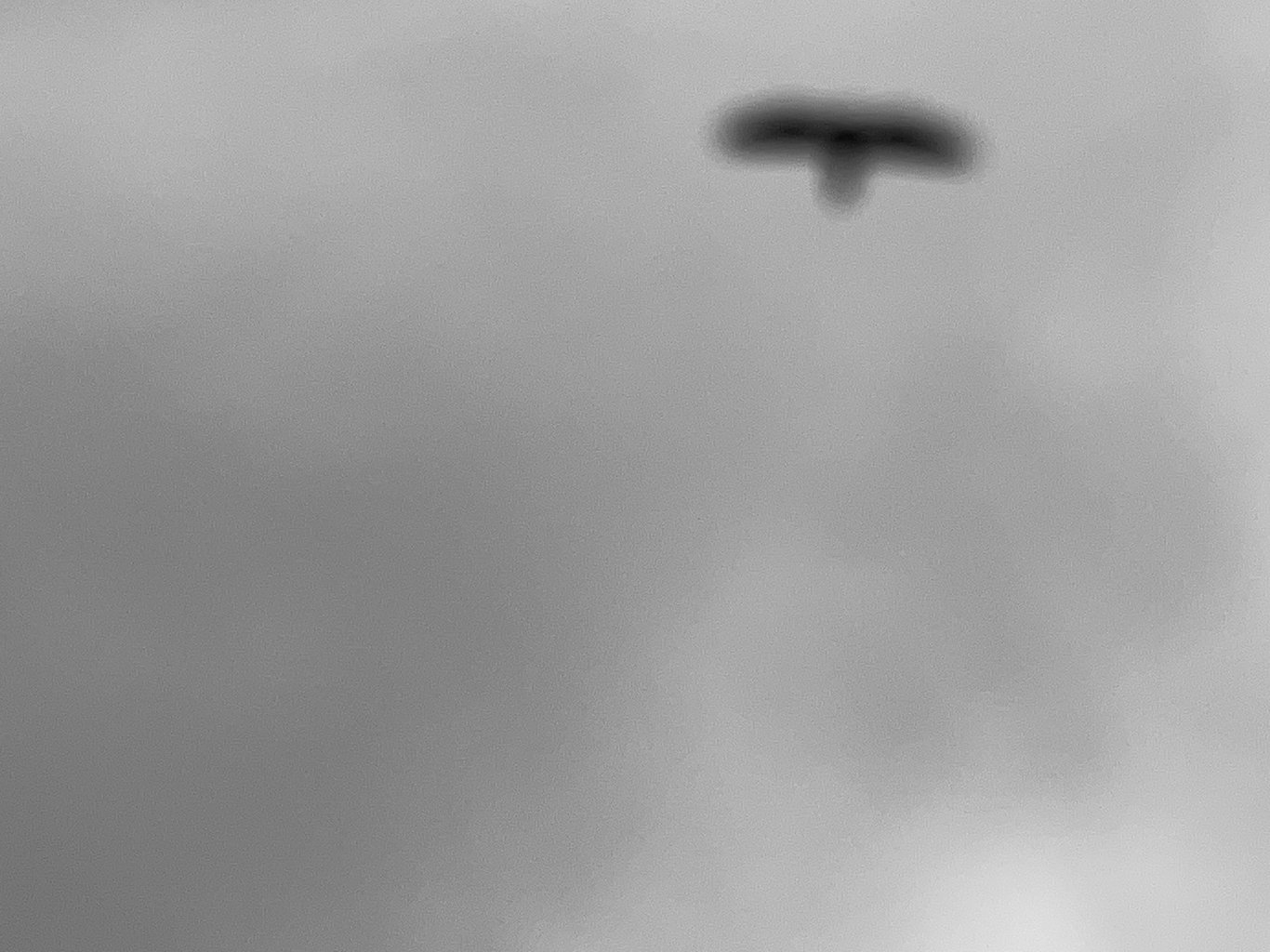關於荷蘭的耶拿學校-Jenaplan School in Heerde
1.校園環境
Jenaplan school in Heerde是一間位在Heerde小鎮,一個年紀相對大的校舍,但校舍並沒有因為經歷比較多的時間,而使人看起來老舊,走進校園反倒感覺像個慈祥且開放的老人張開了雙手歡迎我們。校舍的中間是一個大客廳,以此為中心點,周圍圍繞著各個年段的教室,在教室的外部與客廳之間擺上桌椅,作為教室的延伸,讓孩子能夠有教室外自主學習的空間。整體的裝潢也是使用木質調的配色,給人溫暖的感覺,教育某種程度的意義上,是將關於未來的信念傳遞給孩子的過程,以共同體為基底的耶拿學校,在陪伴孩子長大的過程以溫暖與包容的本質來實踐教育,使孩子在重要的童年經驗裡,能夠相信未來是溫暖且有希望的。
2.重視平衡發展的學校
這間學校重視語言治療與閱讀障礙的協助,這次沒有機會實際看到學校如何操作,但他們有邀請荷蘭一個操作團體/自我覺察課程的團隊BM-Academie進來校園,進行類似體驗教育的課程,協助孩子在課程之中覺察及反思自己在團體之中的狀態。除此之外,這間學校另外感到有趣的部分是有一堂談論生命意義的課,會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主要是以聖經故事作為主題,另一組則是用生命敘事的方式來討論。
我們在這週跟著宗教班組一起上課,老師分享《耶穌升天日》的故事,上一週也因為這個節日,我們也跟著放了假。老師在故事前開始前,在桌上鋪一塊白布,把袋子裡的石頭及小串珠放在桌上,邀請大家先拿一塊石頭,分享自己難以放下與不願失去的事情後,把石頭放下,接著再邀請大家拿一顆小串珠,分享自己如何轉化這段悲傷的記憶,也把小串珠放下。可以感受到過程大家的投入,以及老師與孩子之間有足夠的信任,使得大家能夠在這裡放心掉眼淚。這段暖心的過程結束後,老師帶著課堂上的孩子來到足球場玩鬼抓人,釋放完所有的情緒及力量後,能看見回到教室的孩子似乎脫了一層皮。
3.多元性的教師團隊
擁有這樣強連結的老師,我們原本以為他是這裡的正職老師,後來才知道老師一週只會來一次。這間學校大約有六成的兼職老師,實際上兼職的文化在荷蘭算是盛行的,通常只有年輕的工作者才會做全職。在台灣的兼職者,有時會被直觀地對應到「非專業人士」的這個標籤,但在講求多元視角的耶拿教育裡,似乎兼職者反倒能夠成為這裡的養分,因為他們從不同的職場或是其他類型的生活樣貌,帶進新的觀點與團隊討論,而非僅僅只是一群教師在同溫層裡取暖。當問題這樣思考時,似乎團隊擁有兼職者成為一種必須。只是即便如此仍不能否定長時間投入某個領域所累積的專業度,如何成為一位好的老師,如何打造一個良好的教師團隊,在養成及培訓的過程需要做許多的取捨,究竟如何在教師的教育專業及學校的多元視角之間取得一個適合的平衡,是未來值得討論的問題。
學校的工作者團隊除了正職與兼職的老師外,也有社區的志工,在台灣那些進到學校的志工普遍不會直接接觸到學生,大多是協助校園的行政或各種維修的工作,但在這邊志工主要是協助孩子面對課業以及世界導向的學習,讓孩子與社區的大人連結,同時使得大人能夠在學校發揮教育的價值,進而創造自身存在於此的意義,建立在地與學校之間的連結,或許這也是未來回到台灣開辦學校以後能夠採用的方法。
4.班級管理
相比其他學校,在這裡的教室看到掃地的分工表,打掃的範圍主要針對教室內部,每個人都有自己負責的項目,要做的事情並不多,孩子大多能夠做到自己該做的部分。整理環境的意義是什麼過去在求學期間不明白,只知道就是規定要去做,不做會被罵,後來發現老師不是三頭六臂,所以只在老師注意到的時候才認真打掃,一不注意就跟同學摸魚,但實際上打掃彼此共同使用的環境似乎本就是群體生活裡基本的一環,但過去卻不曾有這個意識。
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還是能看到熟悉的手指放在嘴上,發出「噓」聲來管秩序,似乎這已經是某種程度上的國際手勢,有時也會覺得利用耶拿教育裡,大家常用的「老師舉起手,等待大家都舉起手來表示老師現在要講話」的這個方法其實也帶有某種程度的控制,實際上在課堂上觀察到小孩舉了手,其他人其實也不一定會搭理(除了孩子主持的分享之外),但老師舉起來就有用。如果最終還是只有老師能夠決定此刻的秩序該如何,那用什麼樣的方式似乎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5.課程
這裡的數學課相對其他學校以既有的課本內容為基礎的練習本,這裡多了樂高、桌遊以及電腦遊戲。基本上還是有教學進度,老師會安排不一樣的內容,讓孩子自己分配進度,但原則上還是有一套孩子這學期必須完成的菜單。只是相對這樣多元性的數學練習,在台灣則是一章一章地按照課本的進度往前走,每個人都一樣,像是部隊在行軍一樣,每個人都走在值星官的要求的步伐裡,也能看出兩個地方在看待學習的「按部就班」這件事採用不一樣的視角。
一如「耶拿教育」的往常,孩子很快地就走到早已分好的組別裡開始今天的練習,可能一起討論,也可能各自埋首在眼前的練習本。看了四間學校,能看到小組共同工作時,有些班級很吵,有些則很安靜,老師曾說在耶拿教育裡很重要的精髓在於混齡以及對話,如果混齡小組工作無法創造出共同工作的氛圍,那這樣就失去耶拿教育的意義,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來評估一間耶拿學校夠不夠「耶拿」。
創造出有效的小組共同工作,並不是把孩子隨機分在一組就能好,如何讓孩子與孩子之間產生化學反應,得靠老師不斷地觀察及引導,就好像做菜一樣,如何讓創造不同口味的食材的連結,進而成為好吃的菜,是身為耶拿老師的功夫所在。
在耶拿教育裡強調的是課堂上的練習時間應該多過講課,其實在台灣也是練習時間多過講課,只是我們是把練習的時間留到放學,孩子回家自己做。某種程度上放學後到睡前,其實都是孩子的工作學習時間,假設孩子都能在放學後專心完成作業的練習,老師就能夠在課堂上講更多更豐富的內容,然而這個月我們看見的是比起學習的更深,這裡更在乎學習的更廣,進而產生對學習的樂趣,在台灣我們能夠從小就培養出厲害的考生,但犧牲的是更多曾經可以享受學習的孩子。
6.影音與手機的運用
結束了課程以後是午餐時間,其中一個老師在教室播放類似家庭關係輔導的教學影片給大家看。感覺起來不有趣,但孩子看的很認真,他們的眼神幾乎沒有離開過螢幕。影音似乎有種魔力能夠抓住大家的眼睛,進而能夠潛移默化地植入想法在別人腦中,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以前會有人針對電視兒童做討論,現在則是針對手機成癮的現象來研究。
我以前也是電視兒童,一天可以坐在電視前六七個小時的那種,此刻好像無法具體形容沈迷電視帶來的後果,但現在要我站在手機成癮,損壞孩子腦部發展這個立場而拿起權柄去限制,似乎又有點站不住腳。重要的或許從來都不是「用」與「不用」這種膚淺的解決方式,而是應該要如何使用。我們是經歷過沈迷電視的年代,某種程度上也能稱得上是走在影音席捲人類這個潮流的先行者,身為先行者,或許更應該去思考該如何從過去的經驗來找出更好的面對方式。
7.如何養成學習習慣及改變過去的學習路徑
在牆上會貼如何做世界導向研究的引導指示,孩子如其他學校一樣,使用電腦來找資料,老師在一旁引導,同樣的事情看了一個月以後,也不再感到新奇,這裡的學校的看待學習從來就不是只有語文數學那些既定的科目。一樣的概念在台灣之所以被稱之為「實驗教育」也只是大家不習慣這樣看待教育的方式罷了,做的時間久了,也就正常了,但問題偏偏就出在我們沒有「時間」。
孩子在義務教育裡的求學過程就只有這十二年,小學六年、國中、高中各三年,這段時間學校及老師擁有相對多的決定權去思考該如何養成一個台灣未來需要的成年人,學校在肩負起這樣的責任以後,時間該如何運用就成為大家爭吵的話題,我們能夠有多少的時間證明這樣的理念值得成為日常,又有多少的時間,能夠承受看不見,且尚未到來的結局。
那些我們所期待養成的學習習慣是需要文化作為基底,讓時間去堆疊進而建立出來,就好像那些被設計出來的教具一樣,如果它的存在只是有趣,仍然無法成為每天觸摸的日常。就好像耶拿骰子在有些學校只是一顆骰子,但在這裡就是創造對話與討論的工具。當老師跟孩子跟在乎這個工具,大家就會認真地使用這個東西,這樣工具的設計理念才有發揚的可能性。
養成閱讀的習慣也同樣仰賴在成長的過程中,如何建構閱讀在心裡面的印象。在這間學校,老師設計了不同的遊戲在閱讀時間。面對中年段的孩子,會讓他們每讀完一頁,就從地板坐上椅子,再讀一頁就從坐在椅子變成站上椅子,再讀一頁後就坐回地板,反覆循環。孩子似乎在一頁又一頁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累積,從中得到些許樂趣及成就感,另一個高年段的班級,老師則設計了一個「書本好聲音」的遊戲,所有的孩子背對著老師,老師在這個時候開始讀書裡的內容,如果感到有興趣就轉身,帶走這本書回去讀,如果很多人都轉身,也能夠開啟關於這本書的讀書會。這樣的過程似乎能夠重新打破腦袋不自覺將書本與工作做連結的印象,使閱讀成為探索世界與自我的路徑。
8.遊樂場的意義
跟著孩子一起到外頭的遊樂場玩,有沙堆、有藉由旋轉轉盤來挖土的器材,有盪鞦韆、溜滑梯、有繩索製作出來的洞穴可以穿越,有類似踩高蹺的器材來體驗高低的落差,那天我跟著一個幼兒園的孩子在踩高蹺的器材玩了整整半小時,看著孩子一步又一步地朝著更高的木頭,跨出腳步,再踩到低的木頭,享受著身體在這段過程因為高度變化帶來的興奮,看著他站在最高的木頭往沙坑裡跳進去後,興奮地回頭對我笑後又爬上木頭,來來回回地看見孩子欲罷不能的表情,好像也跟著一起享受了這段身體經驗的新奇感。
耶拿教育強調「遊戲」是孩子在學習過程裡的重要經驗,藉由讓孩子穿梭在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除了練習人際相處以及如何參與遊戲以外,也在遊樂設施的體驗建立自身的身體經驗,看似不起眼遊樂場,或許可以思考如何創造讓孩子有更多合作遊戲的環境,或者創造各種型態的身體經驗的設施。
9.觀課者自身的反思
身為一位觀課者,思考著我們這群觀課者與孩子及老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在課堂前我在外頭跟孩子聊天,他們開了一些玩笑,就是準備走進青春期的男生可能會有興趣的一些黃色笑話,我懂,我也經歷過那段時間,對我來說無傷大雅,跟他們笑一笑也就過去了,回到教室以後,老師突然嚴肅的跟大家說話,可以感受到教室的寂靜,嘗試用手機翻譯老師說的話,才知道上週老師才特別提醒大家我們要來,不要說不該說的話,就做自己平常在做的事情就好。突然覺得在那個當下我們似乎做錯了什麼事情,但又指認不出自己做錯的是什麼,我應該介入去跟孩子談黃色笑話這件事的本質嗎?又或者裝作什麼都不聽不懂?還是應該以一種同理及玩笑的態度先建立連結,事後再來談?
結束以後孩子還是來找我們玩,好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我們想找孩子、老師是因為想認識這裡,老師找我們可能是因為這是他的工作,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們也想認識我們,跟我們交流,孩子找我們可能是因為我們很友善,當然也有可能是這四張亞洲面孔充滿新鮮感,因此吸引了他們。在有些學校能感受到彼此想要建立連結的能量很強,但在有些學校就感覺不太到這個東西,在這一個月裡,不斷地在思考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除此之外,四間學校看完,心裡肯定會有喜好程度的差異,那些讓我感覺很喜歡的原因有哪些?我喜歡氛圍感覺上是充滿熱情及創造力的,看見孩子主動想與各式各樣的人連結讓我感到很喜歡,但在台灣似乎很少看到這樣的畫面,大部分都是我們得主動去找孩子,我會因為這些原因影響我看待這間學校的方式嗎?又或者如果我就是喜歡這樣的環境,我就在學校裡做這樣的老師,讓孩子成為這樣的孩子,只是想到這裡,又感覺自己自以為是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