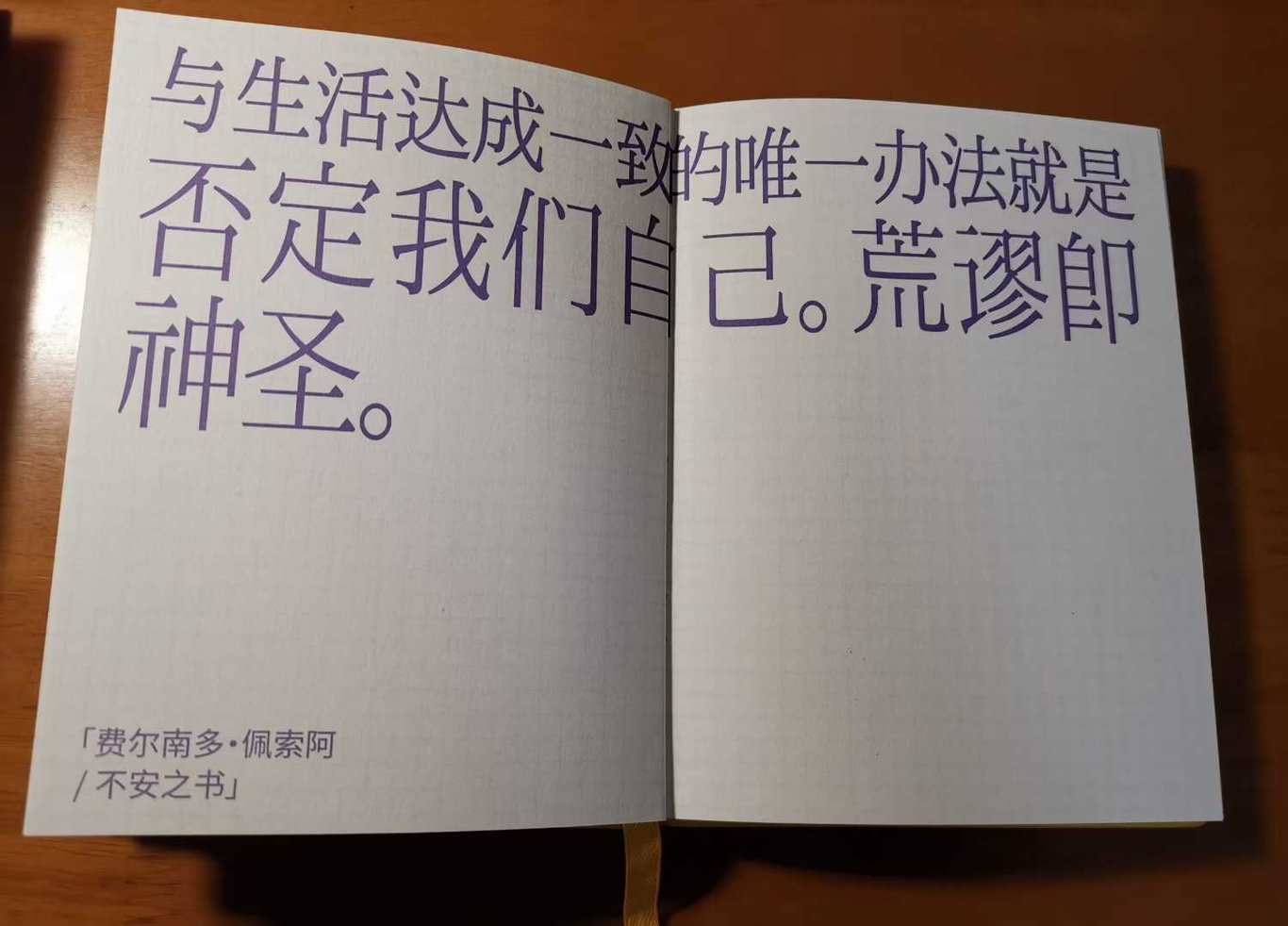館長開通抖音,道長下架播客
上聯:館長開抖音帳號粉絲數十萬人
下聯:道長播客全下架損失數千萬元
橫批:鬆緊由它
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了,華東政法大學的老師張雪忠(他自己也是被噤聲壓制的對象)在朋友圈就不只一次寫著:「雞鳴狗盜之輩鑼鼓喧天,正直有識之士舉步維艱」。
但我為什麼還是要寫?因為只要關注中國社會的人,就不時會有這類感觸。有時候,感觸變得更大,不只是人治的、權力至上的「鬆緊由它」,還讓人無法忽視這個社會的兩面性,特別是檯面上的話語和私底下人們的談論,存在著極大的落差,這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審查的存在。
(「館長」是所謂的網紅陳之漢,滿口粗話卻忽然前往中國賣乖,目標當然是生意;「道長」是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台灣人可能較陌生,但是在大陸相對小眾的文化圈裡卻是「頂流」,20多年來透過《鏗鏘三人行》、《八分》等節目廣為人知。相關新聞,可參考:www.cna.com.tw/news/...)
寫這篇的前幾天,上海律師斯偉江原本8月22日晚上要去成都有杏書店講一場活動,講題是「談談勞東燕的抑鬱與堅守」。原由是法學教授勞東燕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開頭是這樣的:「這些年來,明顯感覺社會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著幾乎所有人向下墜落,並且這股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勞東燕說的,是網上的粗鄙與暴戾,作為仍算積極為公共議題發聲的知識分子,她也不免成為被針對的對象,「在當下的環境下,如果有人不覺得痛苦,不覺得壓抑與有壓力,還一味地歲月靜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反而有更大的問題:看上去快樂平靜,其實病得很重。退一步說,即便不是病得厲害,也是遲鈍得可以」。
活動宣傳不到半天,就宣告取消,開始退款(書店收一人人民幣29元)。斯偉江接到北京公安的電話,不讓他講這活動。
有知識情感、對公義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感到憂鬱的理由還會少嗎?一個活動,說不准辦就不准辦,下指令的人層級還不需要很高。館長今天能開抖音帳號,哪天爭議言論發酵,也可以說關就關。而在這樣的環境裡,「賺錢」往往成了很投機的事,搶時機、鑽空檔、能撈就撈。
事情過去以後,有杏書店老闆張丰寫了一篇文章,裡頭寫道:「斯律師說:『沒必要為當下的困難抑鬱。將來還會更困難,你又該如何呢?』他的建議是立足當下,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而不必去考慮宏大的結果。」
中國社會的上下落差、內外落差
偏偏就是在這種普通民眾都容易哀嘆憂鬱的環境裡,新聞聯播上、中央官媒上說的都是些「大詞」。譬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綜合國力躍上新台階;因為習近平去了西藏,新華社的標題是「書寫美麗西藏新篇章」;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越是中央級的官媒,越是對別人用最惡毒的字眼批評,連罵人都是「大詞」(還記得1990年代,人民日報的標題說要把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覺得,每個字都認得,但沒想過句子可以這樣用的),對國內事卻報喜不報憂。即使在上海封城這種人類史上空前的大事期間,人民日報也不曾為它留下頭版版面。
社會學裡有個運用戲劇概念的「前台與後台」理論,前台是正式的、顧及形象的、滿足社會需要的,後台是私人的、放鬆的、無涉大眾的;任何國家官方機構在話語上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兩面性」,就像政治人物必須說某種免於爭議又帶著表演性質的話一樣。但是像中國這樣落差極大的,除了從蘇聯時期的民間生活上找到共鳴外,當今還想不出其他社會如此。
我總帶著好奇想探究,那些在生活中焦慮著經濟、房價甚至外國圍堵的普通中國人,聽到電視上播送這些大詞時作何感想?現實是,那些不以為然的人根本不會去看央視「新聞聯播」或人民日報;而那些生活中會頻繁接觸到媒體的人則大多視若無睹;但你要說口號無用嗎?也不盡然,它就像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洗腦。
當局對言論管制的邏輯是「便於治理」,但高強度與頻繁的管制介入,造成的結果是一個嚴重表裡不一的社會,甚至也強化民眾之間的對立。
語言重塑:誰影響了誰?
政治影響語言,語言也反映社會氛圍,甚至建構思想。在微信裡,大家用縮寫或錯別字、諧音字取代可能敏感的詞彙早已經是常識,譬如WG是文革、ZF是政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負面的熱點新聞和領導人通常都有代號。久而久之,當你也那麼順暢自如地用起諧音字時,總會有那麼一刻腦海閃過: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在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裡, 創造了那麼一種「新語」, 新語的運用,近乎重寫歷史。在中國社會也不乏這樣的例子,謊話說一百遍、一千遍,客觀來說並不會因此變成真的,但搭配言論管控,卻會影響認知,久了以後,多數人心中這段歷史就真的被改寫了。
譬如,1960-1962年的大饑荒,明明是因為激進的共產社會實驗「人民公社」造成的,但在大陸,直到現在都稱作「三年自然災害」。而在大饑荒期間發生的人吃人事件,河南信陽為此造出了特別的罪名叫作「破壞屍體」,委婉詞語掩飾了殘酷,幾十年後,人們根本不會承認有過人吃人。
想在中國賺錢的網紅,譬如館長,享受「台灣人」身分帶來的優勢之餘,絕對知道在中國社群媒體上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的規則,並且願意遵守。他可以規避敏感話題,也會習慣使用「新語」來對齊當局者。然而,在自以為能掌握的言語詭辯中,他以及還能思考的觀眾們,在笑過、罵過後,彷彿會看到《一九八四》中真相部的口號: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最溫和的人也感到挫敗,未來會如何?
無論是勞東燕的文章、斯偉江未實現的主題分享,還是梁文道的節目《八分半》在大陸全網下架,都是一種公共表達的挫敗,而且是知識人、溫和派的挫敗。同感挫敗與憤怒的,則是一群同樣不張牙舞爪、平常靜靜守在電腦螢幕前,聽他們分享有別於官方宣傳和極端批判之外對世事看法的青年和中年。
據說梁文道節目被下架的原因,是因為在紀念蔡瀾的那一集裡,提及他曾在《蘋果日報》撰文,並感激當時社長董橋和老闆「Jimmy(黎智英)」的寬容。此外,金庸以前寫的報紙社論很銳利,「有些拿出來放到今天的香港,那是能坐牢的言論」,感慨「這輩子沒見過香港這麼蕭條」。
朋友S憤怒地跟我說:為什麼不把「有問題的那集」下架就好,要而是讓所有《八分半》的節目都下架?
在人治主導的規則裡,官方的懲罰邏輯又有誰能完全明白呢?
台灣人可能很難體會這一波「普通人的憤怒」,總覺得中國本來就是管控言論的國家,這種動輒下架的事不是也很正常嗎?其實,中國的特色就是「大」,它所帶來管理上的限制和需要,都使得灰色區域存在,不可能所有的話題都是百分之百高壓禁忌。
S說,他們當然不是天真到以為中國言論都很自由,但總是還能在一些框架和限制中感受到創意甚至犀利的表達。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去年恢復的網上脫口秀節目,很多社會話題都能激發共鳴,讓S覺得,畢竟還是有情緒宣洩的空間。然而,在各類談話節目中陪伴了中國網友約20年的梁文道這次被全網下架,讓她既哀且怒:之前又何必給民眾那些放寬管控的幻象呢?
有小紅書的網友引用艾蜜莉.狄金孫的詩談這次節目下架的感受:
「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 /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 然而陽光已使我的荒涼 / 成為更新的荒涼」
「鬆緊由它」的結果,民心又一次翻騰。看起來終究會被當權者馴服,但那些無法被消化的能量,誰也說不準會以什麼形式、在什麼時候釋放。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