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14
潘愚非拿到了第一个冠军,想到前几天朋友给我发他自己写的一段想法被摘录进公众号,被隐去提及疫情的几句话。恭喜他,敬佩他,为这里感到不值得,因此更佩服他。
在朋友圈发了这些,其实很多已经都在这里讲过了,但一个一个字写完这些话,我还是感到自己十分幸运。我生命里最了解我的人,最了解我的品性我的成长轨迹我的虚荣我的脆弱的人,最亲近的人,最尊重我的选择把一切决定都交给我自己的人,也最懂得我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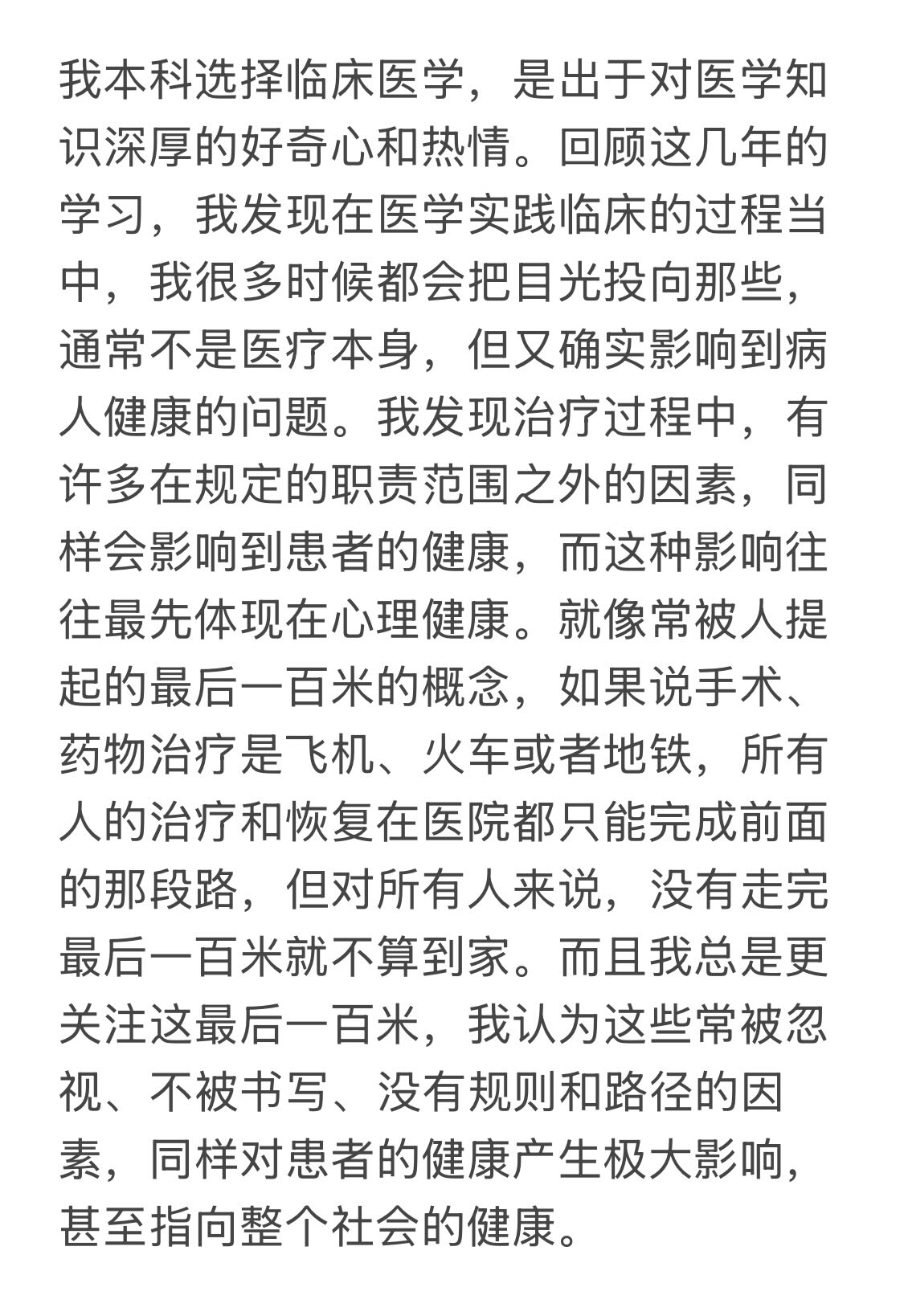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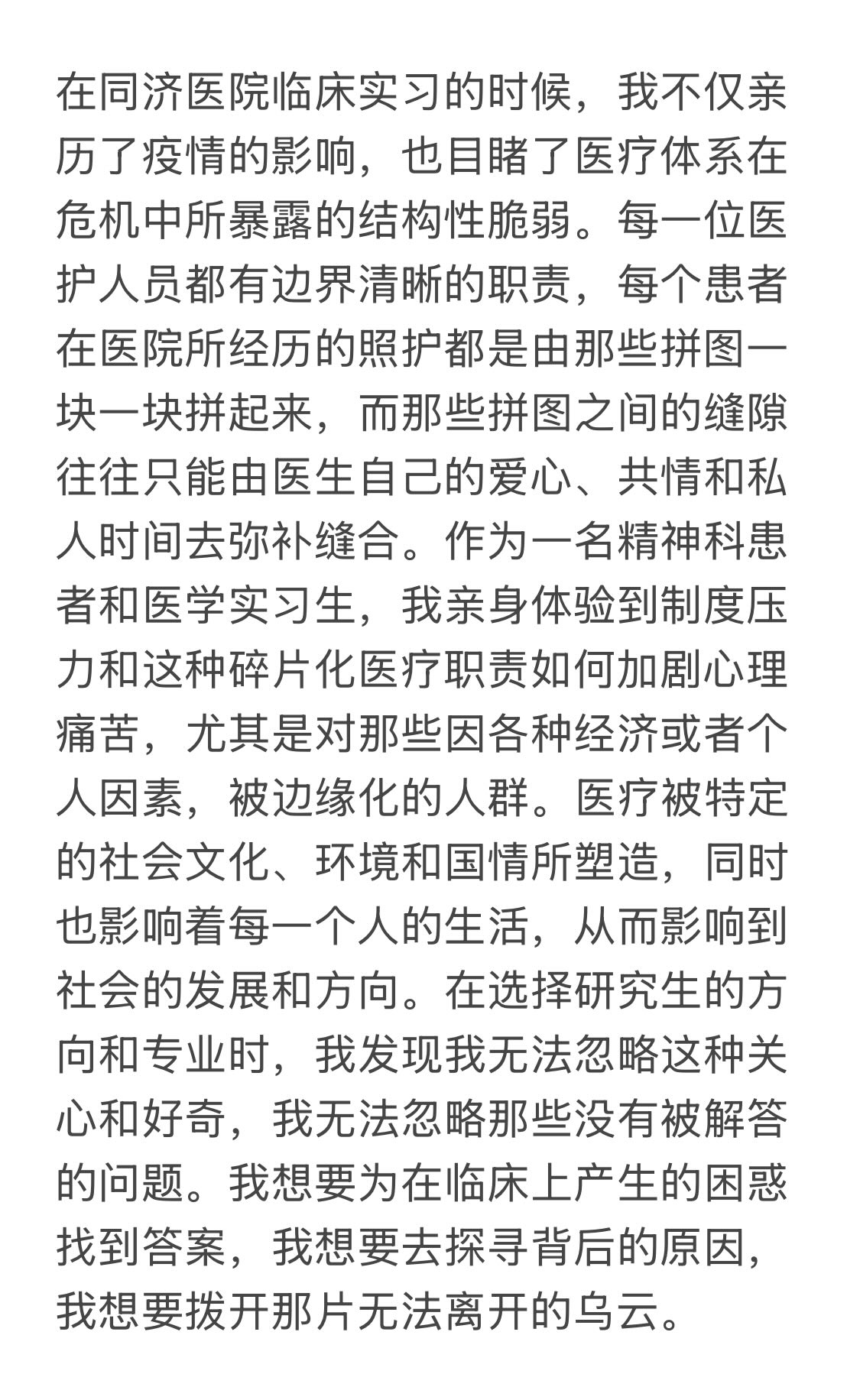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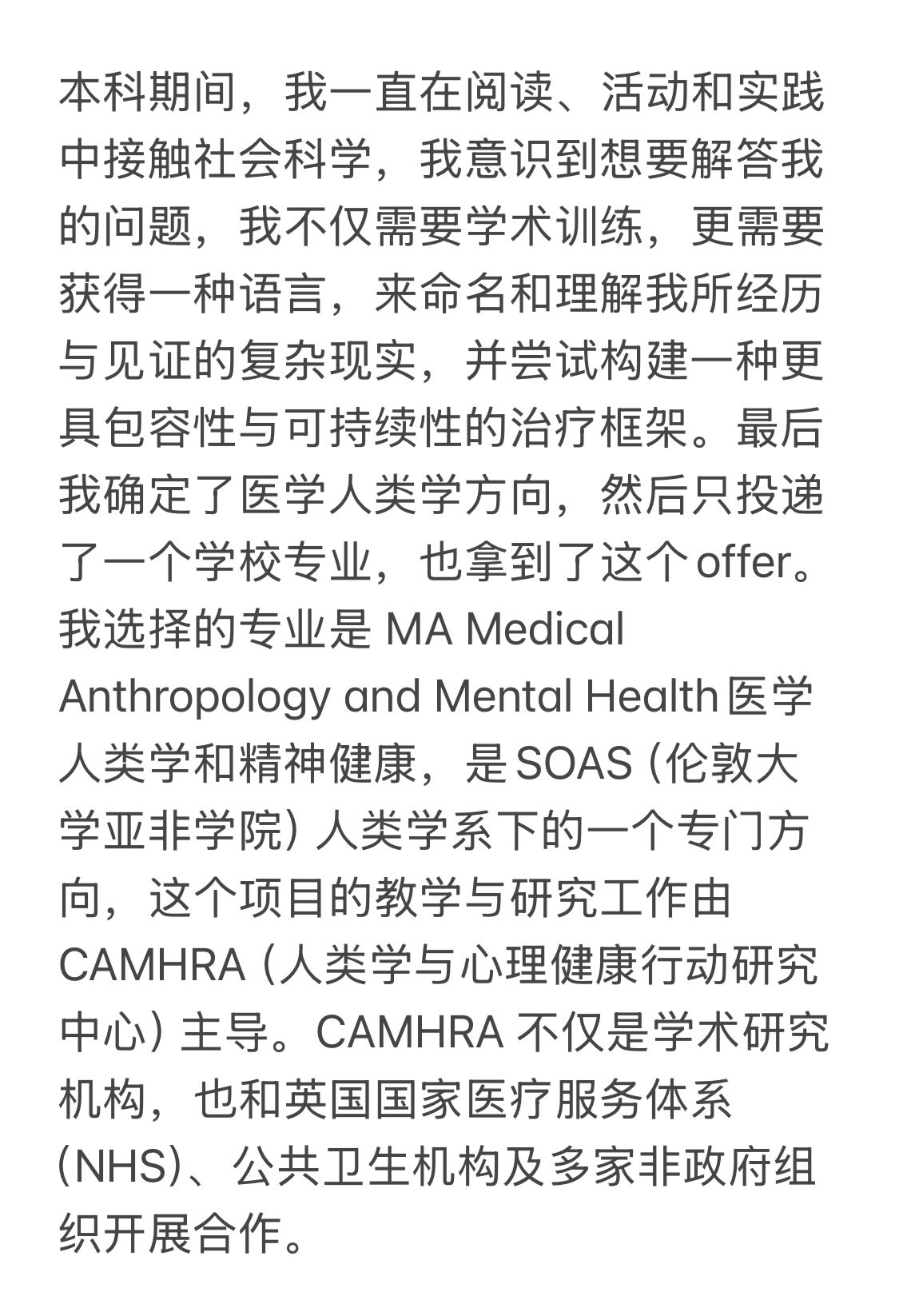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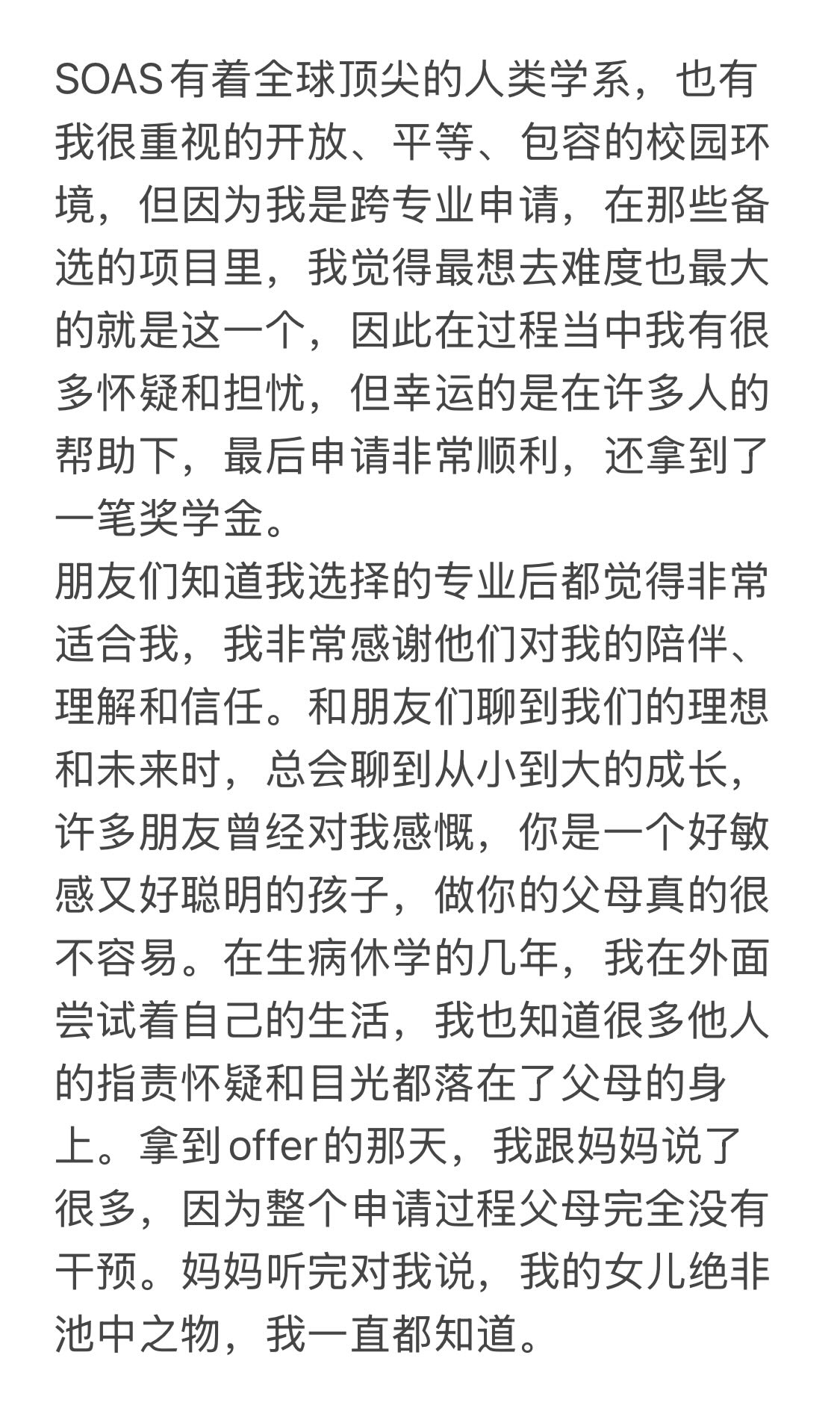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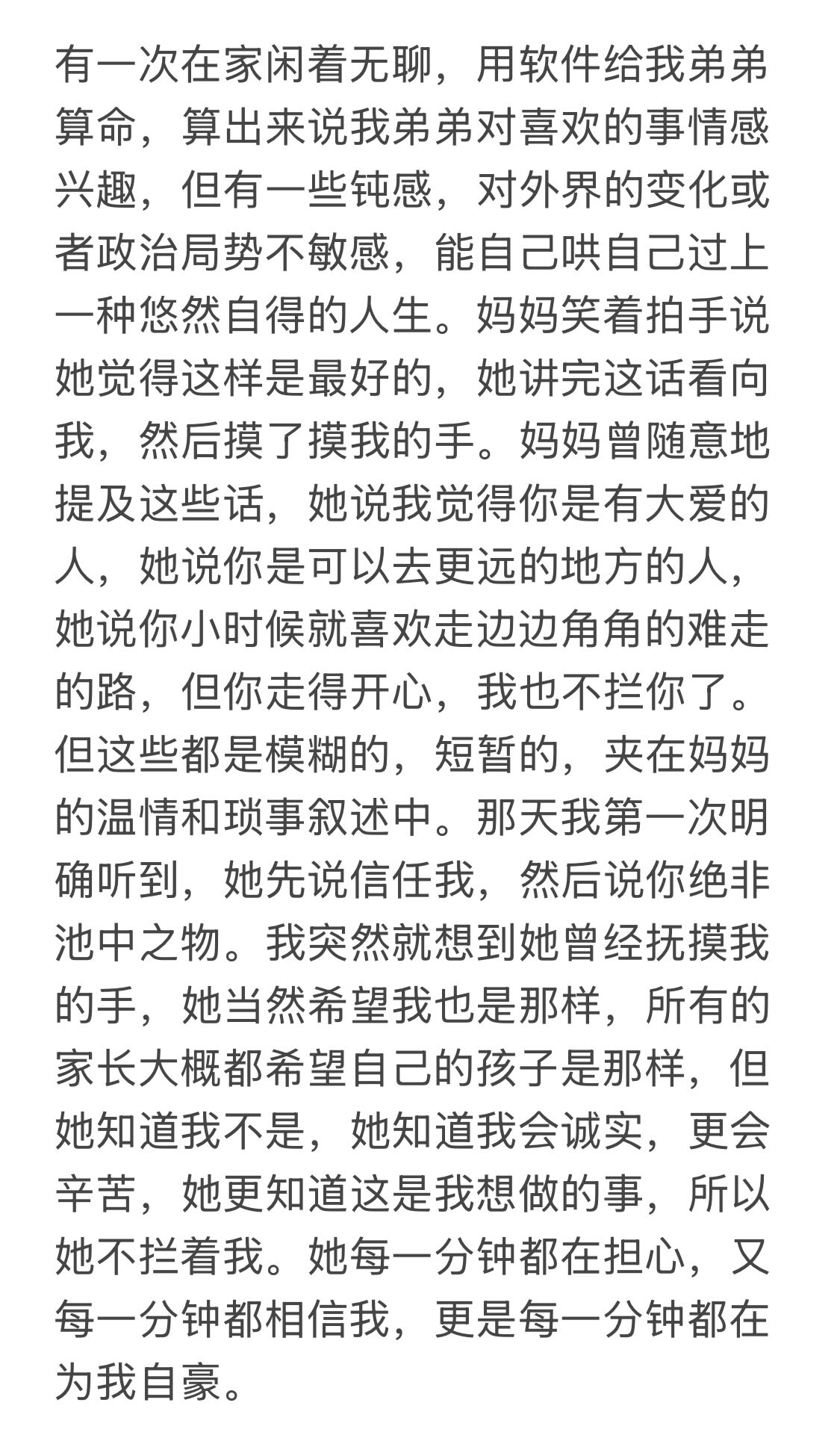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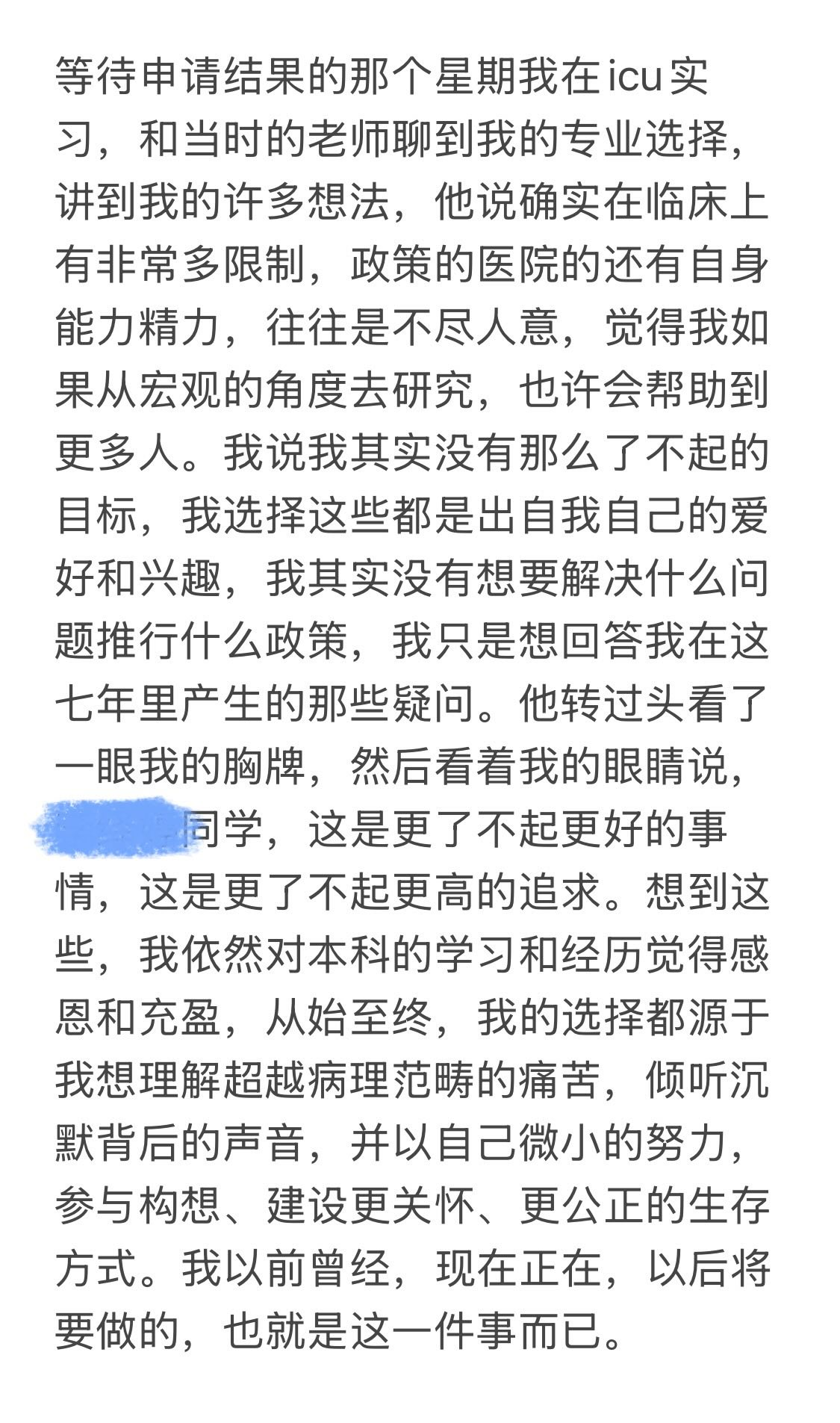
我真想笑,我上午发了那条朋友圈,下午我爹给我发小作文,本来很感动,晚上他又问我能不能评论朋友圈(我朋友圈不屏蔽任何人)我就知道他表演型人格大发作了,跑到下面把小作文复制粘贴过去,烦得我刚上ig story大骂一通,刚刚一看现在我家亲戚一个个在底下给我爹赛博敬酒,我真是一人一巴掌。
我真服了,我做啥准备了,我大学本科这么多年不管是做性别做性少数做社运做放映我都从来没想过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帮助我升学申请的资源,很多工作证明我都是申请的时候看项目觉得有点相关再回过头去开的,而且好几个ngo没法给我开,有两个是我做事情最多的,我做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书面上的证明可以帮助到我的申请。实际上我今年三月份才听说才了解SOAS,医学人类学我也是去年才接触到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我当然是在没有主动的情况下接触了很多相关的知识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我到三月份之前都没想过要转专业。难道我爹以为这几年着我顶着压力和质疑,处心积虑地做了一堆他们觉得没用的事情,只为申请这个专业这个学校的时候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于是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烦的就是我爸在小作文里对我妈的态度,明明我妈妈是什么都干的人,又工作又照顾家人又陪我住院又给我精神支持又给我钱,他就说一句“要感恩妈妈对你的照顾”然后大谈特谈自己如何相信我如何以我为骄傲(我不信)好像我妈就只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了我一下,其他的事情都是他做的,都仰赖他的栽培,实际上他有零点贡献,要是我妈亲戚在下面团建我都不会觉得这么无语。但一想起来我跟我妈姓我就又笑了,我和我妈其实都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但是最在乎这件事的人并没有在这件事上顺心如意,倾尽所有培养的孩子不仅是个女孩还不跟自己姓,什么感受我反正无从得知。我弟倒是跟他姓,但他爱人的能力太弱了,他现在已经没有耐心去从头培养去爱一个孩子了。他宁愿捡现成的头衔享受,哪怕有些许别扭和尴尬。不敢想我如果是个男的还跟他姓他会爽成什么样。
6.16
今天吃完晚饭回到家,径直打开电脑写文章,快零点的时候写完了,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只有词句的斟酌,没有思路的犹疑,把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的小标题落在屏幕上只觉得心安。写完之后感到充实和幸福,第一篇文章我准备了很久,也卡了很久,最后边哭边写出来的,当时想着如果以后写文章都要经历这么大的情绪波动我真写不了。第二篇是访谈,不太算自己写的文章,第三篇是越剧,写的时候也哭了几次,熬夜写了一整晚。到今天写第四篇文章,已经能控制得不影响正常生活节奏,全都想清楚了再开始。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越剧还是避孕药,都是我想过很久要写的议题,总有一种清库存的感觉,也担心我后面都清完了就没得写了,但今天的文章只是我最近的思考而已,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有从阅读、观影、生活、思考的积累里提炼出一篇文章的能力,我已经有这样丰富、活跃又敏捷的思维了。
我觉得翠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中难得的可以完全说真心话的地方,很多帖子我看到都觉得非常赤裸,写下那些文字的人几乎是呕吐的态度,因此我都觉得有些随意评价,甚至特别是那种空泛的安慰的人,像是在占便宜。占一种道德上的便宜。帖子背后的人都有自己真实的生活,但是好像因为这一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评论的人就轻巧地参与了那个人最深的秘密,最痛的心事。但有些事是不应该轻巧的。轻巧是一种怠慢,是一种回避,是一种错误。
想说这个话很久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微妙很难言说的东西,我一直是诚实的人,我在哪里都是说一样的话,翠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特别。但因此我也能辨认出,有哪些人是只在这里说真心话,有哪些人的真心话说得犹豫、磕绊、混乱,有哪些人在这里倾倒痛苦的时候都在撒谎,因此更觉得痛,更是只能沉默。
6.18
天天在心中暗暗求好姻缘其实感觉零个人能跟我谈。刚躺在床上回顾了一下昨晚到现在做了什么,昨天下午去攀岩,晚上和朋友去酒吧,在酒吧里学了一会,他们买了烧烤回来吃,吃完喝完回家洗澡睡觉。中午起床吃饭,回编辑消息,出门路上想文章修改,走去宿舍打包行李寄回家,陪朋友办手续然后一起去领毕业证,该打印的证件文件全部打印好扫描,把朋友送上车,打了五个电话问英文毕业证,跟爸妈聊天聊他们工作上的问题和压力,给我爸选新手机。回家吃晚饭,织帽子,去朋友家传照片,吃冰棍聊天,回来织帽子看电影,拿昨天设计好的织图织了一块织片,洗澡上床。而且我刚看完电影还觉得有非常多复杂的心绪急需跟人聊一下。谁跟我谈感觉能全身心被我耗得灯枯油尽。我每天高频词汇将是老公你说句话呀。
昨天去领毕业证,和朋友一起,领完等电梯的时候她靠在消防柜上,几乎就要哭出来。去年十月份,她跟我一起睡觉,半夜我情绪不好小声哭,她抱着我说这几年那么难我们都过来了,去了欧洲就是好日子了,我没忍住开始嚎啕大哭。走在学校里,她说大二的时候痛苦得在医学院这边一点都待不下去,跑到主校区上网课,给爸妈打电话,在路上毫无形象地尖叫嚎哭,爸妈也只是说你这点苦都吃不得。我突然想起来我高中也有这种时刻,高三的时候每天走在走廊上就只想跳下去,因为被班上同学说声音不好听/很喜欢哭不知道在装什么,所以每次都躲进厕所哭好了再出来。
当时有一天特别崩溃,跑到一楼用电话卡在电话机上给爸妈打电话,只记得妈妈说她可以请假带我出去住一段时间散心,但是要过几天她先安排好工作。最后过了几天我又觉得还能忍,也没请假,咬着牙读完高中,毕业完就把高中同学都删了只剩一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昨天朋友说她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当初我打的电话是我爸接的,我爸肯定说了什么,然后我要妈妈接电话,因为我妈当时在开车。但我完全想不起来我爸爸说了什么,应该是太伤人,所以我彻底忘了,只抓着妈妈给我的那点念想活着。
肯定特别恐怖,我爸肯定说了超级伤人的话,不然我现在不会什么都不记得。大一一整年我经常梦到考上了华科还是要在高中班上上课,就会哭着醒来,然后睁眼躺到天亮。大二还是大三有一次回家,我们家一起去吃饭,我弟弟三四岁还比较小喜欢乱跑,我把他一直拉着因为马上就到饭店了,我爸说你不要拉他他会以为你在跟他做游戏,就更想跑,我说到饭店了再放开,不然这在马路边上他容易被车撞,我爸说你讲话这么难听难怪高中被校园霸凌。当时我就完全大脑宕机只想站在那里哭。我至今不理解他怎么说得出那种话。
还有一次我爸我妈我弟弟来武汉玩,第二天我要回家打hpv九价,我爸说把我带回去,我说我要见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们可以先走,我明天自己回去,他不愿意。我朋友又临时被导师扣住,他们从下午五点等到晚上九点,我一直在说不用等我,我爸一直坚持,最后我和朋友坐在饭店准备吃饭,我爸打电话问你是不是精神病犯了,我当时才开始吃药不到一年,我就坐在饭店里抱着手机哭,哭得饭店老板都看不下去了过来骂我爸,我弟弟在那边直接把电话挂了然后对我爸说能不能别说话。
想起来这些事情我都觉得痛,我其实算不记仇的人,很多小事我都不计较都算了,而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往前看,和谁闹掰分手关系不好,我也会觉得只是不合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的距离,不要强求。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好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我不在不喜欢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如果不做朋友了一分钟都不会想都不会在乎都不会去关心,更不会花时间去视奸或者骂人。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对我爸,因为我没法像对其他人一样把他从我生活里踢走。我能接受他现在对我好,也可以不计较那些事情,但我从来都没有原谅他。他肯定也知道,所有事情我都先跟妈妈说,他后来也对妈妈说过好几次和我不亲热了,他给我写信也会注意写“我个人觉得”。他意识到我不会原谅他,我会永远让他记得。
他是爱你的,只是不会表达,只是方式不对,我再也听不进去一丁点这种话。我们都是人,都是有感受的,嘴笨可以用行动证明,面对领导上司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说话,面对女友就开始嘴笨了,不就是怠慢和轻视吗。感受不到就是没有。
现在和我爸妈的关系到比较平等的阶段,很多事情能沟通,看起来也很好,但随之而来的也是我需要分担他们的很多责任,我妈妈经常把她的所有焦虑都完全丢给我,我爸爸出轨的所有事情她都跟我讲。妈妈给我看过那个时间最长的阿姨的qq空间,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后来结婚了,生的也是女儿,取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字。她不是我爸爸的孩子,但那个阿姨在qq空间里甚至说过希望她是我爸爸的孩子,她说看到我爸爸发我的照片,看到对我的宠爱和自豪,她觉得难堪,觉得心如刀绞,觉得如果生的是他的孩子,会不会更在乎她。我想到这些,又想起来妈妈说曾经在大街上和她迎面碰上,我爸爸毫无波澜。我知道他是那样的人,他打扑克牌的时候从来都只看一次,起牌把每一张都收进手里,然后就合上手捏住不会再看了。他打麻将也是,出牌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靠手摸牌打牌,从来都是带一点点微笑的表情。妈妈说他那天的平静让她觉得可怕,觉得想吐,一段存续十多年的婚外情,毫无预兆的偶遇,他能这样一丁点反应都没有。
我也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承担非常多我父母的责任和情绪劳动,承担我弟弟的教育甚至是我自己的家长责任,到现在我已经熟练掌握课题分离,能非常迅速地意识到什么时候是在沟通问题,什么时候是在情绪宣泄,什么时候是他们试图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我身上,什么情绪我可以不接。我现在有一半的时间跟我爸妈沟通完之后都会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拿这件事来找我,我不会因为你们的投资失败而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觉得愧疚或者紧张,我该怎么花钱还是怎么花钱。
其实仔细想想我也觉得是男的的问题,我现在不主动尝试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被很多男的拿来当不负责任的借口,尤其是那种出轨的男的。而且我从过去的经历里意识到,如果男的不爱我,很容易不尊重我,又觉得自己有性同意权,就更容易伤害我。所以我现在并不是从概念上反对或者不理解性爱分离,只是对男的戒备心更上一层楼而已。我知道我需要非常浓烈的情感流动,而且往往男的是没法接受我们把彼此作为情感第一位,我却和其他人做爱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指向同一个人。大部分男的拿对女友的态度来都满足不了我的情感需求,就更不用说拿对炮友甚至是对小三的态度了,我也不可能接受自己处于次要的位置。我太骄傲了。所有的这些讨论和分类都仅限于和直男的恋爱关系,因为我和朋友的亲密关系是非常复杂多变又流动的。
6.20
下雨天不想出门躺在床上听野花流泪,昨天跟k聊天也说到,可能因为家庭沟通、培养和责任转移,我们都是很擅长课题分离和情绪解离的人,很多时候碰到重大突发事件看起来情绪稳定是一种无情和冷漠,大多数事情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是别人自己需要处理的问题,因此我反应会很淡,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现在想到之间的恋人,那些不再联系的恋人,对于所有关系我都没有觉得要老死不相往来,恨意和愤怒也是太累的情绪,我更倾向于继续做淡淡的朋友,但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做朋友都是不应该的选项,我最想说的其实是请忘记我。
6.21
大半夜听汉密尔顿听得又振奋又想流泪,因为喜欢这部音乐剧而去读美国建国史,最后被麦迪逊折服,在一页页史料中不断寻求着,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活。美国建国史真的太动人、太理想主义、太波澜壮阔。
最近的学习和观察让我意识到很多人的思考都是前人思考过的,包括threads上看到的一些思考其实都可以被涵括进某种经典社科理论。不是说没有思考的必要,而是我发现社科思考也有跟数学一样的路径,就像数学从一加一等于二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学到线性代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社科也有类似的路径,而是思考到一个阶段就停止了,这就像数学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就不学了,然后就一直解各种各样的二元一次方程,实际上零进步。感觉很多人到二十五岁之后就用剩下的五十年解无穷无尽个二元一次方程,因为都解出来了所以觉得自己这一套很管用,不仅是没有继续学习,甚至意识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复杂更奇妙更迷人且可以被思考被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得进步,只是我既然想走学术道路,就有了一种紧迫感,我就意识到大多数人如果纯靠自己的思考和阅读也就走到这里,想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得学习,就像数学一样继续学习,要把前人的基础研究全部学完才有资格去拓展知识新的边界,到那个时候的思考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
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时间很紧张啊!我还要学那么多社科的基础知识,得至少学完基本的发展和框架,才能展开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我现在的思考当然也是好的是我自己的,却是千千万万人都思考过的,是我的同学可能在大一大二就研究过的,那些问题看起来和我的生活非常相关,其实都有人类的共通性,因此大家都有在思考。这条路就是这样,谁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谁就走得越快,就更有可能触及到边界,就更有可能成为那个开拓一点点新的疆域的人。我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才或者特别,我当然有自己的背景和天赋,但我的这些不同只有在我走到最前面,当我有资格选择我的方向的时候,才能make a difference,在那之前我和所有人都应该学一样的知识,爬同一座塔,登同一座山。我的旅程是独一无二的,但又是人人都有的。现在真是汉密尔顿了,why do you write like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不想在乎任何其他事情,可以放弃所有应该放弃的,History has its eyes on me。
这段话是1787年制宪会议结束后富兰克林说的,沉浸读美国史的那段时间建了一个豆列,听过这段话很多次,一直觉得那把椅子会是非常宏丽非常夸张的王座,第一次看到图片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甚至看不出来椅子上刻的太阳在哪里。当时盯着这张图笑了一会,意识到文字、历史、精神意志的力量伟大,意识到权力、物质的短暂,更是感受到那么多年前,富兰克林对着这样一把普通的椅子发出如此的感慨,是出于一种多么激动、复杂、沉静又自信的心情,那是多么风谲云诡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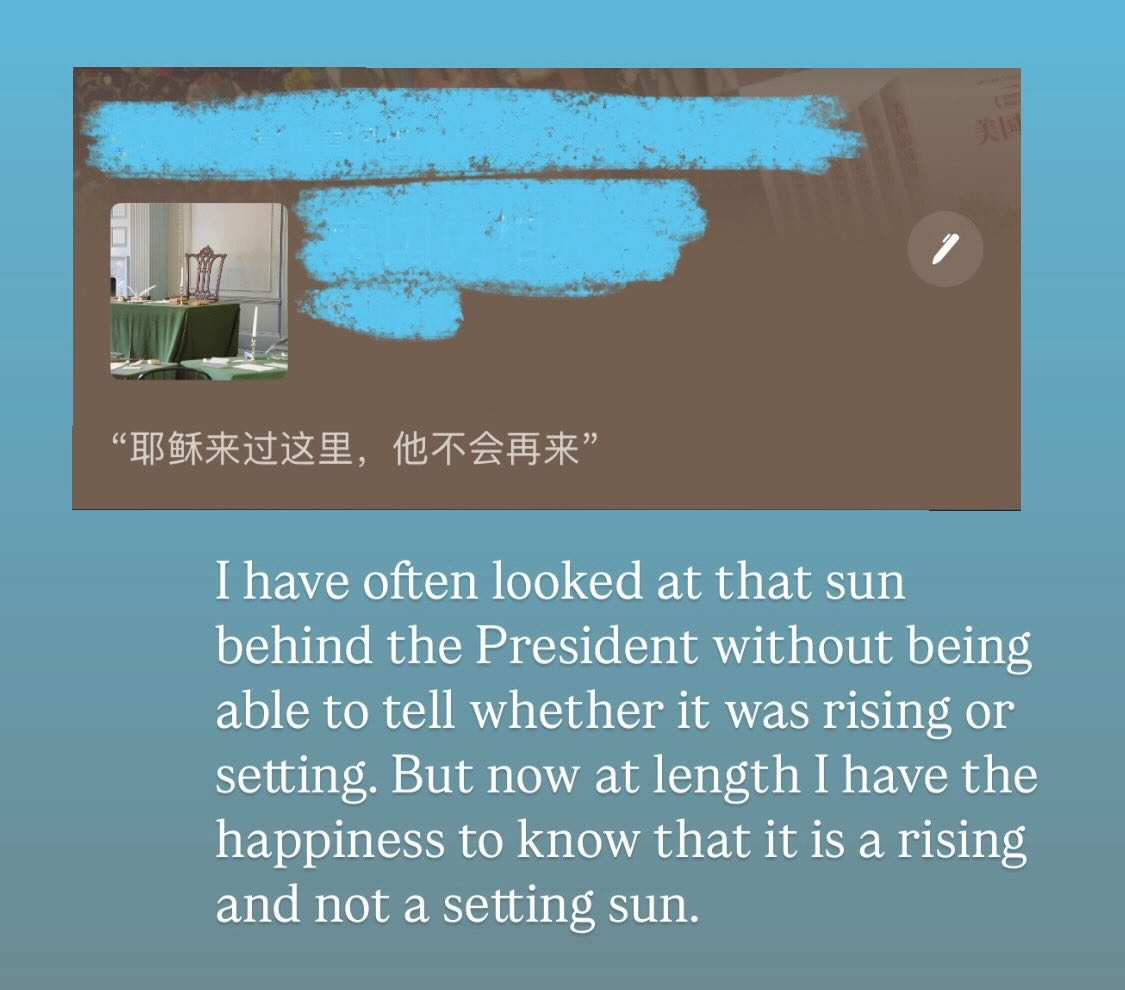
富兰克林的话不仅是对国家的判断,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所投注的道德政治努力的一种确认,而那把椅子的朴素反而是这份信仰的证据。哎天呐,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时刻。
每次在翠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感想都能收获很多有启发的讨论,真的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就像id一样,我一直把这个账号连同我自己视为一条小小的河流,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成为河流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属于我也不再属于任何人。或许有人会喜欢这条小河的某处急弯或缓流,会因为一掬水而感激而喜欢我,也或许会被某段湍流打湿衣衫而选择离开,但无论是怎样,我都觉得很好。当我书写时,我还是会尽力保持最原初的想法,不去考虑、预设这段文字顺流而下会引起如何的风浪,因此更感谢愿意和我讨论的大家。我非常喜欢论语里的一句话,朋友数斯疏矣,让我们像水一样相遇,像树一样坚定,像风一样别离。
朋友一聊父母就特别文采斐然,聊伤痛聊爱恨交织聊理想信念聊矛盾冲突,每次听到她精妙又随意的修辞都想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人生真是漏洞百出,刚刚热了两个面包,等面包的时候拆下昨天晚上给朋友织的织片,定型很完美,边吃面包边点开微信想告诉他,还在心里想今天又做了很多事情很满意,一点开微信发现一不小心又鸽了教练。呵呵,灰头土脸赶紧吃完,收拾收拾去岩馆下跪了。收拾东西的时候还打翻了栀子花,泼了一椅子水,又手忙脚乱收拾一番^^
6.22
我觉得性别这一块断代真的很严重,学术上我不是特别清楚,虽然有认识朋友在读魏伟的研究生,但我也不敢在微信上问这些,从公共场域来说更是这样,我时常对互联网的性别讨论感到乏力,因为我真的觉得有非常多成果没有保存下来,没有得到延续和继续,大家都是靠着一种热情和自觉在参与这个话题,这当然是好的有总比没有好,但感觉就没怎么继续了,永远都在很浅显的议题上翻滚。
想起来傲骨贤妻有一集Alicia在节目里碰到Gloria Steinem,她一转过来我就知道是谁,跟Alicia一起激动,后面Alicia一直幻想她跟自己说话,我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概念,我当时就想美国观众也知道吧,他们肯定也知道Gloria是谁吧,也会理解这种剧情安排吧,那我们呢,都不说普通人了,现在做女权的或者说对女权有兴趣的人知道我们国家曾经有哪些人在做女权吗,知道谁推动了反家暴法吗,完全不让说也不让大众知道,想到我都很难过。
又想到一个好笑的,前一阵子跟人聊天,对方不知道那些以前中国做女权社运或者研究的人,但是知道一个很新的很先锋的教授(教授人在国外),仔细一问原来是因为教授有小红书账号,当然也没有发什么特别敏感的东西,不过她的政治理念肯定是不符合主流要求的。就想到我之前去给中学生做性教育,校长把我ppt里所有涉及性侵和自慰的内容都删掉,反而对社会性别概念、叶永志这种觉得无所谓,就是有时候这个结构体系太过传统刻板,以至于偶尔碰到特别先锋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人家在说什么,所以反而不审核了。
6.24
刚刚看到有个学弟给我朋友圈点赞,想起来是去年年底一个志愿活动认识的,那天下午坐着晒太阳我教他打了一会毛线,他和他女朋友都很可爱,一起组了乐队,两个人都会弹琴但女孩子当了键盘所以男孩子做鼓手,都是我们学校挺好的专业,看起来也保研到本校了,想起来前几天跟一个本校那个专业、一起攀岩的朋友聊天,说他博导纯工资一年一千万,当时还感叹这个学院真有钱。看他们朋友圈里去橘子洲头打卡,去上海演出,喜欢看哪吒也喜欢看好东西,养了一只猫,觉得他们好幸福,未来好光明,又好复杂。为什么我不能那样,为什么我不能接受那样的生活,一起晒太阳拼小积木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到底哪里就和他们不一样,到底哪里不满足。只能想起来林忆莲的歌词,烦恼多因我要得多。我想要生活在一个可以谈论政治不会因言获罪的国家,想要生活在一个迷奸十几个人的人能被定罪的国家,想要生活在一个能去电影院看想看的电影的国家,我只是想以人的身份活着而已。
我时常能从汉语以及其他许多细节察觉到我对这片土地的依恋和热爱,明明该死的另有其人,为了活下去出走的却是我。靠近中国就靠近了痛苦,远离中国就远离了幸福。
我有时候是期望人离开我,因为我更害怕他们留下是出于惯性而不是选择,所以有人离开我的时候,我就会在他身上看到一种主动性,从而觉得好。我有时候还能感受到,有一部分人离开我不是因为不喜欢我,而是因为难以忍受某种情感厚度。我也会珍惜这样的离开,我觉得这种离开比靠近更爱我,也更尊重他自己。不是我不重要,而是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时常做出这种选择伤害到人,我会很难受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因此当我被这样选择被这样放弃,我反而会松了一口气,自己难受是一回事,替对方开心是另外一回事,我也知道我们的关系对他来说不好,我是贪恋着某些好处才没有主动离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于每次都坚定选择我的人拥有更高的信心和更诚挚更深厚的爱。我知道他们爱我不只是因为惯性。
6.25
大部分时候想起离开我的人,都希望他们过得很好,不然真的对不起分离的痛和不舍,如果现在过得还不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你离开我是为什么。对方就算知道会痛苦知道要付出什么,知道生活可能更糟,还是要离开我,会更让我觉得挫败。你为了更好的更稳妥更现实的东西放弃我,我接受,你费尽一切不计代价也要离开我,我无法接受。马上就能意识到这种想法太自我中心了,他离开我可能并不是有更好的东西或者更好的选项,也可能并不是有什么鲜明的目的,只是单纯不想继续和我的这段关系,只是不在乎,我对其他人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我还是控制不住那样想。
回想我的感情经历,我觉得每一段都是彼此很在乎的,但最后都有一个人先放弃了。可能因为我态度一向比较决绝,也很诚实,所以没有那种发现自己被欺骗很久的剧情,但有好几次对方一开始就向我坦诚可能最近有喜欢上别人的情况。分手也不是拖到有谁受不了,基本上都是聊天聊很久然后觉得确实继续不了。所以我想起前任都是觉得,我们放弃了那么好那么幸福的东西,你最好是做了对的选择。说了半天本质就是我是一个把自己的自尊看得最高的人,所以我觉得被欺骗是被轻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行为,就好像根本不相信我有处理面对问题的能力。现在想来前任们也是对我都很坦诚。但其实我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有时候对方不跟我说也不是因为轻视我,就是因为觉得没必要跟我说、懒得说。
烧了一天刚迷迷糊糊在抽屉里找药,翻出来一些小东西又开始难受,我每次喜欢人的时候就爱做特别多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其实对朋友也是这样,总之就是喜欢画点什么写点什么织点什么,关系破裂之后我不想扔也不想转送别人,总感觉很糟践自己当时的心意,所以就这样放着。刚刚翻出来真的停了几秒钟,简直像年初在从来没开过的信箱拿到已经闹掰的朋友的明信片。真的很抱歉我没做到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爱人,也希望他们离开我后有更好一些。
6.26
前段时间写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戏剧,越剧和莎剧还有音乐剧,和近一年认识的朋友聊到文章,他们有点诧异我居然这么喜欢戏剧、看过这么多,可能因为中国(武汉)这方面比较匮乏所以我很少看现场吧。在文章里写了很多分析和想法,但实际上一开始想去看那些剧并不是因为这些,大概也都出于歌好听、故事熟悉、有喜欢的演员这些原因。想到我曾经很执拗,会很抗拒有人夸我漂亮或者其他的,会觉得如果因为这个喜欢我、注意到我就不是真的了解我,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就像我喜欢那些戏剧一样,总有或大或小或高明或俗气的契机,可能并不具备崇高的动机或者要彻底认知的决心,但那并不影响我之后的感情,也不会让感情变得更值得或更无趣,过程本身就可以不断整合、生发出新的意义。
6.27
朋友在路边看到一只垂死的蝴蝶,觉得很漂亮,拍照给我说要是你在就能做成标本了,我看了一眼是青凤蝶。虽然我不会这样做,但也碰到过类似的委托,有一个网友家里飞进一只青凤蝶,在她手上停留,她觉得特别有灵性(其实蝴蝶就是喜欢停在潮湿的地方,可能手上有汗),喂了好几天,想着等它死了寄给我做成标本,每天都会给我拍视频看青凤蝶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到第四天死了,寄到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干燥好腹部已经有点腐烂,我只能挖空,最后做好了标本给她寄回去,在相框里铺了一些假青苔,尽可能让蝴蝶是舒展的姿态。
见面真的很重要,生活里有一些人有时候太久没见,再约好见面的时候会回想起很多事情,偶尔想起的只言片语或许因为隔了太久、失去上下语境而变得悬浮又暧昧,再加上混混沌沌梦的加工,醒来突然觉得,我是不是一直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什么可能性,会不会在此中一直存续着某种爱意,所有这些小心思在见面三句话之后都会完全被打消,两个人只是面对面笑得特别澄澈,那个时候一边想的是果然我们就是朋友,另一边也意识到那些见面就能确认依旧喜欢对方、有吸引力有冲动的瞬间是多么美好,多么不可得,多么无法强求。
以前碰到“性别问题在阶级问题面前不值一提”这种观点,我通常都会举一些跨阶级的性别问题来佐证,对方当然就会举一些跨性别的阶级问题,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我现在就是觉得,明明这二者都同时存在,为什么要剥离出来比较?这种剥离本身就脱离了现实。我认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确实应该被用来在学术领域做提炼和研究,是一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面对庞杂复杂的现实时让研究更清晰的工具,但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讨论中完全依赖这种理论,就会导致二级化。我们不否认分类工具的必要,但我们(至少是我本人)拒绝将复杂现实简化为非此即彼的结构,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能存在一种压迫,也不是某种压迫就更重要影响力更大,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种和平讨论的氛围,更需要一种能容纳交错结构的描述方式。如果理想类型是一种在研究问题时必要的暴力简化工具,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发展出复杂性识别工具(例如交叉性理论)因为交叉性本就不是简单地加总因素,而是要研究这些因素如何构成对方的社会效应。我们的洞察力不应该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
在你举的这个例子中, 我们假设在抽象层面上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相互作用是有一个清晰的结构的, 但是由于人的局限性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这个结构在某一侧面的投影, 所以有的人看到的是一个问题主导另一的问题, 有的人则看到相反的作用.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你提到的交叉性理论,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通过引入更多的隐变量 (如种族、社会阶层、性取向、宗教、能力 etc.) , 然后去观察我们想研究的结构, 在以这些隐变量为坐标轴组成的超平面上的投影所表现出的形式, 从而试图给出对真实结构的一个更加准确的估计. 但是我很好奇你们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研究数据来保证最后得到的结论的普适性呢? (从数学的直觉上来看为了保证估计的准确性, 添加额外的变量就意味着需要成倍的数据, 在你这个topic中可能就是成倍的社会事件/经历的例子) 我感觉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交叉性理论本质就不是在拟合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结构,而是反对任何将社会经验过度抽象、可加总地理解的模型。它强调的是人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同时承受多重权力关系的作用,这些作用并不一定可以投影到一个理性可计算的空间中。这不是隐变量的投影问题,而是范畴本身的动态重构问题。所以交叉性并不应该被理解为“引入更多变量来让拟合更精准的模型”。在方法论上,它也并不依赖大规模数据来建构普适模型。相反,它很多时候强调的是经验中的不可比性、不对称性和权力性,因此更多采用质性研究或反思性的量化方法。以及我觉得你的质疑逻辑是非常数学性的,但这背后有一些更知识政治的问题:谁有资格对社会经验进行建模?谁有资格去定义知识的科学边界?数学式推理被赋予何种权威?
方法论上,交叉性研究确实面临你所说的困难:它拒绝简化,却又必须在经验中寻找可表述的路径。在数据分析中,变量的维度确实会带来指数级的复杂性,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也必须面对个体经验的不可归纳性和比较障碍。所以我认同你所指出的难度,交叉性理论的确要求我们面对复杂而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依赖抽象简化来换取清晰的图像。但这也正是它的伦理要求所在。直到现在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在努力尝试开发不牺牲复杂性又能保证分析性的工具和语言,除了intersectionality 还有中观社会理论(meso-level theory)比如福柯对话语和规训的分析,以及thick description这种概念。
我之前写过自己的反思,自己最后选择医学人类学这个方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现代医疗体系在官僚主义的架构下,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和职责规范,但也造成了个人照护、康复过程中的缝隙,每个患者的医疗都是由这些拼图所拼起来,那去弥合这些缝隙就成了医护人员的份外之事。今天学习Weber的理论之后我突然对这方面有了新的思考。我突然意识到有很多事情,很多小的细节,问题并不在于医护人员做了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在于他没有做什么份外之事。例如患者可能会花钱找关系要帮忙多关注一下,可能有直接认识的熟人,可能跟医生是老乡所以会得到更多关照,可能长得好看有个人魅力,甚至可能长得像医生的亲人(同种族等等),是因为有了这些非常私人的、专业职责以外的驱动力,健康的医患关系更容易建立,职责以外的努力就会有差异,它们就决定了照护的边界能不能延伸。这也就引出我的新的质疑,如果制度本身不能承载感情,而个人又不可能摈弃感情,那么感情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一种新的特权。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就是更容易得到医生超出制度范围规定的照护,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就只能得到冰冷的标准化的服务。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里,这种标准化的医疗服务通常是not enough,因此只有在某些方面有实际特权(例如有钱有关系)或者有我提到的这种隐形特权的人才能获得enough的照护。而那些被制度冷落的人并不是获得明确拒绝,而是在各个小的环节上遭到冷落和拖延。
所以我认为,医疗体系的问题在种族、性别、阶级各个方面都有体现,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医疗系统本身,在于标准化的医疗照护是not enough的,现代医疗系统强调流程、指南、成本效益比、证据等级,这些构成了一种以疾病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系统中,医生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构建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去给医护人员做去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课程有意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是在主动歧视谁,只是没有“更关照”谁。这些课程无法回应照护的结构性分配不均,它只是让医生学会更谨慎,却不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空间、制度授权去关照每一个人。例如我在同济实习这么长时间,我确实是没有遇到种族歧视问题,在临床上的性别歧视也不太常见(你要说生活上言语上对我的那肯定有,但因为患者是女性而区别对待很少,要说到公共卫生那个层面的跟一线临床关系也不大了)最常见的就是家里有没有关系,就是有没有被优待,以及其他的因素影响主治医生的态度,比如患者年纪很轻、很好说话人很开朗等等,这些会让医生产生感情从而更多关照的因素,在某些时候就会影响治疗效果。
我的想法是有两种层面,一方面是提升医疗系统的能力,让基础照护真正覆盖所有关键需要,无需依赖额外情感劳动或个体超额付出,标准化流程照护也是enough。这个的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的定义和对照护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医疗水平提高后,人的要求也提高了,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not enough。第二层就是引入差异性照护,承认不同患者的社会位置与脆弱性,引入制度层面的再分配机制与照护弹性,引入第三方的调节和中介。但正如所有其他差异性政策必须面对的悖论,补偿机制在没有结构性控制的前提下,极易被特权化和工具化。本应帮助底层的渠道,很容易被中产或上层精准捕捉,转化为继承优势。
6.28
学习社科理论之后我才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来只是马克思的理论视角之一,但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却往往把它当作默认的真理。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是客观自然的,而是深受文化与制度灌输所塑形的。而我葡萄牙的朋友在谈论税收和经济正义时,常常以“最合理”“最公平”作为论据,主张高收入者不应被额外征税,因为他们“本事大”,政府不该干预。他坚信市场机制天然公平,政府干预是不正义的。但我现在逐渐意识到,他所说的“合理”,并不比我更理性,只是他的理性是来自于另一套文化。我们的分歧其实并不是意见不同,而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本身不同。他的合理性来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背景,而我从小接触的是结构决定论与集体主义。这让我理解到,任何一种“理性”都是被文化、位置、历史所赋形的,而不是悬浮于社会之外的纯逻辑。这种意识的转变也让我开始从讨论中退后一步,去分析我们各自的理论前提,而不是急于争论谁对谁错。可能社会科学真正的价值,正是在于揭示看起来合理的背后,有多少东西其实是被习得的。
聊到这些我就突然想起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在长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当着他父母面说我觉得你没把自己教育好,争执到某些问题他妈妈小声对我说I didn’t raise him this way I’m sorry,晚饭之后我们还是能一起去散步,开车去喝酒或者只是在海边抽烟,聊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在某些瞬间,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现在所分析出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他肯定是失望也有恨意的,甚至觉得如果他一直是那样的政治态度,他难道一直都在骗我。在那种时候,我曾经笃信的友谊基础是互相理解、达成共识,这种基础破裂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保持着一种和平的关系。好像在那之外,还有某些东西牵引着我们,或许是他们家人作为host的礼节,或许是对我的尊重,或许是曾经累积的感情,或许是一种惯性,我也没法表达清楚,可能是一种接近于social cohesion的概念。我突然就体会到Durkheim所描述的这种概念,在个人意志和情感破碎、被挑战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支撑我们继续,到成长之后、恢复包容心之后、淡忘之后的今天。
今天朋友写完文章发给我,我读得热泪盈眶。无法言说的那些情感和涌动。
6.29
我真是觉得经历了很奇异的几个小时。昨天下午被朋友叫出门唱歌,我下午四点才出门,六点唱完并在ktv吃了卤肉饭,我异想天开拉着一个朋友陪我去射箭,她觉得很好玩并约定后天又去。晚上去她们学校喝酒,在画室乱七八糟兑了一桶,结果一算只有五度毫无酒味。于是我们又分头出发各自买酒,有人拎来一瓶生命之水往里面倒了四百毫升,开始喝。喝到十一点半两个朋友提前走了,剩下四个人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喝多了一直趴着,剩下三个人精心讨论后我们又决定去ktv。此时我们还没有发现不对劲,但是想着先送这个喝得有点多的朋友回宿舍。结果这个朋友一直不肯站起来,也不让我们碰她,只说给她漱口,最后把一壶水都给漱完了。凌晨一点半我们收拾好画室打算把她扛走的时候,艺术学院老师突然来了。老师先是对我们的存在表示诧异(不认识任何人)然后问喝了什么,我们说兑的酒,结果他就看到了生命之水,大叫怎么九十六度!然后他掏出打火机拧开瓶盖倒出来一杯把酒点燃了,他指着火焰说这怎么能喝?!我们说真不是喝的这个。他转悠半天,突然知道我的学校专业之后就拍拍我放心走了。但临走之前还是嘀咕了一句那你怎么染黄头发!
然后我们扛着她下楼,凌晨两点在楼下又碰到一个老师,老师给我们撑着门说怎么了,我们说喝多了,老师说哈哈哈人生能有几多愁!然后扬长而去。我们打到了车,把她扛到了校门口,我不是本校学生所以我先翻出校门,结果发现校门外还拉了一人高的围栏,我们和司机隔栏对望面面相觑,只能大声抱歉取消订单。然后又扛到另一个门,打车去了医院。到医院她又吐了一点,但是卤肉饭是棕色的,吐出来医生护士很慌张担心消化道出血,直接安排住院了。四个人回去了一个,我和另一个继续留着守住,给医生讲大病历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失恋不到三四天。三四点我和朋友饿了,点了外卖,我点的时候也没仔细,送来发现我点了一碗蛋酒。朋友说你他吗怎么还点酒,你让等会护士来了怎么想,我说真不好意思,最后东西全吃完了那碗蛋酒也没敢揭开。我等她血常规结果出来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就打车回家了。下车后在楼下看到了织女和天津四,牛郎星被楼挡住了。离开医院前朋友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小河对不起后天我不去射箭了,我好累我干完导师的活就回家。
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