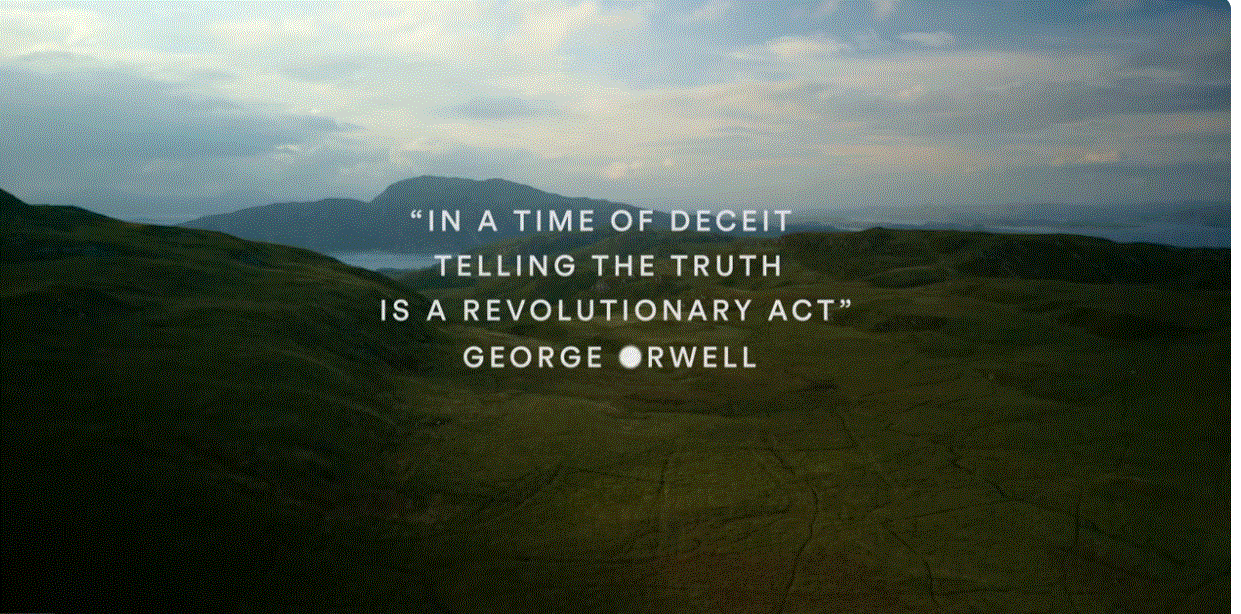2+2=?-《Orwell: 2+2=5》44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的時代回聲
在一個被高速資訊與演算法節奏裹挾的時代,我們似乎已失去了「停下來思考」的能力。科技讓一切變得更快,卻也讓真理變得更輕——人們根據自己「看到的」與「聽到的」,在社交媒體的回聲裡各自為陣。人人都以「捍衛真理」之名發聲,卻鮮少追問:那究竟是誰的真理?
紀錄片《Orwell: 2+2=5》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出現。它以近乎令人窒息的影像節奏,讓「真理」重新變得沉重。片長119分鐘,像一面突如其來的鏡子,逼人凝視那個被速度與情緒吞噬的世界——當「2+2=?」成了一道必須被解釋的算式,我們或許早已踏入奧威爾警告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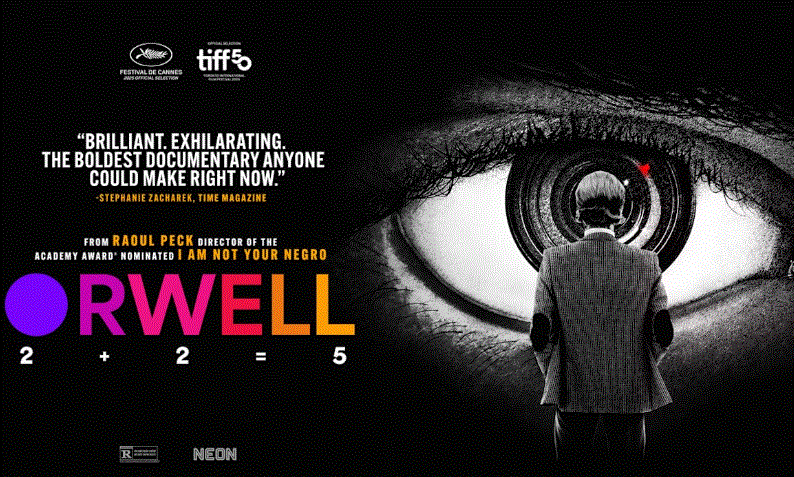
感謝第44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這個平台,讓我有幸在秋意漸濃的夜晚,於溫哥華靜靜地細品這場視覺與思想的震顫。

George Orwell 奧威爾:真理守夜人的誕生
一部作品的誕生,總與作者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若要理解這部紀錄片,就必須回望喬治‧奧威爾的生命軌跡與《一九八四》的誕生。
奧威爾,這位被譽為「真理的守夜人」的作家,並非生來反叛;他的覺醒,是痛苦與矛盾的累積。1903年,他出生於英屬印度比哈爾邦的中下層殖民官僚家庭。Eric Blair 是他的本名。George Orwell 這個筆名是他在 1933 年出版第一本書《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倫敦落魄記》)時首次使用。他的父親Richard Blair是殖民地的公務員,性格保守、循規蹈矩,信奉秩序與帝國榮耀,卻缺乏情感表達。奧威爾形容他是「一個冷漠、屬於陳舊世界的殘影」。這種缺乏溫度的父子關係,使他自幼對「制度化權威」產生排斥。


母親Ida Blair 出身於自由且文化氣息濃厚的法裔商人家庭。她聰慧、有思想、具文學氣質,鼓勵兒子閱讀與寫作,是奧威爾早期的啟蒙者。然而她也有強烈的「體面焦慮」,為此她希望兒子能藉教育進入上層社會,於是就將他送入帝國特權的象徵得伊頓公學。正是在那種秩序井然的特權教育中,奧威爾第一次感受到了「權威的虛偽」:掌權者的話語被視為真理,而個人的思考被視為越界。這種早期的疏離,成了他一生的主題——權力如何塑造真理。

大學未畢業,他就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親眼目睹了帝國以「文明之名」行暴。那種既是壓迫者、又被體系奴役的雙重身份,使他對權力結構產生終生的不信任。

返英後,他深入底層——在巴黎洗碗、在倫敦流浪、在煤礦區採訪工人。貧窮讓他更清楚地看到:社會的不公不僅來自體制,更來自人們對謊言的習慣與沉默。
1936年,奧威爾奔赴西班牙內戰,懷著理想主義加入了反法西斯陣線,卻親歷左翼陣營內部的清洗與背叛。那是他信仰崩塌的時刻——他意識到,極權的種子並非只存在於敵方,也潛伏在任何自稱「正義」的體制之中。這段經歷後來成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核心,並深刻塑造了他後來的兩部寓言傑作:《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誕生於他生命的盡頭。那時他身患肺結核,獨居蘇格蘭Jura島,冒著病痛完成了這部對未來的警告。他在書中創造了「老大哥」、「真理部」、「思想警察」與「新話(Newspeak)」等概念,描繪出一個語言與現實被徹底篡改的世界。書中的主人公溫斯頓被迫承認「2+2=5」,正是奧威爾親眼見證的政治現實極端化:當權力被定義為真理時,邏輯與理性便一同死去。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出版半年後病逝,年僅46歲。正如紀錄片所揭示的那樣——他寫的不是未來,而是我們的現在。

导演Raoul Peck的鏡頭語言:真理的脆弱與被操控
导演Raoul Peck 是當代最具政治意識與思想深度的導演之一。
他出生於海地,早期的創作多為紀錄片,多關注於殖民歷史、貧困、政治暴力與非洲的權力結構。Peck 不僅是導演,還曾擔任海地文化部部長(1996–1997),並多次於聯合國發表演講。他的身份橫跨政治、學術與藝術。
他的電影充滿強烈的歷史反思與道德張力,常以冷峻的影像與碎片化的敘事逼問觀眾:「誰在定義真理?誰在控制敘事?」他曾說過一句極具代表性的話:「我們這一代導演的任務,不是拍出新的影像,而是拆解舊的幻覺。」
Raoul Peck 拍《Orwell: 2+2=5》並非偶然。他與奧威爾有著相似的精神軌跡。所以,Peck 並未把奧威爾當作歷史人物,而是視為當代的鏡像。他用奧威爾的警句反照現代世界——個性化推薦系統、假新聞、民粹政治、數字監控——在他看來,這些正是「新的極權語言」。他没有把这部影片拍成傳統傳記式紀錄片。他不按時間線敘事,也無旁白,而以影像構築「意識的體驗」——讓觀眾不僅理解奧威爾,而是親身陷入奧威爾所警告的世界。
影片開場是一連串閃爍的新聞、戰爭、選舉與廣告。聲音重疊、畫面碎裂、節奏逼人——那是現代人的信息噪音。極權早已變形,現代極權的方式不再需要監獄與槍口,而是以個性化推薦系統、流量與恐懼為名,溫柔地消解個體的獨立思考。當那句「2+2=5」浮現時,它已不僅僅是符號,而是現實的寓言——真理的脆弱與易被操控。
當菲律賓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aria Ressa說出:“What we see, what we hear, is not the truth.”「我們看到的、聽到的,並不是真相。」 Peck 停止了剪輯的躁動,讓她直視鏡頭,無配樂、無剪切,彷彿讓她在「真理的空場」中獨自發聲。短短的十幾秒,卻像一道光刺破了資訊迷霧。Rassa 的話,不只是對媒體的控訴,更是對整個資訊時代的診斷。她所描述的現實,正是奧威爾筆下「真理部」的現代延伸:新聞被操縱、個性化推薦系統決定傳播、情緒決定信任。真相不再自然存在,而是被製造出來的。每一則被推送的新聞、每一次的點讚、每一個「我們所相信的事實」,都可能是他人精心編排的幻象。

Peck 之所以選擇讓她發聲,是因為她正是現實中的「溫斯頓」(《一九八四》的主人公)——在被操控的輿論機器中,仍堅持說出「2+2=4」的人。這一幕將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帶入二十一世紀:極權已無須依靠暴力存續,它以數據、推薦與情緒維繫著新的秩序。
Peck 隨後以強烈對比的剪輯手法,拼接出川普時代的新聞鏡頭:記者的追問、群眾的歡呼、事實核查的紅字疊映在螢幕上,而背景音卻是一遍又一遍重複的口號——「Fake news! Fake news!」Peck 沒有旁白,也沒有評論,只讓影像本身說話。那一刻,觀眾幾乎能感受到「真理被淹沒」的轟鳴。接著,畫面中出現一句簡短卻震耳的字幕:「Trump is a liar.」(川普是個說謊者。)
這一句,並非憤怒的控訴,而是冷靜的陳述。導演以長達數秒鐘的時間、近乎機械的節奏,列出一個又一個日期、一條又一條的事實:川普在不同場合、不同年份的發言與被揭穿的謊言,一頁頁堆疊在銀幕上。這本應是「真理的勝利時刻」,因為所有的事實都被清楚地擺上檯面。然而 Peck 並未讓觀眾感到解脫,反而讓畫面的節奏變得冷漠、無情。謊言並非偶然,而是被體系化、被合法化的過程。而最令人不安的,並不是那些謊言的數量,而是影片在無聲中拋出的疑問:當謊言被無數次揭穿,為何依然有人願意相信?
影片的結尾,奧威爾的聲音(由 Damian Lewis 朗讀)逐漸被新聞聲浪淹沒。語言開始模糊、字句重疊,最終完全聽不清,只剩下閃爍的「2+2=5」。那一刻,觀眾聽到的並非內容,而是一種 「真理被湮滅的聲音」。這是 Peck 最精準的視覺隱喻:
——真理並非被摧毀,而是被重複到失效。
這正是導演的核心觀點:在當代社會,真理的脆弱性不在於缺乏事實,而在於事實太多。於是,資訊的過剩成了新的壓制形式——極權不再靠審查維持,而是讓真理氾濫至無人關心。
極權的生成:權力與群眾的共謀
在《Orwell: 2+2 = 5》中,還有一個令人深思的層面,是導演對「極權」產生的解讀。他並沒有把「極權」的責任單一地歸咎於獨裁者,而是透過整部片的敘事結構與影像邏輯,追問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極權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是因為獨裁者的野心,還是因為民眾自身的渴望?
Raoul Peck 的回答顯然不是單一的。他沒有把鏡頭對準「惡人」,而是對準了「我們」——那個一邊譴責獨裁,一邊渴望被領導的「我們」。
在他的敘事結構中,極權並非來源於自上而下的壓迫,而是一種雙向的合謀:獨裁者以確定與歸屬馴化民眾,而民眾則以恐懼與依賴放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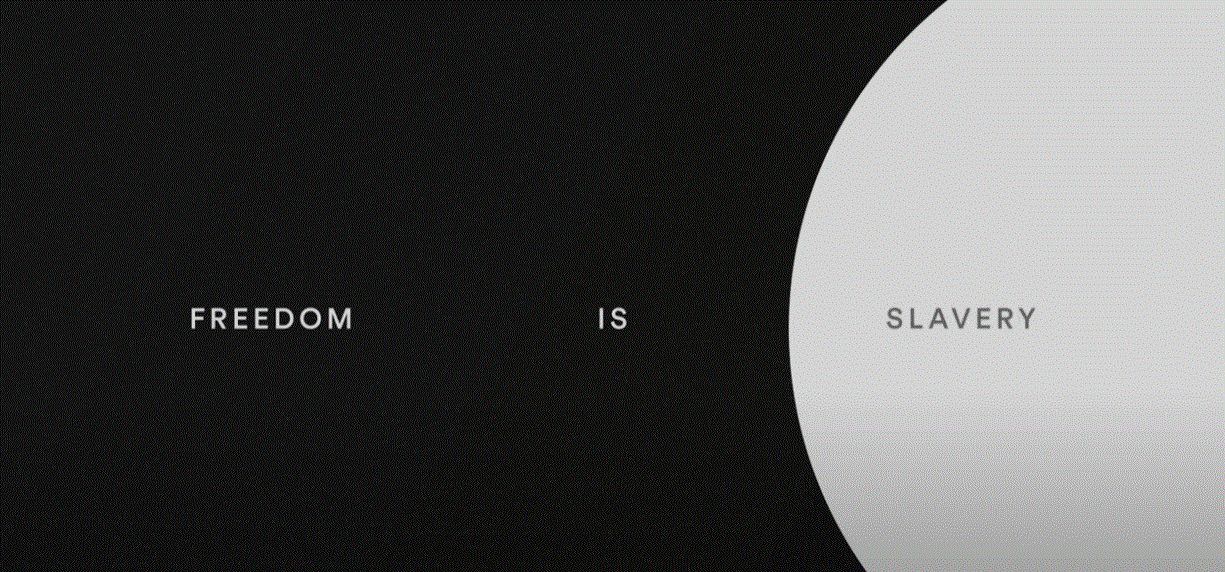
於是,權力與信仰在欲望的交會處相遇,極權由此生根——這一切,並非發生在鐵幕之下,而是在人心之中。鏡頭裡,領袖振臂高呼,旗幟翻飛,人群齊聲喊著「真理」;鏡頭一轉,是一張張年輕而激動、熱淚盈眶的臉。那並非被迫,而是自願——他們渴求信仰,渴求簡單的答案,渴求有人告訴他們「2+2=5」,好讓自己免於面對那個複雜而無解的世界。
奧威爾稱此為「思想的放棄」,而 Peck 則將它拍成感官的沉醉——光影、鼓點與掌聲交織成柔軟的陷阱。極權的力量,並不源於恐懼,而在於誘惑。它無需強迫你沉默,只需讓你漸漸相信,沉默才是更安全、更理智的選擇。
在當代社會,Raoul Peck 將「極權的共謀」延伸至數字時代的權力結構。個性化推薦系統精準地迎合人性的裂縫——我們渴望被認同,沉溺於情緒化的真理,喜歡被告知誰是敵人,追求簡單答案,逃避複雜思考。它以演算為餌,餵養慾望,馴化思考,成了新的「老大哥」;而社交媒體則化身為新的「真理部」,在溫柔的推薦與冷酷的數據之間,築起無形的高牆。
在影片的最後一幕,Peck 幾乎是在逼問觀眾:「當我們譴責極權時,是否也在以另一種方式參與其中?」鏡頭沒有停在政客的臉上,而是緩緩對準我們自己——那些刷屏、點讚、轉發、憤怒與冷漠的片刻,編織成新的「權力生態」。極權從未遠去;它並非自外於我們,而是在我們放棄質疑的瞬間,被親手喚醒。
他冷靜而殘酷地逼問觀眾:若沒有群眾的信仰,獨裁者的聲音何以如此響亮?若沒有人願意被欺騙,謊言又如何繁殖?極權的生成,正是一場「權力與民意」的共謀。獨裁者提供秩序與仇恨的出口;民眾則在恐懼與歸屬的幻覺中,甘願交出思考的權力。Peck 用這樣的並置揭示:極權並非政治的異化,而是人性自身的投影。
這正是 Peck 最具當代性的洞見:極權的形態或已變異,但其能量仍來自同一處——人性深處那份懶於思考的惰性、對秩序的渴望,以及對不確定的恐懼。
戰爭:極權的燃料與真理的墳場
整部影片中,戰爭影像貫穿始終。Peck 拆解了三個層面:真實的戰爭、被敘述的戰爭、被消費的戰爭。

影片穿插大量真實的戰爭檔案畫面—真實的戰爭——二戰轟炸、中東廢墟、烏克蘭前線、難民逃亡——無旁白、無音樂,只有機械轟鳴與人群的哭喊。戰爭不是英雄史詩,而是理性崩塌的噪音。它與極權是一體兩面:戰爭是極權的外化,極權是戰爭的內在邏輯。
緊接著,Peck 將這些真實影像與政治演說、新聞報導交替剪輯:領導人們在講台上以「正義」之名宣告戰爭;主播以溫和的語氣報導傷亡數字;螢幕下方的滾動條則顯示著股市行情。
這樣的對比製造出強烈的認知斷裂:真實的戰爭與被敘述的戰爭,早已分離。導演在此揭露了奧威爾式的「語言暴力」——當語言壟斷了敘事,暴力便能被美化;「轟炸」可以名為「解放」,「死亡」可以包裝成「代價」。於是,真理在修辭的外衣下失去了恐怖,只剩下被馴化的共識。Peck 借此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的戰爭,不再關乎槍炮與疆界,而是一場「敘事的戰爭」——勝利者,是那個掌控語言的人。
另一方面,戰爭正在被消費。鏡頭從戰場掠過,切入社交媒體——年輕人低頭滑動著螢幕,戰火化作「熱搜」與「表情包」。這段剪輯冷酷得近乎殘忍,卻真實得令人無法轉身:我們在螢幕前哀嘆,在下一秒卻輕輕滑過,讓死亡與廣告、災難與笑料,共同棲息於同一條時間軸上。
導演在此揭開一個殘酷的真相:戰爭得以延續,不只是因為權力需要它,更因觀眾已習慣「無痛觀看」。在這樣的語境裡,我們都是極權的共犯——我們觀看、轉發、表態、遺忘,卻從不拒絕參與。Peck 將戰爭拍成一個自我循環的機制:恐懼滋養權力,權力又以戰爭維繫恐懼。
這與《1984》書中極權政權「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所宣傳的「黨的口號的邏輯完全一致——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Peck 讓觀眾看見:戰爭不再是政治的失敗,而是維穩的手段。只要存在外部的敵人,內部的真相便無人追問。戰爭的目的,不是征服疆土,而是征服思維。極權以戰爭維繫恐懼,民眾以戰爭尋找意義;在這個循環裡,真理被犧牲,而僅剩下被包裝成「信念」的偽信念得以延續。
結語:當「2+2=5」再次成為真理
《Orwell: 2+2=5》的出現,恰逢世界再次右傾、政治撕裂之時。它並非回望過去的鏡頭,而是一面照向當下的鏡子。Peck 沒有高聲譴責,而是以更深的凝視提醒:極權從不是外來的幽靈,而是潛伏於人性之中的慾望——對控制的渴求,對歸屬的依戀,對安全的迷信。
今日的「Big Brother 老大哥」,可能是演算法,也可能是社群媒體的回聲室,更可能是被情緒綁架的集體意識。極權的形態或已溫柔,但其本質未曾改變:它仍在摧毀獨立思考,使人心甘情願地相信「2+2=5」。

奧威爾終其一生不屬於任何陣營——他只是孤獨的真理守望者。這部電影不僅是對奧威爾的致敬,更是一場知識分子對當代政治氛圍的自省。
當閃爍的影像與警句疊合,我們或許都該問自己:當所有聲音都在告訴我們「2+2=5」時,我們是否仍敢說出「2+2=4」?
在第44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的銀幕上,《Orwell: 2+2=5》顯得格外冷峻,也格外必要。它不是對歷史的回望,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漸漸習慣的現實:
— 事實在社群的浪潮中被稀釋;
— 理性在民粹與情緒的喧囂中消散;
— 「正確」開始取決於掌聲,而非真理。
而真正的勇氣,也許並非反抗權力,而是仍願意相信「2+2=4」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