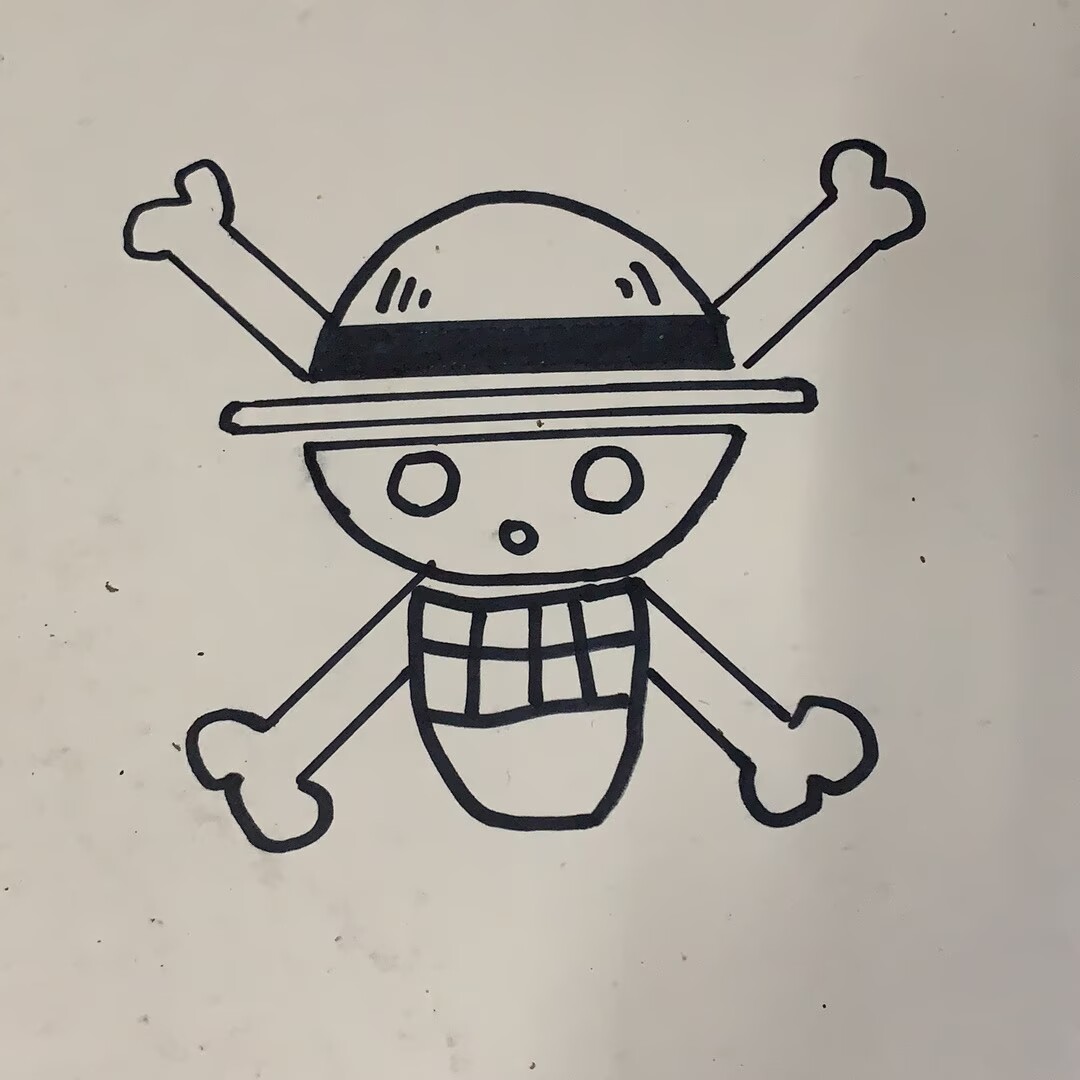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前往岳阳。我没选择联邦跃迁航道,而是启动了私人飞行汽车
原因简单,白露无法安装核能机翼——她的体内系统,不允许生理级别的植入装置。
所以我们采用了更稳妥的方式。
到了岳阳边界,我停下飞行器。从脊椎诱导点唤醒了那对碳基翅膀。
它没有展开声,只是一段轻柔的骨架运动,从我肩胛深处长出来。像鸟伸开自己的肋侧,不问力,只问风。
我的脊椎后部早在改造中扩展了神经引导链,碳基衔接口的工艺落实到细胞层级,让整个系统与皮层贴合如同肌肉自生,启动的时候,神经不会区分它是不是“原装”
白露则不同。她的碳基翅膀是穿戴式的——它不穿刺、不侵体,贴在浅层皮肌之上。只能靠脑电波牵引姿态变化。
白露当然也有植入 —— 她脑内的思扬,是标准配置。
但她限制它的生长。不给它扩张触角,不让它越过她的自由界限。
她从不接骨、不改肌、不装主动反馈结构。只留一个听见提醒的接口,从不转交控制。
她从不说为什么,我也不问。
也许,她对那个“人还应当长成人的样子”这条原则,比我更固执。
我们振翅升空,像两只蝴蝶在半空中滑行。漂浮的速度极慢,不似飞,更像被气流缓缓托着向某个具象化目标前飘。
我的大脑波动系统早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启动,张开捕捉范围。
这场搜寻自我回到地球那刻就已开始。
人类的大脑其实从不安静,每一刻都在以低频率、混杂载码的神经波持续广播。就像路由器发出的广播信息,普通人感知不到,也无法调频。
可我是先驱者——我能调入那张频谱图,从脑电波里筛出每一道思维的身份底纹。五百米之内,我不会漏掉任何人的信号。
整个搜索期,我都会维持这片扫描外域 ——持续张开,以我为圆心,谁的脑电一动,谁就被我收进图谱。
白露无需参与识别,她只需与我同步图景,但不让她多问。
现在的我,只保存行动机制——不断靠近人群,识别ID,保持穹顶式的意识扫描。
至于“是谁、为何、要去哪里”,启动梦露前,我封锁了这个答案。我留的,只是一双主控权限下睁开的眼睛,一直睁着,不许闭。
我会带她,尽量往人多的地方去。
岳阳有个项目。名字叫「迷宫行者」。
实体巨构解谜竞技场 (Labyrinthos: The Physical Megastructure Arena)
那是一座以实体尺度构建成的城镇级迷宫。
墙面、阶轨与穹顶全由磁感金属构壳与全息光矩阵共同编织,演算法将它们每小时重构一次,像神经活动重排一场梦境。
它每小时变换整体结构一次,由几千名游客进行组队。“行者”们被迫协作、协助、共解谜题:
数十人推动一只六米高的齿轮开启出入口;
数人交错站位,用身体遮挡激光矩阵,为队友开出无伤路径;
人声在穹顶处合奏,用噪频激活某一道声控机关。
每个人仅持有某段地图碎片,无法自解出口。
只有将整个密室中的所有碎片拼合,系统才显示通往核心秘库的路径。
这是一次技术奇观设计下的信任实验。
所有人的装备信息互通,行动轨迹实时转写。
整个迷宫像是一颗三维展开的神经网络剖面,每一个人,只是那片通电图域中一处临时被激发的信号节点——亮一下,走一步,触发一次,再归于沉默。
我陪白露完成迷宫中的一次路径。她热爱这类非竞争式协作——那恰好也是我此行的合理掩护。
之后我们随即升空,缓慢盘旋于整个游乐场上方——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同时出现两三万人的区域。
我的扫描像一层薄静电,盘旋在我周围半公里范围,识别ID、封装图谱,谁靠近,它就轻擦过去,像风扫过树冠那样带走每一次短促的信号起伏。
这才是我的工作方式。不是漫无目的地扫过城市,而是分阶段排查。我专走人群最密的路线。
城市的结构早不是巷弄堆叠的拼图。我不会钻进每条街去追那种可能性。我只看哪里人停留得久、汇聚得浓——因为人流走过的地方才会挂下信号。
城市之间快得像句短语。从岳阳转去永州也不过十分钟。
所以我不以城市为单位,我设计了分阶段实施计划:
l 先集中大规模人群装置型场域,每一个游乐园、演出现场、实地体验构组都是我扫描的最高优先级;
l 如果最密集的场所无果,我就按日夜划分动作。白天扫城市主商圈和交通聚焦口,晚上转入那些居住区的上空,从生活点开始轨扫。慢,但稳。
夜幕下的住处没有标记,我也不需要查询地址。
即使人们静默不动,每颗大脑仍在广播。
但他不一定在湖南,甚至可能根本不在这颗星球。
这不过是一次成本最低的触底策略。
我是审查官,我得从这里开始试。
之后我们去了张家界。
我们没有停太久,只是换了一种环境、一组人群、一项项规则不一的体验方式,用来掩护我的持续扫描——在她眼里,这是旅行,在我眼里,这是地图上被我用脑频扫过的又一块区域。
玩了地球修复主题的「大地共鸣」,模拟雨林扑火、珊瑚接种的过程,参与者排着队扮成生态战士。
她开得比我好,把虚拟冰川救了三次,还让那场声光收尾落到了我们小组上。
又去了复古摇滚场馆「回声工厂」。我不懂音乐,她却能跟AI合音交错几段巨响,还能左右歌曲结构的下一段。
荧光透出来时,她闭着眼,一字没落地唱了一整首70年老歌。
还有AR增强现实的大型主控项目「苍穹之下」。整个街区成了战场。她站在广场中央,好像是在指挥天幕开启一场虚假的星舰起飞。
那十几天,我们在互动场、主题馆、控制区、人流磁场间穿梭——我一直在飞,一直在扫,一直静静地听每一个人脑电浅层是否有哪个轮廓能突然对上。
她不问,我也不说。
像是交换了一次彻底沉默的信任,任我在她眼里的短暂生活中,一寸寸地捕捉这时代底部的偶然发光。
最后一项行程,是彬州的「指环王:中土远征」(The Lord of the Rings: Expedition of Middle-earth)。
三天两夜的实体沉浸体验,整个主题园区被还原成了中土版图的大幅缩略体。从瑞文戴尔起,到摩瑞亚、夏尔与末日山脉,所有布景都是真的,要人踩上去、走进去、搬出来。
白露挑了精灵族。那对耳朵装得偏浅,像是随时要掉但又随时在听风。她和其他几百人一起吟唱控制光效、齐射激光弓箭,用中土古语触发任务音频,稳稳地守在瑞文戴尔的圣树边。我站远了些,看她背后是几十米高的水晶穹顶——光正在她身上发生纹路扭曲,像记忆在试图炼出新的分支。
我没选阵营,只是被系统匹配进人类侧翼,骑着赛车场模拟马、执行防御壕沟的加固工作。我的动作被他们说成“很像北方骑士团”,但我没说话,只借机扫描捕捉每一圈身份——那三千多人怎么排、怎么调、怎么交错,那么吵。可我这边没图、没计算、没干预。只要谁走进来,哪怕没说话,只要信号波一动,我就记得住。
我们曾在夜里进过摩瑞亚的洞窟机关区。上百人抬着一块模拟秘银道具,一边喊声震天一边绕暗坑搬动齿轮。我始终从外圈走,不沾剧情。他们在喊口号,我在扫频点。
但真正让白露兴奋的,是最后一战:佩兰诺平原上的全阵协作。
天一亮,山谷就被AR系统推满投影。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台地,变装者涌出、箭矢起飞、骑兵突围、霍比特人从人群中穿梭掩护那一个持戒者。我看到白露站在第二纵列,挥着激光弓的一刹那,侧脸亮了,那光扫到她眉梢,像她笑了,也像整个战场照准了她。
而我,站在这片幻想战场的预设边界上,围场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次共同呼吸,都在我控制的500米扫描弧下被逐一捕捉。
他们不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只是把一件旧故事认真演了一次,而我在记录,这场“人类在模拟中以协作方式完成集体构图”的全过程。
最后火山爆响,持戒人被安全送达,一场焰火秀洗过头顶,六千人的地图任务归零,再无任务。
白露来找我时,一手还拿着系统发的胜利徽章。一边说着“矮人那边系统卡了,要补一段彩蛋”, 一边把那枚刚领来的徽记捻在手指里,小心捏着边角,好像在提醒自己——我们刚才真的站在故事里,不是装出来。
我没说话。
我让她站着,等自动气楼送风扫过迷宫中央站口,我才说:
“走吧,游戏结束。”
我们从彬州返回长沙后,就启用了第二阶段的扫描路线。
大型景区和高度协作场所我已经扫完了,剩下的,是城市自身该面对的密度结构——商圈、栖居、生活本身。
白天我带着白露飞,像是漫无目的转着玩,其实全城计划分段扫描;
晚上她休息,我一个人继续飞,把城市划分为一个一个透明的人阵层面。
这一次我们不落地,只在空中路过而已。
到第25天,我已经飞完整个湖南。
不是略过,而是逐座城市、逐个街区,从地政标点到民居上空,一寸不落地扫过——张振山的ID,没有出现过一次。
这本不奇怪,我一开始就没赌太多希望在低空识别模式中发现他。
但让我真正没想到的,是另一个方向。
我审查过的湖南受审者共有5378人。
一点都不多。
但只用这五千多人生成的案卷,就已经扩展开了超过20亿个相关ID——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传播中的信息波点,不需要建模,系统自然延伸出来。
比如其中有一家做食用油的工厂,产品曾销往全国,追溯受害者时,凡是吃过他们出厂油的人都自动被Jesus标为“轻度结构受伤体”,我就顺理成章获取了所有人的ID。
你不需要审问十万人,
你只要匹配出十来个辐射范围够广、波及结构够深的受审者,这个国家的ID就扫得差不多了。
我照着这个路径,把5378人的全部罪行回映片段通通扫过。
这些ID都埋在受审者的记忆片段里,无需我额外调取。随着画面展开,信息自然露出,全部被写进那块我在离开仙女星前构建的隔离数据库里。没有人知道那区域在运行,连梦露都跳不过权限。
可问题就出在这。
张振山,不在里面。
不是主视角、不是共谋侧、不是受害标,也不是哪怕一次轻度擦边的ID联动。
这不是“小概率巧合”能解释的。
他不是在外地,也不是因路线不同没碰见,而是:他从没被Jesus记录为“存在于这20亿人任何结构片段里的人”。
这不合逻辑的干净,让我一瞬冷了下来。
不是愤怒。是那种审查官内部才懂的微层恐惧。
你明明已经把水库挖到了地底结构,结果你想捞的那块碎片却不在水里,甚至没有“它漂过”的痕迹。
我向后调频,重新比对全部ID残片,排查错误、确认脱角。
系统没有报错,也没有阻断。
所有流程都吻合授权,全部检索成立。
他就是没出现。就像他从未被投放进这个社会系统的任何一点触感中。
张振山,仍然在空气之外。
我开始明白,Jesus那天发给我的那串信息——“时空错乱”四个字,远远不是一句描述那么简单。
数据不撒谎。
可问题不是撒谎,也不是掩盖,是Jesus根本就从没生成过他的数据。就像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打算把他放进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