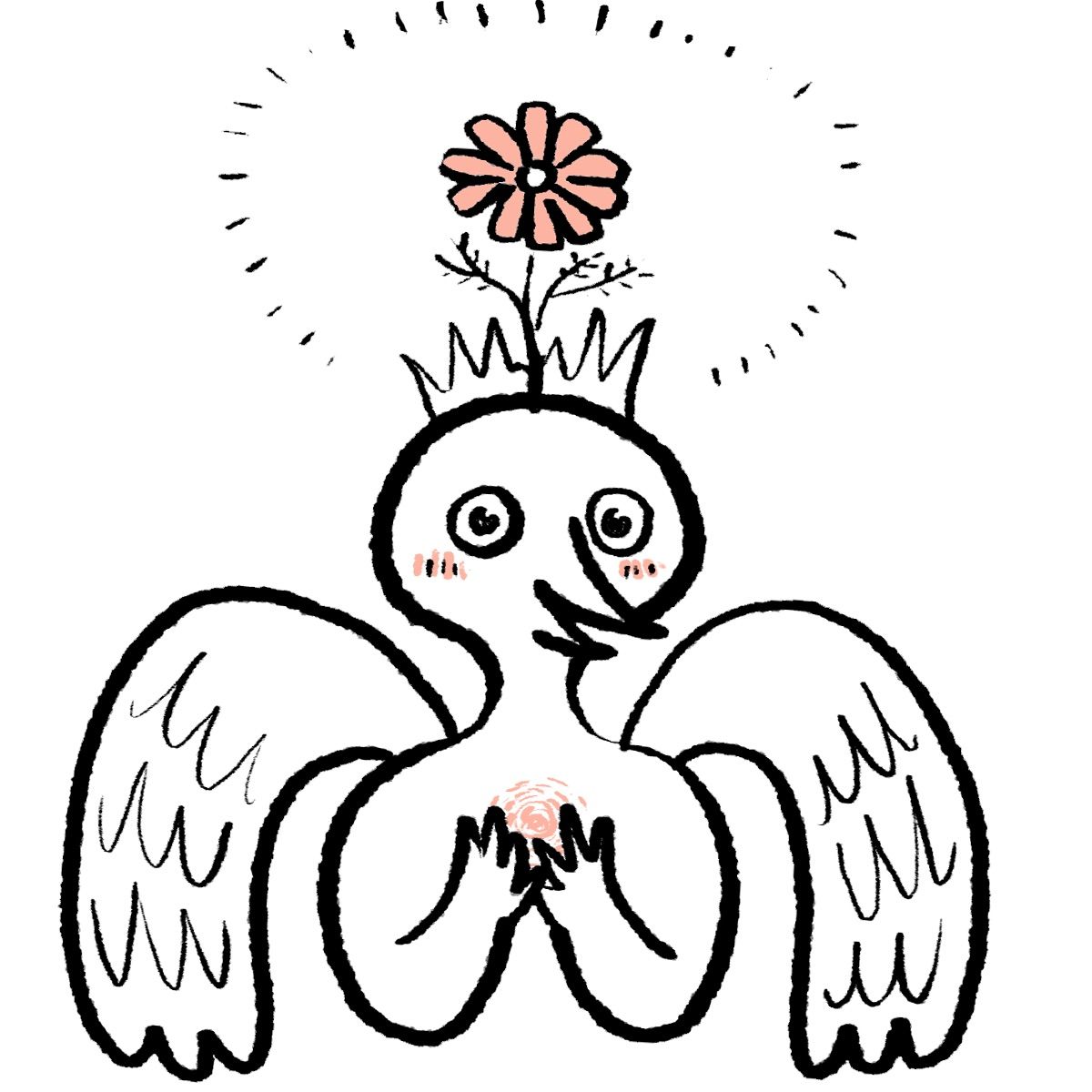如何從搖搖欲墜的身體提煉出更好的錯誤:讀Lily N. Shapiro《結締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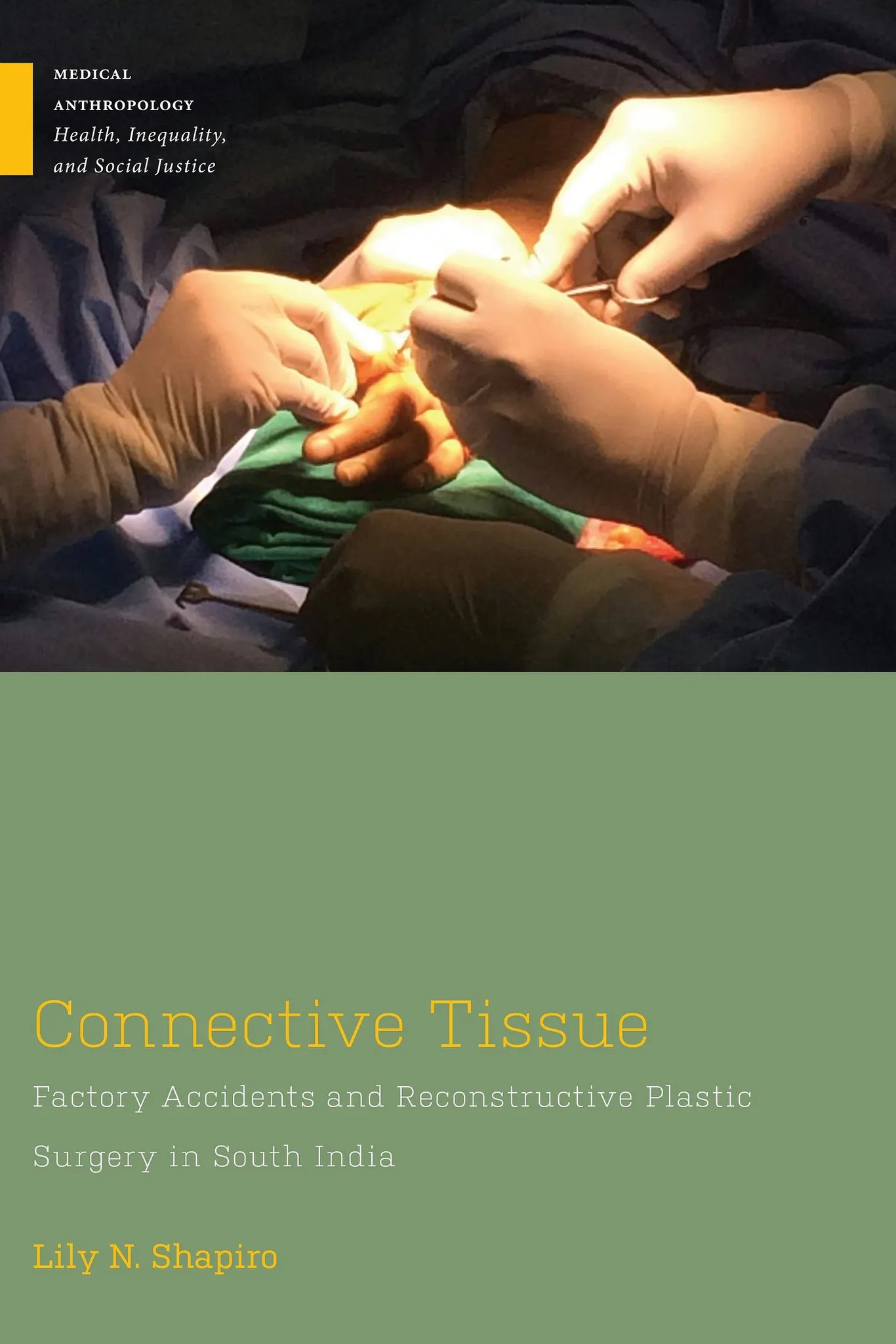
Lily N. Shapiro, 2025, Connective Tissue: Factory Accidents and Reconstructive Plastic Surgery in South Indi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籃球場旁的神明睡著了/模糊的少年們清醒著/ /風吹涼長長的街/如何從搖搖欲墜的身體/提煉出更好的錯誤
──孫梓評〈夢遊人俱樂部〉一次工廠晚班,Mathan Raj忙著修理自己操作的那台液壓機。他切了安全鎖,開始更換故障零件,卻沒想到安全鎖意外鬆脫,機械重新啟動,瞬間切斷自己的右手食指。連同如今裝在滿是冰塊以維持不腐的塑膠袋裡的手指,Mathan Raj被很快送醫,但依舊不敵細胞壞死速度。醫生當場告訴他,手指已經無法接回去,只能截肢。「最後醫生動手術齊根切除我的右手食指」,Mathan Raj說,「就這樣,他們又多切掉了一點點我的手。」
意外事故十五天後Mathan Raj復工,傷害與傷害的影響卻糾纏不休。他的右手時常僵硬,拳頭難以完全緊握,在他騎摩托車通勤時作痛。他也得重學怎麼吃飯寫字,怎麼在銀行櫃檯跟行員解釋自己的簽名長得不一樣,是因為自己負傷,然後,展示自己的手。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有點變樣了」,Mathan Raj告訴人類學者。
「所以你要回去上班會怕嗎?」人類學者問。
「有一點」,他答,「工廠經理有說我不用回去操作同一台機器。他說如果我想,可以去用別的工作。但我決定回去原本的位置。我不想看扁我自己。」

讀Lily Shapiro的《結締組織》,讓我想到以前壹週刊的《人間異語》(後來轉為鏡週刊的《坦白講》),看似白描、沉靜的報導式書寫裡暗伏人世間過熱的劬勞與苦楚。唯一差別大概在那個「異」字:《人間異語》彰顯的是異於常情常理的窺看;《結締組織》裡頭所要捕捉的卻是寫作「意外」、但總是發生的日常。
Paul Virilio說:「發明帆船或蒸汽機意味發明船難。發明火車意味發明火車事故」。Shapiro續寫此句提醒讀者,工廠與工傷事故的緊密相偎。一句話說,工傷不是憑空誕生,而是內建於工廠與其特定的工作形式與環境中。工傷是意外,是無法避免的意外;Shapiro訪談過的工人與雇主皆心知肚明,只要工廠有運作,意外就如影隨形。
話說至此有點曲折晦澀,按照慣例還是先從田野地慢慢繞回來。Shapiro關注印度南部的哥印拜陀(Coimbatore,கோயம்பத்தூர்),「天時地利人和」下催生的工業大城。1888年猶是英國殖民統治下,英商Robert Stanes來此投資設紡織廠大成功,不少商人後續跟進,隨後此城逐漸冠上「印度的曼徹斯特」稱號。紡織廠成功的關鍵之一是1930年代周邊興建的Pykara水力發電大壩,源源不絕為哥印拜陀的工廠提供能源,讓這城市逃過印度其他城市因為缺電而產業蕭條的命運。特定的Kamma Naidu種姓族群同為關鍵,這群當地的企業家自1900年以來掌握大部分的工廠,並逐漸發展其勢力到教育、醫學、藝術等領域,持續以其家業贊助、推動此城發展。時至今日,哥印拜陀約有兩百萬居民、兩萬五千座工廠或工作室,上個十年間失業率大概3.7%──既低於省失業率的4.5%,更遠低於全國5%的失業率,前景一片地好。
然而哥印拜陀的奇特風景不止於此,在工廠林立、製造業發達的城市裡同樣出名的還有Asha醫院。它是全印度最大的整形外科與骨科專門醫院、最大的手部與微手術中心、也是最大的脊椎手術中心。其技術與名氣之盛,年年吸引不少外國醫師飛來見習、取經。Asha醫院能有此成就,憑藉的無非哥印拜陀持續「產出」工傷意外。醫院裡125位外科醫師總計每天至少進行一百起手術,其中多數關於創傷與整形。另一方面說,城裡工廠如果發生意外,所有人第一時間也都知道要馬上送Asha醫院;無論雇主與勞工都清楚,在那裡傷患將得到最好的處置與照顧。
人身事故與醫療發展彼此微妙的勾連、供養於是促使Shapiro發展一套不同的資本市場與勞動理論。過去有關資本主義的討論,往往關注勞工如何困於特定結構,被迫從事高強度、高風險的工作來求溫飽,進而在喪失價值後被恣意拋棄。然而在這些勞動條件與狀態之上,Shapiro探問:如果別於我們想像的免洗勞動故事,照護本身也其實成為資本主義的一環,那又會是什麼風景?
在哥印拜陀,頻繁密集的工廠意外滋養了Asha醫院;Asha醫院的存在卻也因此惠及當地工人,讓傷者有了復健重來的機會。鏡頭轉進醫院,同樣是類似的拉拉扯扯。醫生們日日在手術房裡進行長時間精密手術,付出極大心力確保傷患的傷害與不便降至最低。然而什麼時候該截肢什麼時候應該考慮保留,醫生的處置往往基於「復工」考量。誠如醫生Manoj言,「只要傷患還有大拇指跟另外手指,我就傾向重建(而非截肢)。因為長遠來看這比較划算。」
划算,意思是雖然重建手術比較貴、後續復健程序比較久,但長遠而言傷患可以更容易回到工廠崗位,繼續為家庭經濟貢獻,而不成為負擔。故事說到這,我們當然可以讀此為一則典型的資本主義同謀:勞工如何持續被回收再利用,成為危險職位上賣命的永動機。然而Shapiro也提醒我們勿忘這其中的生之欲望,是醫生盡全力想幫忙傷者克服障礙,而傷者也想重返職場以便「照顧」自己最最親密的家庭。
換言之,從書名《結締組織》始,這本民族誌要捕捉的就是這樣層層疊疊,複雜糾結,難以拆分的「好/壞」連動:哥印拜陀裡有工廠、工業與醫院、醫學的交駁。在傷者漫長的復健與家庭生活裡,照護的親密與暴力同床共眠。在世界聞名的Asha醫院裡,對傷者的關心與資本主義的謀求若即若離。而在概念上,照護在Shapiro眼裡未如其他人類學者那樣被看成是對工業、疏離社會的抵抗,反而往往相依相惜。
行路至此,我們究竟會走到哪裡?讀過中途我就好想好想問Shapiro這問題。在書的尾聲她再次強調,勞動提供了創傷,推進醫學發展;醫學則支撐住勞動(力),讓其生生不息。在這套循環中,正是照護這有愛有恨又複雜的事物予其潤滑,維繫整組循環永動。
然後呢?書沒回答,就此結束。彷彿徒留孫梓評另一首詩給讀者:「身體壞了/則塗抹快速的安慰。/未曾察覺:不遠處有海嘯發生/ /有什麼關係?/ /我們大方/將痛苦傳染給鄰人/閉眼躺臥遼闊的色情之上/夜闇中最平凡的願望/無非是……自由、平等。/或者上述二者的相反」(〈沒有詩也沒有關係〉)。

Mathan Raj其實還算幸運,他是訪談之中唯一拿到超額補償金的人。還有,他是已婚男性。另外一位工人Chittra在早班為壓力機上油的過程中分神,失去她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與部分拇指。正式訪談結束、關掉錄音機後她女兒突然湊近說:「我媽心太軟,總是幫公司說好話,但這根本不是好公司。」女兒抱怨事故發生後,公司最初只給將近二十美元的慰問金。打官司?所有的簽到簿都由公司保管,Chittra沒有任何可出具的證明。名義上,公司甚至能宣稱他們並未雇用Chittra。
關鍵在公司送人去Asha醫院。私人醫院服務好,但同時院方只負責「收錢辦事,然後把人送走」。Chittra女兒指稱,如果媽媽是被送去政府醫院,那就勢必得立案,有存檔,有時甚至會引動稽查員來調查公司是否違法。然而如今Chittra除了逐漸「康復」的半截手掌,一無所有。

還有Sujatha,在訪談時她已經因為機械事故失去了半截右手食指多年。正如大多數傷患,事故當下她意識一片空白,「我不覺得痛,我只記得我的手還在機器裡。不久後我感覺手一陣灼傷,血一直流,那看起來像是果醬。看到的時候,我感覺糟透了。」
對Sujatha而言最艱難的是傷後如何自處,以及,處理他人目光。多年了她仍舊對自己手無握力耿耿於懷,尤其針對所謂「隸屬妻子或媽媽」的家事,Sujatha心常懷陰影,怕東西掉,怕事做不好。
「但當我在工廠用著機器,我沒感覺自己有少手指。我可以完成工作,我沒問題。」

註:Shapiro非常巧妙地取了一個雙關的書名。乍看之下,Connective Tissue指涉的是醫學專有名詞「結締組織」,並連結到她所討論的工傷與整形手術細節。然而透過connective tissue的比喻,Shapiro同時也傳達了工作與照護緊密相連的意象。
Lily N. Shapiro是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類學博士,期間受業於Sareeta Amrute、Janelle Taylor等人,目前在Kaiser Permanente Washington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擔任研究員。作為醫療人類學者,Shapiro長期關注照護(care)相關議題。《結締組織》是她的第一本書。
關鍵字:醫療人類學、職業傷害、照護、勞工、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