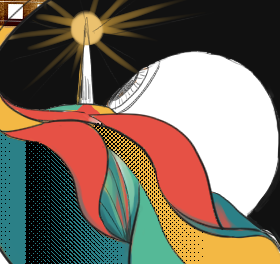《282°26'/+36°37'》
讓思念成為......永恆的東西。
需要變輕的東西。
終有一天會發光的東西。
——《282°26'/+36°37'》入口銘文
一
艾格娜距離上次我看到她遠離了我三公尺。
這是一座美術館,我把我亡妻的肖像放在這,「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問。
「會一直飄向高處,」管理員說,指著上空無盡黑色布幕的一道亮光,「看見了嗎,像星星般的存在,到那時思念就不會是負擔了。」
「你也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停下來,不過放上去的東西都不能撤下來,這是規矩。」
我抬頭遠眺著,那光芒細小得像是飄浮於宇宙間的塵埃,四散在館內螺旋排列的聳立石柱之中,構築出似環形劇場般的宏偉空間。光影流動的黑幕之下,懸掛其上的不是珍寶,而是一具具來自他人生活印記的標本。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人像畫,剩下沒有臉的,我只能從中看見模糊的影子。
有些影子是飄揚的衣服,也有些是帶著凹痕的器具,如黑白相片般的冷光在物體間緩緩流淌,層層疊加在鏽蝕的單車、斑駁的眼鏡,以及眾多已辨不清輪廓的遺物……而艾格娜就在它們的中央。我不知道此刻她在想什麼,因為她始終保持著十年前的一抹微笑。
那微笑定格在帶著亞麻仁油氣味的纖維紙上,畫框是她生前最愛的核桃木。整幅畫像搬來的時候重達十公斤,可一旦它被掛上去後,她看上去比實際還單薄許多。
「整個過程會花費多久?」
「如我先前所述的,這取決於您。」
美術館裡每個物品都有編號,管理員留給艾格娜的數字是二十七……二十七,以後會面時,我要報上這個數字。離去前管理員提醒我,每日下午五點會準時閉館。
我始終沒問出那一直懸於心裡的另一個問題。
二
找到這間美術館所在的位置,遠比它的名字好懂,它座落在利物浦舊港區的一棟未對外開放倉庫,介紹我的人給我一組數字。我原以為它是什麼密碼,或是隱藏的座標號碼,然而抵達後才發現,那不過是倉庫鐵門上早已褪色的編號。
「282263637」,來過這裡的訪客都這麼稱呼它;天琴座[1],某顆黑洞的赤經赤緯,人們賦予想像的數字意義,我猜想這就是這個名字的由來。
要見到艾格娜,從來需要的只是時間。
時隔兩個月的週六上午,利物浦一如既往下著小雨,我在市中心的巴士站牌等候了許久,才等到了一班前往港區的班次。雖然利物浦曾是航運要地,但會前往舊港區的遊客寥寥無幾。我從巴士方窗往外望去,四周是一片靜謐的灰色。
當我凝望河的對岸那棟紅磚矮房,在那短暫的瞬間,記憶攪動了起來:雨聲、花香、午後甜茶,還有那些不合時宜的黑膠唱片……巴士很快地駛離了回憶中的那片景色,在那之後的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出門。
這天傍晚,天色已顯得有些昏暗。寒冷的海風迎面而來,我扣緊大衣最上排的鈕扣,推開了美術館的大門。
進門後的空氣不再帶有冷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停滯感。可館內陳列的物件卻如夜空的星軌般,無可回返地移動著,以不可預測的速度向上飄升。
艾格娜的肖像上個月還在三樓的迴廊,今日卻已到達了第八層。
同樣改變的還有美術館的管理員,這次接待我的是一位約莫二十歲的年輕人。唯一讓我心安的是,在我報上「二十七」這不變的數字後,他沉默地核對了紀錄,隨後引領我踏上螺旋上升的階梯。
美術館以黑色大理石鋪就,大半覆以靛藍絨布,我們沿著螺旋石柱緩緩而上,厚實的地毯吸附了所有足音。起初,我還能依稀分辨每一層的高度,後來卻逐漸失去了這種感覺——越到上層,懸著物品的繩線變得又細又緊,彷彿有兩種不同的引力在上下拉扯。然而,當我仰望天頂,那兒依然是深部不見底的黑,轉角之間盡被垂掛的布幕給遮擋,唯能感受到底下踩踏的空間逐漸縮減。
如果一直上升會發生什麼事?這個念頭再次從我心底浮現。
到達第八層後,所有懸浮的物品皆被厚布嚴實包裹。「出於安全考量。」館方的規章是如此解釋的。
我眺望著黑幕中心,上升到這層的物品皆已染上深紅,從遠處看,它們彷彿著了火般。艾格娜離我而去是如此之快,我心裡湧進一股難以言說的情感,她怎麼能離我而去得那麼快呢?或許管理員還有沒有告訴我的事——這黑色的布幕並不是亡靈安息的終點,相反地,它在吞噬他們,就像黑洞一樣,它使萬物都在加速、加速,直到爆炸。
我吸了一口氣,閉上眼,幾乎可以想像那巨大的光芒爆炸的那刻[2],萬物坍縮又膨脹,那光芒填滿了整個舞台,嗡嗡作鳴——佔據著我血液裡的氧,振動著我骨骼裡的鐵,淹沒了我眼睛裡的碳。
而艾格娜就置身於那裡,成為塵土的一部份,成為了碳、氮、氧、鐵、鈣[3],成為了再也無法擁抱的相框,成了付款三十美金探望的存在。
成了一個我不願再為之稱呼的名字。
三
我想起管理員說的話:「您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停下來。」
但停下來不代表能回頭,博物館內的規矩是死寂的,物品一旦掛上,就再也無法取下。為了再次找回「她」,我開始日以繼夜地流連在當初提及美術館存在的論壇。
我在舊帖子裡翻找,在私訊裡詢問,溺水的人會抓住每一根稻草。
然後,那個男人找到了我。
「所以你有多愛你的妻子?」
螢幕的冷光映在我臉上,我盯著論壇的私訊視窗裡跳出的訊息,屏住了呼吸。
「你是誰?」呼之欲出的疑問在對話框裡閃爍許久,最後被我一個鍵地刪除。這種時候,對方的名字並不重要。
「你去過282263637,每個星期六,然後你後悔了。」
我的指尖懸在鍵盤上,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美術館的訪客雖然稀少,但在那螺旋的石柱林間,偶時我會看見幾張蒼白的熟面孔。如果有人在尋找一個足夠絕望的傢伙,那他確實找對了地方。
我意識到,這或許是我唯一的機會。
「你有辦法讓她下來?」
訊息停頓了幾秒,我能感覺到螢幕另一頭的人正在審視我。
「我知道怎麼讓她下來,但凡事都需要代價。」那行字終於出現,他沒給我多餘提問的空間,只是重複了最初的問題:「所以你有多愛你的妻子?」
「......為了讓她回來,我願意支付任何代價。」
「就算這意味著你得讓別的東西上去?」
有那麼一刻,我的腦海被那抹吞噬萬物的深紅佔據。
令星辰為之毀滅的顏色,它被拉扯成絲線,碎裂成殘影,在那混沌的輪廓中,卻浮出了一張模糊的女性面孔。
她的手朝我伸了過來,裹住我顫抖的掌心......那股毀滅性的色澤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克里特島暮色般的暖意。
「如果需要的是等值的東西,」我緩緩地敲下了我的回應,「只要不是她,什麼都可以。」
「很好。」這次對方回得很快,「凌晨一點,美術館門口。別遲到。」
四
利物浦港區的夜晚一直都很冷。
在早些年,政府不曾言說的歷史裡,這兒曾是孕育毒品、走私、暴力滋長的溫床,在那些尚未翻修的廢棄倉庫下,埋藏過數個未結懸案的無名屍骨。遠隔著河岸另一頭,翻新後的阿爾伯特碼頭正洋溢著璀璨的光彩;夜雨落下,打在發散著炫目倒影的水波上,仍有零星酒吧在營業,不時可見雙雙成對的遊客漫步在人行道上——現在利物浦的夜晚變得非常安全。
可在我看來,那些燈火看起來太正常了,正常到像是在嘲笑我還把自己困在舊港的鐵皮味裡。
「如果你要找喝一杯的地方,演唱會廣場這時間是你最好的選擇。」
時近午夜,我只攜帶了皮夾和手機後便出了門。上了車後,司機那道好奇的視線正透過後視鏡打量著我,見我沒有回話,他聳了聳肩。
「也是,利物浦沒什麼好玩的。你是遊客?聽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
「不,我住河的對岸,我的妻子是伯肯黑德人。」
「挺不錯的,你們認識多久了?」
「我和她認識二十年了。」
他點點頭,車內隨後陷入了寂靜,將車駛進了舊港灣的入口,我們都沒再開口。
計程車很快便抵達了目的地。
一旦皮鞋踏入水坑,利物浦晚風那刺骨的冷意便如細針般穿透大衣縫隙,連帶掃過貨櫃屋發出嗚嗚作響的尖嘯。
凌晨十二點五十分,我將雙手埋進大衣口袋,一口呼出鹹腥的白霧,耳邊突然驟響另一道規律的腳步聲。
我在霧中對上了一雙審視的黑目。
來人遠比想像年輕,偏深的膚色,或許是西班牙人。他身穿再尋常不過的深色工作外套,裡頭搭著鬆垮的連帽衫,壓得低低的帽簷下露出幾縷凌亂的黑髮——是那種你在超市排隊買啤酒時,轉頭就會忘掉的普通面孔。
他沒有朝我走過來,只是露出一副有些無聊的神情。「嘿。」他喊了這麼一聲,朝右手一抬下巴,示意我跟上。
我注意到他提著一只深褐色的行李箱。腦中閃過了許多念頭,我試探地開口:「……我們需要準備什麼嗎?」
他停下腳步,認真地斜了我一眼,那雙眼在暗處亮得有些驚人。或許是我的神情,又或是這問題勾起了他的興致,他嘴角忽然揚起一絲嘲諷。
「你以為箱子裡裝的是什麼?」
什麼東西會和一幅肖像等值?不,重點從來不是這個,我心底其實很清楚他會什麼會挑上我,博物館那些徘徊的訪客。
「你說需要等值的東西。」我吞了唾沫,他冷冷地等著我把話說完:「……我猜是和人命等值的東西。」
男子盯著我的目光看上去更惡劣了:「那你有處理屍體的經驗?」
「我——」
「我想也是,」他打斷了我,語氣已經恢復那副索然無味的調子,眼神帶著點不耐。「所以這部分我處理好了。你只需要跟我進去,拿回你的東西,我送走我的。」
再公平不過的交易,不是嗎?可那句話並非來自男子口中,而是我自從她走後一直被我沉埋在內心深處的聲音——帶走她!你必須帶她走!
不論以何種代價。
這念頭簡直令人難以忍受,我幾乎是壓下那股怒氣,猛地停下腳步。
「你不怕我報警?」
是,很好,停下它,不要在前進了。我不自覺地吸了一大口氣,注視著男子視若無睹繼續前行的腳步,行李箱滾動在石子路上的聲音逐漸變得細碎,不知何時,我們已來到了美術館的後門。
「她走後,你早就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無數次了,不是嗎?」
鑰匙轉動,鬆脫鎖扣的聲響卻引得我一陣戰慄。他回頭看了我最後一眼,說得很平靜:「博物館不允許放上被謀殺者的殘骸。這就是為什麼我找上你。」
五
一名成年女子的平均體重是六十公斤,死後的遺骸只餘約十公斤。靈魂的重量是二十一克[4],含著指骨的手骨則約莫半公斤。
這是男人提出交易所開出的價碼。
「但你還沒講出最關鍵的,到底要怎麼取回她?」
夜晚的美術館顯得更死寂了,空曠的展廳吞噬了所有光線。男人熟稔地穿梭在布幕間,他對這裡的瞭解程度令我心驚——這座美術館的結構像極了一座宏大的歌劇院,而他領著我避開監視器的死角,轉過一道又一道偏廳門廊,最後停在一面垂落的陳舊絨布前,伸手一撥,便揭露了隱藏在其後的小門。
門後只見一條狹窄的長廊:陰暗的走道堆滿了木箱與防塵布,裸露的混凝土牆面斑駁著寒意,與前廳的華麗判若兩個世界。我們來到了走道盡頭,泛著冰冷金屬光澤的載貨電梯正靜靜地等待著。
男人從木箱堆間拎起一把略顯生鏽的鐵梯,隨手掛在臂膀後,按下了電梯鈕。
電梯門打開時散發出一股陳年的空氣味,他毫無遲疑地踏了進去。
他沒有立刻按層數,反倒問了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你知道美術館什麼時候建成的嗎?」
我愣了一下。「什麼?」
「一九九零年。」他這才按下數字「八」,繼續道:「早年這裡是裝滿煙草與奴隸財富的碼頭倉庫[5]。政府需要新氣象,資助了建築翻新案,使得成本格外便宜。美術館的創始人弗瑞德看中了這筆財富的潛在用途——最後只花了二十萬就建成了美術館。」
數字在我們眼前跳動著,他語氣帶著一絲嘲弄:「現在門票卻要三十美元。你問我怎麼知道的?」
「因為這座美術館就是我一磚一瓦搬起來的。」
腳底傳來一陣沉悶的震動,電梯抵達了。第八層。
隨著電梯門緩緩滑開,我第一次看清了這座美術館真實的面貌,四周一片漆黑,我曾經深以為懼的詭譎紅光並不存在,只有無數懸浮在半空的物品在陰影中微微晃動。若仔細觀察牆面,就能發現上頭突起的工業燈管——那些燈管此刻並沒有亮起,卻以此照亮了這個空間的本質:事實證明這一切沒有魔法,也沒有規則。
而「二十七」依然是那不變的數字,我們停在一件用白布層層包裹的長方形物件下,它在半空中靜默地懸掛著。
男人沒有理會我的沉默,只是兀自蹲下身子,打開了那只行李箱。裡面放著一個長型方盒,以及數個灰沉沉的磚頭。當他撥開盒蓋,裡面的東西終於揭曉了——是一截枯槁的、灰白色的手骨。
他這時才確認似地看了我一眼,問道:「你妻子的肖像,是十公斤沒錯吧?」
我張開嘴,卻發現喉嚨乾澀得發不出聲音,只能僵硬地點點頭。
他便開始將箱子裡的磚頭一一塞進盒內,小心地擺放在骨頭周圍。完成後,他拿出一只攜帶式的量測器扣在盒子上方。
「九點八公斤,」他說,又往空隙裡加了一塊小磚頭,「十點一。夠了。」
我啞然地盯著那截被磚頭擠壓的手骨,一道奇異的光澤從我眼前一閃而過——一枚鑽石,就戴在那骸骨的無名指上。
一時間,我突然有股衝動,想問她到底是怎麼死的。但話到了舌尖,脫口而出的卻是另一句。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六
他的手明顯停頓了一下。
「她喜歡跳舞,」可他始終沒有抬頭,只是繼續低頭封好盒子,「華爾滋。那種舞步,我從來都學不來。」
「我們只跳過一次。」
男子站起身,拍了拍褲管上的灰塵。來吧,該結束今晚了。他說。
他拎著那個盒子,走向數字二十七所懸掛的位置,將長廊取來的金屬梯搭好後便爬了上去。一隻手抓著護欄保持平衡,另一隻手俐落地解開懸掛著白布的鋼索。
我在一旁伸手接住,被那股重量幾乎壓得後退一步。十公斤——我緊緊抱著它,感受著這許久未見的重量,我的指尖能清晰描摹畫框堅硬的稜角,聞到那隱約的亞麻仁油氣味。
而那裝滿磚塊與手骨的方盒,則被男人固定在掛勾上。接著,它在沉悶的機械聲中緩緩升起,最終隱入高處那無數懸浮的陰影之中。
我們在黑暗之中凝視著那副景象。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男人從梯上下來,轉過頭看著我,「不打開來確認一下?」
我低頭看著懷中的東西,白布包裹得很緊,我看不到裡面。
但此刻艾格娜就在我身邊,就在我的懷裡。
「我不知道,」我輕聲說,「我從來都還沒想好。」
【後記】
[1] 古希臘有個癡情的音樂家奧菲斯(Orpheus),他在新婚之夜痛失愛妻尤麗狄絲(Eurydice),他請求冥王黑帝士讓他妻子回到人世。
[2] 超新星(Supernova)爆炸。大質量恆星在演化末期,因無法支撐自身的重力而發生劇烈的核心坍縮。在極短的時間內,恆星內部的核融合反應會瘋狂加速,將輕元素一路合成為較重的元素(如:碳、氧、矽、鐵)。
[3] 天文學界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們皆由星塵所鑄」 (We are made of starstuff)
[4] 靈魂的重量。源自 1907 年美國醫生 Duncan MacDougall 的實驗,他測量了多位病人在死亡瞬間減輕的體重,聲稱靈魂的平均重量為 21.3 公克。
[5] 利物浦舊港區的核心建築,建於 1846 年。它見證了利物浦最輝煌的航運時代與奴隸貿易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