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十一偽簡《五紀》用“建星”宿名即知其偽
清華簡十一偽簡《五紀》用“建星”宿名即知其偽
在2021年12月17日,坊間出版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只收錄一個短篇,還算不上是中篇的文章叫做《五紀》,有130支簡及約3000字組成。但其內容蕪雜,構造混亂,後語不對前言,不成體系,己有研究者指出:
『《五紀》篇內容較之於《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或者《管子》中的《幼官》都頗為不及。類似於《五紀》這樣的系統構築,隨便什麼人每天都可以編出無數個來,但無論編出多少,這些系統都自然屬於無功用。』(子居:清華簡十一《五紀》解析).
但更糟糕的,它還是一篇今人寫成的偽簡,吾人前有《清華十一偽簡《五紀》誤用『文后』一辭而露偽》己稍言其偽之一端。
如今,更要舉偽簡《五紀》內,記錄二十八星宿時,一見其用了“建星”以表示原應採用當日戰國時楚國全境所使用的“斗”(南斗),而錯誤引用了周朝至秦漢北方中國中原本部使用的“建星”。
因為這個作偽文本的寫手,主要只是抄了屬於中原系統的北方《呂氏春秋》(《禮記‧月令》乃漢人依呂氏春秋而作)及《史記‧律書》),而沒有廣搜作偽材料,隨便應付上級交辨的寫偽文任務,沒去求備於戰國楚國的二十八宿方面的各種出土文物內的記載,致使寫出的《五紀》,一見即露出其必不是所謂楚人的楚簡之偽跡,即便偽簡上用的是滿滿的假古楚文字,也更加證明是今人作偽仿筆的,於今細說道來。
二十八宿的齊全,首出現在出土文物上,見於戰國前期的曾侯乙墓裡出土的一個漆箱上蓋,於北方中原所用的“建星“宿,寫的是“斗“宿。
“建星”和“斗”是完全不同的星宿,但因為位置靠近,且都是六顆星組成,“斗“宿多位於黃道外側,而“建星”宿位於黃道內側。楚人是使用“斗”(南斗)而不用”建星”宿立宿,像是楚國附庸的曾國就使用“斗”宿,而到了秦統一之後,在原屬於戰國楚國國境的出土竹簡,如睡虎地的,如周家台的秦代竹簡,仍依戰國楚國的舊貫,使用的是”斗”宿,而不用“建星”宿。直到西漢前期,於舊楚地封諸侯王的淮南王劉安招門下寫成的《淮南子》裡,仍是用戰國楚國的“斗”宿。即使到了司馬遷《史記‧天官書》亦言“南斗”而己。
而北方中原周王朝系,則使用的是“建星”宿而沒有用南方荊蠻楚地用的“斗”(南斗)宿,所以,最早記錄周用“建星”的《國語‧周語下》,提到了“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建星”宿名,首見於周朝王家用語。其後戰國末年北方秦國《呂氏春秋》亦言“建星”但也言及“斗”,而《史記‧律書》又和《史記‧天官書》有異,言”建星”了。
於此一見,即知,如果《五紀》是戰國時代楚人所寫,那麼他寫的有關二十八宿裡的“斗”宿,一定是依楚人認作常識的以“斗”宿立宿,而不會寫成北方中原的與其生活上素不相習的“建星”。因為,出土楚竹簡,能有這些思想著作的,都係國君及貴族墓地,平民沒有資本及閒情及門路去抄取這海量竹簡,而真正如係出土竹簡,則以奉行保守傳統的國君及貴族的純正當時主流學說的時代價值,如曾國國君乙的墓裡的漆箱蓋上的二十八宿名及寫法,必為皇家御定認可的二十八宿名,但看一看,《五紀》其它二十七星宿名裡,竟還有去抄西漢成書的《爾雅》裡的,如:氐宿抄《爾雅》的異名“天根”宿,擺明了就是偽作了。
如此看來,就《五紀》篇所談及的二十八宿,乃是抄了不是楚地的北方中原用語的現代偽竹簡寫手,只是參考了《呂氏春秋》及《史記‧律書》的資料而寫下了此一《五紀》文本內有關二十八宿的內容。正見清華簡十一輯裡的《五紀》,就是今人不明戰國楚地的二十八宿宿名為何物之下寫下的外行偽文一篇了。(劉有恒,2025.9.10)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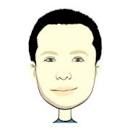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