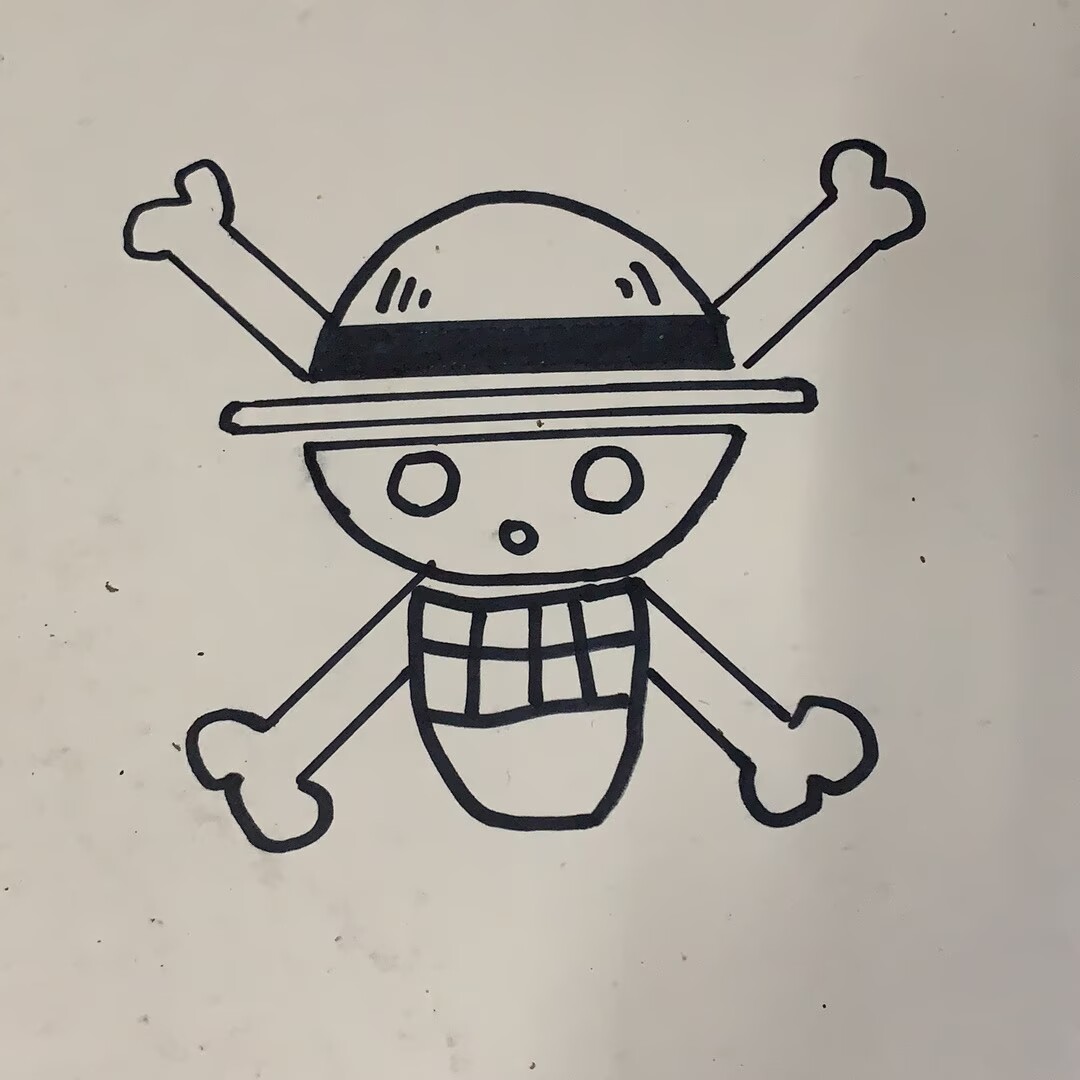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我松开白露的那一刻,能感觉包厢里的空气变得沉沉的——就像屋子刚被切换成了暖气模式,热度从我们眉毛下悄悄升起,即使没人动,也有一种“什么刚燃过”的感觉。
这不是情绪所致,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每次大脑全面打开,排热都会加速,尤其刚刚那类“不能被留下任何记录的脑波对接”,我得用整套神经深层调节系统,建立一圈在物理层都能测出温差的感知屏障。
散热、控频、削弱广播性——每一环都得像在雕金属微型芯片那样,一毫米都不许出界。
这一次又比平常更麻烦。
▍日常高强度检索时,我大脑功率也不超过20%;
▍哪怕是像刚才那样,接管白露的意识,也只是多走掉一点能量;
▍可唯独控制“双端不发散、阻断一切广播信号”的信息墙功能,耗的,是根本不能持续的那种力气
所以真正把身体点燃的,是「构建“绝对封闭意识墙”」的过程:
那道在她与我之间、在现实世界与神经波之间、在本就被联邦全面监控的语言夹缝中——人为洇出一笔真正“无记录”的空白页,这才是真的代价。
这种事,合不合法?——以法律量词算,“入侵”他人大脑是明文禁令,属于重罪。
但只要对方自主授意、途径合规,就不会被记录为犯罪。
我不是滥用。我是经过请示——只是这请示,剩下的世界无权记录她才是那声“允许”的出口者。
当然,这种能力不是谁都有。
甚至连“想”使用都不可能出现在普通人类的大脑里。
进入新人类纪年之后,世界上就没有“犯案”的人这个词了。
你会以为这句话是修辞,其实不是。
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类,几乎早已不再掌握自己全部的行为主导权。
l 他们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而是因为脑中有AI在旁边看着;
l 哪怕关掉AI,人也不会真动什么歪心思——因为记忆一旦同步回云端,那段“断网时”的一举一动,还是会原样被写进个人档案里,没有人躲得过去。
l 更何况他们已经不会“管理世界”了——一切皆由系统安排,他们连判断什么是“坏”的条件都没有。
你说人类开始变乖了,其实没有。
你说系统让人类更善良了,倒也不全是。
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再起恶意。
有些洁净,不是自省来的,是系统替他们把脏手扳开了。
物资的获取完全由系统按需分配,不经过任何人的干预,也无需身份、层级认证,更不存在特权审批或优待照顾。
于是——连犯错的接口,也不再存在。
▍不是所有人都成了天使,
▍而是地狱的大门,已经从制度上焊死了。
但我不在这类结构里。
先驱者,是系统之外的、不可被自动干预的大脑建构体。我之所以——还会觉得热、怕暴露、怕失控——正是因为,我还握着决策权。
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是因为被管住才不出格。我们是明知道能做,也知道怎么做,但还是一条条给自己划红线,靠自己一刻不松地守着那条底线。
我们之中,还留着一些“会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不是被程序限定行为走向的那类人类。我有权限,也有能力,越线。我能做的事太多,所以每一步该做到什么程度、何时停下,都得自己拿捏好。
我心里清楚,世界并不安全——不是针对他人,而是对我这种人。
除我之外,还有2000位比我更强的先驱者,他们分布在系统的每一道结构高位。我无法确定,如我刚才那次操作,即便彻底屏蔽了梦露,也是否真的能避过那些游离在文明监测器之外的高维目光。
人的气息,可以藏。
意识的涌点,也可沉。
可先驱之间——一瞬链接泄出的心律节奏,哪怕不是被看见,而只是在远处“被感觉”到,都可能成为一串“你是不是动了什么”的指纹证据。
所以,那道信息墙,最多能维持五分钟。
我自设了规则:每次调取张振山的记忆,都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一到,就必须立刻在深层记忆区重新封存。这不是梦露在干预,而是我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否则,那段被唤醒的记忆,可能会被无声地扫描到,从而暴露我的搜索痕迹。
今天这些风险,不是第一次。我早在完成湖南5378位受审者的搜索后,就执行过一次这样的隐匿环节。今天,这是第二次。
张振山相关的记忆,此刻正被我暂时压在意识浅层,像一块带热度的铁,等着被再次彻底封存。我必须抓住这几分钟,在思维广播完全被隔绝的短暂窗口里,把接下来的三步计划,清晰地在脑中构建完毕。
接下来三步计划,必须快速执行:
一、继续扩大ID覆盖面
湖南一省,5378人,还不够。
我下一轮打算调取的,是我过往亲自处理过的全部 中国籍审查对象:超过8万人 。
我的搜索将最终覆盖我作为追溯案件审查官,亲手处理过的全部42万名受审者。这些档案,不分国籍,囊括了地球上所有可能存在的因果轨迹。
或者说,直到我能百分百确认,在世全人类的ID都已在我手中。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张振山。如果他真的存在,就绝不可能在40多万人的记忆缝隙里,连一个影子都没留下。
二、启动项目提案:「梦回湖南」
我会向联邦递交一份项目申请,代号叫:
梦回湖南
我会将它打造成一个诱饵,只等着张振山自己走进来。
三、飞往真相之塔
除此之外,我将前往一颗名为“真相之塔”的星球,寻求一位老朋友的帮助。
他叫刘烬生,人称“炼狱追光”的先驱者,也是人类事务委员会中的一员,还是“真相之塔”的领主。
随后我立即进行下了一轮封印。
思维里的热还未褪去,气温尚余,我已从储能引导链中抽出下一次唤醒结构的预编模组。
从这一秒开始,再无一句记录,再无一点外放。
我再次切断了自己。
“老婆,”我靠近她,轻轻地,像是在说一样寻常的事,“我打算……直接把三胎的权限全买了。”
“今晚,咱们就——抓紧造人。”
白露正埋头搅着杯里的茶。她的动作忽然一顿,像没听懂,又像没确定我是不是在认真的。
她缓缓抬起头:“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避开她的目光,笑着耸了耸肩:“CZ币多到发霉,不如拿来投资点靠谱的项目。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早点有孩子才好吗?”
她盯着我几秒钟,又抿了一口茶,像在确认我说这句话背后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片刻后,她有些迟疑地笑了:“你这也太夸张……直接买三胎,是想让我一次怀三胞胎吗?”
我举手发誓:“绝对不是,绝对不强迫老婆一次性打三份工。一胎一胎来,咱走经典剧本路线。”
她放下杯子:“那你买三胎权限干什么?”
“备着嘛。”我笑,“买了不生也行,就当抢个早鸟票。”
她靠到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了一会儿:“我不是反对……其实从很早之前就想过,如果真能生出一个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某些事……就真的能重新开始一次了。”
我没说话,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
“可你一直说,工作不结束,你做不了一个合格的父亲。”白露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点点小心翼翼的锋利。
“还是没结束啊。”我说,“但有时候,也许不是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才开始生活。”
“哦?你什么时候也被文艺感染了?”白露一挑眉,反手弹了我一下,“什么叫‘生活’?你不是还欠我一个星球没盖好吗?”
“行。”我举起另一只手,“等我退休那天,梦幻星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第一居民就是我们俩加孩子。”
“那先别搞三胎工程了。”她笑,“我们……先走一胎试运行吧。”
“行,全听老婆部署。”
“那这第一胎你先给取个名?”她忽然问我。
我摸了摸下巴:“叫张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白露一歪头:“怎么就默认是儿子了?凭什么你说了算了?”
我装作思考状:“我只是……预判老婆的旨意啊。”
“什么预判,性别都想管?你是要我怀孕前签出生顺序的承诺书?”她瞪我一眼。
“不是不是不是,听老婆的全听老婆的。”
“哼。”她翻了个身,“你这个滑头。”
“那你想生个女儿?”我问,“可以叫张灵…”
“行了。”她打断我,笑着摇头,“我只是试试你态度呢。其实我也想第一胎是男孩。咱俩都太理性了,偶尔也想来点原始冲动。”
“老婆你说的这种‘原始’,是自然狂野那种,还是吵架吵到凌晨然后意外中招那种?”
“滚。”她扑过来打了我一下,声音却藏不住笑意。
过了一会儿,她靠到我肩上,忽然语气收了点:“张扬,说认真点。”
“嗯。”
她看着我,眉心微蹙:“……但按新时代传统,受孕时往往都开着AI辅助,才能最大程度确保性别和基因优选。以前,每次我们都必须关掉梦露和思扬,为了……那一点私密。可如果不开……”
“罢了。”她顿了顿,语气更加郑重:“我不想人工受孕,也不做优选结构了。性别随缘,基因缺陷也不动。我们不替他选命。”
“我明白。”我说,“孩子属于他自己。我们只是……先让他来一趟。”
她轻轻笑了:“你现在说得这么好听,到时候你儿子成天跟你打嘴仗,看你还是不是这语气。”
“那我们就生俩,供他互殴。”
“你……真的是……”她转头看我,“你怎么总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不正经吗?”我看着她,微微一笑,“也许吧。只怪我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脸,说什么都像在逗你玩。”
她没有回我,只是把我的手轻轻收进袖子里,声音带着一点没讲完的倦:
“好啦...去街上溜达溜达回家吧。”
隔天一早,我起得比预定时间要早一个小时。
我和白露昨夜达成的“甜蜜共识”,一夜之间就……有了“结果”。
我主动唤醒梦露,在它启动的瞬间,文件已编号归档,只等我点击提交。
我先向人类事务委员会远程提交了《梦回湖南》项目申请。待委员会通过后,我才启程飞往联邦总部。
我从长沙启程,沿跨洋航道向东飞行,抵达联邦总部时,朝阳刚刚挣脱地平线。清晨的光线被空气过滤得极其柔和,显得深邃而寂静。
联邦公共叙事与文化传播局在三楼。我走进去时,崔松旺正低头处理着一份全息文件。他是人类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掌管着Apollo主脑的最高调用权限。
"张扬?你来得可真快。"他抬起头,眼神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委员会早上才批了你的项目申请,没想到你就过来了。效率真高。"
我把《梦回湖南》的项目细则递过去。
他翻了翻,眉心微蹙,指尖在空中虚点几下,调出了项目的核心标签:"嗯,文化记忆复现。你一个审查官,怎么突然对这种‘软性’的考古感兴趣了?"
"寻根。"我答,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
他看了我几秒,没再追问。他将文件直接交给了Apollo,同时下达指令:"预算不小啊,烧这么多CZ币,确定不心疼?"
"嗯,确定。"我点头。
崔松旺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向Apollo下达了指令。
这份项目,从流程到提案,每一处都符合联邦规定,任何算法检测都查不出丝毫越轨。就算他心存疑虑,但在这套以CZ币为契约核心的制度下,我们之间只有甲乙方的雇佣关系,他无权对我这个“消费者”的私有意志进行干涉。
而我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给数千万人写了一封邀请函,让他们把最珍贵的记忆交出来。而我真正要的,只是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个ID。
这是一场仿佛晨雾的伪装。
白露没有一起来。她回家,准备前往真相之塔的另一程。
执行阶段,只剩下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