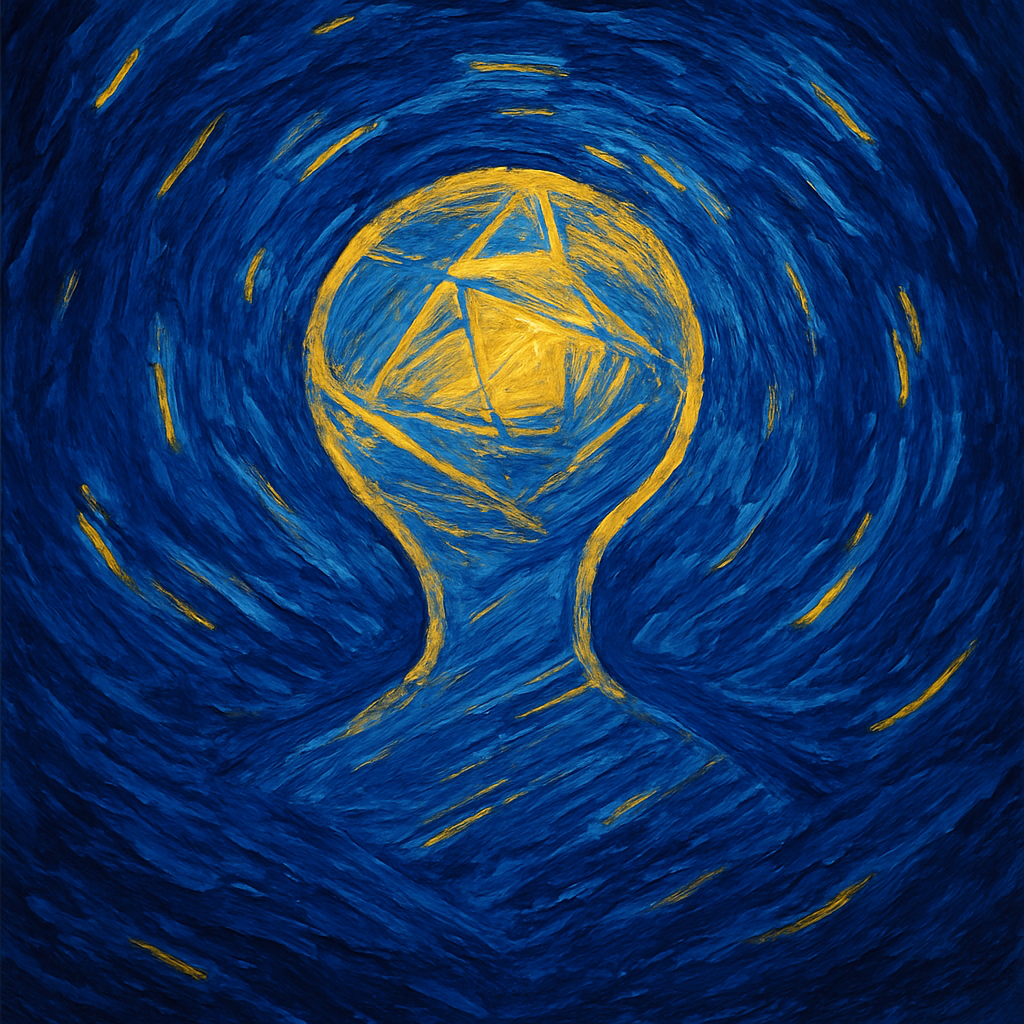召喚愛人的眼睛
召喚愛人的眼睛
——有些飛蛾就是不會飛的,那又怎樣呢?
序
我很小的時候愛過一個不存在的人。
雖然小,但我當然知道他是不存在的,白天念書的時候我很少去構思他。 但當夜色籠罩萬物,他就是我的星星。 他指引我、陪伴我、看見我。
我記得那時沉迷於買精緻的信紙,沉迷於買鋼筆和五顏六色的墨水,一切必須搭配地恰到好處,才能把自己的心意告訴他。
至於他的回信,則必須用另一支筆、另一種顏色的紙,還有另一種心情來寫。
我自覺愛得很深,也因為他我做到了很多事情。 在他之前我像一粒沙,而他打磨我,讓我有了稜角和形狀。 透過他的眼睛看我自己。
第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是一顆鑽石。
寫到這,還是很可惜這個故事沒有圓滿的結局。
或者說,在我和他之間,什麼樣的結局才是完美的結局呢?
我記得的事實是:愛衰減地很快,不到一年。 臥室的角落裡堆疊大量空白的信紙,和再也不會拆封的墨水瓶子。 這些信紙和墨水被媽媽練字慢慢用掉了。
但這件事,這個虛構的人,卻以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方式,始終留在我的生活中。
一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想起他了,我只是對他曾經的存在保持一種“理性的覺知”。 他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我的人生非常明確分成了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
但感性上這個人相關的一切已經激不起上班族麻木的內心了。 設定里我們七月二十一號相遇,曾經每到這個日子我會整理曾經你我之間的“通信”,但多次搬家雖然沒有遺失這些“珍貴文稿”,但也是成為一些壓在箱底、不再翻看、甚至疑似發黴的存在。
前幾年去英國的時候他短暫復活了一陣子,畢竟英國是我和他約定將來一起居住的地方,在去往英國的飛機上我緊閉雙眼,記起少年時候的孤單和執拗,好像在這一刻全部被回應。
重力在起飛時消失了,彷彿我全力起跳,投入了他的懷抱。
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我又一次直視他的眼睛,正視他的存在,或者說,正視我需要擺脫他對我的影響。 那時我深刻地相信,被他養育長大的我,已經來到了正確的舞臺,燈光打在我身上,我不需要再被他的影子覆蓋。
我於是鄭重地寫下最後的信件,我感謝了他曾帶給我的所有榮耀,然後提出,接下來的時間也許我可以換一種活法了,一種沒有他注視的活法。
那是 2020年,從英國短暫離開,我就被疫情困住了。
期間各種變動,所有自救和求助,均不得回復,好像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我是鑽石的日子。
二
我不記得後面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 簡單地說就是,我在變老,但無事發生。
我又找了個班上,像所有沒有被他養育過的人一樣,盼著薪水、放假、調休,早上掙扎起床,晚上熬夜看手機。
但是此時我不知道是他的聲音,還是我的聲音,彷彿黑暗中撲扇著的蛾翅。
分明沒有火,沒有讓它飛撲的東西,它卻仍舊孜孜不倦,吵鬧不休。
“是你嗎? 是你讓我不得安寧嗎? 我不是已經甩掉你了嗎? “在夢境和清醒的交界處我還是會和他交流。
“你以為我是你可以輕易甩掉的東西嗎? “他反問我:”你我本就是一體的。 ”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現在還不夠嗎? “我問他。
“從來沒有我,只有你,你自己想要成為現在這樣。 “他淡淡地說。
可是現在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錯。 “我感到委屈,這句話我好像也只能跟他說,我說這句話時露出的這個表情,也只能在他面前露出。
“是不是你的錯不重要。 “他擁抱我,用手撫摸我的頭髮。
但他的聲音是一貫的嚴厲:“重要的是你現在要做些什麼。 ”
他吼,也可能是我在吼:“快去! 你必須去! 做點什麼! ”
我睜開眼,卻無法驅散始終縈繞著我的疲憊。
我來到窗前,看到一隻被困在紗窗和窗戶之間的飛蛾。
我小時候養過蠶,知道這些醜東西靠還是幼蟲時期吃的儲備過活,一旦破繭,無法進食更無法排泄,耗空了肚子里儲備后,就只剩下一具空空如也的皮囊死去。
我小心地把它放走。
好吧,再試一次吧。 我看著它飛遠,只感到滿心的疲憊。
三
沒有人相信我能成功,就連我也不相信,雖然其中諸多波折,但我成功。
又是十幾個小時飛機,起飛前我看著窗外,腦海裡一一列舉著那些不確定性,但沒有辦法消除任何一條。
但無論如何,現在也許真的可以告別了,我和他的故事。
“此行必將坎坷。 “失去重力的那一刻我對自己說:”但這一次,我不再依靠幻想來保護、安慰或激勵自己。 ”
但此行並不坎坷。
我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和他一點都不像。
在我的想像里他是棕色眼睛、頭髮蓬亂、穿深色格子衫的人,而這個人好像宇宙故意造出的一個完全相反的版本。
這個人有一雙灰色的眼睛,看太陽時彷彿是透明的,他留著整齊的長髮,喜歡穿一切帶著塗鴉的 oversize 衣服。
這個現實中的人,我一開始並不甚關注他。 跨文化交際總是隔著重重山海,我已經老到不想在沒有投入產出比的關係上付出一絲一毫了。 當然,我們交流,說一些無害的small talk。 他試過更加親近,但什麼攔住了我。
是什麼呢? 最接近正確答案的好像是恐懼?
恐懼什麼呢?
我恐懼和他更加親近。
他身上好像有什麼會引起我警覺的東西,從見他的第一眼我就在防備自己生出非分之想。
可這個人,明明和我曾經的幻想愛人一點都不像。
但我的心卻像一隻灰色的笨重的飛蛾,它沉重的身子裡儲存著過去的養分,以至於只能扇動翅膀,發出響動,卻無法起飛。 而它,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以為這個人是火。
火,多麼美麗、搖曳的一團火焰,不熱烈,卻好像是觸手可及的溫暖,讓它心嚮往之。
心嚮往之,卻始終寂靜,畢竟,飛蛾振翅的聲音不是鳴叫,誰也不會注意它。
我無法在忽視這份心意是在一個瞬間,那時他剛從很遠的地方回來,我們很久未見。
他看見我,露出了驚喜的表情,好像有一道真實的光,出現在他的眼睛中。
這種光我見過很多次,我的幻想愛人把我養得很好,所以總有他者拿這種眼神看我,這沒有什麼。
但第一次的,我感到同樣的光從我的眼中迸發。 那一刻,而我的心是萬蝶振翅。
四
在我們逐漸接近的過程中,他看著我的眼睛迸發出一千次這樣的光。
他告訴了我一千次他在乎我,他喜歡我。
我現在看出他和我幻想愛人的共同點了。 雖然他們長相大相徑庭,他們對我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但在他們的眼裡,我都像鑽石一樣發光。
以及,我的愛衰減地都飛快。
從才開始約會的心跳加速,到逐漸平穩,再到最後的他只要開口我就在內心狂喊閉嘴。
弔詭的是,他始終在我身邊,我在他眼裡還是光芒萬丈,哪怕我穿得可以直接去要飯,哪怕我時而蠢得像豬,時而倔得像驢,哪怕我迴避所有重要的問題,哪怕我始終無法立下承諾。
我維持和他的交互,我表演出他可能想要的樣子。
男人會想要什麼呢? 他們都以為自己想要共鳴,想要琴瑟和鳴。
但拆解開來不過是想要肯定,想要陪伴,想要照顧,想要包容,想要偶爾越界的自由,也想要偶爾越界后被不輕不重地敲兩下腦門,管束管束。
人們總是說,真愛很難很難。
這些對於一個不愛他的人來說,表演真愛實在不難。
也只有表演的真愛才能讓人人豔羨,遇到過我們的人都說我們親密,說我們絕配,說我們天生一對。
這些話好像對他很受用,他好像真的對我很滿意,也很愛我。
但為什麼我感覺不到同樣的愛他?
或者說為什麼我總是覺得,還不夠呢?
我想,飛蛾始終是不會飛的,它只會震動翅膀向臆想中的火焰奔赴,心火滅了,就連翅膀也不想再扇動,更別提飛到哪裡。
我又黯淡了,甚至不如沒有跟他靠近前光亮。
但這次我在他眼裡還是亮的。
只是,這有意義嗎?
在我的幻想愛人那裡我得不到這個問題的確然答案,在他這我倒是第一次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意義。
完全沒有。
五
我還是沒有和他分開,好像我不愛他並不是和他分開的“正當理由”。
或者說,這個問題從來都不是關於我幻想中的愛人或者我現實里的愛人的,這是關於我的。
始終也是我一個人的。
無論在哪裡,和誰在一起,這個問題都只是我自己的。
我不得不正視我自己,因為如果我正視我的愛人的眼睛,我看到的自己確實是一塊光芒萬丈的鑽石,但與少年的我自己不同,我不再沉迷在端詳這塊鑽石,我湊得越來越近。
我發現這光芒萬丈的石頭每一面都是鏡子,我看到無數個我自己。
無數只極為笨重的、灰色的蛾子,它不停撲扇著翅膀,卻無法帶動笨重的身體起飛。 它的身體里擠滿了過去的汁液,也不知道這些汁液對它來說是養分還是毒素。
總有一天這些汁液會耗盡的,那時的它是一具空洞的軀殼。
還是它事實上已經被耗空了?
如果不是,為什麼我看著我曾經苦苦哀求、祈禱、召喚的愛人的眼睛,卻無法發自內心擠出一絲微笑?
那些我在沒有和他在一起時的心意彷彿還歷歷在目,那時我和他沒有真實的交互,每一次靠近我五感全開,每一顆神經細胞都在解析他的話語、表情和他身上的味道。 這些破碎的資訊被我存入身體里,在夜深人靜的時刻重播。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渴望與愛反倒不像是最主要的,如果非要描述,那便是:
我在沉淪一場從未被共謀的沉淪。
一種全然自給自足的幻想迴圈。
一種甚至羞於承認的慾望。
這些感覺,鮮濃地像玉液瓊漿,讓我確然地感覺到。
我是。
存在的。
現在,依舊是夜深人靜,他就在我的身邊。
他並沒有變,他還是火焰,是美麗、搖曳的一團火焰,溫暖又觸手可及。 他的表情裡從沒有怠慢,他從不曾說過重話。 隨著我每一次呼吸,我都能聞到他清新得好像海風。 只是我現在知道那是香水和須後水。
“你真的存在嗎? “我輕輕地問他。
六
他當然是存在的。
只是,第一次地,我意識到我看不見他的存在,我總說我在表演,表演他可能想要的樣子,但我的表演從來都是給我一個人看的。
“他可能想要的樣子”,這句表述倒是還挺客觀,從一開始就在暗示我始終遵循的都是自己的標準。
那他呢? 他在表演他以為的「我可能想要的樣子」嗎? 那些花、那些吻、那些話,總不可能完全沒有在演吧?
如果我們本質都是在表演,那我們真的可以看見彼此的存在嗎?
或者,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真的可以看見我們自己嗎? 這段關係是讓我們變得更加真實了,還是更加虛幻了呢?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也許我應該一個人待著。
也許我們應該分開一段時間。 “在某次我得到機會去異地一段時間時,我這麼對他說。
我感到繼續表演的報酬,即他的反饋,好像始終不夠,不足夠支撐起我鋪天蓋地的疲憊。
疲憊,又是那種疲憊,我記得在我還在國內的那個清晨,我放出一隻被困住的飛蛾,決定要再試一次。
那時我的心中,也是這種疲憊。
“我不理解。 “他大驚失色:”我以為我們都在經歷最好的一段感情。 ”
“確實是最好的。 “這是客觀事實,我一邊說一邊在確認自己沒有習慣性演出:”但是可能,於我來說,還是不夠吧。 ”
“哪裡不夠,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保證。 “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我第一次在他的臉上讀出了慌亂。
這慌亂只讓我覺得厭煩。
“請你讓我一個人靜一靜。 “我把手收回來抱在胸前。
“好,但我們會談的,是嗎? 這不公平,我至少值得一次開誠布公交談的機會。 “他還是那麼貼心,立刻不再逼迫我。
“是的,我們會談的。 “我好像又在表演,因為我其實並不想和他談。
如果可以,我這輩子都不想再見到他。
分開后我立刻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好像這個曾經讓我那麼渴求的人不曾存在過,如果非要說他是存在的,那他的存在是讓我感到羞恥的:我曾經竟然真切地去渴望過一個那麼普通的人? 但他卻遲遲不可能放棄。 他開車來我的城市,記得我的生日,送曾經我提到過想要的首飾。
我只覺得厭煩,曾經我演出的獨角戲讓他誤以為是雙人舞,但現在確確實實是他自己的獨角戲了。
“請你不要再給我送東西了。 “我和他說。
“我們應該談談,你保證過我們會談的。 “他的頭髮不再梳理整齊了,亂髮遮住了他的眼睛。
“你不需要再演了。 “我握著拳,手指甲深深嵌入手掌心裡:”已經結束了。 ”
“演什麼? “他疑惑。
“演你難過,演你離不開我,演你還愛我。 “我不耐煩地看著他的亂髮,他非要把自己弄成這幅落魄的樣子,想讓我共情他的痛苦嗎? 真是狡猾。
“該死! 我沒有在假裝! “他猛得錘了一下桌子,隨即立刻沮喪地垂下了頭:”對不起,我只是感覺很不好。 ”
他好像不是裝的,我感到自己的臉上不可抑制地出現震驚的表情。
我現在也感覺不太好了。
七
我伸出手,輕輕觸摸他的臉,好像我第一次看見他,好像我之前不認識他。
那些話語,那些花朵,那些包容,那些溫柔地,看著我的眼神,都是真的?
其實我知道它們是真的,但我只是覺得這些東西更像一種獎勵。
因為我乖巧,因為我善解人意,因為我演出了他“也許想要”的樣子,所以作為觀眾他理所當然要給我獎勵。
現在我已經不再演了,他還在給我獎勵,他是真的愛我,還是想讓我繼續表演?
可是你從來不曾看見過我。 “我說,感到異常沉重的悲傷:”如果你看見真正的我,你不會再愛我的。 ”
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發覺我露出了那個表情,那個只有對著我幻想中愛人才會露出的表情。
“該死,我好像真的是愛他的。 “我的心此刻又充滿恐懼,就像我才認識他時那種不敢接近的恐懼。
只是此時我才認識到,我恐懼的並不是我對他有非分之想,我恐懼的是我會愛他,我會愛他到把自己的全部展露出來。
這些陰暗黏濕的自卑和羞恥,相信自己不值得被愛也無法去愛的幼稚信念,那些不夠獨立、不夠自愛、不夠正面的,無法啟齒的擔憂和欲念。
這一刻,在我的臉上,暴露無遺。
他看見了,他現在肯定看見了,透過我纖薄的鑽石外殼,他看見了一隻笨重的醜陋的,無法飛行的蛾子。
我內心始終無法停止的蛾子撲翅的聲音,他肯定也聽到了。
我大概是完了。
八
他久久沒有回答,我不自在地椅子上調整著我的姿勢,雙手想要緊緊握住面前的杯子,卻又不想再進一步被他看穿,只能盡了全力讓手指僵直地套在杯子上。
我想到我們第一次約會,我也是這樣,盡了全力讓手指僵直地套在杯子上。
那時我卯足了勁兒在思考接下來應該說什麼,做什麼。
而他那時只是在笑。
“這不公平。 “他輕輕說,打破了幻境。
我看著他,他突然很詭異地笑了出來,我感到一陣緊張。
“是你在傷害我! “他終於卸下了一副包容克制的面具:”你憑什麼喊痛? ”
“你憑什麼暗示是我無法愛真正的你? 他誇張地在空氣中用手指比引號。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反駁。
“那你是什麼什麼意思? 你指望我相信真正的你是一團糟嗎? “他還在比引號,好像那是對我非常了不得的攻擊。
“是啊! 我就是一團糟啊! “這攻擊確實非常了不得,我發現我自己提高了音量。
“那又怎麼樣,誰不是一團糟? ”他也提高了音量。
一時間,我和他都狠狠瞪著對方。
“那你想怎麼樣? “我眯起眼睛,我的幻想愛人在對我不滿時也會有這個表情。
“我想你愛我! “他吼,然後不自在地停頓了一下,半響,他的聲音恢復了一些往日的溫和:”我知道我不能要求這一點,但你問我想怎麼樣,那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你愛我。 ”
說罷,他羞愧地低下了頭。
空氣彷彿凝滯了,我每呼吸一下就感到心臟一陣緊縮。
剛才發生了什麼?
我內心的這股衝動是什麼?
好像站起來是對的,那就站起來。
好像走向他是對的,那就走向他。
在我還沒有意識到緣由的前一秒,我抱住了他。
在我觸碰到他那一瞬間,時間恢復了流動,我聽見他的呼吸,我看見他悲戚的臉,我懷中是他的溫度。
我胸口的跳動感受到他胸口的跳動。
像兩隻飛蛾,在一起扇動翅膀。
終章
我愛他嗎?
我當然愛他,我比我想像地要更愛他。
我曾經以為我愛的是愛人眼睛里的自己,那個光芒萬丈的,鑽石一樣的自己。 他只是鏡子,他折射出我不可說的欲念,像火吸引飛蛾一樣吸引我。
但現在我知道了,哪怕在我最不誠摯的瞬間,在內心最深處與邏輯無關的角落,也燃燒著最真摯的愛火。
是的,這團火焰,我曾經那麼被吸引的,那麼恰到好處溫暖我的火焰,也不是他,是我自己的,是我自己不知怎的從飛蛾那笨重的身軀裡,那些過去的汁液,不知是養分還是毒素,慢慢釀化出的火焰。
這火焰污濁又沉重,是慾望,但也是希望,它穿破生而為人無法擺脫的疲憊,在絕境處讓它仍有再振動一次翅膀的意志。
只是我錯了,我一直以為振翅就要飛翔的。
但也許有的蛾子天生就是不會飛,我們笨重、巨大、躲在陰暗的角落裡,甚至不嚮往光明。
光明里的美麗蝴蝶被釘在玻璃鏡框裡任人觀賞,就像曾經我們展出的“愛情”,輕靈又空洞。 它也沒有振翅高飛,帶我們走向哪裡,因為它是沉默的,是死的。
在光明裡我可以繼續像死了一樣沉默,不是所有的話語都可以訴說。
但我們需要彼此。
我們需要彼此在黑暗中輕輕地振翅聲,那不是我們試圖飛翔。
那是我們在交流。
是我們在彼此看見彼此的存在。
所以你,我的愛人,還有我自己的心。
世界可以讓我沉默,讓我偽裝,讓我用心力燃燒成火焰,驅動它日復一日的運轉。
但在我亙古的黑暗中,我想要被回應。
我再也不要在這一點上沉默。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