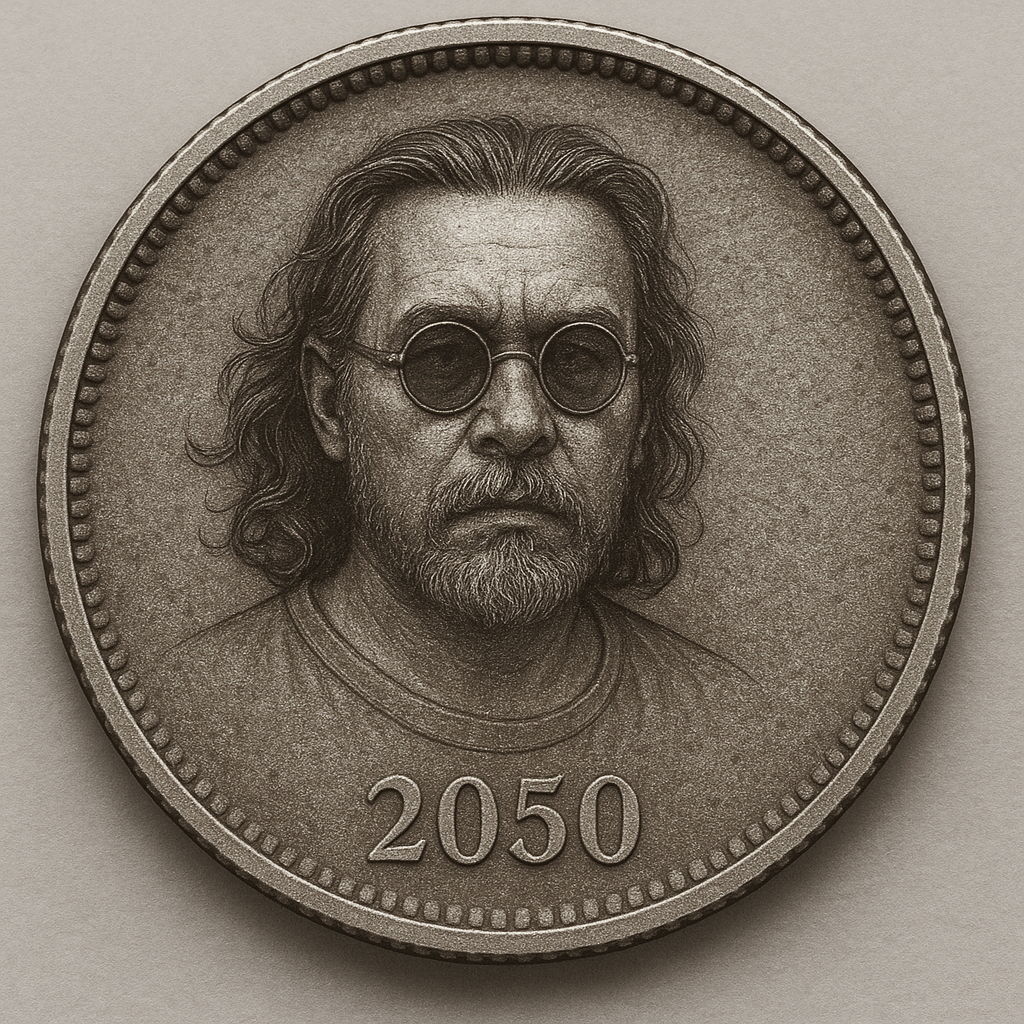被繁華掩埋的根:安邦新村的未竟故事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九龍城吧?那裡亂到沒天沒地,新村跟它很像,只不過我們的是「補平版」的九龍城。九龍城是一棵瘋長的野藤,新村是土壤裡掙扎的根。表面看似整齊,其實隨時能冒出岔枝——房子、學校、工廠、店舖、神廟、茶室、雜貨檔,拼湊成一個凌亂卻完整的社會,靠的不是官府,而是自生自滅的本能。
八十年代,我成長的時候,新村不是三不管之地,只是「少管」。家家戶戶大門整天敞開,晚上睡覺才扣上,從來不操心。
有一次,街尾有人辦喜事,大家全村跑去吃喜酒,結果他家卻進了賊。沒幾天,又有人半夜喊「賊啊!」,全村人立刻衝出來,把臭水溝都翻開,像要照X光。最後乾脆組成自衛隊,每晚輪流巡邏。這隊伍到今天還在,只是工作換了:從追賊變成廟會或遊行裡的秩序維持。這就是新村的邏輯——公權力很少介入,大家被逼練出一身自治功夫。
這樣的新村,全馬各地都有。吉隆坡近郊更是被新村包圍。就是靠這些人,一手一腳,把整個吉隆城建起來的。七十到九十年代,吉隆坡的發展雖比不上亞洲四小龍,也緊追在後。九十年代中期,建設飽和,新村角色從「勞力庫」變成「絆腳石」。官話叫「發展」,土話叫「鏟除」。
安邦新村,從前是吉隆坡第二大新村,如今只剩幾條街。全馬最大的是曾江新村。但大小根本不重要,命運都一樣:被圈起來、被用盡、再被拆掉。
我寫安邦新村,不是替它唱安魂曲,而是不想讓它靜靜坐化。至少,它的消逝不能無聲。不要為了表面上的繁華而忘本。一座城市如果忘了新村,就等於忘了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
——

每次經過公園,老鄰居總要喊我名字。
有時一句:「吃飯啊?!」
我心情好,就回:「你傾偈呀?」
他是我父親那一輩的人,我不能直呼其名。於是我永遠只能當一部二手點唱機,接收信號播歌。
公園不大,兩個籃球場,幾棵老雨樹,一條走道。人家說,新村有多久,它就有多久。官方版本是英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方便召集居民。方便個屁,其實是方便管制。那幾棵號稱「百年老樹」的雨樹,還是從非洲進口的。葉子再大,也遮不住歷史的疤痕。
公園的地契屬教會,對面的教堂從一層變三層。天越蓋越高,人卻越坐越低。市政府最近還加了亭子,老人卻不進去,寧可搬一張破椅子坐在自己的影子裡。因為影子是自己的,亭子是別人的。
疫情之前,他們還各有茶室,分幫結伙喝咖啡聊是非。疫情一來,茶室一間間倒閉。物價飛漲,退休的人四面八方湧到公園,就像雨水流到最低處,慢慢積成一灘。
清晨是太極的天下;週末球場租給國際學校;市政府偶爾搞活動,招不到人,就把阿伯們當臨時演員。最熱鬧的是星期五晚上,Zumba舞蹈一開,阿姨們扭得慢半拍,阿伯們坐旁邊偷看。沒有掌聲,沒有喝采,氣氛卻曖昧得要命。
平常,他們發呆、滑手機、聊賭博。你一走近,他們就收聲;你一走遠,聲浪又冒出來。像池塘的青蛙,怕人聽見,又忍不住要叫。
更殘酷的是,他們在這裡慢慢告別。每隔幾個月,就有人在樹下「坐化」。叫不醒,救護車來,機車飛出去找親人,最後只剩一張空椅子。沒有哀樂,沒有儀式,大家見怪不怪。
所以,這公園不是普通的公園。它是茶室,是舞廳,是會所,也是最後的候車室。一代代人來了又走,只有老樹和走道,記得他們的呼吸。
FB上有個頻道,專門採訪市區的露宿者。問題土得要命:「你露宿多久?現在的生活打幾分?要是一百萬到手,你想做什麼?」聽起來像小學生作文題,可答案往往比主持人聰明,句句帶火花。
看了我也心癢,想學一學。不是模仿露宿者,而是模仿提問的人——跑去公園,把這些阿伯阿姨一個個採訪下來。問題不用複雜,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只是有個難題:我要先克服自己的內向。寫文章容易,字能擋臉;可一旦舉起麥克風,喉嚨就打結。
可想一想,這些老人都是村裡長大的,住了一輩子,從工廠下崗到茶室散場,再一路坐到公園。他們的人生故事,串起來就是一部新村傳奇,比宮鬥還真誠,比歷史課本還荒唐。
如果真拍下來,收集、整理,剪成九十分鐘,上影線都不是問題。那時它既是紀錄片,也是見證。
問題是——誰要跟我一起?我器材都有,就差一顆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