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書之一|標記回憶|下不了班的心
誰真的喜歡上班?
偏偏我,看起來還挺喜歡的。就像那些我曾經仰望的人一樣,那些前輩們,他們都沒有抱怨,每天都會出現,穿得整齊,說話有條理,時間被填得滿滿的,連疲憊都有種體面感。
我害怕我無法下班,永遠被困在辦公室。一格一格的格子間像透明的牢籠,每天把白天吞得乾乾淨淨。
時間拖晚了,錯過孩子的傍晚和夜晚,錯過他今天最喜歡的一個問題,最想分享的一個發現。每次回家,疲憊地沖完澡,頭髮還滴著水,總會看到他窩在玩具堆裡等我。像一個小小的燈,留給我自己點燃。那一刻,我不是想睡,而是覺得抱歉。
現在的我裝得太像了,像極了我年輕時在辦公大樓外仰望的那些大人:套裝筆挺、步伐穩重、眼神堅定,像是知道自己人生要往哪裡走。那個看起來走得很穩的大人。我也有份簡報、無數個會議、固定午餐時間、茶水間的禮貌微笑。甚至還會笑別人說的辦公室小八卦,像是真的在意似的。然後時間一到,我就開始看表,看著那條假想的回家路,心已經提早走了。但依然面對做不完
我怕的從來不是工作本身,是那種「我以為我只是暫時在這裡待著,卻變成永遠」的感覺。
有時候我會停下來問自己:我真的那麼討厭工作嗎?還是我只是無法忍受時間被規劃得死死的、好像每一分鐘都得有產值?
其實我不討厭工作的本質。我喜歡完成事情的感覺,也喜歡把東西做得更好,這些年我做得一直不錯,不是因為逼自己,而是因為我真的有一部分喜歡。可我越做越好,心裡卻越來越累,像是被什麼拖住了,不知道是責任,還是我自己建出來的一個牢。
正好今天包包的書裡上面寫著寫著:「當一個人無法活在與他自己內在經驗一致的情境中時,他就必須扭曲或否認自己的經驗,來適應外在的期待。」看到這邊,車剛好到站了。那不就是現在我想談論的主題嗎?我每天表現得像個稱職的大人,但那不是我全部的經驗,我還有疲憊、遺憾、對自由的渴望,還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痛,好像人生正在穩穩地錯過什麼,而我卻無力喊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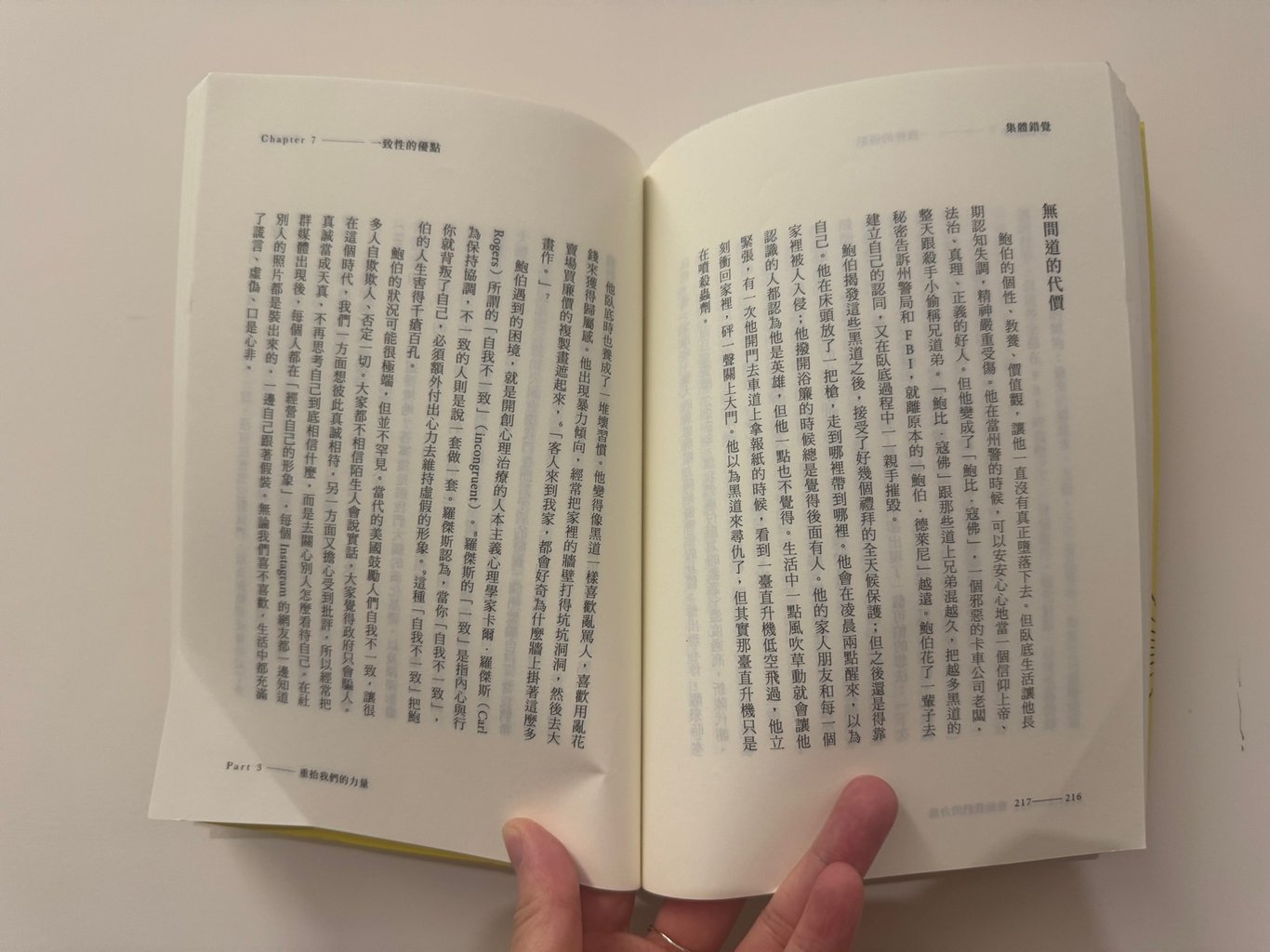
我的不一致,來自於我一邊想做得好,一邊又不想被這套機制吞掉。我既想當一個能給孩子穩定生活的大人,也想當那個會突然在下午帶他去看雲、去追公車、去問一個沒答案的問題的人。
而這兩種我,就在越奢望兩邊都做到完美時,越來越難同時存在。
其實我現在就像是學姊,了解了規則,知道哪裡可以鑽洞,可以前進可以自由,那邊要守秩序,所以過得還算順風順水,但我不是真的滿足這個規則。
剛踏入校園的新鮮人在開學的蜜月期過後,就開始感到不適應,痛苦一陣子後,上了二年級三年級,有了一定的成果和累積,我也在想,要是我在這個學校沒有取得過好成績,我是否仍可以如此泰然自如,在這邊想著奢侈的關於當個壞榜樣又是資優生的願望?
於是越是急著想畢業,就越快跳入了另一個牢籠,渴望自由,但是真的只有在困住我的牢籠裡才能爬出我想要的高度與成就嗎?
那個牢籠裡,辦公室的燈永遠白得過頭。亮得提醒你:還沒完,還不能走。冷氣忽冷忽熱,像是陰晴不定,矛盾如我總是無法安坐在這裡,但也不是總是不安,也有順風順水的時候,像在咖啡廳裡專注打字的自己,連同時間本身都冷靜得過分,產值,我成為一個完美的機器快活地幹活著。
我坐在電腦前,螢幕發出微微的藍光,把我臉照得沒什麼表情。偶爾抬頭,同事在熱烈的線上會議裡討論,有人對著Excel滑動出一張張報表,還有每個人都埋在那個最有生產力工具的PPT裡苦幹著,好像每個格子都比我們的生活還要有邏輯。
有時我會突然想到:我小孩現在在幹嘛?他是不是又把玩具車排成一條長隊伍?是不是又問了他媽一個誰也答不出來的問題?是不是哭了?是不是笑了?這些時刻我都不在。
這種「不在」不像缺席,它更像是一種逐漸習慣的消失。不是被遺忘,是慢慢地被替代。代辦事項替代了晚安故事,加班餐替代了一起吃飯的時光,連那聲「爸爸今天怎麼這麼晚」都漸漸少了,因為他知道我會晚。
那才是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什麼,而是有一天,他不再等我了,他就這樣長大了。
回到家,洗完澡出來的那一刻。
燈光是柔的,水聲剛停,世界安靜得像剛下完雨。我披著浴巾,頭髮還滴著水,腳步輕到幾乎不想驚動地板。然後我總是會看到他,我最愛的那個小人兒,窩在玩具堆裡,眼睛睜著亮晶晶的光,就那樣等著我。
無論怎麼催促都不願意回到舒服的窗上,我知道他在等哄睡,等我跟他說那個每天晚上都要講的故事,等我問他「今天過得怎麼樣」,等我把他的夢蓋好,像蓋一床被子一樣。我每次都只是走過去,停在在他身邊。他小小的身體靠過來,帶著一種完全的信任和依賴,而我那一整天被拆解的自己,才終於在那一刻重新被拼湊起來。
我不是真的討厭工作。我是怕自己一直困在那裡,錯過這些小而真實的時刻。我怕等我終於有時間了,他已經不再需要我、依賴我、等我。我怕最終不是公司奪走了我的自由,而是我親手把它交出去,用一個又一個用「應該」堆出來的現實,慢慢蓋住了我真正的渴望。
他睡著之後,我還是會回去看一下簡報。但我不再騙自己說那就是全部。我只是需要提醒自己,這些夜晚,才是真正屬於我的,不是屬於工作、不是屬於績效報告,而是屬於我和他,一起活過的那一小段時間。
所以,恐懼本身不是錯。
它沒有讓我更脆弱,它只是讓我清楚看見,我還沒麻痺,我想要什麼,還有機會活得更好的最佳解方。那些讓我不安的,不是某個具體的工作日,不是哪一場會議,而是某種失去主導權的感覺。我怕時間不是我自己的,我怕我明明還活著,卻只能在空檔裡偷偷喘氣。我怕那個看起來很好的我,早就不是我。
但越來越清楚的是,我並不是害怕工作,我是害怕那個逐漸離開真實感受的自己。我怕那個學會對孩子說「等一下」、對自己說「先忍著」的自己,會慢慢地,連恐懼都不剩。關於「不一致」的探索,也許那並不是失敗,不是一種要被矯正的狀態。它可能正是我們的線索,像一盞偏離航道的指示燈,提醒我們:你有些地方還沒對齊,你有些東西還不能放。
恐懼不是一種弱。它是我在這個日復一日的節奏裡,還能感受到的抵抗。只要我還會怕,就表示我還在意;只要我還在意,就表示我還沒放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得百分之百一致,也不確定那樣的日子長什麼樣。但我願意把這些恐懼留在心裡,像種子一樣。它提醒我,我還有感覺,還在走路,而且方向,還是朝著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