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与1807年形态的《精神现象学》的关系。一篇概览
关于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与1807年形态的《精神现象学》的关系。一篇概览
布雷迪·鲍曼(Brady Bowman)

【1】. 导言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的第一个主要著作。它于1807年付印出版,在黑格尔离开耶拿(Jena)几个月之后,自1801年以来,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紧张的哲思发展的时期,部分是与谢林(Schelling)紧密合作的。这部著作被构想为对他的哲学的体系的导论,并同时被构想为其第一个部分;《逻辑科学》应当直接地连接于其后,继之以精神的哲学与自然哲学(参见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9,447)【译注:后简称GW,即Gesammelte Werke】。这一构想没有在其完整的范围内被实现。黑格尔最晚在1812年放弃了它,并在1817年通过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一版中被呈现的体系取代了它(参见GW21,9,附注)。由此,《精神现象学》与原本应当连接于其后的《逻辑科学》的关系必然已经改变了,但可惜的是,黑格尔从未明确地规定过这已改变的关系。就这样,黑格尔研究中一个持久的谜题产生了。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因一个情况而加剧,即自《全面教学纲要》(1827)的第二版以来,一门被称为“精神现象学”的学科训练出现在主观精神的哲学之内,但是与1807年的著作相比是明显被缩减了的。【1】这一从属的状态如何与一种导论的功能,或甚至思辨的科学的一种前提预设的功能相容?这个同名的全面教学式的学科训练究竟是否与1807年被构想和被阐述的《精神现象学》是同一的?此外,自《全面教学纲要》(1827)的第二版以来,黑格尔插入了一段对“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立场”的考察,作为“更切近的导论,以便阐明并引出在此被给予逻辑学的意义和立场”(GW19,50/全面教学纲要 §25)【译注:后简称ENZ,即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最晚通过这一点,那被称为“现象学”的学科训练不是被从其导论的角色中排挤出去了吗?【2】
在同一个关联中,他也谈及了1807年出版的著作,并剖析了诸种根据,缘何早前的呈现是“纠缠不清的”,并大概因此在这里不再被偏爱作为导论(GW19,50/ENZ §25,附注)。在一种相似的意义上,他在一个后面的位置上把怀疑论考虑为一种可能的导论方法。然而,“[对]这样一种完成了的和实现了的怀疑论的要求是与此相同的,即对一切的怀疑活动,或更确切地说,对一切的彻底怀疑,亦即,对一切的完全的无前提预设性,都应当先行于科学。它实际上是在想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决断中,通过那种从一切进行抽象并把握其纯粹的抽象,即思维活动的简单性的自由,而被完成的”(GW19,90–91/ENZ §78)。由于他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曾将后者描述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GW9,56),人们就很容易猜测,黑格尔想要用这一表述来修正他早前的看法,即为了导论需要一条详尽的“怀疑的道路”或甚至是“彻底怀疑的道路”(GW9,56)。因此,事情可能看起来就好像是,《精神现象学》已经丧失了与整体的体系,并从而也与《逻辑科学》的任何体系性的关系。然而,黑格尔直到最后都坚持着这一理念,即《精神现象学》是“科学的先行之物”(GW9,448)【3】。这如何与他已改变的体系构想相协调?
因此,关于《逻辑科学》与《精神现象学》的关系的问题就简直是呼之欲出了。因为一方面,黑格尔在被提及的两部著作中都一致地把《精神现象学》规定为思辨的科学的一种辩护或前提预设。【4】另一方面,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精神现象学》不可能在晚期的构想中还保持着这个角色。黑格尔似乎后来修正了、或甚至抛弃了他早前的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目的及其与逻辑学的关系之看法。此外,《精神现象学》向思辨的科学的过渡在内容上和方法论上都提出了谜题。例如,逻辑学以纯粹的存在开端,但《精神现象学》并不引向纯粹的存在的思想,而是引向绝对知识的理念,这个理念此外还与历史的和自然哲学的内容交织在一起。【5】所以,它无论如何都没有汇入逻辑学的明确的开端规定之中。【6】因此,人们究竟可以在何种意义上把《精神现象学》理解为进入思辨的逻辑的立场的导论或过渡?黑格尔也暗示,《精神现象学》自身的科学性植根于思辨的逻辑之中;但如果逻辑学也反过来以《精神现象学》为前提预设,那么一种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的印象就产生了(参见GW9,61,432)。【7】人们再次要问,如果想要免除黑格尔犯下如此一个明显错误的嫌疑,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可以被理解为逻辑学的前提预设。【8】
然而,以这种方式追问两部著作的关系,既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无辜的。在对“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的热情的过程中——这一热情追随着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黑格尔青年史》(1905)中倾向于非理性主义的呈现——,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阐释者,他们想要把《精神现象学》完全地从逻辑学的“经院哲学”中脱离开来,并把它置于一条与其相对立的发展线索中,这条线索可以追溯到1800年之前的时期。除了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黑格尔的编者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之外,在这里尤其要提及黑格尔的法国阐释者们: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9】他们把这部早期的主要著作把握为黑格尔那里一种鲜活的哲思的最后见证,在此之后,他便陷入了“体系”的僵化之中。如此看来,探究《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的问题,充其量只会把人引离他的思维活动的真正的哲学意蕴。【10】由此,一种接受的态度被塑造了出来,它尤其在英语世界中直到今天都持续产生着影响。【11】
因此,追问《精神现象学》如何与逻辑学相关,或甚至追问它自身之内是如何被逻辑地结构起来的,就已经意味着在黑格尔研究之内的一种表态。相应地,这篇文章从这一点出发,即在现象学与逻辑学这两门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和鲜活的关系,并且人们不可以把一个体系性的黑格尔和一个反体系性的黑格尔区分开来。最晚自1801年移居耶拿以来,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从而也包括《精神现象学》的思维活动——就通盘地被体系性所塑造,而这更切近地意指:被逻辑性所塑造,这种逻辑性也标识着他成熟的思维活动。这属于在此将要被遵循的发展史的研究路径的方法论的前提之一。这一进路之所以尤其也是恰当的,是因为我们今天对《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对黑格尔的发展的那些洞见所影响的,这些洞见只有在1960年代新开始的语文学的研究才能够提供。因此,在第一部分中,这两门科学的发展史的关系将被勾勒,并且与此相关的研究意见将被引述。在这里,事情上关涉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在黑格尔于《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前和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里所阐述的不同的逻辑学构想中,哪一个可能曾是这部著作的基础?以及,在体系发展的进程中,是如何产生出名为“精神现象学”的、引入思辨的科学的学科训练这一理念的?
与此同时,这个问题本身也具有体系性的特征。因此,体系性的重构的方法被应用,以便揭示出这样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可以被理解为逻辑学的前提预设,或者说逻辑学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现象学》的前提预设。因此,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将要探讨方法论的和内容上的问题,也即是说,第一,在何种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应当被理解为对逻辑学的导论,以及第二,人们必须如何更切近地去设想从一门科学向另一门科学的过渡。然而,这两个发展史的问题都提出了在此不能被最终澄清的问题。在此仅应当提供一个关于这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研究的概览。因此,本文首先是面向那些初次接触《逻辑科学》或《精神现象学》的读者。如果读者能够被置于这样一种状态,即能够认识到,《精神现象学》的构成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起源史在何种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以及有哪些体系性的问题连接于《精神现象学》相对于思辨的科学的体系的立场,那么这篇文章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2】. 《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的早期的《逻辑科学》的起源的语境中
【2.1】 发展史的引导性问题
在这里首先应当呈现一个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构想在耶拿(Jena)时期(1801–7)的发展的简要纲要。这个纲要服务于对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a) 哪一种逻辑学是《精神现象学》的基础?(b) 究竟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即“精神现象学”——一门直到那时为止被黑格尔所未提及的哲学的学科训练——能够承担起一种对思辨的逻辑学的导论或引导的功能?第一个问题之所以是相关的,是因为黑格尔明确地断言了现象学的意识的诸形态与“科学的抽象的诸环节”的明确的归属,亦即,与逻辑学的归属(GW9,432)。此外,他似乎把《精神现象学》自身的科学的要求建立在它与《逻辑科学》的关系之上:
“这种纯粹的本质[亦即,逻辑学的纯粹的思维规定们/B.B.]的运动,总地构成了科学性的本性。作为其内容的关联来看,它是其内容向着有机的整体的必然性和扩展。那条通过它知识的概念被达及的道路,通过它同样也成为一个必然的和完整的转变”(GW9,28)。
因此,从一切映象来看,逻辑学呈现了《精神现象学》的科学的基础。【12】因此,关于这些“抽象的诸环节”及其运动的更切近的说明,有望进一步阐明《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和方法。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在耶拿时期曾处于持续的转变之中。他本人将在致尼特哈默(Niethammer)的信中(1808年5月20日),大约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一年后承认,他为他的“逻辑学,正如它现在开始转变的那样,……在耶拿几乎没有奠定根据”(HBr 1: 244)。然而,逻辑的科学,就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撰写之前或期间的时期内阐发过它的范围而言,只能从先后次序的诸草稿中被重构出来,这些草稿部分只以残篇的状态被流传下来,部分但甚至也只能从一些粗略的草图中被推断出来。因此,如果想要获得所期望的说明,人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时而颇为不确定的重构尝试。
第二个问题,除其他原因外,也因此而是有趣的,因为在黑格尔研究中存在争议,即《精神现象学》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总地被视为对逻辑学的导论。【13】基本上,这里存在着一种乞题(petitio principii)的威胁,人们很愿意为黑格尔辩护以反对它:如果《精神现象学》的科学性建立在逻辑学自身的科学性之上,而同时又被称为逻辑学的一种前提预设,那么这个圆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参见GW21,54)。【14】考虑到《精神现象学》在成熟的体系中的不确定的地位,人们终究可以追问,在耶拿时期的末尾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即这门当时映象上完全新颖的“现象学”的学科训练,能够被理解为体系的必然的第一个部分并作为其导论。
【2.2】 哪一种逻辑学构想是《精神现象学》的基础?
黑格尔的耶拿的逻辑学构想可以被有意义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与在成熟的著作中不同,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开端(1801–1802/3)将逻辑学和思辨的科学或形而上学构想为两门彼此清晰区分的学科训练。【15】在这第一个阶段,逻辑学承担了一种纯粹否定的功能:它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的有限者的呈现,从有限者的消灭中,绝对者的否定的认识应当产生出来。【16】作为“有限者”,更切近地被指称的是由康德(Kant)所标识出的质、(纯)量、关系和模态的诸范畴,以及概念、判断和推论的诸形式,在这些形式中,知性产生出一种仅仅是“形式的”、缺乏真的无限者的二律背反的结构的同一性。这种逻辑学,黑格尔将之与古代的怀疑论联系起来,【17】展示出辩证的特征,正如人们从晚期的构想中也同样了解的那样:从对立的诸规定的统一中,诸矛盾被建构出来,这些矛盾证明了这样一些规定在把握思辨的真理方面的无能。然而,与在晚期的逻辑学中不同,在此时刻,黑格尔认为辩证法并非作为内在包含于有限的形式自身之中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由进行考察的哲学家从外部对它们引来的东西。只有在完成了有限者的辩证的消灭之后,才向着形而上学中绝对者的肯定的认识迈进。【18】
在从第二个发展阶段(1804/05)流传下来的关于逻辑学的诸草稿中,人们已经可以在黑格尔那里认识到一种趋势,即扬弃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分离。在这里,来自思辨的科学的诸肯定规定(例如“真的无限性”)部分地已经在逻辑学内部被论述,这应被解释为一个符号,表明黑格尔已经开始至少在有限的程度上承认逻辑学的肯定意义,并相应地也在思辨的意蕴自身之中发现辩证的特征。尽管如此,在这里,逻辑学依然还被理解为对要与它区分开来的形而上学的导论。因此,这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只有在第三个阶段(1805/06),我们才找到迹象,表明黑格尔可能已经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合并为一门单一的、以统一的方式操作流程的科学,正如这对他成熟的思维活动而言是标志性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人们固然不能再援引一个已阐述的草稿;流传下来的只是在关于自然哲学和精神的哲学的讲授课的手稿末尾的一条粗略的笔记,在其中黑格尔用简练的词语勾勒了“思辨的哲学”的内容:“绝对的存在,它自身他者,(关系转变)生命和认识活动——以及有知识的知识,精神,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GW8,286)。这一猜测,即黑格尔在此将“思辨的哲学”理解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一种内容上-方法论上的统一,主要通过与1804/05年的体系草稿的比较而得到证实,在该草稿中,存在、关系以及部分地认识活动属于逻辑学,而认识活动的其他方面以及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和精神则被归入形而上学。【19】
然而,从这种措辞中并不能明确地看出,黑格尔在此已经完成了向“成熟的”体系形态的步骤。因为在他的讲授课通告中,黑格尔多次通过提及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来阐明和精确化“思辨的哲学”这一术语。【20】因此,如果他在这里有一次含蓄地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并将各个子学科训练的特定的内容主题归纳在“思辨的哲学”这个共同的标题之下,我们就不必必然地将此评价为相对于之前的诸草稿而言体系构想的一种变化的迹象。
黑格尔在此时刻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把握为一种统一,这一点因此或许可以通过1806年夏季学期的一份讲授课通告得到额外的证明,其中谈到了`»philosophia speculativa s[ive] logica«` (latin)。如果像杜辛(Düsing)所建议的那样,将“s”补全为`»sive«` (latin)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简短的短语大概可以被解读为这两个术语的同义性的表达:逻辑学,之前被归入“形而上学”的诸肯定环节已经被整合入其中,现在被视为与作为这样一种东西的和在整体中的思辨的哲学是同一的。【21】那么,如果黑格尔为接下来的1806/07年冬季学期再次宣布“`Logicam et Metaphysicam s[ive] philosophiam speculativam, praemissa Phenomenologia mentis ex libri sui: System der Wissenschaft` (latin)”并从术语上再次区分这两门子学科训练,人们固然必然会感到困惑。【22】但为此,反过来应当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在其中黑格尔解释说,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内容中还带有意识的对立。而在逻辑学中,则“精神的诸环节……不再分裂为存在与知识的对立,而是停留在知识的简单性中,是在真相的形式中的真相,而它们的差别只是内容的差别。它们的运动,在这种要素中把自己组织成整体,”他如此结束他的解释,“就是逻辑学或思辨的哲学”(GW9,30)。【23】这段话固然不能最终决定这个问题,但它确实支持了(其中包括)由杜辛所代表的对1806年夏季学期通告文本的阐释。【24】
为了通过更多的迹象来支持对在《精神现象学》起源时期大概已经存在的逻辑学构想的重构,人们将无法避免地也要回顾一些草稿,这些草稿固然要追溯到著作完成之后的时期,但尽管如此在时间上是紧密相邻的。黑格尔最初曾意图让科学的第二个部分紧随《精神现象学》之后,这个部分除了逻辑学之外,本还会包含自然和精神这两门实在哲学(参见GW21,8–9)。这个计划他固然没有实现,并且后来他放弃了作为其基础的体系构想。然而,在他迁居纽伦堡(Nürnberg)后不久,他在1808/09年讲授了一个版本的逻辑学,这个版本比所有之前的版本都更接近于后来出版的版本,即纽伦堡的预备训练的逻辑学(GW10,1,62–79)。这种逻辑学按如下方式细分:
第一章:本体论的
逻辑学
I. 存在
A. 质
a. 存在
b. 定在
c. 变化
B. (纯)量
a. 自为存在(观念性)
b. 定量
C. 无限性
II. 本质
A. 本质的概念
B. 命题
C. 根据与被奠基者
【1】. 整体与诸部分
【2】. 力及其表现
【3】. 内部与外部
III. 现实性
【1】. 实体
【2】. 原因
【3】. 交互作用
第二章:主观的
逻辑学
I. 概念
II. 判断
III. 推论
第三章:理念学说
I. 生命的理念
II. 认识活动的理念
III. 绝对理念或知识
比在1805/06年的草图中还要更明确地,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完整的整合在这里昭然若揭。因此,它能够被视为黑格尔的成熟的逻辑学构想的第一次详尽的阐述,即便这个构想直到最终的形态为止还应当经历若干修改。【25】
现在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即与《精神现象学》的构成在时间上紧密相邻的这两个逻辑学版本中的哪一个,可能曾是那部著作的基础——除非是某一个第三种的、未流传下来的构想曾对《精神现象学》起引导作用,而其踪迹将只能在著作自身之中被找到。【26】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是因为它与黑格尔研究中一个古老的、被深入讨论的并且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精神现象学》究竟是否总地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构想之上,或者它的形态不是或许还在其起源活动期间就被原始计划中的一个深刻的变更所规定了,而这个变更已经不再能与这个计划完全地被中介了?
《精神现象学》并非基于一个统一的构想这一猜测,最早于1857年由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提出。【27】直到1960年代,一种意见占据着主导地位,即黑格尔已经抛弃了他原始的计划,并试图事后掩盖这一断裂,例如通过用一个第二种的、以大写字母为标志的分节来补充人们在文本中找到的以罗马数字进行的章节的连续编号,而这种分节只在作为最后被印刷的目录中才被找到。这一论点以极其尖锐的方式被特奥多尔·哈林(Theodor Haering)(1934)所阐述,其他的学者也附议了他,例如黑格尔的著作的编者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28】
然而,在1960年代中期在黑格尔的著作的历史考订版的背景中开始的研究,能够在一个远为精确的年代确定和对相关文献的认识的基础之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通过回顾《精神现象学》构成之前和之后的时期的逻辑学草稿或草图,尤其是富尔达(Fulda)、海因里希斯(Heinrichs)和特雷德(Trede)努力于对一种被严格贯彻的著作统一性的证明。【29】珀格勒(Pöggeler)在有限的程度上也属于这个阵营,因为他固然从语文学的视角认为著作构成中的断裂是无可怀疑的,但尽管如此承认一种统摄性的构想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奠基于对思辨的科学的历史性的追问之中,并且可以被追溯到黑格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时期。【30】
尤其对于富尔达和特雷德的研究而言,1805/06年的草图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它允许人们将由黑格尔映象上补充的逻辑学纲要的字母分节明确地进行归属:【31】
[1] 绝对的存在,它自身转变为他者(关系)
[2] 生命与认识活动
[3] 有知识的知识
[4] 精神,
[5] 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
(A) 意识 [精神的自在存在]
(B) 自我意识 [精神的自为存在]
(C) (AA) 理性 [自在的精神的自在且自为存在]
(C) (BB) 精神 [自为的精神的自在且自为存在]
(C) (CC) 宗教 与 (DD) 绝对知识 [自在且自为的精神的自在且自为存在]
一方面,这种归类使得将该作品的所有章节整合到一个总括性的统一之中成为可能;此外,它能够用作一个对在个别的章节里起作用的那些逻辑学的范畴的更进一步的重构的基础。【32】
人们将无法完全否认这些重构尝试的合理性;它们自在地也已经施加了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承诺了对一个作品的融贯性的洞见,这个作品似乎处处在暗示它的统一,却从未让它完全地显露出来。尽管如此,它们未能迫使那些持对立见解的代表们让步。福斯特(Forster)的在Hegel’s Idea of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1998)中的重构尝试是从纽伦堡(Nürnberg)的预备训练出发的。他展示了,这个后来的逻辑学的次级划分如何能够严谨地映射到《精神现象学》上——当然仅仅是映射到第I章至第V章,也就是直到“理性”那一章的结尾。【33】福斯特的分析就此而言为统一性怀疑论者们的阵营呈现了一个真正的进步,因为他第一次能够在对史料的充分知晓中并且在黑格尔(Hegel)的逻辑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主张断裂的这个论点。近来,埃卡特·福斯特(Eckart Förster)也出于另外的、可追溯到黑格尔的对歌德(Goethe)的方法论的接受的那些理由,主张了即便不是一种断裂,也至少是一种重要的构想上的移位的论点。【34】福斯特由此给出了一个独立于《逻辑科学》的证明,这个证明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对断裂的这个论点的一个额外的确证。因此,人们即便在今天也不可以将这个旧的问题看作是最终被解决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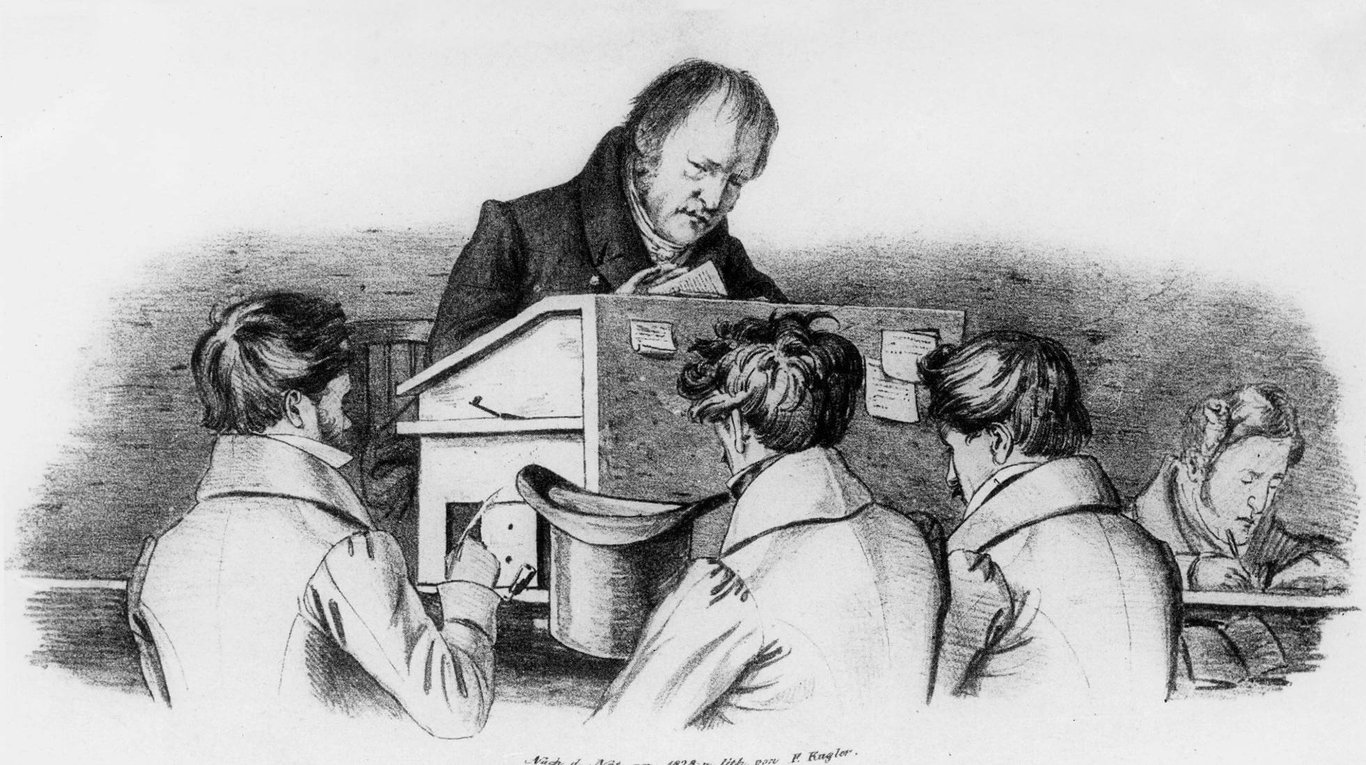
【2.3】《精神现象学》是如何成为科学的体系的第一个部分的?
在前一个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如何在耶拿(Jena)时期的进程中逐步地转变了逻辑学的体系性的地位。它起初呈现为一个通往与逻辑学有明确区分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活动的否定的导论,这个导论应当通过一种对纯然有限的认识形式的“怀疑的”摧毁的路径,引导人们达到这样一种洞见,即对绝对者的真实的认识要求一种不同于知性的形式。但是,正如不难认识到的——以及正如黑格尔自己明确证实的那样——早期的怀疑的逻辑学只有当从读者方面可以预设一种与绝对者的熟识,比如以一种“先验直观”的形式(参见GW4, 27–28, 207–09),它才能够满足这个目的。因为对有限的形式的纯然否定的摧毁或扬弃单凭其自身尚不足以去展示一种另类的认识方式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人们毋宁想要猜测,它就其自身来看必然会把一种无限制的怀疑论作为其后果。因此,怀疑的逻辑学只有当它已经预设了它才声称要引介进去的那种认识时,才能满足它的导论功能。因此,它既是循环的,也是对于那个它应当对其有用的个体来说是多余的。【35】
这个难题或许已经产生了那种张力,它逐渐地驱使黑格尔将一种同时具有摧毁性的和建构性的功能归于逻辑学。【36】最终,它在一种精确的意义上成为了思辨的逻辑学,即它将先前与它分离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那些实定的意蕴整合进自身,并因此不再与后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如果那些实定的意蕴如今在同一个进程中与对纯然有限的范畴的批判性的拆解一道被产生出来,那么人们在原则上可以将循环性的难题看作是被解决了的。但为此,它可能会显得,仿佛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难题。在其怀疑的形态中,逻辑学应当呈现一个与科学有别的、才要引导至科学的导论,这个导论也能够将思辨的科学的那个立场中介给那些尚未从自身出发占据它的人们。现在,问题出现了:通过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同化而成为一个单一的、在自身中封闭的思辨的科学,那个导论的位置是否变得空缺了?或者,难道不是相反,将一个分立的地位指派给通往科学的导论,已经被证明是多余的了,因为对纯然有限的前提预设的有意识的拆解如今已经被整合进科学自身之中了?
在我看来,这个二选一的抉择标示了黑格尔后来对《精神现象学》的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正是在1806年进入了那个——在此期间或许已经变得多余的——从前的怀疑的逻辑学的位置。【37】黑格尔自己也如此理解它的迹象之一,在于他将《精神现象学》刻画为一种“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它作为“彻底怀疑的道路”将自然的意识逐渐地引导至科学的立场(GW9, 56)。在这个时间点上,黑格尔不再认为一个导论的必要性是由于有限性的那些形式本身必须被拆解这一事实而得到理据的,因为这个证明毕竟已经属于实定的科学的体系自身的范围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个思考变得具有引导性。一方面,科学就此而言需要一种辩护,即它起初仅仅作为在其他立场中的一个可能的立场而出现:
“它的出现还不是它在它的真理中被执行和被展开。在此,将它表象为显象,因为它在别的东西旁边出现,或者将那个别的非真的知识称作它的显现,是漠不相关的。但是科学必须使自身摆脱这个映象,而它只能通过它转向这个映象来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不能把一个并非是真的知识仅仅当作一种对事情的庸常的看法来抛弃,并断言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而那个知识对它而言根本什么都不是;也不能求助于在它自身之中的对一个更好的东西的预感”(GW【9, 55】)。
另一方面,黑格尔承认自然的意识自身是一种精神的显现方式。因此,自然的意识的那个要求,即科学的立场应当被向它阐明得可以理解,是必须被无条件地承认的:
“在绝对的他者存在中的纯粹的自身认识活动,这个作为此类的以太,是科学的根基和地界,或总体而言的知识。哲学的开端做出了这样的前提预设或要求,即意识处在这个要素之中。但这个要素自身只有通过它的转变的运动才拥有它的完满性和明晰性。……科学从它那方面要求自我意识,它已经将自身提升到这个以太之中,以便能够与它一起并且在它之中生活并且去生活。反过来说,个体拥有权利去要求,科学至少将通往这个立场的阶梯递给他,在他自身之中向他指明这个立场。他的法权建立在他的绝对的独立性之上,他知道在它的知识的每一种形态中都拥有这种独立性……。这个科学的总体而言的转变,或知识的转变,正是这个《精神现象学》……所呈现的东西”(GW9, 22–24)
但是,这些思考是否必然地引向一个通往《逻辑科学》的导论的这个思想呢?人们可以问,意识恰恰自在地已经是精神这个事实,是否不会使所有分立的导论变得多余。黑格尔后来会将上面引述的“想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决断”称作是足以提升到科学的要素之中的(参见GW19, 91/ENZ§78)。但早在1804/05年的体系草稿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似乎指向一个先行于科学的导论的多余性的评论:
“逻辑学是以统一自身开始的,作为自身等同者。它[没有]就此为自身辩护;这在这里才发生;因为自在体在这里设定自身,作为一个自身一致性,在其中所有的环节都被消灭了,它[亦即,作为自在体/B.B.]来自于这种消灭。那个开端的统一是结果,但它是结果这一点,在它那里完全没有被道出;它是一个主观的结果,关于它,可以猜测,必然有很多东西先行于它,为了能够以它来开端。在这里,在向自身的绝对返回中,它就是作为这个结果。就它没有被设定为结果而言,它是一个任意的开端,它绝对地有很多东西在它旁边,一个偶然的第一者;在这里它证明自身是绝对的第一者”(GW7, 129)。
如同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一样,我们在这里已经发现了同一个仅是显现的科学的难题,它应当证明它相对于另类立场的无条件的法权。在《精神现象学》中,这个难题被指出,以为了给一个先行于科学的导论的必要性奠定理据。与此相反,在体系草稿中则主张,逻辑学自身在呈现的进程中拆解了它的前提预设,并由此实现了精神的返回自身。【38】
因此人们看到,在黑格尔的耶拿的逻辑学构想中的那些同样的变迁,它们一方面使得一个先行于科学自身的、“怀疑的”导论的位置可以说空了出来,另一方面也趋向于使这个位置变得多余。从发展史的视角来看,《精神现象学》因此可以显现为在逻辑科学的基础构想中的构造性移位的一种中间产物——一个被遗留下来的纪念碑,它在其宏伟中虽然强索着人们的赞叹,但最终却未能在成熟的体系中主张它的地位。然而,与此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黑格尔即便在后来的《逻辑学》的版本中,也仍然将《精神现象学》指认为一个先行于逻辑学并构成其前提预设的科学。因此,在本论文的第二部分中,将必须去寻找体系性的根据,为何《精神现象学》至今仍然应当与科学处于一种鲜活的关系之中。
【3.】 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的体系性的关系
【3.1】 体系性的主导问题
主要是有两个体系性的问题,将在下文中起主导作用。(【1】)《精神现象学》的每一个意识形态都与科学的一个抽象的环节相匹配,这是什么意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人们将各种不同的逻辑学构想中的哪一个视为是基础性的,甚至也独立于人们是否相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无断裂地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构想。只要人们根本上承认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有任何意义,人们就将被迫就纯粹的思维规定应当如何在意识形态中呈现自身给出原则性的说明。当然,对这一或那一逻辑学构想的决断将会对人们在文本的何处寻找个别的规定以及如何指明它们产生影响;但在体系性的视角下,应当有一个,并且至多只有一个回答。(【2】)在何种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可以被视为通往或引导至《逻辑科学》的导论?无论如何,对于每一个曾钻研过这部作品的人来说,以下这点应当是清楚的,即它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导论,比如那种通过中介必要的预备知识或通过提供引理来简化通往科学的路径的导论。毋宁说,随着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双重的难题。一方面,如果《精神现象学》的科学性的必要性只能从《逻辑科学》的立场才能被看到,那将意味着一个*circulos vitiosus*,因为它那样就会陷入与早期的“怀疑的”逻辑学同样的判决,即既是循环的又是多余的。【39】另一方面,如果思辨的科学在《精神现象学》中终究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前提预设,那么它对无前提预设性的声称就会落空。
在下文中,将勾勒解决这些问题的进路。
【3.2】 意识形态与逻辑学的纯粹规定之间的契合存在于何处?
黑格尔写道:“科学的每一个抽象的环节”,都契合“显现的精神的总体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一个广义上的“意识形态”(GW【9, 432】)。这个契合关系是怎么回事?它立足于什么?这个问题预设了对《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特定的差别的先行理解。因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以精神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内容,精神在这一情形和另一情形中都将自身分解为其分立的环节,以便最终将它们重新收回到自身之中,并在它们的统一中认识它们。在逻辑学中,综合发生在绝对理念之中(黑格尔在与《精神现象学》时间上邻近的纽伦堡的预备训练中有一次也将其称作“绝对知识”),因为逻辑科学的形式和内容合而为一了(参见GW10, 1, 79;GW12, 237)。在《精神现象学》中,一个类比的综合似乎在发生,因为精神将那个由个别的精神形态的先后次序所呈现的“图像画廊”内化为它的转变的历史,并由此成为“作为精神而认识自身的精神”(GW9, 433)。因此,如果在两种情况下——尤其是在早期的逻辑学草稿中——精神的达到自身构成了内容,那么这两个科学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黑格尔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回答。精神知道它的定在的两个有差别的要素:一方面是它的纯粹的定在的要素,另一方面是它的直接的定在的要素。前者被称为概念,并且是《逻辑科学》的对象;后者被称为意识,并且是《精神现象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参见GW9, 29, 432)。在概念中,我和对象的一切差别以及一切经验性的内容都被消灭了。在作为科学的要素的它之中,“精神的那些环节如今在简单性的形式中展开,这种简单性将它的对象认识为它自身。它们不再分裂为存在和知识的对立,而是停留在知识的简单性之中,是在真理的形式中的真相,而它们的有差别性仅仅是内容的有差别性”(GW9, 30;参见GW21, 54)。与此相反,《精神现象学》的要素是精神的直接的定在,在其中我和对象、确知和真理分离开来并需要中介:“因此,直接的定在的要素是那种规定性,这一部分的科学通过它而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GW9, 29;参见GW12, 17)。
我们关于两者契合的更具体方式的问题,现在更多地变成了这样:一个在其他方面是纯粹的概念规定,存在于直接的定在的要素中,并由此构成一个意识的形态,这意味着什么?回答是:在精神的直接的定在的要素中,亦即在意识中,一个概念规定显现为一个通过(纯然“显现的”)知识而在对象上被设定的本质规定及其辩证的展开。这个命题意味着什么,现在将要逐一说明。
对黑格尔而言,“意识”的特征在于一种结构,这种结构部分地与今天在很多地方被理解为“意向性”的东西相重合:意识
“……亦即从自身区分出某种东西,它同时又与此物相关联;或者如其所表达的,有某种东西为了它而存在;而这种关联的、或某种东西为了一个意识而存在的被规定的方面,就是知识。但是,我们从这个为了一个他者的存在,区分出自在存在;与知识相关联的东西同样也与它区分开来,并被设定为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这个自在的方面被称为真理”(GW9, 58)
这个规定的决定性的东西,以及它借以超越今天对意向性的理解的东西,在于将与知识相关联的东西“设定为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因为只有通过这一点,知识才证明自身为据信为真。因为(正如我们今天会说的)意向性的客体或我的表象的客体被我如此理解或设定,以至于它以它为我的表象所具有的那些规定,也存在于这个表象之外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绝对地存在的,我便提出了一个真理主张。
现在,下面的思想也变得顺理成章:如果我认真对待我的那些真理主张,那么这些主张必须可以说在自身之中包含一个标准,我的确知据此得以确立,并且它们的真理可以借此被第三方检验。我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是可验证的。一些思考或许还能进一步引向将这个标准普遍地设定的思想。通过这一点,一个被规定的知识类型被标识为科学性的;同时,一个与之契合的客体类型被规定为在范式意义上可知的或有待被知的东西。这一点可以借助一个具体的、尽管有些简化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现代的科学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即只承认那些能够以一种对质量和电荷的归属的形式来陈述并因此可以被检验的东西为真正的知识。因此,在人们没有设定某个可以被规定为质量m和电荷u的客体——比如一个原子——的存在之前,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真正有能力承载真理的主张。但这将完全契合通常的语言用法,即说:‘本质的东西是原子,如果一个人声称要知道某种真正为真的东西,那么这个知识最终必须能够被表述为一个原子科学的命题。’
在我看来,黑格尔关于“真相”、“自在存在”或“本质”的言说,应当按照这个模式来理解。一个意识的形态的特征在于,它将一个被规定的客体类型规定为在强的意义上是可知的,并将其知识的形式依此来安排。随着这个客体类型的规定——它然后被称作“真相”、“自在存在者”或“本质的东西”——知识便在对象上设定了一个本质规定。正是这个本质规定,一个被规定的意识的形态通过它而被特定化。【40】
根据我的理解,正是这个将各自的意识形态特定化的本质规定,我们应当将其与一个“科学的抽象的环节”等同起来。
让我们来看一个来自《精神现象学》自身的应用案例。在那里,第二章的标题是“知觉;或物,与错觉”(GW9, 71)。现在,物在《逻辑科学》中也作为纯粹的思想规定出现(参见GW11, 327–340,GW7, 5–12)。与此相反,知觉和错觉是纯粹的科学所陌生的规定,因为它们是意识的状态。这些规定是怎么回事?在对先行结果的简要重述之后,黑格尔将我们引入这一章:
“这个[新的/B.B.]对象现在需要被更切近地规定,并且这个规定要从[在前一章/B.B.]得出的那个结果中简要地发展出来;更详尽的发展不属于这里。”(GW【9, 71】/B.B.所强调)
在我看来,“更详尽的发展”应当被解读为对逻辑学的一个提示,因此黑格尔接下来所作的评论相应地应当被视为对“物”的一个缩略的逻辑学的规定。真理的标准被等同为“自身一致性”(GW9, 74)——这是一个与普遍者的规定紧密结合的规定。
正如从第一章“感性确知”中可以看出的那样,一个简单的自身等同的普遍者只能通过对质的规定性的杂多的否定或抽象来把握;因此,它应当被称作一个被中介的东西(GW9, 71)。这个自在的被中介状态导致的结果是,自身等同者同时必须在自身那里展示那个有待被否定的杂多。因此,被设定为本质的是一个对象,它在简单的自身一致性并且同时是多样的他异性的这个对立的意义上呈现了普遍性。正是这个对象,黑格尔称之为“具有许多属性的物”。一方面,每一个属性似乎都可以在撇开所有其他属性的情况下被理解和存在;就此而言,每一个属性只关联自身,并在此之中是“纯粹的普遍者自身”(GW9, 72)。另一方面,每一个属性都与其他每一个属性有差别,并因此是一个排他的统一或一个“数上的一”。由此,“属性”这个规定分裂为存在(普遍者)和否定(特殊化)的对立的环节。这些规定被一并把握并被设定在其内在的统一中,得出了“物”这个规定。当然,“物”这个规定可以被认识为与属性是同一个规定。差别仅仅在于,“物”呈现了环节的统一,而“属性”则表达了分裂或特殊化。
到此为止,我们处理的完全是逻辑学的规定,而这个简要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认识到,存在和否定(或普遍性和特殊化)的这两个极虽然可以彼此区分,但不能被实在地分离开来。《逻辑科学》现在的任务,将是详尽地呈现这个辩证的统一的展开,并给出它的结果。与此相反,在现象学的考察中,这个逻辑学的辩证法被置于上面描述的意识结构之下。进行知觉活动的意识将本质理解为自身一致性——这是它特定的真理标准。同时,它“知道”那个在自身等同者那里被否定并因此中介了它的杂多,因为这是前一章的结果。这个与自身一致性相对立的杂多,现在对它而言必须被视为非本质的东西,或者,如果愿意的话,被视为虚假的东西和仅是表面上现实性的东西——作为一种混淆或遮蔽真理的错觉。以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知觉”这个意识形态如何最终被特定化为一种对在其他方面是纯粹逻辑学的规定的不恰当的知识论态度:它把握了自身一致性和为他存在或否定就此而言是相互归属的规定这一事实,即人们必须明确地将它们一起主题化并彼此区分——这正是它超越其更贫乏的前行形态,即感性确知的地方。然而,它的错误在于,它起初将这种相互归属理解为这些规定的纯然外在的结合,并误认了它们的内在的、最终将它们推向矛盾的统一。这个意识形态的“经验”在于一系列徒劳的尝试,以保护这个错误的理解免于矛盾和瓦解。
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前三章中,现在可以就哪些逻辑学的规定可能在起作用提出切实的假说,以便在其基础之上逐一重构黑格尔的论证。【41】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这变得更加困难;从第六章,即题为“精神”的那一章开始,文本就顽固地抗拒这样一种分析。这其中就存在着某些阐释者假定在该作品的构想中存在一个断裂的理由之一。无论如何,至少可以确定这一点:科学的抽象的环节与意识的形态之间的契合关系,只要在各自的情况下存在,就存在于在对象上规定一个属于逻辑学的本质规定,这个规定随后被理解为真理标准,并因此被用来作为现象学的检验操作流程的基础。
【3.3】 关于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的相互前提预设:显象与现实性
【3.3.1】 《精神现象学》是否预设了逻辑学?
在较近的黑格尔阐释者中,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rster)以最大的强调力度主张了这样的论点,即《精神现象学》基于一个完全独立于逻辑学的科学性的基础。福斯特认为,该作品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在事前就确保思辨的科学免遭怀疑论攻击的可能性,并提供一个对其有效性的证明,这个证明也必须被那些尚未分享“科学的立场”并且带着他们自己业已存在的信念和标准来接触该作品的人们承认为是有强制力的。【42】福斯特由此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逻辑科学需要一种外在的辩护。初步看来(Prima facie),由此产生了一种张力,它既与思辨的逻辑学对无前提预设性的声称相张,也与黑格尔对“解释的倾向”的拒绝以及他所推荐的,可以说通过一种“想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决断”来决断主义地设定开端的做法相张。【43】当然,与此同时,这也增大了将《精神现象学》置于一个独立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压力,因为它否则将无法胜任它被预定的任务。
福斯特试图通过诉诸怀疑论的那个阶梯的正位论来瓦解与逻辑学的内容上的无前提预设性的表面张力,人们在顺着它爬上去之后便会把它踢开。【44】《精神现象学》中介逻辑学,并非根据是其理据的东西来中介那个理据的意义,而是通过反驳并拆解那些表面上与科学对立的根据。诚然,为了这个目的,它利用了前提预设,但是,第一,这些前提预设是从那些有待被反驳的非科学的立场中接手过来的——而非从科学自身;并且,第二,《精神现象学》的结果并非作为在别处被证明了的并且从外部被带入科学之中的东西而实定地进入科学。毋宁说,《精神现象学》被扬弃入《逻辑科学》之中。【45】
但是,那么意识形态与纯粹的思维规定之间的契合又该如何解释呢?《精神现象学》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它们并利用了它们吗?以及,黑格尔对两种视角的声称又如何解释,即一个“为了[有待被现象学地考察的]意识”的不恰当的或部分错误的视角,以及一个恰当的或真实的视角,只有从后者出发,形态的先后次序的必然性才变得可见,并且它只“为了我们”而存在(参见,例如GW9, 61–62)?——福斯特认为,关键点在于,《精神现象学》的读者不需要来自《逻辑科学》的信息,以便认识并理解那些规定的辩证法和进展的必然性。【46】诚然,形态的先后次序的必然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现象学》整体的科学性,或许可以从在《逻辑科学》中被展示的纯粹概念的本质得到解释;换言之,该作品的科学性的可理解性或许根植于并且被奠基于逻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已经认识这个源头,才能共同理解《精神现象学》的必然的进展。因此,从纯粹知识论的观点来看,它的科学性并不依赖于逻辑学。但重要的恰恰是这个观点,如果《精神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知识论的特征的话。与此相应,根据福斯特的看法,视角的二元性应当被如此理解。“为了我们”这个标识并不必然只指涉一个根本上被清除了意识对立的立场,亦即逻辑学的立场。因为如果“为了意识”这个视角只与各自有待考察的意识相关,那么就还有一个另外的选项是开放的:
“在‘我们’之中,即观察着各自新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生的我们之中,或许存在着非科学性的意识,亦即那些不仅仅是考察的对象的意识,因为正是它们,才要被《精神现象学》引导至黑格尔的科学……。”【47】
换言之,“我们”并不必然需要已经站在由《精神现象学》所呈现的教化之路的终点或之外;呈现的科学性完全也可以从一个仍然处在那条道路之上并因此也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之中的视角来理解。【48】
福斯特以这种方式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关于人们如何能够将《精神现象学》的“官方”任务,即引导入《逻辑科学》,与黑格尔的那些毋宁说似乎将逻辑学规定为《精神现象学》的前提预设的其他言论相协调。他的建议具有巨大的优点,即让黑格尔摆脱了循环论的嫌疑,并同时保有了这部早期主要著作的自身意义和独立性。然而,无论如何,以下这点或许仍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即一部被规定用来反驳所有与思辨的科学相对立的立场的文本,其自身却提出了如此多的谜题——而且即便在那些福斯特算作“原初精神现象学”的还相对清晰的部分也是如此。【49】作为这个意义上的导论,人们或许可以对这部尽管如此仍令人敬重的作品的成功提出疑问。
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最近发展出了一个建议,它使得将《逻辑科学》与《精神现象学》相互关联起来成为可能,而无需将后者阐释为前者的引导,甚或前提预设。他的进路基于“科学的立场”与狭义上的逻辑学的立场之间的区分。【50】霍斯特曼将“科学的立场”称作这样一种洞见,“即所有那些在任何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对象(或显象)的东西,都已被证明是概念性地构成的。只有这种洞见才具有科学的状态。”【51】他引用了黑格尔在《存在学说》(1812)第一版的导论中的话,根据这些话,科学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包含着思想,就思想同样也是事情本身而言,或者说,包含着事情本身,就它同样也是纯粹的思想而言”(GW11, 21),并如下阐释它们:
“它(这种科学性的洞见)因此是所有(黑格尔式的)真理的基础,亦即(再次以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所有实在性的基础。思想就是事情,反之亦然——这是黑格尔的基础性的形而上学的信条,而《精神现象学》应当已经‘演证’了这一信条。”【52】
根据霍斯特曼的说法,如果人们想要避免不得不将体系建构中的严重错误归咎于黑格尔,那么如此被理解的“科学”本身的立场,便不可与作为科学性的分支学科的逻辑学的立场相混淆。【53】因为每一个阐释者都面临着如下三个问题:
“(【1】)什么东西范导着现象学的进程?(【2】)如果——正如在修订说明中所暗示的——‘逻辑学,处在意识的背后’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如何能够避免这样的嫌疑,即通过现象学的进程来为科学的立场的不可避免性所作的理据是循环的?(【3】)如果《精神现象学》是科学的方法‘在一个更具体的对象上’(GW11, 24)的一个例子,那么它又如何能够承担一种辩护功能?”【54】
根据霍斯特曼的看法,如果人们不区分这两个立场,那么人们将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黑格尔最终在将《精神现象学》整合进一个科学的体系方面,手法绝非非常高明,这个体系虽然不与一门《逻辑科学》同一,但却必须以它来开始。”【55】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恰当地将它们分离开来,那么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人们就会得出一个远为更具建构性的结论。第一:
“在《精神现象学》中被投入使用的那些操作性的中介,绝非应归功于逻辑学,而是这样一些中介,它们的辩护在于,它们才使得像(黑格尔式的)科学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就此而言,它们既不能在《精神现象学》的框架内,也不能在逻辑学的框架内获得理据,而是……使得事态能够‘在科学的要素中’呈现为发展进程的那些条件。”【56】
第二,逻辑学并非在大致这样的意义上“处在”现象学的经验进程“背后”,即它保证了后者的知识论的必然性,而是它在一个“后继的”意义上处在它背后:
“‘科学的立场’,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然的’立场,必须首先通过现象学的进程向意识敞开,并且只有到那时,对那些构成逻辑学的对象的、建构世界的概念性的进程的呈现才能开始。逻辑学因此处在意识的背后……。它的呈现只有通过贯穿意识的进程才成为可能。”【57】
第三,最终,一个成功的例子能够为某事辩护,而无需循环地已经声称了那个被辩护的东西:
“也就是说,正如一个人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走过的一条路,当他在这条路上达到了目标时,这条路就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例子,同样,这个目标作为可达到的东西,也通过所走过的路得到了辩护。因此,一个例子完全可以具有一种辩护功能,而无需已经声称了那个有待被辩护的东西。”【58】
霍斯特曼(Horstmann)的进路的优点在于,它顾及了黑格尔将《精神现象学》规定为科学的“前提”(GW9, 448)的做法,而无需将这两个学科置于一种直接的并因此是简化的相互关系之中。根据霍斯特曼的看法,“直接的关联……只存在于《精神现象学》和科学的体系之间……。逻辑学呈现了它的第一部分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它成为值得引导入或引导至的对象——毋宁说,是‘科学’,需要引导或引导至。”【59】从相反的视角来看,《逻辑科学》就其存在而言,显然依赖于科学的概念本身已经被阐发出来并因此是现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呈现为“科学的前提”: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先行于《逻辑科学》,即它产生了科学的概念。
“但是,它对这个概念在体系的形式中的发生论的展示没有影响,也不依赖于它。科学的概念在体系形式中的发生论的展示,也就是黑格尔也称之为科学的概念的(自我说明的)发展的东西,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其第一部分出于被规定的那些理由而是《逻辑科学》,后者的内在结构和进程形式与现象学的进程的任何结果都毫无关系。”【60】
尽管如此,人们将无法毫无保留地同意霍斯特曼的建议。因为第一,每一个旨在澄清《精神现象学》与《逻辑科学》(既指以这些标题出版的各种不同的文本,也指由此所标示的哲学学科)的关系的进路,其有效性都因语文学的和发展史的证据和见证的不完整性而受到限制。霍斯特曼的证明过程,正如已经提到的,部分也依赖于间接证据:如果黑格尔直到他从事《精神现象学》工作的那个时间点,事实上确实已经完成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合并,使之成为一个在内容上-方法上统一地操作流程的思辨的逻辑学,那么霍斯特曼的反对将“思辨的科学”与“《逻辑科学》”等同起来的那些论证中,至少有一个就失效了,并因此也连带反对了将一个导论功能归于1807年形态的《精神现象学》的论证。【61】现存的见证支持两种猜测,但它们对两种猜测的支持在同等程度上都是不充分的。
此外,除了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那个报告,即黑格尔在他1806年夏季学期所做的讲授课中,已经将《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与逻辑学开端的纯粹存在直接联系起来,【62】也还有黑格尔在内容上的陈述,它们至今仍然支持《精神现象学》应当直接汇入逻辑学的看法。例如在《全面教学纲要》第【25】节的附注中,黑格尔在那里自我批判地讨论了这部早期著作的特征及其与逻辑学的关系。在那里,他首先承认,由于“哲学科学的立场”是从现象学的呈现中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因此它也已经“预设了意识的那些具体的形态,比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GW20, 68–69/ ENZ §25)。这个陈述到此为止或许与霍斯特曼的阐释相和谐:那个丰富的、具体的历史是必要的,以便产生科学的概念并使之进入存在。但此外,黑格尔同样也承认,“哲学科学的那些特有的部分的内容的、对象的展开,……因此同时也落入那个起初似乎只局限于形式方面的意识的展开之中”(GW20, 69),“那个展开可以说必须在它的背后进行”(GW20, 69,B.B.所强调)。在这里,黑格尔自己在一个显然不仅仅是“后继的”意义上使用了“背后”这个词,而是为了标示一个内容性质的前提预设。
但尤其是,黑格尔所作的将《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呈现的“先行概念”与《精神现象学》进行的比较,——刚才引用的那些话正是引向这个比较的——使人倾向于将一个至少非常相似的功能归于后者,如同归于前者一样:据说,“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立场”应当“主要有助于达成这样的洞见,即人们在表象中就认识的本性、就信仰等等所面对的、并认为是完全具体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思想规定,但它们只有在逻辑学中才获得其真正的处理”(GW20, 69)。
特别是这最后一个表述与霍斯特曼的阐释相冲突。因为如果(【1】)先行概念应当引导至的那个洞见在于,认识活动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亦即逻辑学的规定,并且如果(【2】)这个洞见也应当是《精神现象学》的目标,那么后者就也汇入了逻辑学,或者至少汇入了逻辑学的立场。但上面已经引用的来自序言的段落似乎恰恰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黑格尔解释说,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中,“精神的那些环节……不再分裂为存在和知识的对立,而是……停留在知识的简单性之中,……是在真理的形式中的真相”(GW9, 30)。这从事情本身来看,与刚才引用的《全面教学纲要》的那个陈述是吻合的,“即人们在表象中就认识的本性……所面对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思想规定”(GW20, 69/ ENZ §25)。因此,如果这些规定“只有在逻辑学中才获得其真正的处理”(同上),那么当黑格尔在序言中谈到“逻辑学或思辨的哲学”(GW9, 30)时,他所指的与这门完全相同的《逻辑科学》的关联,又应当通过什么来区分呢?因此,如果两个学科的关系无法被明确地规定,这并不仅仅应归咎于语文学的和发展史的见证的不完整性。黑格尔自己也未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瓦解它们关系的这种模棱两可性。
【3.3.2】 逻辑学是否预设了《精神现象学》?
我们知道,《逻辑科学》通过《精神现象学》而被“辩护”,因为黑格尔自己明确地这样说了(参见GW21, 32 )。但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呢?我们刚才已经考察了由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发展的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进路。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Hans Friedrich Fulda)也同样试图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他将黑格尔后来关于导论难题和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以及后者从《全面教学纲要》第一版(1817)起所获得的被修正的地位,阐释为这样的符号,即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新阐释。在1807年以及(根据黑格尔在《存在逻辑》第一版中的评论)大概在1812年,他都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讨论过的福斯特的阐释相吻合的方式来构想《精神现象学》。据此,《精神现象学》本应通过将非科学性的意识“引向对自身的彻底怀疑,引向放弃它的那些自明之事,并让它自己的、它在其中说服非科学性的意识相信其不真实的那个要素,将自身扬弃入科学之中……”,来引导入科学。【63】
如此被理解,《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与科学自身的开端有一种本质的关系,因为只有通过被要求的非科学性的意识的自我扬弃,那个纯粹的科学能够在其中进行的要素才形成。【64】因此,通过那种自我扬弃,它才达到现实的存在,并脱去那种历史的映象,仿佛它“只是哲学的又一种形态,对其难题的一个新贡献。”【65】然而,最晚从《全面教学纲要》第一版起,——黑格尔在其中第一次以印刷形式呈现了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从富尔达的视角来看,这种与开端以及与作为此类的科学的要素的关系就失效了。据他看来,黑格尔在此期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洞见,即思辨的科学必须在自身之中为自身奠定理据,并在其自身之内返回其开端。因此,它不再可以被如此理解,仿佛它依赖于一个才要去准备它的纯粹的要素的导论学科。在严格的体系性的视角下,科学因此是无前提预设的,并且不需要外在的辩护。《逻辑科学》因此无论如何不再在它根据原初的构想曾经预设过《精神现象学》的那个意义上预设它了。
从富尔达的视角来看,从【1817】年起,《精神现象学》虽然仍然被视为通往科学的导论,但它如今不再被置于科学之前,而只是被本质地归属于科学。【66】尽管如此,它在关涉体系方面仍然履行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的科学,黑格尔说,逻辑学考察一个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上帝的呈现”的内容,“即他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之前的永恒本质中的样子”(GW21, 34)。然而,与这个声称相冲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在一个被规定的、在某些方面显然是偶然的历史时间点上出现。因此,它在关涉那个进行科学活动的主体方面,并非显现为一个永恒的必然之物,而是显现为历史上的偶然之物。这种显象,“它从一开始就附着于科学,并且只有在终点才规定自身为它的概念的显示”,使得“一种体系性的验证成为必要……,通过它,那种关联被中介,即开端虽然不与作为此类的科学相关,但却与那个想要决断去进行哲思的主体相关。”【67】
如果我们从《逻辑科学》的体系内部的建构出发,这个要求可以被最好地理解。逻辑学以不被规定的直接性或纯粹存在开始。属于存在的直接性的是,它向虚无缥缈之物的过渡显现为一个向一个与它外在地对立的、漠不相关的东西的过渡。然而,在逻辑学的整个进程中表明,那个构成逻辑学的显现的开端的存在,在真理中与被实现的、即绝对理念是同一的。【68】因此,将会证明,它的不被规定的直接性只是那个绝对地自身规定并被自身中介的理念从其开端起就附着于其上的必然的显象。因此,那个开端的映象,仿佛过渡是一个纯然外在的、可以说从外部在存在的思想上被设定的东西,将被拆解,通过展示出,它是理念的在自身中分化的统一的显象。因此,逻辑学的真正的逻辑学的开端不是存在,而是理念自身。【69】
当我们向自己呈现《逻辑科学》的这个进程时,我们不可以忽略,它是由一个有限的、进行哲思的主体来完成的,这个主体根据黑格尔的要求已经决断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科学的这个主观的、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决断主义的开端,因此也显现为如同纯粹存在自身一样是不被规定的和未被中介的。【70】那个决断,科学通过它而获得其现实性,可以说与其他可能的精神的立场并列地进入世界。因此,历史的偶然性的显象附着于它,而它作为科学的声称,起初除了任何其他的真理主张之外,没有别的验证。于是,《精神现象学》的任务将是,在关涉那个进行决断的、进行哲思的主体方面去展示,为何科学的真正的、在自身之中被中介的开端,起初显现在主观的决断的直接性之中。它必须展示,那个如此显现的知识,是理念最初意识到其自身的必然的方式。或者,换用另外的话说:《精神现象学》的任务如今被如此规定,即它必须给出与《逻辑科学》平行的证明,证明那个显现的知识实际上是理念的显示。【71】
这个思想进程引向对“绝对知识”一章的结尾段落的一个有说服力的阐释。在那里,黑格尔说,科学在它自身之中包含着“放弃纯粹概念的形式并实现概念向意识的过渡的必然性”:
“因为认识其自身的精神,正因为它把握了它的概念,它就是与自身的直接的一致,它在其差别中是关于直接的东西的确知,或感性的意识,——即我们曾由之出发的那个开端;它的这种从它的自我的形式中的释放,是它的关于自身的知识的最高的自由和确信。”(GW9, 432)
乍一看,这种向作为感性意识的开端的返回,如何与《逻辑科学》的开端相关联,是不太清楚的。富尔达能够使这一点变得可以理解,尽管只是从一个对《精神现象学》的后来的重新阐释的视角来看。
正因为意识或显现的知识自在地是精神,它才绝对有理据地带着对无条件的真理的主张而出现。因此,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达到自身的精神,必须承认那个主张在其根本的理据性中的地位。但这更切近地意味着,要就那个主张在它被提出的每一种形态中,考察其理据的根据,并展示这个根据。因此,如果达到自身的精神去理会意识的那些形态的真理主张,这便具有这样的体系性的意义,即它要真正地证明自身是这些形态中每一个的自在存在;这属于它返回自身的一部分。用富尔达的话来说:
“附着于科学的开端并在其终点才瓦解的显象,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科学由于其源自绝对精神的有限的知识形式而无法摆脱;而是,它的这个有限的、根据客观的中介来看是从那些有缺陷的显象书写而来的特征,在与逻辑的东西的统一中,恰恰构成了科学的绝对性、真理和自由。诚然,科学如同作为整体的绝对精神一样,仍然是一个知识的完满过程。但是,一个关于绝对内容的知识,如果它不也是其不纯粹的意识——如果愿意的话:其无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知识。难道不可能是这样吗,即科学,当它在结尾不仅把握了这种无知的必然性,而且也把握了其合理性时,它就使自己能够作为体系来超越自身?”【72】
这个运动是双重的。在一个方向上,它呈现为科学的立场的的一种外化,以及对知识的真理的一种承认,而且恰恰也在其直接的定在(意识形态)的不完满的形式中。然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它同时又呈现为科学的立场从其开端的直接性向自身的自我中介和返回——它证明科学的那个开端的显现是一个与意识的那些形态分享同一个理据根据的显现。
如果富尔达是对的,那么这也就是《精神现象学》构成逻辑学的“前提”的意义。因为决断去进行纯粹的思维活动的主体在开始逻辑学时,设定了其活动性的意义在于,它将由此达到对真理的知识,或者至少应当达到。用《精神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达:它预设了确知与真理的内在的相互归属性,这是每一个真理主张本身就蕴含的。现在,这个内在的相互归属性虽然本身就是《逻辑科学》的主题,因为它在人格性的设定中达到顶峰,亦即在客观的理念向个体的主观性的自身深化中(参见GW12, 246)。【73】因为确知与真理的相互归属性最终就植根于此。尽管如此,在那个现实的、进行思辨的逻辑学活动的进行哲思的主体那里,仍然存留着一个不可扬弃的直接性的环节。它在于他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决断之中,因为这个决断无非是说,他相信思维活动自在地并且无需关联从别处被给予的对象,就能够使确知与真理的内在的相互归属性现实化。关于这个前提预设,主体必须在一个与科学的体系有别的学科中达成理解。这更切近地意味着,要就以下两点达成理解:第一,真理主张的提出,总体而言并作为此类,是精神或理念的直接的定在方式。因此,他自己借以开始逻辑学的那个被预设的对真理的主张,本身就已经是精神的一种定在方式。但第二,这意味着,思辨的逻辑学家的活动性与每一种形式的据信为真都是本质上同一的,因为每一种都是一种对真理提出主张的方式。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进入一种与据信为真的其他方式的现实的共同体和交锋之中,以便证明这种本质的同一性。科学的主体恰恰是通过《精神现象学》的道路来确保这一点的,因为它投入到意识在其杂多中的经验之中。
【4.】 结束语
我们最后了解了一个建议,关于人们如何能够坚持逻辑学预设了《精神现象学》这个理念,而又不损害《逻辑科学》对无前提预设性的声称。《精神现象学》是一门学科,在其中,思辨的逻辑学家就他自己的认识活动性的状态,既着眼于逻辑学也着眼于其他据信为真的方式,达成理解。在此,关键在于,要将在他自己进入科学时所做出的那个前提预设,即对真理的知识是可能的,在其普遍性中作为理念的直接的定在方式而使其变得明晰。然而,这个前提预设在其直接性中并不属于《逻辑科学》,因为后者证明了理念与存在的同一性,而非理念与想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那个决断的同一性。由此,循环性的嫌疑便被消除了。
这个进路是否也对这里处理的其他两个问题有影响呢?就科学的抽象的环节与意识的形态之间的契合而言,将要得出如下的结论:提出一个科学性的真理主张意味着,在对象上设定一个本质规定,并由此规定一个被规定的知识类型。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标示了这样一个点,即一个各自的意识的形态应当与一个纯粹的思维规定在其中相对应。从最后所介绍的进路的视角来看,这只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恰恰应当是《精神现象学》所关涉的:展示思辨的真理主张与其他据信为真的方式的内在的同一性。但是,《精神现象学》在关涉真理主张的主观的提出方面所完成的事情,《逻辑科学》则在关涉在这种主张中所蕴含的确知与真理的相互归属性的最终的根据方面来完成。因此,如果意识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一种阐明确知与真理的相互归属性的被规定的方式,那么在它们与那种归属性在逻辑学中被展开的那些环节之间,甚至必须存在一种契合。
《精神现象学》是否预设了逻辑学?根据我对富尔达的进路的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以‘是’来回答。因为它的意义只有从想要纯粹地进行思维活动的那个决断的视角才能被领会。在尚未占据科学的立场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亲身体验那个《精神现象学》应当去回答的难题。人们在其中至多只能看到彻底怀疑的道路,而这毕竟只呈现了该作品的否定的方面。然而,本质上关键在于,肯定思辨的知识与显现的知识的内在的共同体,而这个肯定的方面将一直被隐藏,直到人们不再感受到需要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而与在《逻辑科学》中被呈现的绝对的主观性相中介。
最后,人们或许可以触及这个问题,即《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这种关系规定在何种程度上与今天的思维活动相关。首先,原则上必须与霍尔姆·特滕斯(Holm Tetens)一道确认,哲学是一门更高阶的学科:“哲学从来不会绕过人而只朝向世界。哲学最终追问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它们对于人和他的生活意味着什么。”【74】这在同等程度上也适用于那个被称为“哲学”的世俗世界内的事件;它的定在及其与进行哲思的主体的关联,同样是更高阶段的自我反思的对象。但仅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人们就可以说,《精神现象学》大概是前所未有地试图以如此全面、体系性并且方法上严格的方式,就哲思对于人意味着什么给出说明,并将自身的科学性的进路完全地塑形入哲学的有限的、被历史地特定化的主体的自我反思之中。仅凭这一点,《精神现象学》就保有一种不容高估的、作为科学性的自我理解的范式的价值,无论人们在其他方面如何看待这个事业的进路和成败。
我们今天经历着科学的多样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碎片化,这是黑格尔几乎无法预感到的。许多科学革命此外还为我们磨练出一种对历史性地被规定的东西的感觉,并教会了我们谦逊,当事关以绝对的有效性提出知识主张时。黑格尔的统一思维活动及其为他的体系声索绝对真理的意愿,因此离我们很远。但恰恰也着眼于科学性的和哲学性的自我理解,我们不可以压抑关于实在性的基础的结构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的那个问题。【75】这其中包含着对一个(更高阶段的)问题的理解,即为何以及以何种形态,这个问题为了我们而在此时此地提出。自1970 年代以来,人们已经重新开始更多地思考意识的本性及其与被物理主义地理解的自然的关系。将这个问题理解为一个并非偶然产生的问题,是否可能?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必然性,而且不仅为了我们,也自在地存在,即自然通过这个问题而返回其自身?或许甚至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这个问题将今天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卷入其中的那些困境,其自身展示出一种体系性,它可以说在剪影中暗示了其在实在性中的根据。这些无疑是非常思辨的问题。但它们因此并非无意义的问题。但是过去五十年的主流哲学中的普遍情绪对它们并非特别开放。因此,普遍缺乏用以回答它们,甚至用以对它们进行切合事情的表述的中介。诚然,我们既无需在形式上也无需在内容上追随黑格尔,但是,如果一个人作为哲学家,既想要真正严肃地对待他自己的思维活动,也想要严肃地对待作为此类的思维活动这个事实的话,那么他仍然被明智地建议去接续由他所开启的哲学传统。
【1.】 文献来源
黑格尔(Hegel),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Georg Wilhelm Friedrich):全集。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Nordrhein-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en)与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合作编辑。汉堡(Hamburg)1968年起。
- (GW 4):《耶拿批判著作》,《全集》第【4】卷,由哈特穆特·布赫纳(Hartmut Buchner)与奥托·珀格勒(Otto Pöggeler)编辑,汉堡【1968】年。
- (GW 7):《耶拿体系草稿II》,《全集》第【7】卷,由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与约翰·海因里希·特雷德(Johann Heinrich Trede)编辑,汉堡【1971】年。
- (GW 8):《耶拿体系草稿III》,《全集》第【8】卷,在约翰·海因里希·特雷德的协助下由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编辑,汉堡【1976】年。
- (GW 9):《精神现象学》,《全集》第【9】卷,由沃尔夫冈·邦西彭(Wolfgang Bonsiepen)与莱因哈德·黑德(Reinhard Heede)编辑,汉堡【1980】年。
- (GW 10,1):《纽伦堡中学课程与中学演讲(1808–1816)》。第【1】卷。《中学课程与中学演讲》,由克劳斯·格罗奇(Klaus Grotsch)编辑,汉堡【2006】年。
- (GW 10,2):《纽伦堡中学课程与中学演讲(1808–1816)》。第【2】卷。《附录与补遗》,由克劳斯·格罗奇编辑,汉堡【2006】年。
- (GW 11):《逻辑科学》。第一卷。《客观逻辑(1812/13)》,《全集》第【11】卷,由弗里德里希·霍格曼(Friedrich Hogemann)与瓦尔特·耶什克(Walter Jaeschke)编辑,汉堡【1978】年。
- (GW 12):《逻辑科学》。第二卷。《主观逻辑(1816)》,由弗里德里希·霍格曼与瓦尔特·耶什克编辑,汉堡【1981】年。
- (GW 13):《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17)》,《全集》第【13】卷,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Hans-Christian Lucas)与乌多·拉梅尔(Udo Rameil)的协助下,由沃尔冈·邦西彭与克劳斯·格罗奇编辑,汉堡【2001】年。
- (GW 19):《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27)》,《全集》第【19】卷,由沃尔夫冈·邦西彭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编辑,汉堡【1989】年。
- (GW 20 / ENZ):《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全集》第【20】卷,由沃尔夫冈·邦西彭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在乌多·拉梅尔的协助下编辑,汉堡【1992】年。
- (GW 21):《逻辑科学》。第一部分。《客观逻辑》。第一卷。《存在学说(1832)》,《全集》第【21】卷,由弗里德里希·霍格曼与瓦尔特·耶什克编辑,汉堡【1985】年。
- (HBr):《黑格尔往来书信》。由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编辑,汉堡。
【2.】 研究文献
阿尔恩特(Arndt),安德烈亚斯(Andreas)(【2000】):《开端的反思:关于<逻辑科学>的开端的评论》,载于:阿尔恩特/伊贝尔(Iber)(编):《黑格尔的存在逻辑:阐释与视角》,第【126–139】页,柏林(Berlin)。
鲍(Baugh),布鲁斯(Bruce)(【1993】):《现代法国哲学中的黑格尔:不幸的意识》,载于:《拉瓦尔神学与哲学》【49】(【3】),第【423–438】页。
- (【2003】):《法国的黑格尔:从超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奥克森(Oxon)/纽约(New York)。
布赫纳,哈特穆特(【1969】):《论怀疑论在青年黑格尔那里的意义》。载于:《黑格尔研究》,别册【4】,第【49–56】页。
狄尔泰(Dilthey),威廉(Wilhelm)(【1959】):《黑格尔的青年史以及关于德国观念论历史的其他论文》,载于:同上作者,《文集》,第【4】卷。斯图加特(Stuttgart)/哥廷根(Göttingen)。
杜辛(Düsing),克劳斯(Klaus)(【1976】):《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观性难题。关于观念论的原则与辩证法的体系性的与发展史的研究》,波恩(Bonn)。
- (编)(【1988】):《谢林与黑格尔的第一个绝对形而上学(1801–1802)》。I. P. V. 特罗克斯勒(I. P. V. Troxler)的讲授课综合笔记,科隆(Köln)。
- (【1969】):《思辨与反思。论谢林与黑格尔在耶拿的合作》,载于:《黑格尔研究》【5】,第【95–128】页。
福斯特,埃卡特(【2011】):《哲学的2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Main)。
- (【2002】):《<判断力批判>第76、77节对于后康德哲学的发展的意义》,载于:《哲学研究杂志》【56】,第【170–90】,【321–45】页。
- (【2008】):《黑格尔的“发现之旅”。<精神现象学>的产生与建构》,载于:韦尔施(Welsch)/维韦格(Vieweg)(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一部现代关键著作的合作评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福斯特,迈克尔(Michael)(【1998】):《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理念》,芝加哥(Chicago)。
富尔达,汉斯·弗里德里希(【21975】):《黑格尔<逻辑科学>的一个导论难题》,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1966】):《论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学》,载于:《黑格尔研究》,别册【3】,第【75–101】页。
格洛克纳(Glockner),赫尔曼(Hermann)(【1952】):《黑格尔》,斯图加特。
哈贝马斯(Habermas),尤尔根(Jürgen)(【1973】):《认识与旨趣》,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哈林(Haering),特奥多尔(Theodor)(【1934】):《<精神现象学>的产生史》,载于:B. 维格斯马(Wigersma)(编):《第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会刊》,第【118–38】页。图宾根(Tübingen)。
- (【1929】):《黑格尔。他的意欲与他的著作:黑格尔的思想与语言的一部编年发展史》,【2】卷,莱比锡(Leipzig)与柏林。
哈伊姆(Haym),鲁道夫(Rudolf)(【1857】):《黑格尔与他的时代。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本质与价值的讲授课》,柏林。
海因里希斯(Heinrichs),约翰内斯(Johannes)(【1974】):《<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学》,波恩。
霍夫迈斯特,约翰内斯(Johannes)(编)(【1934】):《G.W.F.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载于:《全集》(考订版),由格奥尔格·拉松(Georg Lasson),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编辑,第【11】卷,莱比锡。
霍斯特曼,罗尔夫-彼得(【2003】):《将知性引向理性?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对康德的交锋》,载于:韦尔施/维韦格(编):《思维活动的旨趣。从今日视角看黑格尔》,慕尼黑(München),第【89–108】页。
- (【2006】):《黑格尔的事物的秩序。<精神现象学>作为一种一元论的本体论的“先验主义的”论证及其知识论的蕴涵》,载于:《黑格尔研究》【41】,第【9–50】页。
- (【2014】):《开端之前的开端。论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的关系》,载于:科赫(Koch)/维韦格/希克(Schick)等人(编):《黑格尔<逻辑科学>200年》,汉堡,第【43–58】页。
伊波利特(Hyppolite),让(Jean)(【1935】):《依据新近著作看黑格尔的青年时期作品》,载于:《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42】。
- (【197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法文原版译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巴黎【1946】年。],埃文斯顿(Evanston),伊利诺伊州(IL)。
耶什克,瓦尔特(【2003】):《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影响》,斯图加特。
基默勒(Kimmerle),海因茨(Heinz)(编)(【1967】):《关于黑格尔教职活动(1801–7)的文献》,载于:《黑格尔研究》【4】,第【21–99】页。
科耶夫(Kojève),亚历山大(Alexandre)(【1969】):《黑格尔导读:<精神现象学>讲座》,由布鲁姆(Bloom)编辑,由尼科尔斯(Nichols)翻译。[法文原版译本:《黑格尔导读:<精神现象学>讲座》。由奎诺(Queneau)编辑。巴黎第【2】版【1947】年],伊萨卡(Ithaca)/伦敦(London)。
洛(Lowe),E. J. (【2002】):《形而上学概览》,牛津(Oxford)【2002】年。
卢卡奇(Lukács),格奥尔格(Georg)(【1948】):《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苏黎世(Zürich)/维也纳(Wien)【1948】年。
珀格勒,奥托(【1973a】):《<精神现象学>的构篇》,载于: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与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编):《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材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329–90】页。
- (【1973b】):《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现象学》,载于:同上作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理念》,弗莱堡(Freiburg)/慕尼黑。
匡特(Quante),米夏埃尔(Michael)(【2001】):《“意志的人格性”与“作为这个的我”。关于黑格尔自我意识构想中的个体化难题的评论》,载于:M. 匡特/E. 罗饶(Rózsa)(编):《中介与和解。黑格尔思维活动对于一个日益融合的欧洲的现实意义》,明斯特(Münster),第【53–67】页。
罗森克兰茨,卡尔(Karl)(【1844】):《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生平》,柏林,[重印本:法兰克福第【2】版【1988】年。]
舍费尔(Schäfer),莱纳(Rainer)(【2001】):《辩证法及其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特殊形式》,《黑格尔研究》,别册【45】。
特滕斯(Tetens),霍尔姆(Holm)(【2006】):《哲学论证。一个导论》,慕尼黑。
特雷德,约翰·海因里希(【1975】):《现象学与逻辑学。论一场讨论的基础》,载于:《黑格尔研究》【10】,第【173–209】页。
瓦尔(Wahl),让(Jean)(【1929】):《黑格尔哲学中意识的不幸》,布里奥讷(Brion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