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光州走向了民主,而我們沒有?
1980年的光州和1989年的北京,都曾站上時代的轉捩點。兩地的青年走上街頭,呼喊著自由、選舉和反對腐敗;政權的回應卻是槍口、鎮壓與封鎖。兩場運動,一場成了民主的起點,一場卻成了禁忌的起點。
人們常用「韓國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來簡化和對比這兩段歷史,但歷史從來不只是選擇題。若要誠實面對那個問題——「為什麼光州之後韓國走向了民主,而我們沒有?」——就得放大時間的座標,把視野放回到當時的世界:1980年代,那是一個民主正在世界各地發酵的時代。
這場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從南歐延燒到拉美,再進入東亞。韓國是這波浪潮的典型受益者,而中國,則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把自己鎖進了孤島。

一、什麼是「第三波民主化」?
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經典著作《第三波民主化》中指出,從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開始,全球出現了一波劇烈的民主轉型浪潮。這波浪潮席捲了南歐(葡萄牙、西班牙、希臘)、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東亞(南韓、台灣、菲律賓),以及中東歐與蘇聯集團的部分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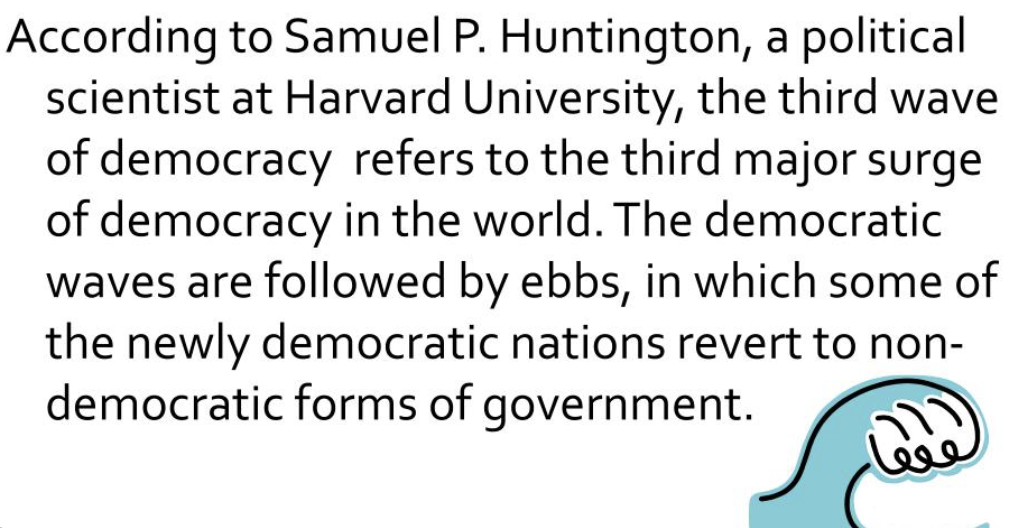
在1974到1991年之間,超過30個威權政體轉向了民主選舉制度。這種選擇,並不能簡單的歸類為哪個政權突然「醒悟」。它的背後有許多不同力量的推動。例如經濟現代化帶來的中產階級的崛起,冷戰末期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以及技術傳播與跨國公民社會的興起。
1979年的韓國就在這個浪潮的中心之一。從1979年朴正熙遭刺殺後的動盪開始,民間對全斗煥軍事政權的不滿逐年升高。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光州事件固然是一場血腥鎮壓,但並未終結掉民眾對於民主的追求,反而成為了集體記憶核心。自1984年開始,每年的5月18日都有人上街紀念,1987年更是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迫使政權開放總統直選。
當時的中國同樣正處在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但在1989年之後,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向民主邁進時,中國卻用武力與封鎖將自己重新拉回威權與穩定的軌道。
二、 從歷史的視角看光州與六四
如果將光州與六四放在這場全球浪潮之中,它們其實是非常接近的歷史節點:
如果我們嘗試將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放在這場全球的民主浪潮之中,我們會發現他們有非常相近的時間節點。韓國的光州事件發生於1980年5月,帶來的後果是民間的持續抗爭,餅逐步推進了民主化進程。
在1986年2月,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導致了馬可仕政權倒台。
1987年6月,南韓總統直選改革開始,民間壓力迫使政權讓步。
1989年6月,六四運動發生,中國的言論自由等在鎮壓後全面收緊,改革急轉彎。
1989年下半年,伴隨東歐劇變,多國共產政權垮台。
我們看到一些微妙的不同。在光州事件後的幾年,韓國與中國的民間社會都曾經歷一段高壓與壓抑時期。但是韓國在這個時期,逐步建立起一個跨世代和跨階層的民主聯盟,中國在六四後則被系統性地拆解了這些連結的可能。中國的抗爭運動、記憶與組織都發生了斷裂。這三點是民主化運動最需要的基礎。
三、體制的差異與軍隊立場的不同
民主轉型能夠實現,單單依靠民間的推動可能難以實現。制度內部的裂縫也是重要的一環。
我們看到,在韓國,鎮壓光州的元兇是軍方,但是軍方內部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在1980年代後期,在韓國的軍方內部,部分年輕軍官開始反思軍事介入政治的代價,加上美國開始施壓「去軍事化」,最終軍隊開始接受退出政治的妥協。
而在中國,情況則有所不同。解放軍從誕生起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其效忠對象是黨而非國家。這種結構性設計,讓軍隊在後期得以成為政權施壓的工具,而不可能是中立力量甚至是潛在改革推手。在六四鎮壓後,軍方不僅未受懲處,還被稱為共和國衛士,他們的地位在體制中也獲得了進一步鞏固。
在實施鎮壓的時候,中國的軍隊既沒有外部的壓力,也沒有內部的制衡,它們的存在,讓社會的抵抗更難轉化為制度的鬆動。
四、國際大環境和地緣政治
別忘了,那時正值冷戰的尾聲。韓國作為美國的軍事盟友,在光州事件發生時,美國政府曾一度默許全斗煥政權的行為。但到了1987年,面對美國國內的輿論與國會壓力,華府追蹤選擇支持韓國民主化。西方世界在道德上站隊的同時,也對韓國實施了經濟與外交上的壓力。
對比中國呢?在六四之後,中國雖然遭遇了短暫的制裁,但是西方很快調整了立場。歐洲與美國開始施行「接觸政策」,他們試圖透過貿易與合作「溫和改造」中國。當時有一種廣為流傳的想法,許多人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自由,在政治上,中國也勢必走向自由。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獲利巨大,而人權議題則被擱置、遺忘甚至視為干涉內政。這二者之間並沒有絕對的聯繫。
歷史有時的確是現實主義的。
韓國的人民得到了壓力與支持,而中國的人民,得到了等待與迴避。
五、記憶作為手段
光州事件在韓國的社會中從禁忌走向公共紀念,經歷了一段長達十數年的記憶建構過程。如今,南韓的每一個中小學生都會在五月學習那段歷史,有紀念館、有教育資源、有文學與影像作品將其轉化為集體文化。
六四事件在中國則截然不同。這一事件不只從課本中消失,連在網路、親子對話與城市空間中也被移除。唯一留下的是那些不斷被封鎖的詞彙、圖片、與流亡者的記憶。
記憶若無法流通,就無法產生社會連結;沒有連結,就無法轉化為政治壓力。這也是中國在六四之後,被鎖進沉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寫在最後的話
1980年代,是亞洲街頭最有民主希望的一段時期。從台北、高雄、馬尼拉、光州、首爾到北京……我們都能看到年輕人們拿著標語走上街頭,高呼著民主,盼望著未來。三十年後,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社會走向了不同的軌道。台灣轉型成功,韓國雖動盪但制度逐漸成熟,菲律賓動盪不安但仍維持選舉政治;而中國,則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威權資本主義國家之一。
民主不是一次抗爭,而是一種不讓記憶被奪走的能力。光州做到了這件事,而我們,還沒放棄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只要這個問題還被提出,它的答案,就還在路上。
七、參考文獻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im, S. (2000). Kwangju Uprising: A Miracle of Asian Democracy as Seen by the Western and the Korean Press. EastBridge.
Snyder, R., & Mahoney, J. (1999). The Missing Variabl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32(1), 10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