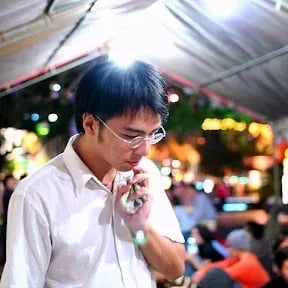組織者視角下《受壓迫者教育學》
「受壓迫者教育學」是巴西群眾教育工作者 Paulo Freire (保羅‧弗雷勒 )的著作。這本書影響全世界的群眾組織工作者,說是群眾組織工作者的聖經也不為過。在台灣,最近的譯作是2004年由方永泉教授所譯,並由巨流圖書出版。因為書名,可能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談「教育學」,吸引到的讀者為教育工作者為多。大多數的群眾組織工作者,並不認為自已是在做「教育」工作,或許他們也有意識地避免人們認為自己是在做「教育」工作,畢竟在台灣社會,「教育」等於「上對下」的「填鴨式」教育。
實際上,Freire所著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是1960s至1970s年代間,巴西農民組織工作者與巴西農民一同發展出來的知識。當時的農民大多是文盲,幾乎終其一生都在大地主的莊園中生活,除了在自己的農作中有些許自主性之外,生活幾乎都被大地主控制,身陷日復一日的繁重勞動,更難主動去認識與改變自身的處境。因此巴西的農民組織工作者,透過識字教育,使農民自我組織,認識並改變自己的處境。
我們可以想見,「識字教育」聽起來並不這麼政治性,讓農民能夠看懂報章雜誌,也不代表他們會反抗統治者。但將時間尺度拉長來看,從「識字教育」到「媒體識讀」,甚至到眼前的「對抗假新聞」,有個共通性,就是在對抗「無知」,因為這使讓受壓迫者不識字,剝奪他們認識世界的能力;讓受壓迫者接收到,受到統治者設定與篩選過後的訊息;讓受壓迫者接受到海量訊息,卻無從分辨真假。
我們現在似乎可以用「資訊不對稱」去形容這種處境,但也是因為我們生活在資訊時代,早就知道人類文明有超乎我們無法想像的知識累積,而我們終其一生只能接觸到極少部份,因此我們才能意識到,統治者或許並沒有將知識「藏」起來,只是我們「不知道在哪裡」,這也衍生了「資訊公開」或是「主動資訊揭露」的概念。
或許是因為「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具體行動就是在做「識字教育」,所以大多數人認為「受壓迫者教育學」,聽起來似乎只是一種教育理論,一種教育方法論。雖然我也在前文引申至目前台灣當前與在地的脈絡,在台灣,若要讓受壓迫的人們開始行動,就要使他們擁有「媒體識讀」的能力,並且要團結起來「打擊假新聞」。似乎「受壓迫者教育學」就是一種「解決無知狀態」的理論與方法而已,但「『知道更多』就等於會去主動『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嗎?當然不會,當時「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實踐,及其理論發展的背景也告訴我們,人們要脫離無知狀態,是來自於「不斷對話的實踐」[1],壓迫者會長存在受壓迫者心中,時刻影響他們看待世界的觀點、判斷與行動,因此去除「無知」狀態這件事情,其實就是組織工作者與民眾在對話中的「邂逅」[2],讓民眾開始奪回自己認識世界的主動權,重新「命名」[3]週遭的一切,或是自信地提出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或是面對其他人的質疑,逐步地使自己的認識,延展到自己目前所感受到一切,這些一連串的行動本就指向現實,並且隨著對話的開展,將改變現實,或是隨著現實被改變,而對話也逐步推進,這將使「沉陷」在現實中的受壓迫者,逐步「覺醒」。因此,「受壓迫者教育學」並不只是一種台灣社會普遍認知到的「教育」(就算是體制外教育的實踐也不一定指向社會改造),並不是組織工作者將對其有益的知識塞進受壓迫者腦袋,而是受壓迫者擁有主動地去改變的受壓迫處境。而這個過程當中,組織者也與受壓迫者一起學習。
因此「受壓迫者教育學」所提到的「教育」觀點,也就與目前「老師─學生」的關係不同,本書第二章也闡明了「壓迫社會」下的教育傾向:
(a) 由教師來教學,而學生只能被教;
(b) 教師知曉一切,而學生一無所知;
(c) 由教師來思考,至於學生只能是被思考的對象;
(d) 由教師發表談話,至於學生則只能乖乖地在旁邊聽話;
(e) 由教師來施予紀律,至於學生則只是被訓練的;
(f) 教師可以決定並強化他的選擇,則學生則必須服從;
(g) 教師可以行動,但學生只能透過教師的影響產生自己也有行動的幻覺;
(h) 教師選擇教學的內容,而學生(未經過協商)只能去適應它;
(i) 在教師身上混淆了知識與人格的權威,而其所處的地位則是與學生自由相對立的;
(j) 教師是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學生只是客體。
壓迫社會的教育傾向,不僅只是為了鞏固教育場域當中的權力關係,也是使學生適應出社會之後將面對到的統治秩序。若將上述十點當中的「教師」替換成「組織者」,「學生」替換為「群眾」,「教學」替換為「組織」:
(a) 由組織者來組織,而群眾只能被組織;
(b) 組織者知曉一切,而群眾一無所知;
(c) 由組織者來思考,至於群眾只能是被思考的對象;
(d) 由組織者發表談話,至於群眾則只能乖乖地在旁邊聽話;
(e) 由組織者來施予紀律,至於群眾則只是被訓練的;
(f) 組織者可以決定並強化他的選擇,則群眾則必須服從;
(g) 組織者可以行動,但群眾只能透過組織者的影響產生自己也有行動的幻覺;
(h) 組織者選擇組織的內容,而群眾(未經過協商)只能去適應它;
(i) 在組織者身上混淆了知識與人格的權威,而其所處的地位則是與群眾自由相對立的;
(j) 組織者是組織過程中的主體,群眾只是客體。
「壓迫」與「受壓迫」關係,並不是全有全無的兩種狀態,時常是在兩極當中遊走。各位可以回頭去思考自己參與運動的經驗,是否「受壓迫」?對此,我無意譴責引領各位進入改革運動的組織者們,畢竟花了不少心力與你建立合作關係,也與各位有一定的信任程度。更何況,或許你也認為,你倆之間的互動,並不帶有壓迫性質,也確實完成了某些目標。因此我想強調的重點是,你適應某一種組織關係,那不只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對一個基進的[4]組織者來說,組織關係是否能夠使雙方一起學習,真正「把他們自己與民眾一起組織起來」,而不是只將民眾當自己的聽眾、自己的手腳、自己的…什麼東西(例如選票)。畢竟,我常在運動場域中發現,一個較依賴權威的人,可能就會接受運動中權威者的思考與安排,當然也不太會對行動發展出自己的意見;或是,某些人已習慣像壓迫者,就算言詞全部是進步語言,但實際上並沒有與其他人有對話的空間,以自己的意見為主。切記,「解放的教育包括了認知的行動,而不只是資訊的轉移。它是一種學習情境」在這個情境中,人們互相分享對現實的不同認知,並且採取對策一同行動。
「解放是一種實踐─是人們對於他們的世界進行行動與反省,以進一步改造世界。」[5]
但一個組織者、運動者該如何察覺到自己其實也跟那些壓迫者一樣,把群眾當作無知的、只能被控制的人呢?大致上可以先從三個方面來思考。
第一個方面是,想和群眾結合的組織者,會有什麼原因使自己無法跨出這一步?書中提到,這些想和群眾結合的組織者,大多是原屬於壓迫者階級的成員。這些人「仍然帶著其出身的標記:他們的偏見、他們的缺陷(包括了他們對於民眾之思考。)因此,…他們會落入「假慷慨」之中。…這群常會自認是這場改造的實際執行者。他們所談論的固然與民眾有關,但他們並不信任民眾,然而相信民眾才是革命改造中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或這些組織者反對話的教育體制訓練成專業者,「即使他們的專業會讓其與民眾有所接觸,他們仍然堅信他們的工作是在「給予」民眾,知識與技術」。他們推出的行動方案都是自己的目標、信念與看法[6]。「對話需要對於人性有高度的信心」,信任民眾的組織者甚至在遇見對方前已然信任對方,但也不是沒有批判性,他知道人有創造與轉化的力量,人處在異化的環境下,人能受到傷害,但他將這種可能性是為組織者必須回應的挑戰。[7]
第二個方面,想和群眾結合的組織者,因為對民眾的不信任,也「原則性」[8]的否定基進的組織實踐。壓迫者嘗試操控民眾,「在某些歷史情境中,操控是透過宰制階級與被宰制階級間的「協定」而完成的─表面上,這些協定也許會給人一種是兩個階級對話的印象。…到最後,這些協定會被宰制者利用來完成其自身目的」[9]而「在一個操縱的情境中,左派幾乎總是受到『快速重返權力』的誘惑,因而忘記了們必須加入受壓迫者形成組織,他們也會誤入歧途試圖與宰制菁英進行一場不可能的『對話』。結果,左派將會為菁英們所操控,落入菁英們的遊戲中,但左派卻還以為這樣是『務實』」[10]。不與民眾結合的組織運動,在台灣司空見慣,在此我們可以回憶蔡有全先生於逝世前在政經看民視的一段話:「希望民進黨的公職人員,不管縣市長、或者立委、或者縣市議員,不要只會顧樁腳而已。要透過你們的人脈,你們的資源,一批一批的,把你的支持者轉換成為台灣建國的一個締造者,一個參與者,一個歷史的覺醒者,一個想自我解放的人。若不是這樣,我們會死在這種選舉的輪迴裡面,四年一次四年一次四年一次...」[11]
第三個方面,想和群眾結合的組織者,不知道從何著手起。Paulo Freire在書中直言:「向民眾靠攏的轉變,所需要的是一種深刻的重生(rebirth)。凡是經歷過此種重生經驗的人都必須採取一種新的存在形式:他們不能再是從前的自己。只有透過與受壓迫者的革命情誼,這群改宗者才能理解:在不同時刻中,受壓者的生活與行為方式實則都反映了宰制結構」[12]。「新的存在形式」,我認為意指一種新的關係、新的身分,而這也只能在某一組織過程中才能落實,用現在的概念來理解,若一個組織內部連「內部民主」也沒有:每個人有對等的知情權與發言權,也不會真正產生對話。另外,目前組織被當作一種「行動模式」,只為當下的目標存在;或是一種聯誼性質的聚合,到底誰是組織成員也無法確定,但我想大多數組織者的考慮來自於,自己有多少對話的成本:時間、體力與經驗,才決定是否要與特定對象展開對話。另外一個考慮也在於,眼前的群眾是否也一同投入了組織運動中,因此決定是否要花時間開展對話。但確定組織的邊界,不也劃開了某些接近自己的群眾可以對話,而某些群眾我不願意花時間對話嗎?
若將組織視為一種高度教育性的過程,目前組織者所面對的「無法組織」,其實就反映了目前的組織者,面對到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群眾,群眾本身可能處於某一種壓迫情境下,或是處於多重複雜的壓迫處境中,而組織者本身並不一定能與所有群眾開展對話,原因並不是無法理解對方的處境,我的經驗中,更常是因為感到陌生,甚至未察覺自己心中對其帶有偏見。因此,我想「是否要與眼前的人開展對話」,是個假問題,所有迎面而來的人都可以開展對話,但我們仍然需要記得,對話指向行動,因此與他人間的對話,不僅期待能延續下去,並且將此對話擴展出你與對方之間,擴散到你們社群之外,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對話,並採取行動。當然,你也可能會遇到「咬文嚼字」或是「盲動」[13]的人,「光說不練」、「一受刺激就反應」,或是「時間到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的群眾,難以展開對話,但我想組織者唯一可做的事情,仍是持續不輟的對話,在本身的組織或是社群中建立對話的文化。
「在對話理論中,革命行動在每個階段都不能放棄與民眾的融為一體。融為一體會再度引發合作,而合作則會使領導者與民眾達到格瓦拉所形容的水乳交融。這種水乳交融只有當革命行動是真正的人性化,能夠設身處地為人設想、充滿愛、溝通的、謙遜時,才會存在,它的目的是為了解放。」[14]
篇幅有限,先簡單分享我對「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的理解。這份文件並不是以研究生做摘要的習慣去完整介紹書中篇章,而是考慮到目前在校學生組織工作者的狀態,感謝過去與現在,在校內組織的朋友們,幾年來願意與我分享在校組織的經驗,我也才能反芻這本書,扼要介紹這本書當中的問題意識,做為眼下展開「2019年推進各校組織工作」的對話材料。
[1] 頁209。
[2] 頁128。「對話是人與人之間的邂逅(encounter),是以世界為中介,目的是為世界命名」。頁129。「對話不能是一種人與人間充滿敵意的、具有爭論性論辯,因為在這樣充滿敵意的行動中,也不是為了尋求真理,而只是將自己他們自己的「真理」強加在別人身上。
[3] 頁128。「為了要生存得更人性化,其實便是要去命名(to name)這個世界,去改變這個世界。一旦被命名後,這個世界就會轉以一種「問題的形式」出現於命名者前,並且要求命名者在一次給予新的命名。
[4] 在西方思想中,「radical」是指「從問題根源進行革命實踐」,與當前台灣政治現狀中,某黨使用此詞彙,並且重新詮釋為「基本又進步」無關,特此澄清。
[5] 頁166。
[6] 頁204。
[7] 頁131。原段落。
[8] 我是指,根本不認為與民眾結合是組織運動的根本原則,而只是當作一種手段:一時一地為了增強自己政治主張的正當性,或是取得政治授權,所以才與民眾結合。
[9] 頁196。
[10] 頁197。
[12] 頁54。
[13] 頁127。行動+反省→字詞=勞動=實踐。(只反省卻)犧牲掉行動=咬文嚼字;(只行動卻)犧牲掉反省=盲動。「()」括號與括號內的字,為筆者所加。
[14] 頁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