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安玲|种族的忧郁
本文是郑安玲(Anne A. Cheng)的《种族的忧郁:精神分析、同化与隐秘的哀恸》的第一章。郑安玲,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任性别与性研究项目教师及电影研究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研究项目主任。作为跨学科比较种族研究学者,她专注于政治与美学之间微妙的交汇点,广泛借鉴文学与视觉研究、种族与性别研究、电影与建筑理论、法律研究及精神分析等领域。其研究主要聚焦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与视觉文化,尤其侧重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文学领域。
译文去掉了注释部分,并加粗了部分文体,这是译者所为。侵删。
种族的忧郁:精神分析、同化与隐秘的哀恸
郑安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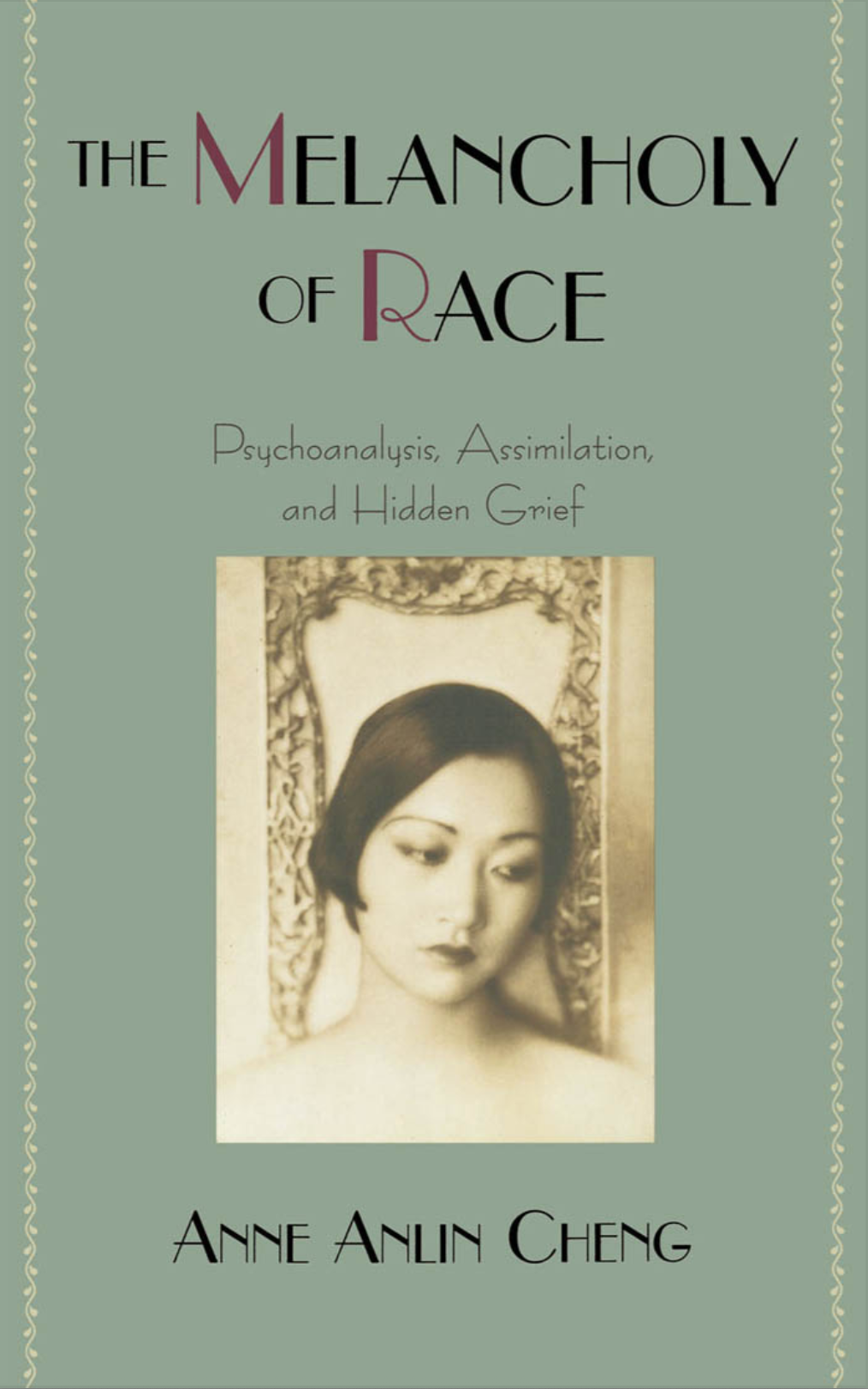
第一章:种族的忧郁
量化哀恸 Quantifying Grief
一个人,如何从承受哀恸的主体(subject of grief),转变为发出怨诉的主体(subject of grievance)?在此过程中,政治与精神层面又会经历怎样的嬗变,得失几何?
从哀恸到怨诉,从默默承受创伤到大声疾呼不公,这一转变总是引发着关于伤害之内涵及其影响的深邃诘问。尽管在这个国度,种族创伤的存在似乎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但恰恰是在种族创伤被最公开地提及之时,其真实性与可感性反而会遭受最严苛的质疑。例如,将种族哀恸转化为社会诉求的斗争,便构成了这个国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戏剧。可以说,美国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莫过于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它一举推翻了法院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的判决——后者曾以“隔离但平等”的虚妄幻象为黑人与白人提供公共设施与机构,从而为“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张目。这是美式种族隔离制度开始瓦解的历史性时刻。为了挑战“普莱西案”并论证“即便物质设施对等,隔离本身即是不平等”,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律师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求助于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玛米·克拉克(Mamie Clark)夫妇,他们的研究聚焦于种族主义对有色人种儿童的有害影响。
心理学证据在世纪之交已被引入法庭,但马歇尔的运用却不啻为一场赌博。正如马歇尔警告克拉克的,他们收集的任何心理学证据都“必须‘证明损害’的存在”。肯尼斯·克拉克召集了一批社会心理学家,共同撰写了一份题为《种族隔离的影响与废除隔离的后果——一份社会科学声明》的文件,作为马歇尔口头辩论的附录。在撰写过程中,他们历经艰辛的修订,被几个难题所困扰,其中最棘手的莫过于“损害”一词的定义、哀恸的量化,以及如何将所谓的科学数据转化为社会意义。果不其然,在法庭上,被上诉方的辩护状宣称,上诉方提供的“事实调查结果”根本不包含任何事实,只是一些“宽泛笼统的结论”,无法证明“实际的个人伤害”或可量化利益的被剥夺。
然而,最高法院的回应出人意料。他们摒弃了宪法历史的唯一权威性(认为围绕第十四修正案的辩论史“尚无定论”,不足以解决当前问题),反而采纳了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证据。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特别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家的“权威”以及那份“社会科学声明”,将其作为推翻“普莱西案”裁决的决定性因素,并赞同马歇尔“隔离本身即是不平等”的论点。法院的判决意见书写道:
我们的判决……不能仅仅基于对这些案件中黑人与白人学校……有形因素的比较。我们必须转而审视种族隔离本身对公共教育的影响……
在公立学校中,仅仅因为种族而将孩子们隔离,即便物质设施和其他“有形”因素可能平等,这是否剥夺了少数族裔儿童平等的教育机会?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仅仅因为种族,就将【少数族裔儿童】与年龄和资质相仿的他人分离开来,这会在他们心中催生一种关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感,其对心灵与思想的创伤,恐怕永难磨灭。
这项裁决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诸多,但其中之一必然是,它扩展了正义的内涵,将种族主义那些“无形”的影响也纳入了考量。因此,最初的“布朗案”裁决可以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判决,它关乎审视种族主义那不可见却根深蒂固的层面之必要性——它允许种族的哀恸发声,即便它无法用物质性怨诉的语言来进行确切的表达。
事实证明,这种接纳态度无论对种族隔离主义者还是自由派人士而言,都产生了深远的法律和哲学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暗藏威胁。自那时起,对有色人种主体“内心与思想”的关注,在岁月中呈现出许多相互矛盾的微妙色彩。在“布朗案”这一关键裁决近十年后,同样的证据在另一起集体诉讼中再次浮现——而这一次,竟是为了南方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辩护。1963年,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一些非裔美国人父母对查塔姆县教育委员会提起诉讼(即“斯特尔诉萨凡纳-查塔姆县教育委员会案”,Stell v. Savannah-Chatham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指控其推行“双种族”教育;也就是说,该县虽然整合了学校里的黑人与白人儿童,但在教室内并未如此。一群白人家长作为支持性介入方加入了被告的辩护,并出人意料地引用了“布朗案”中的社会心理学证据,以此作为支持种族隔离的论据。他们声称,隔离将给予黑人儿童机会,去发展一种更强大、“更健康”、更独立的黑人身份认同。这些“介入方”(即案件中未被点名,但因自身利益相关而提供证据的第三方)还引入了进一步的心理学证据,声称“白人与黑人儿童在学习能力模式上存在重大差异”,因此,隔离教育对黑人与白人儿童都有益。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提出的这一论点,旨在将社会伤害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转化为一种固有的能力缺陷。源于“布朗案”的那个最初具有解放意义的精神创伤概念,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种族主义者手中令人生厌的武器。在这一新语境下,首席大法官沃伦声明中关于种族主义影响的最后一句话(“永难磨灭”),开始回响着别样的余韵。简而言之,我们正目睹着一种滑落的开端:从承认创伤,滑向将创伤“自然化”。
在这段简史中,我们看到了围绕种族创伤之表述的种种紧迫与复杂。时至今日,这场辩论仍在继续。用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的话来说,“布朗案”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股抵抗之源;既是骄傲的象征,也是诋毁的对象”。随着法律、社会学、心理学和倡导运动等领域不断地叙述与重述此案,布朗案的遗产也在持续演变。当代种族研究学者已加入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研究者的行列,挑战克拉克研究方法的科学合法性,并时而尖锐地批判其结论(例如,詹姆斯·阿尔斯布鲁克(James Alsbrook)、H. S. 阿什莫尔(H. S. Ashmore)、利昂·琼斯(Leon Jones)、朱迪丝·波特(Judith Porter)与罗伯特·华盛顿(Robert Washington)、格洛丽亚·鲍威尔-霍普森(Gloria Powell-Hopson)以及奥斯汀·萨拉特(Austen Sarat))。另一些人则强调少数族裔群体在面对歧视时的坚韧(哈丽雅特·麦卡杜(Harriette McAdoo))。例如,七十年代的非裔美国人被鼓励内化“黑即是美”(Black Is Beautiful)的信条,并积极反抗歧视,而非任由自我贬低。尽管这种重拾种族之美的渴望,似乎更多地诉说着创伤的剧痛而非治愈,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如今某些左翼、反同化的倡导者,其立场竟与种族主义的言论诡异地相似:团结的辞令,说的却是孤立的语言。
与此同时,同样有大量的研究重申并扩展了克拉克最初的研究思路及其发现。多年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持续进行着各种版本的克拉克“玩偶实验”,这表明精神创伤的问题依然紧迫。就在1999年8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M. Steele)的研究。他在探究黑人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与其“较差”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时,尽管断言社会经济差异等物质因素并非唯一甚至非主要元凶,却也急于避免重蹈“损害假说”的覆辙。斯蒂尔精炼了心理影响这一概念:他称之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这种威胁萦绕在非裔美国学生心头,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并阻碍着他们的表现。
种族理想持续地驱动着那些被它压迫最深的人。甚至市场研究者也开始投入到这个关于种族偏好的问题中。1995年,《波士顿先驱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玩具巨头美泰公司(Mattel)的文章。文章感叹道,该公司斥资数百万美元进行市场调研和新产品开发,结果却发现了一个肯尼斯·克拉克在近五十年前就能告诉他们的事实:非裔美国(及其他族裔)儿童若有机会,宁愿玩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Barbie),也不愿玩那些“更像自己”的娃娃。在非裔美国人社区,美白霜有着漫长而利润丰厚的历史。(美国最早的黑人百万富翁之一,阿莱利亚·沃克(A'Lelia Walker),继承的便是一笔通过黑人直发剂和美白霜创造的财富。)1996年,著名的“布朗案”因之得名的琳达·布朗(Linda Brown),再次对她父母四十多年前起诉过的同一个托皮卡(Topeka)学区提起了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及那些玩偶所上演的戏剧,在过去四十年间,已在美国的法庭、教室、董事会会议室和家庭中,被反复重演。
我在此的意图,并非要将克拉克的实验奉为圭臬,也非要证明白人优越论的偏好,而是想引导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种族偏好及其反面,一直是一个充满阐释与意识形态角力的议题。此外,我们几乎不知该如何面对种族哀恸留下的精神印记,除了漠视或滥情。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疗愈,以及我们倾向于完全依赖物质或可量化的术语来言说那种创伤。构成美国政治话语绝大部分的怨诉词汇(及其隐含的可比性与补偿逻辑),具有讽刺意味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严肃审视那更难以言喻、无法量化的,由公共与私人哀恸汇成的巨大渊薮。正是这渊薮,塑造了所谓的“少数族裔主体”,并维系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
要将一段充满剧烈差异、社会不公和精神创伤的历史,整合进一个国家,这已被证明是社会进步中最顽固不化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第一课必须是:切勿将对精神层面的关注误解为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将歧视的深层心理影响本质化或全然否认,两者同样令人不安。
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推崇他们永不可及之理想的主导知识型(ruling episteme)中的人们而言,依旧存在着根深蒂固、无以名状的精神困境。这绝不意味着少数族裔主体没有发展出其他与那种规训性理想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自我肯定的或支撑性的——而是说,他们必须,在某个时刻,如果不是持续地,与那种社会理想的要求,与那种总被强调的差异之现实,进行一场痛苦的协商。在“自卑情结”或“白人偏好”这类简单化、威胁性的诊断之下,涌动着一个由种族主义所激发并制度化的、充满矛盾的持续精神协商网络。我们需要用比“让有色人种屈从于不可挽回的‘自我憎恨’”或“否认种族主义深远持久的影响”更复杂的术语,来阐述主体性与社会损害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一种传统的补偿方式,是将被剥夺权利者从承受哀恸的主体,转变为言说怨诉的主体,那么这一转变的利弊何在?对于一个在已经预设其为“赤字”的象征性文化经济中运作的人来说,政治能动性(political agency)意味着什么?当代美国人对进步与疗愈的执着,热切期盼着一个色盲社会的到来,但这恰恰回避了对种族化(racialization)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视:一个种族身份是如何被固化的?它如何持续地对主导者和边缘化者产生诱惑?而那段绵延至今的历史,又会带来怎样的历史与个人层面的反响?
尽管大量的批判能量被用于解构诸如性别与种族之类的范畴,但较少有人关注个体与社群为何依然执着于维持这些范畴,即便这些身份被证明是限制性的或使人衰弱的。进步或治愈的辞令,会产生其自身的盲点。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言:“对过去的否认,表面上是进步和乐观的,但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它体现了一个无法面对未来的社会的绝望。”而当谈及种族问题的未来时,借用福克纳的话说,过去未曾消亡,它甚至未曾过去。与其开出药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该如何“克服”那段历史,不如去追问,对于社会、政治和主观的生命体而言,去哀恸,究竟意味着什么。
忧郁的构成
1917年,弗洛伊德写下《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哀恸类型。据弗洛伊德所言,“哀悼”(mourning)是对失落的健康反应;它有其终点,且接受替代(即,失落的客体可以被放弃并最终被取代)。哀悼是健康的,因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我们确信,假以时日,它终将被克服”。而“忧郁”(melancholia),则是病理性的;它本质上无休无止,且拒绝替代(即,忧郁者无法“走出”失落)。可以说,忧郁者在精神上被困住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瘠空虚;而在忧郁中,则是自我本身。”因此,忧郁指代一种无尽的自我贫瘠状态。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贫瘠同时也是滋养性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将忧郁描述为一种吞噬:
曾几何时,存在着一种客体选择,一种力比多对某个特定的人的依恋;然后,由于来自这个被爱之人的真实怠慢或失望,客体关系被粉碎了。其结果并非力比多从该客体撤回并转移至一个新客体的正常过程,而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自由的力比多】……被撤回到自我之中……以建立自我与被弃客体的一种认同。于是,**客体的阴影投射到了自我之上**……
自我希望将这个客体吸纳(incorporate)进自身,而在这种口欲期或食人期(oral or cannibalistic stage),它实现此目的的方式,便是通过**吞食**它。(MM, 248-25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译注:改为星号标记,下同】
忧郁者吃掉失落的客体——可以说,以之为食。
这种看似异常的消化失落的方式,似乎在精神构成中扮演着一种反向的、首要的角色,因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忧郁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自我之构成”的罕见机会。弗洛伊德式的忧郁,指代一个由失落、否认和内摄(incorporation)构成的链条,自我由此诞生。正如弗洛伊德的其他解读指出的,在他的文章中,并不清楚在忧郁之前是否可能存在一个自我,因为自我只有在“客体的阴影”投射其上之后,才作为一个精神客体、一个可感知的客体而存在。通过吸纳那个变得鬼魅般的他者,忧郁的主体强化了自身,并在贫瘠中变得丰盈。因此,自我的历史,便是其失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忧郁并非仅指失落本身,而是指与失落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或可说,忧郁不仅指代一种哀恸的状态,它更是对哀恸的一种规制(legislation)。
此外,这种“进食”和自我构建的体验也有其弊端。“吞咽”的过程并不顺畅。随着力比多转向自我,最初附着于那个失落与失望之客体上的罪疚、愤怒和惩罚感也随之转向自我(弗洛伊德式的忧郁绝非温和!)。投射在自我之上的“客体的阴影”携带着一种谴责。由于忧郁的主体对其所认同的失落客体体验到怨恨与贬低,忧郁者最终便施加于自身的自我贬低。文章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情感,它持续地围绕着那个被“吞咽”的客体而产生。忧郁者与客体的关系,如今不再仅仅是爱或怀旧,还包含了深刻的怨恨。忧郁者之所以忧郁,并非因为他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内摄了(introjected)那个他如今所憎恶的东西。因此,忧郁者不仅在时间上被困住;他被卡住了——几乎要被他刚刚吞下的那个既爱又恨之物噎住。弗洛伊德写道,忧郁症患者的“抱怨(complaints)实际上是古意中的‘哀诉’(plaint)。他们不以为耻,也不加掩饰,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贬损之词,归根结底都是在说别人”。
尽管弗洛伊德正确地指出哀诉的源头是针对客体,但如果我们遵循他的逻辑,即内在之物如今已是自我,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哀诉已不再能恰当地归属于主体或客体,因为两者如今已内在地(被)混淆了。
在忧郁的图景中,此刻,失落变成了排斥。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未曾言及,但必然是这场精神戏剧之后果的,是忧郁者为了维持这个“失落-但-未失落”的精巧结构而必须施行的多重否认与排斥。首先,忧郁者必须否认失落即是失落,以维持拥有的幻象。其次,忧郁者必须确保那个“客体”永不回归,因为这样的回归必将危及那个食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比任何物质关系所能产生的都更为亲密的占有形式。因此,尽管想象哀恸者可能希望所爱之人归来似乎合情合理,但一旦这个消化过程发生,自我实际上可能不想要,或无法承受这样的归来。正如托马斯·曼曾言:
唤回逝者,或唤回逝者的愿望,终究是个棘手的问题。说到底,坦白承认吧,这种愿望并不存在;它是一种误解,其不可能的程度恰如其事本身,倘若自然让它发生一次,我们便会立刻看到。我们所谓的对逝者的哀悼,或许与其说是悲伤于无法将他们唤回,不如说是悲伤于我们根本就不想这么做。
曼对哀恸困境的描述,实则阐明了忧郁者对客体的矛盾情感。在失落的核心,存在着一种对客体的主动排斥与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斥,而非失落,才是忧郁式保留的真正赌注。的确,弗洛伊德的文本本身,就其对客体的无情排斥而言,也可被认为是相当忧郁的。因为自我并非本文中唯一的幽灵在场。也就是说,忧郁的自我是个被萦绕的自我,既变得鬼魅,又在其鬼魅性中被具身化,但那个“客体”也是鬼魅的——不仅因为其形象已被内摄或吸纳进忧郁者的心灵,也因为弗洛伊德最终对客体发生了什么或其成为主体的潜能并不那么感兴趣。
因此,忧郁的自我由一场幽灵戏剧所形成并巩固,主体借由一个失落他者的鬼魅空虚来维系自身。这场精神戏剧的几个方面,与本研究对美国种族动态的兴趣息息相关。首先,正是这种保留一个被贬低但又具支撑作用的失落之物的奇特而不稳定的动态,与这个国家业已形成的种族想象机制产生了最尖锐的共鸣。虽然对忧郁的心理分析解读多被理论化为与性别构成相关,但忧郁也为阐明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活动与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尤为贴切的范式。美国的种族化,可以说,是通过生产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标准的、白人国家理想的制度化过程来运作的,而这一理想又通过排斥并保留那些被官方化的他者来维系。国家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地形学,通过追溯性地将种族他者设定为永远是他者、永远失落于国家心脏之外,来使自身合法化。法律上的排斥,将对那个不可同化的种族他者的更为复杂的“失落”自然化了。
其次,弗洛伊德关于这种不舒服的吞咽及其对失落如何被处理并固化为排斥的启示,为被视为美国“内部的异乡人”的种族他者之本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洞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种族他者事实上已被相当“同化”进——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最不安地消化进——美国的国族性之中。美国国家理想主义的历史,一直被困于这种吸纳与排斥之间的忧郁纠葛。如果说,自美国立国以来支撑其国家理想的信念之一,是其“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特主张,那么,美国持续的国家屈辱之一,必然是其言行不一的历史。虽然所有国家都有其被压抑的历史和创伤性的暴行,但美国的忧郁尤为尖锐,因为美国恰恰建立在自由与解放的理想之上,而对其的背叛却被一再掩盖。即便国家的经济、物质和哲学进步建立在一系列合法化的排斥(对非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等等)以及由这些被排斥者提供的劳动之上,这段历史也忙于否认那些背弃。在《美国独立的两份宣言》一文中,迈克尔·罗金(Michael Rogin)指出,这一悖论在《独立宣言》的字里行间便已爆发:
《独立宣言》,为一个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新国家要求摆脱英国的奴役而获得自由,正是政治理论中那场错位联姻的核心产物……【《宣言》】为新国家留下了一份双面神(Janus-faced)般的遗产——一方面,是白人天生享有的平等可以扩展至女性和奴隶的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将白人自由建立在黑人奴役之上的基石。
因此,忧郁同时描述了一种美国的意识形态困境及其宪政实践。
罗金在《黑脸,白噪音》(Blackface, White Noise)中进一步断言:“种族排斥,无论是动产奴隶制、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掠夺,还是对华裔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劳工的压迫性使用与排斥,都是美国自由的条件,而非其例外。”正是在那些美国因背叛自身民主意识形态(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奴隶制、种族隔离、移民歧视)而感到最为羞愧和创伤的时刻,它才最猛烈地——也最忧郁地——拥护人类价值与手足情谊。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沉思于《独立宣言》与殖民地奴隶制实践之间的明显差异所带来的不安,最终却通过安抚自己和读者,声称黑人的非人性使他们被排除在人权、自由和平等等考量之外,来获得慰藉。黑人被视为失落于道德与人类关怀之外。通过这种哲学的慰藉(这体现了他与黑人性(blackness)的忧郁关系),杰斐逊将新共和国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重负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使奴隶制与新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调和。正因为美国排斥、帝国主义和殖民的历史,与同样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由与个人主义叙事背道而驰,文化记忆在美国构成了一个持续棘手的问题:国家如何在铭记那些罪行的同时“继续前行”?它如何维系那些以进步和美国身份认同之名所创造的贬损与厌恶的残余?
美国的主导性白人身份认同,以一种忧郁的方式运作——作为一个基于精神与社会层面“消费-并-否认”的精巧认同系统。这个勤勉的忧郁式保留系统以不同面目出现。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自由派的话语都参与了这一动态,尽管动机不同。种族主义者需要发展出精巧的意识形态,以使其行为与官方的美国理想相协调;而白人自由派则需要不断埋葬种族他者,以便纪念他们。那些看不见种族问题的人,或那些自称非意识形态的人,是所有之中最忧郁的,因为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下,正如托妮·莫里森在《在黑暗中弹奏》(Playing in the Dark)中所言:“要做到看不见,是需要下苦功的。”暴力的诋毁和对诋毁的漠视,都表达而非否定了这种忧郁动态。的确,忧郁之所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批判工具,恰恰因为它在理论上解释了种族主义想象中的罪疚与对罪疚的否认,以及羞耻与全能感的交织。
如同忧郁一样,种族主义几乎从不是对他人的一种纯粹排斥。虽然种族主义多被视为一种暴力排斥,但种族主义制度事实上常常不愿完全驱逐种族他者;相反,它们希望将他者维持在现有结构之内。对于诸如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等现象,种族问题是一个位置问题(弗洛伊德式忧郁悬置状态的字面化),而非完全放弃的问题。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是内部充满矛盾的制度,并非因为它们消除了他者,而是因为它们需要那个它们所憎恨或恐惧之物。(这就是为什么创伤,这个常与种族贬损讨论相关的概念,在关注受害者一方的危机结构时,忽略了施害者在贬损过程中自身的动态过程。忧郁则更强有力地触及了那种以暴力和无声方式表达自身的构成性失落之概念,它既产生确认也产生危机,既产生知识也产生困境。)
美国的价值观,往往是通过(而非不顾)由奴隶制和其他歧视制度所激发的投资与焦虑的交汇点,才获得其最鲜明的轮廓。正如埃里克·洛特(Eric Lott)和迈克尔·罗金在其关于黑脸滑稽剧(blackface minstrelsy)的著作中出色展示的那样,主导文化与种族他者的关系,展现了一个由排斥与同情、恐惧与欲望、拒绝与认同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正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中观察到的,“欧洲定居者的意识,与他们所奴役的非洲人、所屠杀的‘印第安人’、所契约的亚洲人的意识,即便在最极端的暴行情境下,也并非密不透风地相互隔绝。”正是这种被牵连但又被否认的关系,构成了白人种族忧郁的基础。
种族忧郁不仅在国家构成中上演,也在其一种表现形式——经典文学的构成中上演。托妮·莫里森通过指出非裔美国人的在场是美国文学核心中那个被塑造但又被否认的幽灵,实质上已将国家文学经典认定为一个忧郁的语料库(corpus)。在《在黑暗中弹奏》中,莫里森呼吁“对美国经典,即那些奠基性的十九世纪作品,进行一番审视与重释,寻找那些‘不可言说的未言之事’;寻找非裔美国人的在场如何塑造了如此多美国文学的选择、语言、结构与意义”。经典之所以是一个忧郁的语料库,是因为它所排斥却无法忘却之物——莫里森称之为“机器中的幽灵”。其他批评家也观察到,那些体现边缘处境的社会范畴,事实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塑造“主流”的核心,因为它们起到了定义和限定那个被承认的“中心”的作用。吉尔罗伊提出,“现代世界中黑人的文化史,对‘西方曾经是什么以及今天是什么’的观念具有重大影响”。而在谈论黑白关系的心理动态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写道,“黑人根植于一个必须将他从中解脱出来的宇宙核心”。
美国文学与国族性还包含着其他被悬置的、被种族化的“幽灵”。罗金指出,从D.H.劳伦斯(D. H. Lawrence)到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的批评家们都主张,“美国文学……是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斗争中确立其国家身份的”。朱莉娅·斯特恩(Julia Stern)在其对联邦主义时期早期美国小说的研究中提出,美利坚共和国的奠基本身就体现了与“他者”种族身体的复杂关系,她指出,早期美国小说记录了国父们愿景的巨大代价:
此类文学表明,共和国的基石实际上是一个墓穴,国家的非公民——女性、穷人、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及外来者——在社会意义上已死,且未被妥善埋葬,他们是后革命时期政治封锁的牺牲品。
斯特恩充分领会了莫里森幽灵寓言的全部含义,清晰地阐述了失落、哀恸与埋葬的结构,而美国梦的起源正是建立于此之上:
这些无形的美国人,被过早地埋葬在他们实际上促成了其建立的宏伟国家大厦之下,为共和特权的构建提供了一个不安的平台,以强有力的方式扰动着联邦主义的巨石。
斯特恩将种族化置于美国建国的死寂中心,论证种族构成了美国国族性一个独特的排斥点。
启蒙理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只是民主理想中至今仍困扰我们的根本性张力的一种积极表现。在追溯另一条美国边疆时,刘大卫(David Palumbo-Liu)在其《亚裔/美国人:一条种族边疆的历史跨越》(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中论证,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美国的公民身份是通过对亚洲移民的同时排斥与不可见的种族化来合法、经济和文化地定义的。种族,在美国民主的演进中,一直且继续构成一个未解的议题。
但是,认识到主导权力之下潜藏的这种忧郁困境,对那些被埋葬、然后仅作为有用的幽灵被复活的人们有何帮助?揭示权威的内部矛盾与亏欠是一回事;想象这种批判能解决那些据说已被埋葬之人的苦难,则是另一回事。的确,忧郁的悬置,而非埋葬,或许是对这个消费与否认系统中种族他者地位更富有成效、也可能更准确的描述。让我们来问一个弗洛伊德没有问的问题:忧郁的客体,其主体性是什么?它是否也忧郁?当我们复活它时,我们会发现什么?换言之,对美国种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忧郁起源的洞见,对研究被种族化的主体有何启示?
忧郁的回应
谈论被种族化人群的“忧郁”似乎极为困难,特别是因为这似乎会重新铭刻一整段苦难史,或冒着将那种痛苦自然化的风险。在《超越族裔》(Beyond Ethnicity)中,沃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谈到“印第安忧郁”,指的并非美洲原住民如何处理其种族灭绝史,而是主导的美国文化如何浪漫化并自然化“对正在消逝的印第安人的崇拜”。“忧郁的印第安人及其命运”的辞令,服务于为白人征服者的未来正名。在非裔美国人传统中,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注意到,非裔美国人社群体现了一种“苦涩的传统……如此复杂……以至于呈现出一种如此紧密、有机的形式,以至于大多数白人审视它时会认为,大多数黑人的血肉骨骼中都嵌有一种抱怨哀叹的特殊倾向”。因此,谈论种族哀恸也冒着重蹈覆辙的风险,即重复一种历史上由权威施行的遏制工具。担忧当然在于,这种对创伤的关注可能被自然化并被用来对付原告,正如“斯特尔诉萨凡纳-查塔姆教育委员会案”那样。从创伤到同情,再到轻蔑,其间的路径可能短得惊人。简而言之,言说种族主义的伤害有多大,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伤害。
然而,不谈论这段悲伤史,无疑也同样有害。一个被塑造成“客体”、“失落”、“不可见”或“幻影”的社会主体,其本体论和精神状态从未被充分探索过,因为这样一项研究的意涵,一方面对一个种族主义文化而言不便,另一方面对倡导事业——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倡导事业——具有潜在威胁。从精神创伤到固有残疾的迅速跳跃(如“斯特尔案”所示),提供了一个围绕精神反应与社会影响之间关系认知的粗疏思维范例。历史上,心理学在种族分析中的运用,饱受一系列混淆之苦:(1)将心理分析与开具药方混为一谈的倾向;(2)假设“损害”(以内化了有害的主导理想的形式)等同于没有能动性,或者反过来说,假设拥有能动性或“强大的自我”就能使人免受此类侵袭;(3)对权威的忧郁依恋的忽视;以及最后,(4)未能探讨心理脆弱性的心理动态及其与认同和主体构成的内在关系——这些构成既不稳定又具历史性,既多面又具强制性。
我们需要做的,是严肃地重新思考“能动性”一词与各种形式的种族哀恸之间的关系,将该词的内涵扩展至纯粹主权主体之外的其他表现形式、形态、音调和治理层次。在面对歧视时,我们需要将主观能动性理解为一种与痛苦进行的、错综复杂、持续不断、富有生成性且时而自相矛盾的协商。将精神创伤问题简化为对黑人自我憎恨的简单化、指令性宣告,是错失了克拉克及其后继者们的研究揭示的一个根本性洞见:那些玩偶实验中的孩子们所戏剧化展现的心理,揭示的是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原因。至少,克拉克毕生的工作表明,社会关系活在精神动态的核心,而这些动态的复杂性,诉说着一系列复杂、冲突、环环相扣的情感:欲望与怀疑,肯定与排斥,投射与认同,驾驭与失调。这场实际上已持续五十多年且毫无平息迹象的辩论,其实是一场关于如何为精神过程赋予社会意义的辩论。而限制这场辩论的,是倡导运动与更复杂的文化欲望及不安迹象之间顽固的对立。
文学,是这样一个场所,在此,这类复杂的迹象得以发挥作用,这类复杂性得以被理论化。我在此的目的,并非要在文学作品中定位有色人种自我憎恨的“真相”,或在文学文本中诊断种族创伤的症状。相反,我的意图是辨识这些文化文本(它们虽不受某些直接的政治-法律规程约束,却仍与那些要求对话)如何梳理出种族哀恸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病源学。在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中——这部关于黑人不可见性的论述可被视为莫里森“机器中的幽灵”的先驱——埃里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种族遭遇的谜样画面。在开篇,叙述者告诉我们他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人们拒绝看见【他】”之后,他遭遇了一场暴力冲突:
一天晚上,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他用他那双蓝眼睛轻蔑地看着我,咒骂我……我大喊:“道歉!道歉!”但他继续咒骂和挣扎,我一次又一次地用头撞他,直到他重重倒下……我猛踢他……这时我突然想到,那个人实际上并没有看见我;就他所知,他正走在一场行走的噩梦之中……一个差点被一个幻影杀死的人。
我称此场景为谜,因为这段描述开启了一系列关于感知与投射、行动与反应之间差异的问题。首先,从叙述者的视角,我们看到白人的“轻蔑”是因不得不面对他大概不想看见之物而生的愤怒。白人在被撞后发出的咒骂,表达了一种主动的愿望,即否认那个此刻要求与之竞争的在场的不可见之物。叙述者认为,困扰那个白人的是“碰撞”——那个与不可见之物的接触点——而正是这种不可见性,在历史上确保了白人看见与看不见的能力。那个白人在小巷里既看见又看不见那个黑人。在描述《最蓝的眼睛》中一位白人店主难以看见近在眼前、试图向他购买糖果的黑人小女孩时,托妮·莫里森描绘了一个类似的“看见/不看见”的时刻。她将那个男人描述为被“一种永久的失落感所麻木”。通过这个巧妙的措辞,莫里森定位了白人种族忧郁中“失落”的精确而奇特的本质:在已知与未知、看见与刻意看不见之间摇摆,种族他者构成了一种被有意识地变得无意识的“忽视”——随着时间被自然化为“缺席”,作为一种互补的负空间。正是失落与排斥之间那段滑溜的距离,造成了种族的短视。主导性种族忧郁的核心困境之一便是——既然其权威是由这个被悬置的他者系统所构成、维持并变得富有生产力的——它其实并不希望那个失落的他者回归(或要求其应有的权利)。
与此同时,当我们更深入地进入埃里森的场景时,我们必须追问:在这个情境中,只有白人因看不见而受苦吗?文本是含糊的。谁是那个看不见的人?如果叙述者撞上了白人,难道不是白人对黑人而言是不可见的吗?叙述者撞上了他没看见的东西,然后指责对方眼盲。如果我们不从表面价值看待叙述者的叙述,可以想见,白人咒骂黑人是因为他的笨拙而非种族主义原因(可能是在场的男性气概而非种族冲突),而叙述者对“轻蔑”的解读,本身可能是一种忧郁的回应,源于“蓝眼睛”这个(历史上)煽动性的符号,以及他自身的自我贬低和受伤的自尊。不可见性很少是单行道,这是其最阴险的效应之一。在这场冲突中,存在着潜在的相互不可见和相互投射。的确,种族性时刻(racial moment)便在二人相互投射的动态僵持中诞生了。叙述者以一种既充满男子气概又歇斯底里的反应,表明他被困住了,并非因为被视为不可见,而是因为怀疑自己如此。这就是被种族化主体的种族忧郁:规训与排斥的内化——以及一个被写定的感知语境的植入。看不见的人的种族雷达,既是他的洞察力,也是他的偏执狂,是有其道理的。因为看不见的人既是忧郁的客体,也是忧郁的主体,既是被失落者,也是失落者。
这种内化,远非表示一种屈服状态,它体现了一个协商之网,既表达了能动性也表达了卑贱。在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场(女性的)与蓝眼睛符号的对峙,以及一种相似的自我贬低与自尊的回应。莫里森的儿童叙述者描述了她每年圣诞节如何收到一个“充满爱意的礼物”——一个“大大的、蓝眼睛的娃娃”:
我只有一个愿望:肢解它……但肢解娃娃并非真正的恐怖。真正恐怖的,是这种冲动转移到了白人小女孩身上……是什么让人们看着她们,说“哇……”,却不对我说?是黑人妇女在街上走近她们时的眼神游移,是她们触摸她们时那种占有式的温柔。
如果我捏她们,她们的眼睛——不像娃娃眼睛里疯狂的闪光——会因痛苦而闭合,她们的哭声也不会是冰箱的声音,而是一种迷人的痛苦哭喊。当我了解到这种无所谓的暴力是多么令人厌恶时……我的羞耻感四处寻找庇护所。最好的藏身之处是爱。于是,从纯粹的施虐欲到捏造的仇恨,再到虚假的爱,发生了转变。离雪莉·邓波儿(Shirley Temple)只有一小步。很久以后,我学会了崇拜她。
对于一个初次面对种族歧视的孩子来说,情感的形成与辨别(如何区分爱与恨)变得如此纠缠扭曲,以至于爱与恨都成了“捏造的”和“虚假的”。我们正目睹着在种族歧视面前,情感辨别能力的丧失。种族少数化的社会教训,通过对一个永不可能实现的完美的想象性失落而自我强化,而小女孩必须将这种失落认同为对她自身的排斥。
然而,孩子一方对这一教训的内在过程,也体现了一种批判。因为在“自卑情结”这一通俗心理学洞见之下,潜藏着一个由相互交织的情感与力比多动态构成的网络——一个由自我肯定、自我贬低、投射、欲望、认同和敌意交织而成的网。声称被种族化主体的种族差异激起了导致补偿性白人偏好的自我羞耻,是极大地缩短了走向种族化/社会化的复杂过程。歧视的教育学,是在多个阶段被痛苦地植入的。白人偏好并非一个简单地从社会传给黑人妇女再传给黑人女孩的现象;相反,它走过一条疏离、抵抗、攻击,然后最终将那份攻击驯化为“爱”的曲折忧郁之路。在此,文化教训与种族教训相吻合:也就是说,将身为黑人的哀恸转化为对白人身份的享受,这难道不正是将个人不快掌控为社会愉悦的一种非常文化性的教训吗?
尽管文化适应与种族化之间存在共谋,《最蓝的眼睛》追踪而非自然化了白人偏好的病源学。莫里森向我们展示,羞耻并非来自孩子自身的黑人性本身(她黑人身份被赋予的贬低价值让孩子愤怒,这本应如此,事实上揭示了相当强的自我拥有感),而是来自这样一种社会信息:这种愤怒和哀恸无处安放,必须躲藏起来。小女孩不仅必须内化白人理想,还必须内化作为对白人理想之向往的黑人女性理想。也就是说,难以吞咽的不仅是作为注意力竞争对手的雪莉·邓波儿,而恰恰是黑人母亲们的“眼神游移”。
这种对理想的深刻内化,在其历史与实践中,出人意料地既指向了抵抗的色彩,也指向了默许:“离雪莉·邓波儿只有一小步。很久以后我才学会崇拜她,正如我学会了喜爱洁净,并在学习中知道,这种改变是适应,而非改进。”这最后的断言,是在陈述自我持续无法完全承担那个白人理想吗?是在提醒我们,那种“虚假”实际上制约着这种崇拜吗?是在承认这种“偏好”所产生的自我伤害吗?还是甚至更宏大地暗指非裔美国人社会进步的理念本身?答案必然是以上所有,或者至少,这句话的含糊性告诉我们,对于歧视的客体而言,要理清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几年后,当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写下那部被广泛承认为亚裔美国女权主义杰出文本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时,她上演了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亚裔美国女孩叙述者站在学校洗手间里,实践着莫里森笔下叙述者克劳迪娅所幻想之事:捏、扯头发,以及用其他方式虐待另一个女孩——只是这一次,对方不是一个白人女孩,而是某个长得像她自己的人。克劳迪娅最初对“白人小女孩”感到的暴力,在《最蓝的眼睛》中被转向内在,而在汤婷婷的遭遇中,则达到了一种狂热的重演,愤怒的对象是自身的幻象性相似物。汤婷婷笔下这幕在学校洗手间里主体间与主体内冲突坍塌的场景(我将在第三章更充分地探讨),无疑正在与“布朗案”的遗产、莫里森的文本,以及由种族主义教育学所植入的自我贬低的历史性问题进行对话。的确,莫里森和汤婷婷的文本都提醒我们,肯尼斯·克拉克五十多年前在那些尘土飞扬的教室里进行的实验,并非给了我们关于黑人儿童心理本身的信息;相反,它给了我们一场关于黑人儿童之教育的戏剧化呈现。莫里森和汤婷婷强调了这样一个洞见:种族主义的教育是一种欲望的教育,一种将精神与社会密不可分地捆绑在一起的教育学。政治统治在个人经验的层面上被复制。
汤婷婷对洗手间(作为性别区分的经典场所)的选择,进一步戏剧化了在“布朗案”玩偶实验中未曾言明,而在莫里森文本中隐含的东西:在紧迫但排他的种族理想面前,性别价值的配置。虽然性别并非最初克拉克实验的分析元素,但成年人自己对玩偶的反应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性别不适。对该实验的描述,无论是与案件同时代还是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以关于玩偶的笑话形式提及性别。(的确,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在其权威著作《简单的正义》(A Simple Justice)中,反复指出诉讼双方的成年男性律师在处理玩偶时都感到不自在。克鲁格甚至提供了一个幽默的小插曲,描述克拉克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的初次会面,他们发现一个成年男人提着一箱子玩偶“很怪异”,令人不安。当他们得到口头保证,说这些玩偶是“为了公事”而非“为了取乐”时,他们才明显松了一口气,放下了心。这些男人愿意解读种族的符号,却不愿解读孩子们所承受的性别符号。)但在莫里森和汤婷婷的演绎中,阅读种族是阅读女性气质的前提。也就是说,克劳迪娅和汤婷婷的女孩叙述者都展示了女性气质(作为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如何在种族差异的符号下获得其社会与美学价值。正如伊丽莎白·亚伯(Elizabeth Abel)在其文章《洗手间门与饮水机》中揭示的,支撑吉姆·克劳法的视觉想象,围绕着洗手间和饮水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命题:“种族(在此案例中是黑与白)而非性别,才是奠定象征秩序的二元对立。”这一洞见不仅扰乱了通常心理分析中性别认同优先于种族认同的排序,也提醒我们,美国的种族象征秩序实际上并非二元的,而是多元的。
我们持续见证着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文学中关于精神、种族和性别创伤的沉思之间的联系(甚至是对话)。亚裔美国批评界对汤婷婷据称对社群(尤其是亚裔美国男性气概)的破坏性描写的焦虑,与非裔美国人对肯尼斯·克拉克发现的不安并无二致。即便我们认识到,谈论被种族化的少数族裔如何像主导主体一样受缚于种族忧郁是何等令人不安,我们也必须看到,开始审视种族创伤的历史、文化和跨种族后果,并将这些影响定位为个体、国家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关键构成元素,是何等紧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进而分析,被种族化的人们作为复杂的精神生命体,如何处理被强加于他们的客体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如何协商社会性和国族性。在“内化”这个简单化的概念之下,潜藏着一个关系世界,它既关乎在哀恸中幸存,也关乎体现哀恸。
鬼魅形态学
当我们转向边缘化、被种族化的人们那漫长的哀恸史,以及同样漫长的在身体与情感上驾驭那份哀恸的历史时,我们看到,作为情感的通俗意义上的忧郁,即“悲伤”或“蓝调”(the "blues"),与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认同性的构成之意义上的忧郁症(melancholia)之间,始终存在着互动,后者的基础是——同时也是对之进行主动协商的——作为合法性的自我的丧失。的确,我所定义的种族忧郁,对被种族化的主体而言,一直以来既是排斥的标志,也是应对那种排斥的一种精神策略。
黑人文化形式一直接纳甚至培育了与死亡和苦难在场的一种动态共鸣。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曾写到“悲伤之歌”(sorrow songs)——奴隶们所唱的民歌,它们不仅是悲伤的表达,更是一种在一个充满巨大悲伤的世界里,与意义和自由进行的深刻精神搏斗:“它们诉说着死亡、苦难和对一个更真实世界的无声渴望,诉说着迷雾中的漫游与隐秘的路径……它们摸索着走向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并为最终的安息而叹息。”在《黑色大西洋》中,保罗·吉尔罗伊指出,对于无权者而言,将死亡与自由联系起来,并非仅仅是一种病态心理。相反,他论证道,奴隶与死亡的亲密关系,不仅标志着对可能威胁的反应,也标志着一种选择。吉尔罗伊援引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著作,提出“奴隶主动地选择死亡的可能性,而非继续忍受种植园奴隶制所依赖的那种非人状况”。吉尔罗伊并不认为这种转向死亡是放弃或空洞的胜利;他将其视为在一种毫无意志可言的情境下,一种主动的意志行为。既然奴隶制依赖于奴隶的存活,那么在此语境下,自杀的威胁便昭示着一种非法的反叛与自我主张。因此,这种转向死亡的举动“指明了将奴隶意识视为一种延长的哀悼行为的价值”。在《服从的场景》(Scenes of Subjection)中,赛迪娅·哈特曼(Saidiya Hartman)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悲伤之歌中错综复杂的情感与精神:
【沉】溺于歌唱既不反映对奴隶制的拥抱,也不反映情感的统一,而是……对奴隶制极端且矛盾状况的一种含蓄表达……我的任务是……充分重视这些由劳作、恐怖和悲伤所铸就的文本的不透明性……【去强调】这种不透明性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搅乱了欢乐与悲伤、劳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别。
哈特曼论证道,由于奴隶制的残酷,“欢乐与悲伤、劳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提供富有成效的分析尺度。言下之意,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生存与哀恸的驾驭,超出了我们对能动性——即掌控自我与周遭环境之意——的通俗理解。
在探究被种族化的少数族裔对主导性种族忧郁的忧郁式回应时,本研究同意吉尔罗伊和哈特曼的洞见,即对主导压迫的内化,可能并不标志着纯粹的顺从或失败,而是指向了思考对于被剥夺了能动性的人而言,能动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新方式。正如吉尔罗伊和哈特曼所展示的,悲伤之歌混淆了情感的简单归类(如悲伤或顺从);它们实际上完全混淆了单一的意义。同样,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展示了种族主义教育的后果之一,是情感辨别能力的丧失。在难以想象的、持续的种族哀恸语境下,我们必须开始承认其中所涉及的复杂精神协商网络,并相应地发展出一套政治词汇。
今天,我们需要面对那个历史性的否定原则的遗产——不仅在非裔美国人社群内部,也关乎其他被边缘化、被种族化的人群。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化是两个独特但相关的过程。本研究聚焦于后者(指非裔美国人),因为如此多的历史与当代种族话语都以该范畴为模型,也因为非裔美国人研究构成了种族研究领域最成熟的学科。作为美国最持久、最显见的种族范畴,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构成与文化表现,为我们追踪美国种族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我同样也专注于亚裔美国人的构成,或许是出于我自己的“部落”归属感,也因为我想理解一些关于我自己与这个范畴的关系。但也有其他原因。作为美国移民政策中被针对的、被种族化的群体,却又是在种族辩论中最不“有色”的群体,亚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美国国族性在此投注了其大量的矛盾、欲望与焦虑。虽然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尤其但不限于在加州)承载着巨大的贬损与虐待,但那段历史在美国意识中的地位,远不如非裔美国人的苦难那般显赫。这与几个事实有关:与非裔美国人相比,亚裔美国人缺乏政治体量;针对亚洲移民和亚洲劳工的种族主义有其特定历史(即,与白人劳工阶级存在不同的经济竞争史);移民与奴隶对美国国族性的关系不同;以及“亚洲人”在美国种族观念中的奇特地位——这种观念主要被理解为黑与白。针对亚洲人与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被十九世纪欧洲继承的东方主义及其宣传所深度过滤,也被主导美国种族话语的黑白二元对立所遮蔽。在他们极为流行的论著《黑与白的美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1997)中,斯蒂芬·瑟恩斯特罗姆(Stephen Thernstrom)和阿比盖尔·瑟恩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夫妇,就明确地将亚裔美国人排除在美国的被种族化群体之外。他们引用了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话——后者在二战前夕曾将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比作“不可同化的种姓”——然后声称缪尔达尔的论断已不再成立,因为亚裔美国人近几十年来已取得了惊人的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作者写道:“很难找到有谁真正在意【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是什么。”人们不禁要问,瑟恩斯特罗姆夫妇是否考虑过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移民和法律史中的种族化过程,或者他们是否关注过每日新闻。此外,因亚裔美国人所谓的经济与社会成功而否认针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是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经济竞争常常为种族主义背后的能量火上浇油,并加剧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
在“黑”与“白”作为主导种族范畴的情况下,历史记忆倾向于忽略那些中间地带的激烈争夺——这些冲突不仅涉及意识形态差异,还涉及经济和社会特权。的确,政府排外的至高权力的形成,在历史上与外来者和公民的定义紧密相连。远在“布朗案”之前,除著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外,还有一系列关于学校隔离的关键裁决,涉及在这个国家将亚洲人种族化的问题。1929年,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华裔移民后代,尽管一度与黑人社交甚至通婚,却在“吉姆·克劳”学校系统中应将华人置于何处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抗议,最终导致了“龚伦诉赖斯案”(Gong Lum v. Rice)。(在该案中,华裔上诉人声称,既然他们显然不是黑人,就应被视为更接近白人。)在“布朗案”的诉讼期间,以日裔拘留营形式出现的“种族化即隔离”的合宪性(见“是松诉合众国案”,Korematsu v. U.S.),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再次合法化。(在阿瑟·董(Arthur Dong)关于四五十年代巡演的亚裔美国表演者的纪录片中,有亚裔表演者痛陈心迹,说他们长途跋涉后找不到洗手间,因为提供的选项只有“黑人”和“白人”。)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中显得更为明显的忧郁,因为针对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恶毒种族主义史,被持续地坚持着,又被持续地否认着。在“黑”与“白”之间穿梭——这是所有美国移民都必须“通过”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Scylla and Charybdis)——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种族化的故事中,占据了一个真正鬼魅般的位置。
二十世纪初现代美国的形成,与“东方”的幻象有着深刻而特殊的联系。在其开创性著作《移民法案》(Immigrant Acts)中,丽莎·洛(Lisa Lowe)提出,无论在美国之内还是之外,“亚洲”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场域,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多种焦虑都在此被塑造。
从历史上和物质上说,中国、日本、韩国、亚裔印度和菲律宾移民在美国的建设与维系中扮演了绝对关键的角色;在特定时期,这些移民对于将国家建构为一个包容性的拟像至关重要。然而,将国家想象为同质的这一工程,需要一种东方主义的建构,即把亚洲移民来源的文化和地理建构为与那个‘发现’、‘欢迎’并‘驯化’他们的现代美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根本上‘异域’的源头。
因此,对亚裔美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种族化的分析,对于理解美国的国家建构工程至关重要。在这个国家被黑人民权斗争所攫住的背景之下——有时甚至是作为其陪衬——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种族想象中占据了一个奇特的位置,既体现了欣喜,也体现了憎恶。我想到的是,例如,“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这个形象不仅被同化,还欣喜若狂地歌颂美国方式。(我将在第二章讨论罗杰斯与汉默斯坦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中一个尤为铺张的版本)。亚洲移民本身远非同质的历史,常常被用来在亚洲移民一方,折射出一种对美国梦的狂躁关系。美国这种亚裔的狂喜之情,反过来又服务于遏制亚裔卑贱的历史,并规训美国其他的被种族化群体。因此,从非裔美国人到亚裔美国人,悲伤与欢乐的叙事同样编码了与流散史和对未言说之失落的记忆相关的渴望与哀悼。
对被种族化主体所体验的忧郁的理解,必须超越对悲伤的肤浅或纯粹情感性的描述,而深入到一种深层的感知:那种悲伤——作为一种流动的绝望或狂躁的欣快——如何制约着被剥夺权利者的生活,并确实地构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塑造了他们的主体性。从罗杰斯与汉默斯坦的戏剧到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戏剧,从汤婷婷的小说到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从白南准的妻子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实验作品到安娜·迪弗里·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的实验作品,本研究的其余部分将在此基础上,探索种族忧郁在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主体身上的表现形式与变迁。
当我们开始如莫里森所提议的那样,发掘美国文学心脏中那具被埋葬的尸体时,我们看到,被揭示的“在场”之本质,覆盖着政治、智识、心理和伦理的多重意涵。墓穴揭示的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在被玷污之前的完整主体,而是鬼魅形态学本身。本研究将证明,理解这种形态学,将改变我们对一系列术语,如公民身份、同化、幻想、创伤和表演等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种族与精神分析
将种族身份认同视为一种忧郁的构成,就是要理解该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及其对它同时也在声称的“非认同”(dis-identity)的亏欠。如果说种族和族裔研究源于民权运动,并至今仍与政治行动主义保持着联系,那么质疑身份认同的基础,就可能被视为一种奢侈,或者更糟,一种不负责任。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中所论证的,维持一系列将认同与非认同、创伤与力量、政治与美学隔绝开来的二元对立观,是有害地限制了我们对种族哀恸的理解,即将其理解为社会性与精神动态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塑造此互动)。下一代种族学者必须面对少数族裔话语核心处的根本悖论:一旦我们承认(我们也必须承认),“身份认同”正是进步与歧视得以发生的共同基础,我们该如何前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族裔研究的未来,可能会呈现出一种与其最初构想截然不同的形式。新的探究路线甚至可能显得与(即便它们受惠于)创立族裔研究的政治行动主义相对立。政治化的学术与具有政治性的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困扰着更为成熟的非裔美国人研究学科。1987年,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就在《批判性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辩论“高深”的批判理论是否有能力处理被种族化的主体和文学产品。十多年后,类似的辩论再次出现——这次是在《纽约时报》艺术与休闲版的头版,辩论双方是亨利·路易斯·盖茨和曼宁·马拉布尔(Manning Marable)。
我总是为“理论”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分野而感到困扰。一方面,我理解理论化常被视为一种放纵,因为其实践可能产生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这似乎与政治必要性的要求背道而驰。对于精神分析的探究模式而言尤其如此;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开篇所写:“你无法唤起主观维度并将其固定在位。”(这也是为何王云裳(Sau-ling Cynthia Wong)对亚裔美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奢侈”与“必需”双重冲动的刻画,如此有力地概括了任何族裔-种族艺术作品核心处,政治紧迫性与私人想象之间的根本性双重束缚。)因此,我最终将我的研究视为一个智识项目,而非一本政治手册。另一方面,我深信,审视并解锁种族动态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在制度化和精神过程中实现——的工作,最终必须为长期的政治重构指明方向。因为害怕种族的主观维度难以驾驭而对其视而不见,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建议,恰恰是在政治调解最难以驾驭的时刻,我们才开始理解种族归属与拒绝的影响。正是当我们逼近政治不适最剧烈的点时,我们才看到采取一种政治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研究不声称对“种族问题”有任何解决方案;相反,它探究的是“解决方案”这一概念本身背后的假设。我们尚不知道,让政治去容纳一个基于构成性失落的身份认同概念,或者让政治去探索那些将我们锁链于爱与恨的压迫性、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制约着“主导者”与“被剥权者”的相互纠缠——的精神与社会锚点,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拒绝思考种族动态的这些方面,也并未带来成效,持续上演的种族拒绝与报复的国家戏剧便是明证。
在许多关于种族关系与再现的批判性分析中,所缺失的,是一种直面那种萦绕不去的否定性之精神意涵的意愿,这种否定性不仅附着于,而且帮助构成了“被种族化”这一范畴本身。事实是,种族研究仍然更安逸地求助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而非文学或哲学。这种不适感,完全源于一种执着的依恋,即认为我们必须将种族主体作为“真实”主体来谈论。这种倾向不难理解,因为非人化长期以来一直是歧视的工具。然而,问题在于,在试图补偿那段历史时,我们常常牺牲掉对所有构成“现实”的那些非物质的、紧迫的、无法量化的元素的讨论,最终得到一个关于何为“物质”历史的极为狭隘的定义。同样,这种依恋在方法论层面上被复制,即“物质分析”优先于其他据称更短暂或更寂静主义的分析工具,并取得了合法性。本研究主张,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概念化种族研究的主体与客体,还需要重新概念化其方法论。
在试图使身份认同概念变得更加精微时,一些批评家转向了多元性与杂交性的话语。虽然这两个概念都有助于使主观完整性的假设复杂化,但它们的援引也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命名,身份认同由此变得多元和序列化,却未触及认同(identification)的根本过程。丽莎·洛的重要文章《异质性、杂交性、多元性:亚裔美国人的差异》强调了将异质性与杂交性设定为抵御种族与学科范畴构成中本质主义的保障的紧迫性与局限性。洛呼应了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策略性本质主义”概念,写道:
我主张亚裔美国人有其必要性——政治上、智识上和个人上——作为亚裔美国人去组织、抵抗和理论化,但同时我将这种必要性置于一场关于风险的讨论之中,即一种依赖于建构同一性并排斥差异性的文化政治的风险。(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但这种平衡之举究竟如何运作?这个想法,在政治层面上清晰明了,但在主观层面上则不然。它无法处理认同作为一个精神过程的复杂性。简而言之,在策略性问题之外,还有精神问题:支持这种双重意识的条件和代价是什么?
我禁不住想,是否在杂交性与本质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幻的对立,仿佛前者能治愈后者;仿佛阶级、性别和国籍的差异能消除本质主义立场,而显然那些不同的立场本身各自都在实施其自身的归属品牌,各自都在要求“一个”身份认同。当我们转向洛对汤婷婷小说《女勇士》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了有待探索的问题:
亚裔美国文化的形成,可能是一个远比从一代到另一代的未经中介的垂直传播“更混乱”的过程,它包含部分继承、部分修改,**以及部分发明的实践**……
【汤婷婷】问道:“华裔美国人,当你们试图理解你们身上哪些东西是‘中国’的,你们如何将那些童年特有的、贫穷特有的、疯狂特有的、某个家庭特有的……与‘中国’的东西分离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又是电影?”(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洛提醒我们,“唐人街”和“华裔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人口、语言和族群”的象征。然而,我想将注意力集中在洛称之为“部分发明”的那部分亚裔美国文化上。要触及那“部分发明”之物,似乎需要一套不同于协商策略性自我定位或虚假同质化的探究,而与围绕自我认同的问题、对此类虚构的渴望,以及对一种并非总能获得的谱系之不在场证明的向往,有更多关系。
在洛所引述的汤婷婷段落中,叙述者触及了私人与公共欲望的纠缠,并进而触及了个人与公共自我再现的纠缠。在“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又是电影?”这句话中,汤婷婷恰恰质疑了在主体性作为一个离散领域已被根本性地损害时,维持一种清晰、界限分明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我们被深刻地提醒,对“差异的构成”(即“阶级、性别、国籍多样性”)的解构(即“拆解”),虽然至关重要,但仍不足以理解认同过程本身是如何总在生成差异与同一性的。心灵有其自身的异质性系统,我们应当追问:在何种本体论条件下,“认同”才得以发生?在学术界,我们常常害怕谈论本体论,因为害怕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或智识上的寂静主义。然而,有时对本质主义或本质主义标签的严苛恐惧,反而阻碍了对某些范畴的讨论,而这些范畴,尽管其内在不稳定,却以强有力的、幻象般的方式运作着。
一个调解社会性与本体论关系的关键术语,必然是幻想(fantasy),正是那“部分被发明”之物的根本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汤婷婷笔下叙述者的困境,解读为一个关于我们方法论的元问题:我们如何将本体的(ontic)和家庭的“自我”(这是从精神分析继承来的一个假设与关注点)与由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发明的各种主体位置分离开来?事实上,恰恰是这种无法分辨的能力告诉我们,社会的与精神的投注(cathexes)是协同运作的。社会形式的强迫与压迫之所以能站稳脚跟,恰恰因为它们模仿或援引了本体的认同模式。
如果说,美国民主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威胁要将其瓦解之物——是种族化过程,那么,种族幻想与种族忧郁的本质,必然会改变我们对伦理与政治的构想。正是在这些方面,精神分析可以阐明种族问题:并非因为它阐明了私人欲望与心理,而是因为精神分析将那些私人欲望理解为与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我对精神分析的运用,对纯粹主义者来说,很可能显得特异。我并非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诊断工具,或作为普遍心理或家庭发展的处方来部署。我同意霍滕斯·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的观点,她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核心家庭的俄狄浦斯戏剧,不足以处理那些“在历史上,其性别功能的仪式与权利已被瓦解的被占领或被俘获的个人与社群”。然而,我确实在精神分析思想中,找到了一套强有力的词汇,用以处理种族认同中那富有想象力支撑的、既张扬又哀婉的组成部分。
目前,有几种模式可将精神分析塑造为一种政治上可行的工具。一种方法来自揭示精神分析的社会历史根源,无论是将其发展分析为始于反犹的奥地利的一种文化史(桑德·L·吉尔曼(Sander L. Gilman)),还是解读精神分析治疗中固有的阶级动态(简·加洛普(Jane Gallop)论多拉(Dora)),或是将弗洛伊德的著作置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和殖民想象的遗产中(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另一种策略则是通过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来颠覆其内部术语,以将其重塑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工具(简·加洛普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与“女性书写”学派,斯皮勒斯论乱伦,泰特(Tate)论俄狄浦斯戏剧)。
然而,这些通过精神分析进行的介入形式,仍未回答我们为何要转向精神分析。人们可以揭示精神分析本身的社会构成、内部矛盾或隐藏的意识形态假设,但我们为何要转向那个范式呢?本书希望开启一场对话,不是关于我们为何能用精神分析,而是关于我们为何已然在用。也就是说,从“布朗案”到埃里森和莫里森,种族政治一直都在用心理学的语言言说。精神分析的教诲,首先诉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主体内性(intrasubjectivity)作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形式而存在,而主体间性又常常以主体内性的声音言说:一个相互支持的系统。一种不承认主观同谋之位的进步政治,只能是短视的。
精神分析思想远非铭刻本质主义,它承认本质主义不过是主体性的一种伪装。精神分析的主体之所以是普遍的,只因它将每一个主观生命体都设定为历史性的生命体,嵌入于时间、家庭和社会性之中。在《假设主体》(Supposing the Subject)的导言中,琼·科普杰克(Joan Copjec)警示了将历史视为与精神分析范畴对立的短视。她指出,线性构想的历史才是真正的非历史,而精神分析的视角教导我们去关注历史那断裂的、追溯性的萦绕特质——而且,我还要补充,是那段历史在主体内部的萦绕。我们不应将一段被萦绕的历史与非特定性混为一谈;相反,被萦绕的历史提醒我们关注语境。而正是在对语境的关注之中,我们或许能够开始重新构想一种与哀恸的现实——及其所有物质与非物质的证据——相协调的政治。
通过在忧郁的框架下审视种族构成,本研究生成了一系列批判性术语,以处理失落、幻想和哀悼在美国种族史中的反响。目标是锻造一套词汇,用以谈论在倡导运动的直接要求之外,与种族地理学相关的各种主观状态。我希望,这项对种族忧郁的研究,将抵制我们想象中对政治行为至关重要的那些范畴的封闭性。如果我们愿意倾听,那段支离破碎的哀恸史仍在通过生者言说,而社会变革的未来,则取决于我们以何等开放的心态,去面对那份哀恸的错综复杂与悖论,以及它所遗赠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