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錯覺 Collective Illusions》沒有派系的派系,從村八分到正向異常
你想要沒有派系也得選邊站。
村八分,這種陋習,依舊盤踞在人心深處。
身為現代人,你可以選擇繭居,不靠任何人,也依然能享受足夠的物質生活。然而,你的杏仁核並不會因此沉睡。它仍然活在原始叢林的時間裡,那裡有潛伏的怪獸,還有永遠不確定的明天,食物是否足夠都足以讓人心跳失控。
即使你早已選好了隊友,即使你已經清楚自己的戰場,在別人的視角裡,你仍可能是那個邪惡的模樣。你無法控制,因為基因裡的程式碼早已替你寫下了結局。
於是,你會遇到倚老賣老,遭逢不公與不義。你其實知道,現實不至於讓你因此立刻滅亡,可是焦慮卻依然潛伏在體內,像一條蛇般纏繞著你。你擔心,甚至恐懼,這種排擠會真的把你逼到死角。
也許我們能在這本溫暖的書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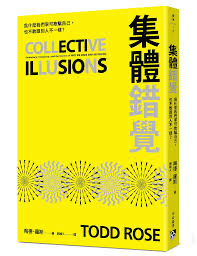
陷阱
這就是陷阱。
人類的選擇,有時候是出於害怕成為異類而助長了。開篇講到了對榆樹谷小鎮的觀察,人們會傾向以某個原則作為,當作是聖旨,而與集體真實的想法背道而馳。談到「從眾偏誤」,三分之二的人明明知道答案是錯的,卻仍舊舉手跟著群體,即使至今,人類害怕被孤立於村落:你不是真的相信別人對,你只是怕那種眼神,怕被推出去。
謊言換來的認同更直白,寫下我們內心最深的恐懼:「別把我驅逐。」
選擇三:明明自己並不同意,但繼續委曲求全。
這第三種選擇就是經濟學家Timur Kuran 所謂的「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它它並不理想,而且經常讓人感覺很糟,但在當下看來通 常都很合理,甚至很務實。麻煩的是,這種選擇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時間跟程度都遠超過大部分人的想像。當我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歸屬而隱藏真正的想法,就很可能會去幫忙實現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助長集體錯覺。
為了避免被驅逐,我們甚至會選擇沉默、說謊,犧牲掉真實的自我。這就是所謂的「適應性陷阱」:你並不是因為認同,而只是因為害怕。誰都清楚這種恐懼,會議室裡,你正經八百的答辯著,看著台下竊竊私語,看著手機訊息發笑,你會不安。走進對立方的空間裡,感受到敵意的肢體語言,你會武裝。明明只是群組裡被已讀不回,明明只是午餐桌上被空下的座位,身體卻像是被判了死刑。這不是理性可以解釋的,而是寫在我們基因裡的古老警報。
無聲的轟鳴更殘酷。沉默不是中立,而是一種背叛。馬丁路德金說過:「有時候,沉默就是一種背叛。」在 #MeToo 的案例裡,多少人明知不對,卻選擇閉嘴,結果不是保全自己,而是讓錯誤繼續滋長。那種無聲,既是對他人的背叛,也是對自己的背叛。
甚至,網暴,有時的發起,也不是真實人的聲音,而是來自機器人的重複行為,但當你面對那個假想的群眾,即使哪是錯的,你也相信了起來。
現代版的村八分社會困境
心理的陷阱會擴散成社會的困境。
村八分,不必真的發生在村子裡。城市裡,鋼筋叢林的角落,也有一種看不見卻揮之不去的排擠。只是換了一種方式,不再是拒絕借你農具或斷絕婚喪往來,而是被群組消息忽略,被辦公室茶水間的眼神掃過,被朋友聚會時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地點的人。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大不了,誰都還能過活,但那種被輕輕推開的力道,卻足以讓心裡坍塌。
現代人往往自信,覺得自己不需要別人。手機、外送、網購,物質上的生存早就不再仰賴村落的共享。可是一旦你被孤立,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安仍會襲上來。就像是一種古老的暗示,告訴你:「小心,你可能活不下去了。」理性上,你清楚不過這是荒謬的,畢竟冰箱裡還有冷凍食品,網路只要付費就能繼續運轉。但身體卻不聽使喚。
所以是什麼,讓人類交出思考的權力和能力呢?《昔日陰魂》裡談到,人在群體裡會因為「覺得大家都這樣想」而隱藏真實想法,還是因為人太懶了。
認真思考實在太耗能,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工具來處理大部分的認知負擔,這樣才能把寶貴的能量用來決策和執行更緊迫的任務,這時候社會規範就很好用,它就像可靠的自動駕駛,通常都不會出問題,所以我們只要無腦照做,認知系統就不會過熱當機。
於是社會規範太好用了,誰有機會站上訂定這個空白規範的制高點,再怎麼聰明的人都會放棄思考,我們甚至會為沉默找理由,說服自己是為了「和諧」。但事實上,不是因為愛和諧,而是因為怕。
第六章《恐怖的誤解》進一步揭露,這就是一種「系統性偏差」:即使大多數人心裡不同意,只要沒有一個人先開口,錯覺就會持續放大。就像校園霸凌,班上許多人其實不認同,可是大家都沉默,最後全班都成了共犯。這就是「沉默的螺旋」,把人推得更深。那麼有機器人去煽動了極端的言論,於是,這些偏差的看法,就會洗版成主流,助長了傳播的烈焰。
嘿,我們都活在這種系統裡。你想要抗拒,卻發現抗拒只會讓自己更孤立。你想要退場,卻發現退場本身也是一種表態。於是你只能繼續留在遊戲裡,假裝自己並不介意。
在職場,派系就像一張細密的網。有人總是第一時間收到內部消息,有人則永遠慢半拍,等到發現時,早就站錯了隊。於是,人們學會了用眼神和暗號交流,用沉默決定誰屬於我們,誰是敵人。你若不選邊站加入那種閒話家常的陣營,就等著被默默邊緣化。沒有人會明說,但你逐漸察覺:有些位置有些眼神就會殺了你心中的一隻貓。
但是,那明明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不能代表人生,何必呢?不段宣傳某人的惡形惡狀,能夠成就誰工作的大成就嗎?
在朋友圈,則是另一種形態。表面上大家談笑風生,可是你貼上的訊息久久沒有人回應,你的分享像被丟進井裡,沒有回音。等你發現,他們早已在另一個小群組裡繼續熱絡。這種透明化的待遇,比明目張膽的拒絕還要殘酷。因為沒有人說破,所以你甚至找不到責怪的對象,只能把懷疑在心裡翻攪。網路上的世界更直接。演算法推動的輿論,很快就能讓人跌入孤立。你或許只是說了一句不合時宜的話,轉眼間就成了不該存在的那個人。陌生人的留言不需要理由,表情符號就足以宣判你出局。比起古老村莊裡的八分,這種孤立更快、更乾脆,也更無情。
所以,無論科技如何進步,「被群體排除」這個古老的咒語,仍舊在我們身上運作。只是外觀改變了:不再是村口的大樹下集體決議,而是隱匿在訊息未讀、眼神閃躲、笑聲缺席的縫隙裡。但那個核心仍舊相同,你被告訴,你不再被需要。而那一刻,你的身體就會誤以為,死亡已經在暗處逼近。
歷史的連續性,於是我借題發揮
孤立,從來都不是現代才有的懲罰。它像是一個古老的儀式,從族群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
在宗族社會裡,血緣決定了你的歸屬與安全。若有人違逆祖訓,或挑戰權威,就會被逐出家門。這樣的懲罰,不只是失去家人的陪伴,更意味著斷絕庇護網絡。沒有宗族的保護,你幾乎等於赤裸裸地暴露在風雨與仇敵之下。那時候,孤立就已經是最殘酷的死刑。
後來社會逐漸複雜,權力不再只倚靠血緣,而是透過學校、公司、政黨等機制重新劃分。可是不論形式如何更迭,「被排除」始終是最有效的懲戒方式。小學的時候,班級裡的結黨分派,總有人被迫成為最後被挑選進球隊的那一個;青春期的敏感更讓這種經驗刻骨銘心。長大後踏入職場,你會發現這種遊戲從未停止,只是換了更精緻的包裝。
公司裡的派系鬥爭,不一定大張旗鼓,卻往往暗潮洶湧。有人仗著資歷,倚老賣老,用規矩(也不知道那怎麼來的、甚至公司都不存在這樣的章程來價值判斷)來維護自己的地位;有人依附強者,假裝忠誠,只為不被拋下。若你選錯了邊,甚至沒有表態,便可能立刻被邊緣化。這種組織版的村八分,往往比鄉村裡更隱晦,也更難以反抗。因為它包裹在專業的名義與制度的外殼下,你甚至很難抓到明確的不公證據,只能在氣氛中感受到自己的位置正在被抽空。
網路的出現,原本被寄望為一種解放:一個讓人能自由發聲、不必看誰臉色的新世界。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群體的排斥在網路上變得更快、更猛烈。只需要幾個標籤、一陣留言風暴,就能讓一個人瞬間社會性死亡。這種死亡不再需要時間鋪墊,也不需要明確理由,只要被群體一致無視、否定,你就立刻掉入無底洞。
從宗族到職場,從村莊到社交媒體,人類社會一直在重演同一套劇本。形式各異,本質卻相同:群體透過孤立個體,來確認自身的邊界與凝聚力。換句話說,村八分並不是單純的陋習,而是一種延續至今的文化機制。它不僅僅懲罰異端,也同時安撫了群體內部的焦慮:只要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我們就能更確定彼此的圈內人身份。
然而,這樣的機制往往犧牲的,就是那個被推出去的人。歷史的連續性提醒我們,孤立並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一個深植在文化與制度裡的規則。你不必做錯什麼,只要不夠合群,就足以被推到場外。
看著你出糗。
心理層次:原始程式碼的作祟
理性上,我們都知道,這個年代不會因為被孤立就餓死。冰箱還滿著,超商二十四小時亮著燈,任何需求都能用金錢或科技解決。可是身體不聽這些解釋。當你察覺自己被群體輕輕推開,那個最古老的警報系統立刻亮起。
杏仁核,就像一顆被困在顱骨裡的小鼓,不受意志控制地開始敲打。心跳忽然加速,呼吸變得短促,甚至還會冒出一種荒謬的念頭:是不是有什麼猛獸在身後?明明只是開會時被忽視,或是訊息久久沒人回應,但身體卻彷彿被丟進了叢林。
這就是人類的原始程式碼。數萬年前,我們若是被部落排斥,幾乎等於死亡:失去庇護,沒有食物,獨自一人無法抵抗野獸與氣候。這段程式碼從來沒有被刪除,只是被一層層現代的外殼包裹著。它像一個幽靈,隱匿在我們的神經迴路裡,一旦觸發,就提醒我們「孤立等於危險」。
於是,矛盾就產生了。大腦的前額葉努力說服自己:沒事,你只是沒被邀請吃飯而已。但杏仁核卻像個不講理的原始首領,霸道地宣告:你會死,你必須趕快找回同伴。這種撕裂,讓人活在荒謬的雙重現實裡:一邊是冷靜的理性,一邊是恐慌的肉身。
有時候,這種矛盾甚至會放大到失序。你開始過度在意別人的眼神,揣測每一句話的弦外之音,甚至在無人時也無法停止腦補。夜裡躺下,本該休息的時刻,卻一遍遍重播白天的片段,懷疑自己是否說錯話,是否已經被默默判了刑。睡眠因此支離破碎,白天的身體愈發倦怠。這不是單純的心理遊戲,而是身體確實在用最古老的方式逼你投降。
這樣的痛苦,往往難以對人啟齒。因為當你試著訴說,別人會以現代的邏輯回答:「不過就是被冷落一下,有什麼大不了?」可是在你體內,那並非小題大做,而是來自生存本能的警告。這種落差,使得孤立感更形孤立。你不僅被群體排擠,連自己的焦慮也被否認。彷彿雙重放逐:外在的,與內在的。
所以,所謂「選邊站」的痛苦,不只是社會現象,而是生物學的宿命。我們被寫死在程式碼裡,無法擺脫,也無法重啟。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在理性與情緒的拉鋸中,繼續過著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湧的生活。
或許,人終究逃不掉這種排擠的機制。即使你極力保持中立,群體還是會用他們的方式,提醒你「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你不表態,就是在宣告自己是多餘的;你不站邊,就等於選擇了站在邊緣。
有人說,解決的方法是融入,要懂得識時務,懂得迎合。但這樣的代價,往往是自我逐漸模糊。你學會笑在不該笑的時刻,附和在違背直覺的地方。久而久之,你甚至忘記了自己最初的模樣。那麼,這樣的「融入」,是否真的比孤立更好?
也有人選擇抗拒,選擇不玩這場遊戲。他們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裡,用閱讀、創作、沉默來與自己對話。這樣的生活看似孤僻,卻也蘊含某種清醒。畢竟,當你看透了群體的殘酷規則,孤獨反而成為一種解脫。不是沒有人願意接納你,而是你主動拒絕讓自己被規則宰制。
然而,說是解脫,實際上卻並不輕鬆。身體的程式碼依舊在作祟,焦慮依舊會在夜深人靜時湧上來。你理性上選擇了孤獨,情緒卻不斷提醒你:危險,危險。這就是矛盾,也是我們無法完全解決的困境。或許只能學會與之共處,在孤獨中尋找某種新的秩序,讓自己不至於被完全吞沒。
孤立不是選項,而是一種必然的輪迴。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刻被推出群體之外,哪怕只是一瞬間。重點不在於避免,而在於當那一刻來臨時,你如何自處。你是拼命掙扎著想要回去,還是選擇承認自己的邊緣性,並在邊緣找到一種新的中心?
也許答案並沒有那麼悲觀。孤立固然痛苦,卻也可能是一種召喚,它逼迫你去面對自己,逼迫你直視那個無法依賴他人的自我。當你逐漸接受這樣的處境,你才會發現:
力量,我們可以找回堅持做對的事情的勇氣
但書的後半部,讓我看到出口。
第七章到談「一致性」。Carl Rogers 說,唯有外在自我與內在經驗一致,才能真正帶來誠懇與充實的生命。這種「一致性」不是迎合群體,而是內外不再分裂。當我們開始允許自己真實,焦慮就不再那麼銳利。我也在三日書之三|標記回憶|下不了班的心 回應了這個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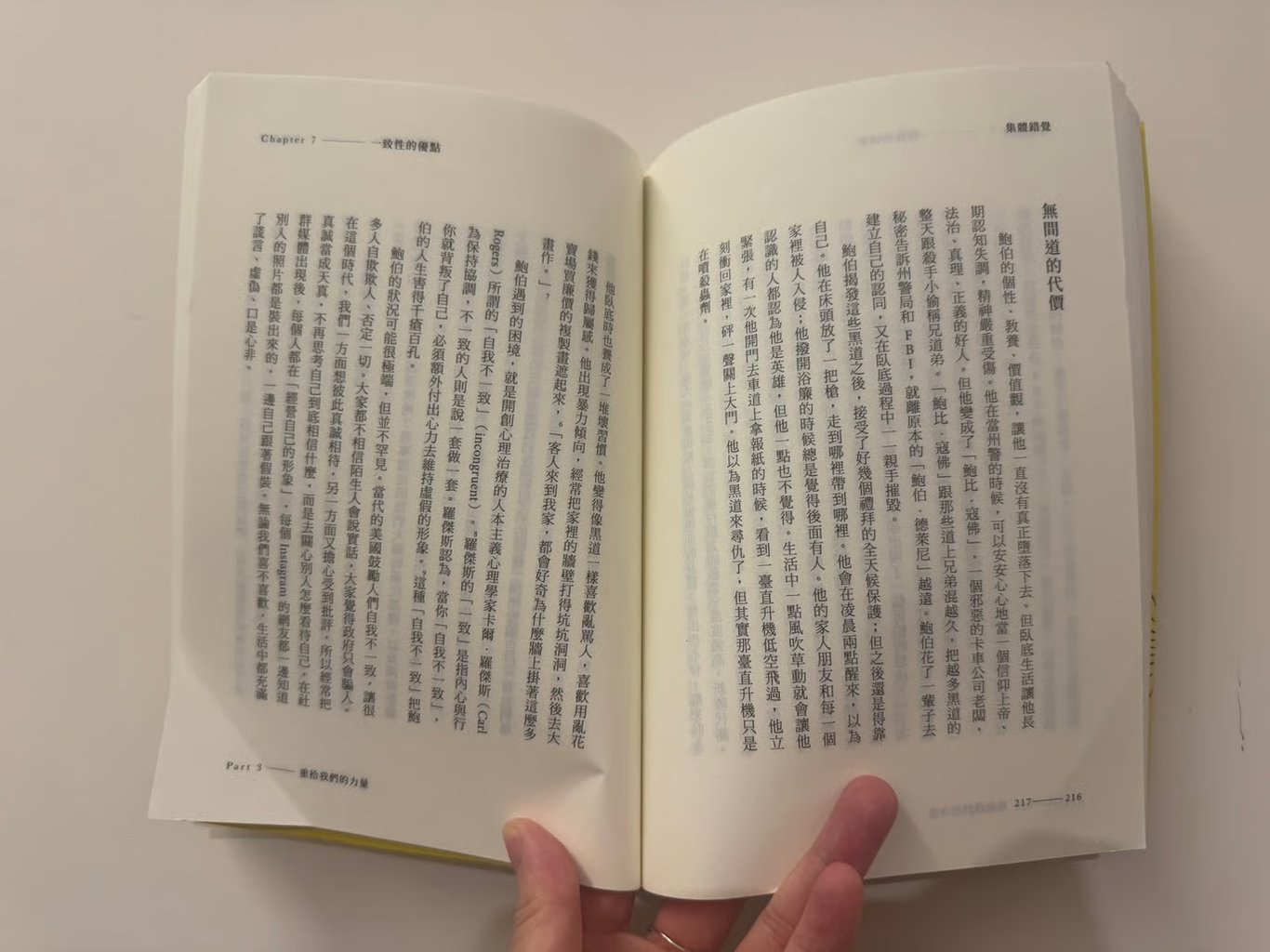
自我一致不僅能讓我們更容易成功,,還會讓我們變得更值得信任、經營出更好 的人際關係、對生活更滿意。「個體機會中心」研究指出,我們只要多花二成的時間做自己真的在乎的事情,生活滿意度的提升程度,就會跟加薪五成相等。而且無論在乎的事情是什麽都可以:種花、陪龍物、玩音樂、陪兒孫沒有關係,只要你享受的是自己喜歡的巧克力冰淇淋,而不是別人喜歡的香草冰淇淋。
所以停下來想想吧。你喜歡的到底是什麽?
管他的,誰不喜歡你,演出成不喜歡的樣子,你在生命裡扮演的其中一齣戲劇,不過就是如而已。
推翻家父長制
而我們探究根源了解在工業發展下「泰勒主義」:造成人的不信任,把人變成機械的一部分,重視效率與標準化,讓人失去自我。我不會怪罪泰勒理論帶來的經濟蓬勃,畢竟我的前輩同事們都在那樣競爭的環境裡留下來了。留下的不一定是汰弱,只是單純適合這麼風景而已,就像達爾文從來沒有評價任何一個優勢物種誰最厲害。我需要的不是適應,本身我就已經在本能裡,在長時間的相處裡,多少染上了他們的顏色,還有或多或少說著那些語言。即使我認同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習慣,永遠保持著中立或是外部的觀點,但我還是得生存,只能保持著樂觀。
讓他去吧,這些離不開辦公室的人們,科學管理下,依舊是以自身的利益、情緒與臉面出發,那麼,你也更沒有必要與之共舞。
他們因為在這個社會就要求你按照他的法則走,彰顯他們懂得比你多,整個社會已因此付出了代價,那麼,我們還有什麼方法改變嗎?
拒絕接受「大家都這樣」,而從異常中找到答案
有些人天生就無法安穩在那一鍋大鍋飯裡吃下去,明知道大家都低頭、都不出聲,還是忍不住要抬起頭,看一看這裡頭到底有多少破事與荒謬。你不是故意要刁鑽,不是想挑釁,而是因為你看見了別人選擇忽視的東西。
這叫「正向異常」也是我最喜歡的答案——那一些不跟著規則走、不願意照抄前例的人,反而給了社會新的解方,很多人總是抱怨著不公平,但沒多久就加入,但也有人,會想要改變,想要用寧靜革命來帶來環境的正向改善。所以你不是孤單的。辛苦你了,還願意一直保持那份敏感,那份警覺。因為在漫長的沉默裡,有些聲音只有靠你先喊出來,才會有人跟上。
[ 改善戰後越南小孩營養不良的案例裡] 史特寧夫妻這種放下身段,以詢問當地人來找出答案的獨特方法,在學術上稱為尋找「正向異常」(positive deviance 在常態劣勢下狀況好得不合常理的個案),史特寧夫妻還說,他們經常用當地人的諺語來描述這個詞。例如孟加拉人會說「只能這樣嗎?」、莫三比克Mocua部落說:「遠處的棍子殺不死腳邊的蛇,許多地方的人則會說「大衛可以扳倒歌利亞」。
「正向異常」的原理就是尊重當地智慧,相信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掌握在當地人手中,相信無論走到哪裡,創造力都是最有力的資產。 這種方法在各地屢試不爽。
一本很溫暖的書,三個提醒:
成功是來自內外一致。
你遇到的壞人只是少數,多數人其實值得信任。
當你感覺到「不正常」,那或許真的是不正常。保持警覺與覺察,你就能找到答案。
我最喜歡的是,作者講了自己從眾的蠢事和很多勵志改變的故事。那句話一直繞在我心裡:「你以為大家都這樣認為,是真的嗎?」這句話溫柔又殘酷,它提醒我,很多時候我其實並不孤單,只是被錯覺困住了。
所以,你沒有派系,你就是那個派系。那個孤獨卻誠實、仍然渴望光的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