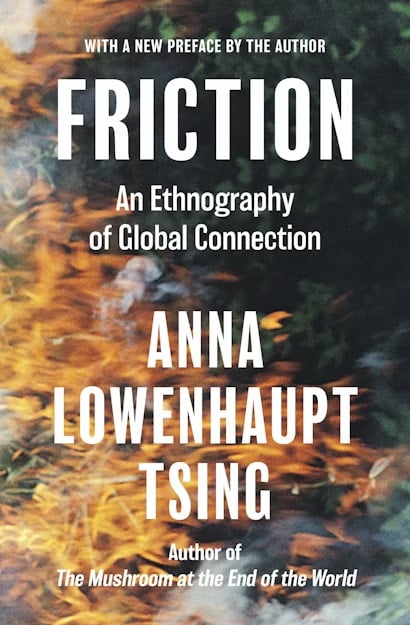罗安清|普世化与在地的摩擦
本文是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著作《摩擦:全球连结的民族志》的前言与引言部分,题目另拟。罗安清,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研究多样性、多物种的民族志与普世化过程中的“摩擦”等,其著作《末日松茸》已得到引介。
摩擦:全球联结的民族志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罗安清 Anna Lowenhaupt Tsing

前言
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熙熙攘攘却又宁静的地方,以其海滩和商机而闻名。然后——突然之间——世纪之交前后,这个国家似乎分崩离析了。金融危机、政治丑闻、族群与宗教冲突、资源争夺的故事充斥着新闻。然而,哪怕只是稍微走近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动荡与灾难的爆发,都直接根植于此前三十年那个想象中的和平与进步时代所施行的政策与实践。
不妨想一想印尼著名的雨林及其原住民文化的境况。苏哈托将军(1966-1998)的“新秩序”政权将商业变成了一头掠食者,它诞生于裙带关系、国际金融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体,靠着从乡野社群非法掠夺的廉价资源为食。难怪1998年苏哈托辞职后,村民们变得胆气十足,开始伸张他们的地方权利。并且,鉴于企业征地过程中伴随的暴力,也难怪各种各样的地方怨言会卷入一场危险的混战。社群团体与非法伐木者、企业保安、黑帮、倡导团体、宗教派系、地方官员、警察和军人,时而争斗,时而合流。
本书描述了两种文化过程:一方面,某些掠夺性的商业行为如何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地方赋权斗争如何兴起。这两种过程共同塑造了印尼雨林的特质。我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在南加里曼丹山区的田野工作,但这并非一个可以被局限于某个村庄、某个省份或某个国家的故事。它关乎北美洲的投资实践与股票市场,关乎巴西橡胶采集者的森林倡导运动与联合国的环境基金,关乎国际登山与探险运动,也关乎民主政治与苏哈托政权的倾覆,等等。通过跨越这些领域,我提供了一份关于“全球联结”(global connection)的民族志。“全球”一词在此并非意在宣称能同时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相反,它引入了一种思考社会项目(包括“商业”和“地方赋权”)历史的方式。首先,这类项目生长于空间上分布遥远的协作与相互联结之中。其次,文化多样性并未在这种相互联结中消失;正是它,才使这些联结——及其所有的特殊性——成为可能。文化多样性为全球联结带来了“创造性的摩擦”(creative friction)。本书的主题,正是这种摩擦。
1994年,我在印尼进行田野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误解,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为研究跨越差异的环境联结的可能性而感到兴奋。虽然能见到老朋友和我认的家人是件好事,但在我持续进行研究的地点——南加里曼丹的马鹿都斯(Meratus)山区——的那段时光却令人不安。木材公司新近侵入了马鹿都斯的地景。我的许多马鹿都斯达雅族(Meratus Dayak)朋友,因森林遭到破坏而意志消沉,那些森林曾是他们作为刀耕火种的农人与森林采集者的生计之本。当我在乡间游走,倾听马鹿都斯人对伐木危机的看法时,不少人向我提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1986年,一场成功的运动将一家伐木公司从一个马鹿都斯村庄里赶了出去。我决定去了解这场运动,它是由村庄长者与省会的“自然爱好者”团体以及来自雅加达的国家级环保主义者共同组织的。机缘巧合,其中许多关键人物我或者认识,或者听说过,因此得以访谈到主要的参与者。当然,最初那场运动发生时我并不在场。但这反而让我更能体会相关叙事的精妙之处。因为故事中浮现出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它们似乎在描述完全不同的事件。当被问及其他参与者的故事时,每一位受访者都觉得其他人的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很不真实。我忍不住注意到,将村庄长者、省城的自然爱好者和国家级环保活动家区隔开来的是一种系统性的误解。然而,这些误解非但没有引发冲突,反而让他们得以合作!
这些无法通约的访谈为我阐明了所有社会动员的一个核心特征:它建立在对事业的目标、对象和策略上或多或少已被认识到的差异进行协商的基础之上。理解这一点的意义,并非要将各种视角同质化,而是要懂得如何尽可能地善用多样性。(我将在第七章更详细地讨论这场马鹿都斯反伐木运动的故事及其分析意义。)这些访谈也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就这些议题所做的那种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的田野工作,在实践上是行之有效的。一方面,我不愿放弃民族志方法,它关注的是民族志学者的意外发现,而非预先制定的研究计划。另一方面,要对构成一条全球链条中所有联结的每个社会群体都进行全面的民族志考察,又是不可能的。
*关于“拼布民族志”,见https://tyingknots.net/2024/07/教与学-拼布民族志宣言/我的实验是在马鹿都斯山区——我在这里有长期的民族志背景——和我所追踪的链条中牵涉到的其他地方之间来回穿梭。¹ 我的知识是民族志、新闻调查和档案研究等不同类型的混合,并且以零散的“补丁”形式构成。我寻找的是奇特的联结,而非无缝的概括、包罗万象的表格或可供比较的框架。
如何为全球联结做民族志?由于民族志最初是为小型社群设计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社会科学家一段时间。我的答案是,聚焦于“尴尬接触的地带”(zones of awkward engagement)。在这些地带,即便人们同意对话,言辞的意义在分歧的两端却不尽相同。这些文化摩擦地带是短暂的;它们源于相遇和互动,又随着事件的变化在新的地方重现。我能想到的研究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这种拼布式的、随缘而遇的方法。这类研究的成果或许不是一部经典的民族志,但它可以从民族志学者的学习体验中汲取养分,因而可以是非常深刻的民族志研究。
许多民族志的学习体验塑造了本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来自我早期在马鹿都斯山区研究的经历:森林景观是社会性的。我最初是以博物学家的眼光进入马鹿都斯森林的。我惊叹于物种的多样性,也曾在许多山脊上赞叹森林的景致。只有通过与马鹿都斯达雅人一同行走、一同劳作,我才学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森林。他们向我展示的森林,是一片承载着个人生命轨迹与社群历史的场域。个人和家庭在森林中追溯他们的历史:房子的立柱重新发芽长成树木;旧垦荒地上,林木再度生长;果树和藤条被种植在成长中的森林里;为了吸引蜜蜂,人们清理并认领巨大的林木。人们阅读这片土地,既读它的自然故事,也读它的社会故事。社群正是在这些交叠的历史中,以及在流动的公共场所中(旧的场所则由丰茂树木构成的岛屿标记出来)得以构成。(第五章将描述这片景观。)然而,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都继续将森林描绘成外在于社会的、野生的自然空间。如果马鹿都斯的森林被承认为社会性的,那么强加于该地区的那些主流的资源开采和保育模式,就会显得无比怪异了。
当我回到马鹿都斯山区继续这项研究时,一些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占据了更优先的位置。伐木公司进驻了,用推土机推平了果园、藤本植物种植地和古老的村社遗址。我最熟悉的人们愤怒而不安;几年后,他们变得顺从和沮丧。(再后来,经济危机和一场新的反伐木运动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愤怒。)我发现自己深陷于他们的情绪之中,并且——我认为这完全合乎情理——无法写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叙述。但我该写什么呢?一方面,关于公司盘剥原住民的激进叙事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我的故事或许只是多余的——且很容易被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我的学术同仁们对这类叙事的简单化处理感到不满,他们提醒我,许多人从木材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采矿和种植园热潮中受益。我认识一些城里人、移民,甚至一些有抱负的当地人,他们确实赚了大钱。但我最了解的那些农人和采集者塑造了我的视角。我想讲述他们的故事。为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必须将“痛苦”(distress)的问题置于中心舞台,而不是试图回避它:聚焦于最痛苦的地区,专门书写痛苦,并运用一种民族志的书写风格,尽我所能地让其轮廓变得生动鲜明(见第一章)。如果这是一个应该被讲述的故事,它就值得拥有一条“听得见”的声轨。
我对马鹿都斯人被剥夺处境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印尼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见第六章)。尽管有军事统治、审查制度和公众的恐惧,但这场运动却旗帜鲜明地主张民主的重要性、边缘群体的权利,以及保育与正义的不可分割性!能有这样一个对话者伴随我的研究,我感到无比激动。然而,我也明白,我参与的任何对话都要求我为自己的田野工作和写作承担一些责任。印尼的环保主义者在一种国际性的科学与政治文化中工作;他们对美国学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发言、却不考虑其言论在当地可能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敏感。我与活动家们的民族志交往教会了我克制与审慎的习惯:有很多事情我不会去研究或书写。我并非说我粉饰了我的记述,而是说,我对自己认为何种研究课题是恰当的,甚至是“有用的”——有助于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彼此协作的国际公共文化——做出了选择。
从1966年到1998年,印尼由苏哈托总统的威权政权统治。在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之后,苏哈托下台,一个改革与转型的时代缓缓开启。政治的性质、城乡关系、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的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我继续我的研究以了解这些新情况,但我将本书的重点放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这一时期。在当时,资源开采由中央授权,迅猛而不负责任,而反对这一切的环保运动正处于其最具英雄色彩的时期。这一时期确立的形式和范畴,持续塑造着晚近的政策和政治斗争。
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权更迭也影响了我的写作。美国的全球野心塑造了北美内外大众对文化和政治的理解,特别是通过两个宏大而危险的概念。其一,“全球化”的概念,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下,助长了一种幻想,即世界万物都已成为一个单一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其二,“恐怖主义”的概念,在其最骇人的形式下,认定所有差异的本质都是旨在折磨正派人的野蛮行径。当公共辩论被这两个误导性的概念及其催生的普世主义和文明论所主导时,要书写文化差异变得十分棘手,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或许需要一种不合理的乐观,即相信在全球联结中酝酿的差异,将比这些窒息与死亡的理论所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富奇趣和创造力。
本书的写作成就得益于许多合作。对于我在加里曼丹马鹿都斯山区持续进行的研究,我尤其感谢我认的兄妹乌玛·阿当(Uma Adang)和马·萨拉姆(Ma Salam),他们给了我如此多的洞见。在南加里曼丹,哈桑(Hasan)和扎伊娜布(Zainab)一家,以及伊延(Iyan)和阿尼西亚(Anisyah)一家,一如既往地热情款待我。已故的科斯诺(Koesnoe)教授和拉丹(Radam)教授是最慷慨的对话者。我近期的工作得到了许多活动家和积极介入的学者的帮助。我尤其感谢艾美·哈菲尔德(Emmy Hafild)、桑德拉·莫尼亚加(Sandra Moniaga)、班邦·维佐扬托(Bambang Widjojanto)、阿林比·赫罗普特里(Arimbi Heroepoetri)、特里·努格罗霍(Tri Nugroho)、阿古斯·普尔诺莫(Agus Purnomo)、德亚·苏达曼(Dea Sudarman)、哈立德·穆罕默德(Chalid Mohammad)、阿卜杜拉赫曼(Abdurrahman)教授、阿比(Abby)教授、布代里(Budairi)教授、拉赫米娜(Rahmina)以及“原住民社群捍卫者协会”(Lembaga Pembelaan Masyarakat Adat)的所有活动家所给予的多方协助与款待。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杰弗里·坎贝尔(Jeffrey Campbell)、菲利普·扬波尔斯基(Philip Yampolsky)和玛丽·祖布兴(Mary Zurbuchen)在雅加达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朱迪思·迈耶(Judith Mayer)和斯蒂芬妮·弗里德(Stephanie Fried)为我拓展了人脉并与我讨论了研究。
本书的不同部分需要专门的研究协助。关于自然爱好者的章节之所以能够完成,得益于与梅赛德斯·查韦斯·P(Mercedes Chavez P.)的合作,她通过自己在日惹(Yogyakarta)的人脉帮助启动了这个项目。研究自然爱好者的一个最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们自己也对研究着迷。我刚一介绍我的问题,我的访谈对象们就跑去采访他们的朋友,给我提供报纸文章和自然爱好者通讯,有时甚至会写一些关于热爱自然的小短文来帮助我。因此,我在此处报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热爱自然的人士的协同研究。我特别感谢“切普利斯”·迪亚·苏特吉宁蒂亚斯(“Ceplies” Dyah Sutjiningtyas)、班邦·庞科·苏万托(Bambang Ponco Soewanto)和西吉特·穆尔达瓦(Sigit Murdawa)。与彼得·阿德尼(Peter Adeney)的对话也很有帮助。我希望我没有曲解这支热情的团队教给我的主旨。
美国国内外的学者和朋友也为本书做出了贡献。事实上,与所有学术研究一样,很难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洞见,哪些是他人的想法。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凯瑟琳·切特科维奇(Kathryn Chetkovich)、蔡志浩(Timothy Choy)、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保拉·埃布龙(Paulla Ebron)、莉芭·费尔(Lieba Faier)、苏珊·哈丁(Susan Harding)、迈克尔·哈撒韦(Michael Hathaway)、埃本·柯克西(Eben Kirksey)、塔尼亚·李(Tania Li)、西莉亚·洛(Celia Lowe)、伊特卡·马莱科娃(Jitka Maleckova)、南希·佩卢索(Nancy Peluso)、丽莎·罗费尔(Lisa Rofel)、丹尼尔·罗森伯格(Daniel Rosenberg)、萨冢志穗(Shiho Satsuka)、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和玛丽·斯蒂德利(Mary Steedly)阅读了我章节的早期草稿并从中受益。其中一些同事非常有耐心,多年来阅读了多个稿本并提供建议。我几乎不知该如何感谢他们。与伊蒂·亚伯拉罕(Itty Abraham)、彼得·布罗修斯(Peter Brosius)、卡罗尔·格拉克(Carol Gluck)、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贺萧(Gail Hershatter)、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安·斯托勒(Ann Stoler)、托比·沃尔克曼(Toby Volkman)、萧凤霞(Sylvia Yanagisako)、查尔斯·泽纳(Charles Zerner)以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东南亚区域顾问小组的对话也帮助了我思考。
在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我得到了朱莉·贝克(Julie Beck)、本杰明·布雷(Benjamin Bray)、何柔宛(Karen Ho)、莫拉·麦克拉根(Mora McLagen)、斯科特·摩根森(Scott Morgensen)、雷安娜·帕雷纳斯(Rheana Parrenas)、贝蒂娜·施特策(Bettina Stoetzer)和蔡晏霖(Yen-ling Tsai)的研究协助。苏珊·沃特劳斯(Susan Watrous)以她的技巧和热情将所有细节整合在一起。我对此深表感激。
1994-95年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时光让我在环境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1997年,加州大学人文研究所的一个驻地研讨班让我起草了第一章。1999-2000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一项奖学金让我得以充实本书的内容。我也感谢那些邀请我就这部逐步成形的作品发表演讲的大学的师生们。
本书中出现的普通人的名字均为化名,村庄的名字也是如此。对于重要的公众人物和主要城市,我使用了真实姓名。
第一章前半部分的不同版本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38[48, 2003]: 5100–06)以及由苏珊·哈丁和丹尼尔·罗森伯格编辑、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未来的历史》(Histories of the Future)。第二章的一个版本发表于《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12[1, 2000]: 115–44)。
本书前后环衬页上的清单,是基于与一个个体的讨论,他仅凭记忆,在没有任何实物提示的情况下回忆起这些生命形式。这些清单并非意在成为一个总名录。制作这份清单的过程在第五章前的间奏部分有描述。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前的照片分别由作者于1994年和2000年拍摄。第三部分之前的照片是一张海报,经马鹿都斯联盟(Aliansi Meratus)许可复制。
注释
1. 我最初熟悉马鹿都斯人的社会生活,是在1979至1981年间,通过在马鹿都斯山区为期两年的“深度沉浸式”田野工作。我曾计划进行其他几次长期的田野考察,起初是为了研究社会性景观的形成,后来是为了研究环保动员,但我无法协调好我的研究许可、健康状况、经费和教职。于是,我的田野研究被组织成一系列较短的时段,通常为期几个月。幸运的是,我关注的其他群体——自然爱好者、活动家、捐助者、学者——对我的社会地位感到足够的亲近感,使得安排民族志田野工作相对容易。(我曾尝试对木材和矿业公司的代表进行不止于肤浅的访谈,但都失败了。他们的敌意也让我不敢去接触在职的雇员。)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主要是在北美的夏季——从雅加达出发,前往各个省会、城镇以及马鹿都斯山区,让自己跟随熟人关系网,以及我能在他们之间进行三角验证的雨林政治事件和议题。我的田野工作包括1986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的几次短期考察。

引言
全球联结无处不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研究“全球”?
本书探讨的是对全球联结的向往,以及这些向往如何在“摩擦”——即尘世相遇的纠缠之力中——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科学和政治都依赖于全球联结。每一种都通过实现普世梦想和方案的向往而传播。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普世性:它唯有在实践相遇那黏着而具体的物质性中,才能被赋予能量、得以践行。本书将这种实践性的、介入性的普世性作为一份指南,用以探寻我们时代的渴望与噩梦。
后殖民理论向学者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将研究置于普世性与文化特殊性这两个陷阱之间。¹ 这两种观念都曾是殖民知识的伎俩,即那种通过将西方定义为其“他者”的对立面,来合法化西方优越性的知识。然而,在研究殖民话语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却将自己局限于等式的“文化特殊性”这一边。对于普世性的历史,人们的关注则少得多,而它同样是在殖民相遇中被生产出来的。在此,一种普世性的特定意涵被生产出来;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言,普世性是“我们不可能不想要”的东西,即便它常常将我们排斥在外。² 普世性为我们提供了参与全球人类洪流的机会。我们无法拒绝。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在不注入我们自身的承诺与主张的谱系的情况下,去复制它先前的版本。无论我们自居于西方之内还是之外,我们都无法摆脱在文化对话中被创造出来的普世性。正是这种后殖民与新殖民的普世性,为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新自由主义注入了活力,使它们自冷战结束以来,如此生气勃勃地传遍世界。学术知识也概莫能外;每一种真理都是在与普世性向往的协商中形成的,无论这一过程多么混乱。
本书并非一部哲学史,而是一部关于全球联结的民族志。全球联结的特殊性时刻提醒着我们,普世性的宣称并不会真的让万事万物在任何地方都变得一模一样。全球联结让普世性的向往有了着力点。本书通过全球联结的视角,探索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普世性如何运作。一旦我们不再将普世性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抽象真理,我们就必须卷入具体的处境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从事情的中间地带开始。
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印尼的雨林中开始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历经数百万年才聚集起来的物种多样性,被砍伐、焚烧,最终沦为水土流失的牺牲品。地景转变的速度令观察者们措手不及。人口、需求或市场的任何渐进式扩张,都不可能解释这一切;况且,这些森林的产物早已在全球市场上行销了数百年。企业的增长在摧毁自身资源方面,显得莫名地混乱、低效和暴力。更奇怪的是,普通民众——甚至那些靠森林为生的人——似乎也加入了远方公司的行列,共同创造着不宜人居的地景。³
在印尼国内,这一丑陋的局面成了帝国主义危险和腐败政权劣迹的象征。反对国家和企业破坏森林民族生计的斗争,成为1980和1990年代新兴民主运动的一项关键纲领。一种创新的政治应运而生,它联结城乡,让活动家、学生和村民跨越视角与经验的差异,展开对话。这场动员的洞见与波折在国外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然而,它们却触及了我们时代的核心困境:全球资本主义为何如此混乱?谁为自然代言?在二十一世纪,何种社会正义才有意义?
这些问题,若不理解全球联结,便无一能解。印尼的森林并非为满足地方需求而遭毁灭;其林产品是为全世界而攫取的。环保行动主义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一场全球运动的鼓动与支持。然而,关于全球文化形成的流行叙事,对于理解这些现象几乎毫无帮助。这里没有全球一体化的凯歌;地景破坏的混乱混战,以及激进批评者尖锐的抗议,都是在纷争、碎片化和区域不平等中锻造而成的。我们看到的是特定历史相遇所产生的出人意料且持续存在的影响。一个村民给北美矿工看金子;胶合板贸易采用了日本模式;被禁止参与政治的学生们开始徒步旅行;一位部长受到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启发:这些看似狭小的事件,为未来的“全球”发展铺设了轨道。我的故事并非要讲述一个新时代的演化式展开,而是要探究那些跨越距离与差异、塑造着全球未来——并注定了其不确定状态——的临时搭建的联结。
本书展示了新生的文化形态——包括森林破坏和环境倡导——如何成为跨越差异的全球相遇所产生的持续而又不可预测的效应。这一论点延伸了我早前的研究,在那项研究中,我探讨了即使是看似孤立的文化,如印尼的雨林居民,也是在国家和跨国对话中被塑造的(Tsing 1993)。学者们曾将这类文化视为文化自身“自我生成”属性的典范。然而,越来越清晰的是,所有人类文化都是在从区域到全球的权力、贸易和意义网络的长久历史中被塑造和转化的。随着来自各方的新证据涌入学术界,学者们已经有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无权的少数群体已经适应了全球力量。但要反过来说,全球力量本身就是地方/全球互动的聚合体,则要更具挑战性得多。
挑战来自几个方面。一些强大的思维定式阻碍了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例如,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将所有文化发展都打包进一个单一的程序中:一个全球时代的降临。如果全球化可以被预先断定,那么除了看细节如何支撑这个蓝图之外,研究本身就没什么可学的了。并且,如果世界中心为全球变化提供了动力,那又何必去研究更边缘的地方呢?对边缘地带的创造性研究也同样步履维艰。强大的社会科学指令在一种疏离的帝国凝视下,对“全球南方”的发展进行编目和比较,将我们排除在文化后果真正攸关紧要的竞技场之外。如果印尼只是一堆数据碎片,它或许能给世界主义的读者提供信息,但它的全球相遇却永远无法塑造那个印尼人与非印尼人共同体验恐惧、紧张和不确定性的共享空间。在这个共享空间里,相遇的偶然性至关重要。为了将我们引向那里,我必须清理出一条远远超出印尼森林的理论路径。然而,我们能为全球联结找到一个民族志的立足点吗?为了研究“全球”,我们该将它定位在何处?即使是那些决心从事此类研究的人,也仍在摸索该如何进行。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书发展出一套方法组合,用以研究全球联结的“生产性摩擦”。当日本商人购买印尼的树木,当军官与自然爱好者达成交易,或者当大学生与村庄长者坐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我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这类跨越差异的相遇所具有的混乱和出人意料的特征,应当为我们的文化生产模型提供信息。与大众对程序化的全球预测的过度热情相反,我强调全球互动中出人意料和不稳定的方面。为了丰富那种只关注内部蓝图以求复制和增长的单一文化解释,我强调跨文化和长距离的相遇,在塑造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化构成中的重要性(例如,Clifford 1997)。文化是在我称之为“摩擦”的互动中被持续地共同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种跨越差异的相互联结所具有的尴尬、不平等、不稳定和创造性的品质。本书的每一章都发展出一种方法,用以了解偶然相遇的这些方面。
虽然印尼的情况很独特,但它也能将我们带到当代学术界最活跃的辩论与讨论的中心。
因此,左翼学者们一直忧心于如何最好地描述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性伪装。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倾向于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前者常常发现资本主义的普世化特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例如,詹明信 2002),而后者则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中寻找其不均衡性与特殊性(例如,萧凤霞 2002;米切尔 2002)。前者想象将普世性动员起来是有效反抗剥削的关键(例如,哈特和奈格里 2000),而后者则在基于地方的斗争(马西 1995)和出人意料的联结(吉布森-格雷厄姆 1996)中寻找抵抗。
这些著作的贡献都令人惊叹;然而,将它们置于对话中,却似乎相互掣肘。这里存在一种跨学科的术语误解;正如詹明信(2002: 182)所解释的,“普世性并[不是]某种你将特殊性作为其一个纯粹类型来归类的东西。”⁴ 而社会科学家们却常常正是这么做的。但我的目标并非要纠正这些学科,而是要把握住这一误解所具有的生产性时刻。正是在这个交汇点上,普世性与特殊性走到一起,创造出我们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形态。研究完全分立的“诸种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播,正是因为生产者、分销者和消费者努力将资本、货币和商品拜物教的范畴普世化。这种努力使得跨越全球的资本链和商品链成为可能。然而,这些链条是由不均衡且笨拙的环节构成的。资本主义形态的文化特殊性,源于必须通过尘世相遇将资本主义的普世性付诸行动。印尼雨林中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正是全球资本链和商品链得以形成的那些相遇的缩影。
另一组相关的辩论,也体现在对二十世纪末作为抗议载体而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的讨论中:人权、族群认同政治、原住民权利、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和环保主义。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人将这些运动视为一种可怕的全球强制力的新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将其描绘为承载着自由的希望。这里的划分并非跨学科的,而是跨越听众的。那些面向文化理论家发言的人,强调的是新型规训权力的形成(例如,拉比诺 2002);而那些将活动家纳入其听众的人,则强调这些运动的潜力(例如,凯克和辛金克 1998)。⁵ 前者解释自由主义主权和生命权力的普世化逻辑;后者则告诉我们具体案例的紧迫性。同样,这些评论者各说各话,彼此错过;也同样,他们的交集本可以更富生产性。我们必须注意到,抗议动员——包括1980和1990年代的印尼民主运动——是如何依赖权利与正义的普世化修辞的。通过这些修辞,它们向世界陈述自己的理由;也同样通过这些,它们被自由主义的逻辑所塑造。然而,它们必须让这些修辞在它们特定处境的妥协与协作中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新的意义和谱系被增添到自由主义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然而,若能想象自由主义主权——及其普世性——在世界上获得具体着力点的样子,我们对它的看法就会改变。
这两场讨论都能从对全球联结的聚焦审视中获益。在全球联结的历史特殊性中,统治与规训得以成形,但其形式并非总如其倡导者所规划的那样。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避免那种认为新帝国形式是全副武装、从欧美父辈头脑中一跃而出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项工作也避免了对一种能够吸收和转化任何帝国指令的“南方”文化自主性过于急切的赞颂。相反,对全球联结的研究揭示了相遇的纠缠之力:摩擦。车轮之所以能转动,是因为它与路面相遇;在空中空转,则寸步难行。两根木棍相互摩擦,才能生热发光;一根木棍就只是一根木棍。作为一个隐喻性的意象,“摩擦”提醒我们,异质且不平等的相遇可以引向文化与权力的新布局。
“摩擦”这个隐喻之所以浮现,是因为在1990年代,关于一个全球流动新时代的叙事非常流行。从此以后,商品、思想、金钱和人员的流动将无孔不入、畅通无阻。在这个想象的全球时代,运动将完全没有摩擦地进行。通过摆脱国家壁垒和专制或保护主义的国家政策,每个人都将拥有去往任何地方的自由。的确,运动本身将被体验为自我实现,而无所约束的自我实现将为经济、科学和社会的机器上油。⁶
事实上,运动根本不是这样进行的。我们能怎么跑,取决于我们脚上穿着什么鞋。资金不足、公交晚点、安全检查和非正式的隔离线阻碍着我们的旅行;而铁轨和固定的航班时刻表虽然加速了旅行,却也规定了其路线。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想走,只有当家园被炸毁时才离开城镇。这些形形色色的“摩擦”扭转着运动,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当运动被社会性地塑造时,强制与挫败感便与自由相伴而行。
谈论摩擦,是在提醒我们互动在定义运动、文化形态和能动性方面的重要性。摩擦并不仅仅是让事物减速。全球权力要保持运转,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一则广告语所言)“轮胎与路面接触的地方”。道路是概念化摩擦如何运作的绝佳意象:道路创造了使运动更容易、更高效的路径,但在此过程中也限制了我们能去往何方。它们所提供的便利交通,同时也是一种限制的结构。摩擦扭转着历史的轨迹,既促成、也排斥,并赋予其特殊性。
跨越差异的相遇,其效果可能是妥协退让,也可能是赋权增能。摩擦并非抵抗的同义词。霸权在摩擦中得以建立,也在摩擦中被消解。想想橡胶。从美洲原住民那里被强取,被农民和种植园主偷走并种遍世界,被化学家模仿和取代,在有或没有工会的情况下被制成轮胎,并最终为最新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热潮而营销。⁷ 工业橡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欧洲征服的野蛮、殖民植物学的竞争热情、农民的抵抗策略、战争与技术科学的混杂、围绕工业目标与等级的斗争,以及更多从工业进步的目的论中无法看出的东西。我称之为摩擦的,正是这些兴衰沉浮。摩擦使全球联结变得强大而有效。与此同时,摩擦也毫不费力地阻碍着全球权力的顺畅运作。差异可以造成扰乱,引发日常的失灵和意想不到的灾难。摩擦戳破了全球权力如同一台润滑良好的机器般运转的谎言。此外,差异有时会激起反抗。摩擦可以是那只钻进大象鼻子里的苍蝇。
对摩擦的关注,为我们开启了对全球互联进行民族志叙述的可能性。关于全球的抽象宣称,可以在其于世界中运作时被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追问普世性,不把它当作真理或谎言,而看作是黏着的纠缠。
介入普世性
在追溯全球联结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走得很远而不遭遇关于普世性的种种主张。普世性是当代人文主义事业的核心:科学家、经济改革者和社会正义倡导者都诉诸于普世性。然而,普世性若按其表面价值来看,却抹杀了全球联结的建构过程。这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普世性预设了一个早已统一、无需再做联结工作的世界,那它又如何能如此有效地锻造全球联结呢?
学者们对此问题着墨不多,因为“普世性”这个理念暗示着抽象,使他们偏离了对普世性主张在实践中成败的关注。无论是那些将自己的思想置于普世性之内的人,还是那些因其虚假而加以否定的人,都没有停下来思考普世性在实践层面是如何运作的。要超越这一点,重要的是将朝向普世性的普遍化视为一种向往,一种永远未竟的成就,而非对一条既定法则的确认。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注意到,普世性的向往必须穿越距离与差异,而我们可以将这种穿越本身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
民族志学者理应尊重他们的研究对象。然而,文化人类学家对普世性一直怀有一种乖戾的怀疑。在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的加持下,人类学家认为,普世性是民间信仰,就像神或鬼一样,只在其赋予其生命的文化体系内才有效力。我正是在这种信条下被培养成一名学者的,我花了很长时间——以及大量与非人类学家之间令人沮丧的交流——才决定,这并非一个进入对话的好起点。普世性的确是“地方性知识”,因为若不借助特定的历史文化假设,就无法理解它。但止步于此,对话便无从谈起。而且,这也错失了要点。转向普世性,就是要识别那种能够移动的——既是流动的又是动员性的——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知识。无论被视为深植于文化差异之下,还是超越文化差异,普世性的使命都是搭建桥梁、道路和流通的渠道。从特定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渗透进这些渠道,拓宽而非中断它们。我们必须走出地方性的边界,去追问“普世”究竟意指为何。⁸
一个起点是考察普世性的成就。以环境政治为例。在1980和1990年代,环保主义者开创了跨界方法,让人们认识到那些无法被局限于单个国家的问题——污染、气候变化、物种丧失。跨国科学家团体,怀着对环境知识客体的共同普世主义信念,有时——在打破了诸多先例之后——能够克服国家政治的阻碍,共同合作并锻造出共同的标准。事实证明,最成功的跨国动员,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有界限的,例如研究跨界酸雨的科学家与政治家合作以巩固欧盟(Rotmans 1995a)。⁹ 它们也与特定的历史时刻相关,并因此富有成效,例如东欧和前苏联的环保主义在1980年代末致力于普及对国家的反对(Jancar-Webster 1993)。环境政治的普世主义,清晰地表达了人们对不受国家管制的知识以及与西欧文化遗产联结的普遍渴望。自由与科学相互增强了彼此的普世性主张。苏联解体后,随着公民身份政治而非普世主义政治占据主导,环境政治几乎销声匿迹。
1980年代末,正在解体中的苏联的环境政治在国外被解读为反共鼓动。这种联想为印尼的环保主义者铺平了道路,他们必须在一个暴力反共的国家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当共产主义的指控阻碍了其他社会运动时,环保主义者却能够诉诸科学与现代性的普世理想。如同在社会主义欧洲一样,普世性通过构建一个比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更宏大的参照框架,为改革乃至社会批判开启了可能性。¹⁰ 但是,也如同在欧洲一样,这种诉诸科学与政治的组合,在威权国家的阴影下效果最好。当政权倒台,政治便朝着多个新的方向分化发展。
因此,那些动员人们的普世性,并不能实现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通行的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和无关紧要的。处理此问题的批判性环境学者常常直接将我们引向地方,支持将地方或原住民知识作为普世主义专业知识的对应物。这种反应虽然引人关注文化特殊性,却再次错失了要点。能够在改变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知识,是那种能够旅行和动员的知识,它在行进的道路上改变并创造出新的历史力量和行动者。然而,那些声称掌握了普世性的人,却出了名地拙于看到其知识的局限与排斥。这正是我挑战的切入点。
普世性在赋予其内容和力量的特定历史情境中才有效。我们可以通过谈论“介入”(engagement)来具体说明普世性在实践中的这种情境性特征。介入性的普世性穿越差异,并在其旅程中被赋予能量、得以改变。通过摩擦,普世性变得在实践上有效。然而,它们永远无法兑现其普世的承诺。即使在超越地方性时,它们也并未占领整个世界。它们受到动员追随者这一实践必要性的限制。介入性的普世性必须说服我们去关注它们。当被视为在异质世界中完成的实践项目时,所有的普世性都是介入性的。
要研究“介入”,就需要从形式化的抽象转向,去观察普世性是如何被使用的。¹¹ 普世主义在政治上并非中立。它们曾深度卷入欧洲殖民权力的建立过程。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下,普世主义是支撑一种对理性之旅行力量的信念的框架:唯有理性才能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知识与习俗的碎片,以实现进步、科学和善治。在殖民主义的母体中,普世理性成为在时间上充满活力、在空间上不断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形式的标志。当然,普世理性最好是由殖民者来阐述。相比之下,被殖民者则被以特殊主义的文化为特征;在这里,“特殊”即是无法成长之物。然而,普世性则为不断完善的真理,甚至在其功利主义的形式下,为全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这些对比至今仍在塑造着全球的不对称性。
与此同时,这段历史并不能涵盖我们时代所有形形色色的普世性主张。现实存在的普世主义是杂糅的、短暂的,并通过对话不断地被重塑。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与科学、世界性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内的解放哲学的普世性相互混合、交融。此外,对普世性的拥抱并不仅限于地球上的某一小块区域。“西方”无法对普世性学说提出排他性的主张。欧洲殖民地的激进思想家们很久以前就拓展了启蒙运动的普世性,主张被殖民者应该获得自由,从而将普世自由的学说确立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基础。¹² 权利与理性的普世主义持续启发着批判性的后殖民理论。与此同时,那些为强迫他者遵循国际强制的进步与秩序标准进行辩护的普世性主张,也正处于新殖民规训计划的中心——正如它们曾为殖民主义服务一样。¹³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讽刺:普世主义既卷入了控制世界的帝国图谋,也卷入了争取正义与赋权的解放动员。普世主义激发着扩张——无论是对强者还是弱者。的确,当那些被排除在普世权利之外的人们抗议其被排斥的处境时,这种抗议本身具有双重效应:它扩展了他们所抗议的权力形式的触及范围,即便它也为他们的愤怒与希望发出了声音。政治理论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将“正常化”与“起义”称为同样受到普世性启发的两种力量(2002)。这种二元性将我们带回到普世性易于旅行的特性上。普世性向精英与被排斥者同样发出召唤。¹⁴
“摩擦”的概念承认这种二元性,并将其置于我们理解“现代”全球互联的核心,即那些在启蒙普世主义庇护下发展起来的互联。“摩擦”为普世性提供了着力点,使普世性得以作为权力实践的框架而传播。但正是因为这同样的摩擦,介入性的普世性永远无法完全成功地在任何地方都保持一致。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些普世性如何通过摩擦,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作的故事。
本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都对应一个普世主义的梦想:繁荣、知识和自由。然而,这些标签不应误导读者,以为本书讲述的是哲学或政策的故事。恰恰相反,我的叙述直接深入历史经验的领域。什么是繁荣?在1990年代的印尼加里曼丹,繁荣撕裂了森林地景,剥夺了其人类居民的家园,只为少数特权者或投机者提供快钱。本书的第一部分探究的正是,对繁荣与进步的向往究竟是如何造成这种局面的。在这片历史地景中,成为一个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在进入这个充满抢劫、暴力和混乱的地带时,市场理性的普世性几乎算不上什么庇护性的指南。摩擦无处不在。
什么是知识?如果理性的审议总能汇聚成共同的理解,那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容易得多。但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相信某些知识主张优于其他的人,也很难否认,即便是最好的主张也保留着某种不可通约性。这是因为知识主张是在与具体问题和对话可能性的关系中浮现的——这正是摩擦的生产性特征。本书的第二部分思考摩擦如何改变关于全球的知识和在全球旅行的知识。
那么自由呢?纵观其历史,自由拒绝固守于可预测的原则;它开花结果,结出了无数前所未见的果实。即便在启蒙时代,财产权的自由无法与被剥夺者的解放相协调这一事实,也让倡导者们忙于设计各种相互矛盾的方案。二十世纪末的环境政治受到了许多不同自由含义的启发——而它们之所以作为自由的形式吸引我,恰恰因为它们并非人们一想到自由就会联想到的最纯粹形式。在这里,权利话语被扩展到其人本主义的界限之外。其他物种——或许甚至地景和生态系统——难道不该拥有超越并先于人类社会习俗的权利吗?现代性的管辖权被彻底颠覆:原住民文化之所以值得拥有启蒙运动的权利与自由,恰恰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设法在没有这些的情况下生活。正是在这些纷杂而乌托邦式的事业中,自由的概念被注入活力,并为我们的时代赋予了价值。我的第三部分思考自由的意义与谱系的积累,正是这种积累将森林保护置于为创造一个宜居世界而奋斗的诸项事业的前沿。
这些关切将我带回到我在本引言开头提出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为何如此混乱?谁为自然代言?在二十一世纪,何种社会正义才有意义?
超越全球化
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积聚力量的反企业全球化抗议活动,其伟大的洞见在于:当前资本主义扩张的形式并非不可避免。尽管公共演说一再安抚,但资本主义的传播一直是暴力、混乱和分裂的,而非平顺地包罗万象。观察家们嘲笑抗议者不懂全球一体化的力量,甚至嘲笑他们看不到自身的“全球化”。然而,事实证明,抗议者比那些深陷于展示一个金钱、人员和文化无处不流动的、一体化全球主义之程序性进展的资深社会理论家们,更具洞察力。
为了把握过去十年全球变化的巨大规模,社会理论家们描绘了一幅行星尺度上的演化变迁图景。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和西式自由民主传播的乐观通俗叙述尤其具有影响力(例如,福山 1992;弗里德曼 2000)。然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学者,都将全球化描绘为向一个全球时代的普世性迈进。¹⁵ 他们的故事共同执着于一个协调一致的世界转型,它从全球中心兴起,并通过技术的助力消弭距离,延展至整个地球。
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随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的再军事化之后,那个关于向全球一体化进行不可避免的和平过渡的故事,越来越像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梦呓。这并非因为全球联结的力量消失了——而是它看起来不再那么整洁。十年前,社会分析家们对新生的全球流动的规模和力量印象深刻,因此他们聚焦于全球的连贯性,无论其好坏。而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转向不连续性和笨拙的联结了,因为这已被证明是新生恐惧与希望之源的关键。
关于资本主义
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建立改变了资本主义,这些规则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资本在全球飞速流转。自由贸易区和新的通讯技术鼓励公司将其业务扩展到成本愈发低廉的地区。跨国专业分工——如货币交易员、能源交易员——蓬勃发展。私有化倡议和自由贸易法规瓦解了国家经济,使曾经的公共资源可供私人占有。
社会分析家们对这一工程的规模感到敬畏。或许最重要的回应是那些提醒读者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化的社会体系,而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堆积。这样的回应必然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连贯性。它们揭示的不仅是过度腐败的危险,更是剥削基本原则的危险。正是这种回归基本,使分析家们聚焦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新组合的全球性复制。然而现在,这样的简化似乎已不敷使用。区域历史的独特性以及持续存在的暴力和种族分层问题已变得紧迫。战争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文化的谱系似乎再也不是经济变化的附带现象了。
二十世纪末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都聚焦于那些被想象为处于一个单一资本主义演化前沿的形态——如后现代主义。¹⁶ 然而,一旦我们放弃这种演化观,我们就可以关注那些其故事从官方进步阶梯上“跌落”的人们的经验(Tadiar 即将出版)。新的联结与霸权工程正在这里涌现。例如,我们在农村地区的重要性中看到了这一点——农村在演化文化理论(文化演化论)中被完全忽略,却在关键的资本主义重组和反全球化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里正是摩擦的领域:意想不到的联盟出现,重塑着全球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假定自己甚至在它到来之前就确切地知道全球资本主义是什么,而需要去发现它在摩擦中如何运作。第一章和第二章发展了这一思想。我没有急于奔向全球空间压缩的结论,而是审视了异质的空间与尺度塑造工程之间的联结,因为这些联结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扩散,又使其卷入混乱的时刻。在追溯企业家精神运作所依赖的联结时,相遇的文化工作作为一种塑造性力量浮现出来。
关于作为知识的自然
二十世纪末对全球一体化的兴奋,为那些希望利用科学知识的进步来推动全球进步的人们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一点在环境保护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环保主义者一直热切地推动全球知识与共识,希望能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濒危的物种和环境。
然而,环保主义者的努力受到了其他形式的全球流通知识兴起的阻碍。跨国的政治和信息网络使得对环保项目的公众批评得以广泛传播。即使是环保活动家,也未必认同既有的保护科学的真理。与此同时,公关公司通过传播“另类”科学以及刻意的虚假信息,使得对抗环保运动成为可能。结果,政治领袖和法院,以及普通公民,都被相互竞争的环境观点所淹没。这些批评的每一个来源都迫使环保主义者回想起,全球知识既非铁板一块,也非一成不变。¹⁷
许多评论者从这一观察出发,转向了所谓的“科学战争”,即关于科学是一种特权形式的真理还是一种政治强加的辩论。¹⁸ 然而,探索知识究竟是如何移动的,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为此,了解知识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协作过程至关重要。环境保护激发了科学家、商界、森林居民、国家监管者、公众和非人类之间的协作。通过这类协作的摩擦,全球环保项目——如同其他形式的旅行知识一样——获得了它们的形态。¹⁹
协作并非简单的信息共享。没有理由假定协作者拥有共同的目标。在跨国协作中,重叠但有差异的世界主义形式可能会影响贡献者,使他们能够对话——但却是跨越差异的对话。
对协作的关注将讨论推向了超越对立利益集团(例如,南方与北方;富人与穷人)之间永恒僵局的境地,但并非因为它假定妥协总是唾手可得。协作创造了新的利益和身份,但并非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将全球知识标准化的过程中,不兼容的真理被压制了。全球流通的知识在通过相遇的摩擦而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鸿沟。
借鉴科学研究和环境史的洞见,第三、四、五章发展了这些思想。在这里,我更深入地探讨了协作与朝向普世性的普遍化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正义
全球性思考的可能性激发了各种社会运动去构想全球性的事业。然而,全球政治也创造了特殊的问题。社会正义的目标不仅必须跨越阶级、种族、性别、国籍、文化和宗教进行协商,还必须在“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以及在世界特大城市与其乡村和边远腹地之间进行协商。联盟政治至关重要。然而,在联盟中工作意味着什么?二十世纪基于阶级的团结模式要求联盟盟友像平行的对等体一样排列整齐。但盟友们很少能如此整齐地站队。他们即便无意破坏队形,也会朝新的方向推进。他们的摩擦改变了每个人的轨迹。
此外,没有国家的统一框架,跨国盟友有什么共同的政治可言?后冷战时期的社会正义运动倾向于通过援引启蒙运动的普世语言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语言将正义与自由并置。人权、女性主义和环保事业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使用了普世权利的语言。无论活动家们在建立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联盟方面做出何种尝试,都必须在对普世权利的这一承诺内进行。
然而,这种语言是否提供了其自身的政治条件,从而使有意义的联盟变得无效?教授一种普世权利的语言可能会堵塞其他轨迹。参与者可能会被卷入一个全球观察和分类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里,文化差异变成了又一块行政数据的砖头,人们被其围困。自由主义框架在全球社会正义政治中的重要性,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活动家们如何利用全球流通的政治修辞来设计和管理联盟?分类的逻辑如何在使联盟伙伴能够合作的同时,又整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跨越差异的相遇又如何超越其被规训的边界,从而使新的政治形式成为可能?
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摩擦中的政治”的这些特征。
本不该如此
一小段历史为“摩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也为接下来的章节铺设了舞台。尽管资源开采的故事在事后看来似乎不可避免,但必须指出的是,直到1970年代,印尼的热带雨林才被作为工业木材来采伐。印尼群岛地处印度洋和中国南海悠久商业历史的交汇处,绝非世界贸易的新手。数百年来,来自印尼雨林的产品已遍布世界。然而,正是那种使这些森林成为丰富商品来源的生物生产力,也阻碍了它们被用作工业木材。大规模伐木者偏爱单一有价物种占主导的森林;而热带雨林在生物学上实在太过多样。虽然殖民时期的伐木者珍视爪哇岛的亚热带柚木林,但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加里曼丹、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巴布亚等岛屿上更湿润、更异质的热带雨林。²⁰
这一切在1970年代初突然改变,当时日本的综合商社(即“sogo shosha”)与苏哈托总统的“新秩序”政权搭上了线。这个政权是在一场大屠杀的血泊中上台的,并承诺通过外国投资和贷款的魔力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²¹ 政府全力投入伐木业;外国投资随之如潮水般涌入。²² 国家建构很快便与伐木业纠缠在一起,因为特许权被分配给政治附庸,而他们则向政权青睐的发展项目提供“自愿”捐款。²³ 旨在控制贸易而非生产的综合商社,提供了贷款并安排了贸易协定。他们渴求大量廉价生产的原木,而非质量控制,因此对生态上的短视安之若素。1971年,他们将所有非机械化(且对生态危害较小)采伐生产的原木从日本贸易中剔除,从而巩固了新的伐木体制。到1973年,印尼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木材出口国(Ascher 1998)。
关于跨国公司和腐败政客的灾难性项目的故事已变得司空见惯,这次相遇或许也只是全球链条上一个普通的环节。然而,我的重点在于,这个环节的具体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实践、自然资源管理和阶级形成的新轨迹,正是从这些具体特征中凝结而成。这些轨迹的三个特征与我的故事尤其相关。首先,在日本贸易公司和印尼政治家的相遇中,雨林的重要性被放大、被简化,并被误塑为一种可持续资源。森林简化成为资源管理乃至更广泛的商业组织的典范。后来,工业林场被种植起来,取代了天然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巴西的养牛牧场,那是一种同样糟糕但截然不同的“生产性森林转化”的比喻。)其次,采纳贸易公司那种囤积和市场控制的模式,迎合了那种公共与私人界限变得无可救药地混淆的国家建构形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私有化模式是持续地将公共产品转化为私人物品。)第三,合法与非法企业家在不同尺度上的合谋,取代了原住民的权利,并助长了区域性的繁荣-萧条经济。我将简要阐述。
日本贸易公司与印尼政治家的联结,创造了一种看待森林的新方式。伐木者看到的不再是生物多样性,而只有一个树种科——龙脑香科(dipterocarps)。龙脑香是出众的巨木,从较低的林冠层中拔地而起,高耸于森林之上。但龙脑香的物种是多样的,且个体生长在许多其他科属物种之中;并不存在纯林。只有在日本-印尼联结的特殊情境下,伐木者才得以将雨林想象成仿佛是纯林。²⁴ 龙脑香——被改造为供日本建筑业使用的一次性胶合板——看起来都一样,而其余的树木、草本、真菌和动物群则成了废品。这种变化也在概念上清空了森林里的人类居民,因为森林居民的果园、藤条和其他人工照管的植物,如今都成了纯粹的废品。伐木公司可以自由地采伐这些新近“无人居住”的森林景观。
1980年代,印尼商人开始反对利润出口到日本,但他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模仿综合商社。印尼禁止了原木出口,并建立了自己的胶合板产业。²⁵ 在总统的密友穆罕默德·“鲍勃”·哈桑(Mohamad “Bob” Hasan)的领导下,印尼木材板业协会(APKINDO)成立,作为一个控制胶合板出口的国家级营销机构。APKINDO有意识地采纳了日本的贸易模式:强制推行特定的贸易链;接管所有中间商功能;控制产量、价格和低成本融资;并利用政府支持来维持主导地位。所有胶合板公司都必须参与。凭借这种控制地位,APKINDO用低成本的胶合板充斥了世界市场。²⁶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打入了日本市场,尽管有保护性关税,其售价仍低于日本制造商。“我们是东南亚唯一敢和综合商社斗的人。”哈桑吹嘘道。²⁷
“新秩序”倒台后,APKINDO成了腐败的象征:哈桑利用他的关系迫使整个行业屈服,并在此过程中大发横财。²⁸ 但在“新秩序”时期,他的成功构成了建设国家的典范。其他产品也被组织成类似的卡特尔和垄断组织。1998年,在他担任财政和贸易部长的短暂辉煌时刻,哈桑解释了这种以商业为导向的爱国主义:“垄断没问题。只要垄断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就没问题。”²⁹
随着国家认同与森林破坏纠缠在一起,伐木特许权成了与政权有关系的明确标志。³⁰ 国家越来越依赖从这类恩惠中获得的预算外资金。森林的退化变得更加严重。日本贸易公司与印尼政治家的相遇是卓有成效的。综合商社的模式依然盛行,尽管印尼的裙带亲信取代了日本人。而将森林简化为无人居住的龙脑香林——那次相遇的产物——则构成了一种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后“新秩序”时代的印尼人所称的“KKN”,即腐败、勾结和裙带关系(korupsi, kolusi, nepotisme)。
到了1990年代,KKN已自上而下地分布。随着国家话语从社群发展转向私人企业家精神,小商人、村长、有抱负的青年、移民、小偷、警察和地痞流氓都卷入了将公共资源转为私利的活动中。当资源开采许可证无法通过国家渠道获得时,它们就在地方上被伪造或搞定;非法伐木和采矿成了合法开采的系统性附属品。非法开采以合法开采的缩小版形式进行。在伐木业,地方官员与私人经营者达成协议,为他们的项目获取预算外资金。村长有时也被拉入这些安排中,用准许采伐村庄森林的许可来换取他们自己的预算外资金。³¹ 1998年“新秩序”的倒台并未改善情况。2000年自然资源许可证的权力下放,扩大了腐败的可能性。³² 非法资源开采急剧失控。
非法与合法企业之间的联系一直很紧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协作破坏了原有的财产权和使用惯例,使一切都变得可以自由攫取。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单独一方都可能受到挑战,但它们联手则压倒了当地居民,后者通常无法在这种合法与非法、大与小的组合面前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资源。它们共同将乡村变成了一个人人皆可争抢的边疆。
我刚才回顾的同一时期,也见证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全国性环保运动的兴起。³³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一个政府严厉镇压的时期,环保主义基本上是唯一在印尼各地蓬勃发展的多元化社会正义运动。³⁴ 因此,它吸引了各种社会改革者,并成为许多(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希望的载体。这场运动是各种奇特部分的混合体:工程师、自然爱好者、改革者、技术官僚。现代化专家和浪漫的民粹主义者在此并肩而行。社会正义倡导者与富有同情心的政权官僚共同制定计划。在那些年压抑的政治气候下,即使是最勇敢的活动家也对自己的言行保持谨慎。尽管如此,关于自由的问题仍在涌现,活动家们用人权、农民权利和原住民权利的理念来反对中央集权式发展的霸权。³⁵ 1990年代中期,国家警惕的放松使得其他事业得以走上公共舞台,包括民主、劳工、学生运动、言论自由。然而,通过那些导致苏哈托于1998年辞职的决定性动员,环保主义在表达对国家的不满——尤其是在农村问题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³⁶
在1980和1990年代,这场运动是在民族主义倡导的框架内,围绕着差异组织起来的。运动没有建立一个单一的中央决策委员会,而是致力于在按地点、议题或运动组织起来的小团体之间进行协商。在这大部分时间里,运动将自身想象为协调那些已经存在但分散无序的农村怨言。活动家们想象自己的工作,是把底层民众的要求翻译成当权者的语言,包括英语。他们自告奋勇去记录不公,会见部长,并提起法庭诉讼。同样重要的议程是反向翻译,通过赤脚法律诊所、会议或国际协议的地方语言版本,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在他们的公开表述中,活动家们或许低估了翻译工作的复杂性,但他们的实践却一头扎了进去。(女性在领导职位上的突出地位,有人向我解释是与女性的语言能力有关。³⁷)特别是农村的运动,要求跨越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多重生活经验维度的差异。
在这些被笨拙地跨越的差异所构成的联结中,环保运动试图为森林破坏和原住民权利的侵蚀提供一种替代方案。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探讨这一主题。为了抵达那里,我首先在第一部分探讨那些使森林砍伐成为一种破坏性“常规”的社会联结和文化实践。然后,我转向跨国、国家和区域层面关于森林的知识形态之间更广泛的互动。当我描述环保运动时,我将其置于与它的两个持久对话者——学生自然爱好者和村庄领袖——的关系中。我将展示环保运动如何在发展自己独特视角的同时,逐渐依赖与这些群体的联结。在最后一章,我将考察一个案例,其中这三个群体跨越他们的差异,共同收回了“社区森林”。
他们的协作——就像合法与非法商人之间的协作一样——重新安排了财产权。正如日本贸易公司与印尼政治家的相遇生产出简化的龙脑香林一样,这些由活动家启发的相遇,或许终将生产出新型的森林。这个主题——摩擦的可能性——将在接下来的所有章节中得到探索和延伸。
注释
1. 我尤其想到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 1999)、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2000)、谢永平(Pheng Cheah, 2003)和V. Y. 穆丁贝(V. Y. Mudimbe, 1988)。
2. 斯皮瓦克在几处思考启蒙运动项目的论述中使用了这个双重否定。例如,见Najmabadi (1991)。
3. 最近发现,过去二十五年里加里曼丹的森林砍伐率远高于以往任何想象。Curran等人(2004)记录了官方指定的“保护区”内森林砍伐日益加剧的情况。他们指出,在1985至2001年间,加里曼丹受保护的低地森林减少了超过56%。
4. “对于辩证法而言,普世性是一种概念建构,它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经验上的体现或实现:它的所有特殊性也都是具体的、历史独特的,普世性在分析中的功能并非要将它们全部化约为同一性,而是要让每一个都能在其历史差异中被感知”(Jameson 2002: 182–83)。
5. 在原住民权利领域,人们可以将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 2002)的著作与金伯利·克里森(Kimberly Christen, 2004)的著作进行对比,前者强调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规训,后者则主张为批判性表达开辟新的空间。在女性主义方面,可以将旨在改革国际发展的Bhavani, Foran, and Kurian (2003)与揭示非政府组织政治之形式主义束缚的Riles (2000)进行对比。关于环保主义的更多内容,见第六章和第七章。
6. 莱斯利·费尔德曼(Leslie Feldman, 2001)指出,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如何帮助激发了将自由视为运动的自由主义观念。霍布斯将其思想想象为伽利略物理运动定律的社会应用,而伽利略的定律有意识地忽略了摩擦。在许多社会理论中,对摩擦的忽略至今仍然存在。
7. 关于橡胶贸易中的摩擦,已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萨满、殖民主义与野人》(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1987)和露西尔·布罗克韦(Lucile Brockway)的《科学与殖民扩张》(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2002)是绝佳的入门读物。
8. 思考普世性涉及形式抽象的技巧。人们必须学会从一个实例推广到另一个实例,在表面的差异中看到一个潜在的或涌现的共性原则。这个原则必须将两个实例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联系到一个至少在潜力上可以涵盖所有其他实例的、彻底开放的领域。正是这些普遍化和抽象化的习惯,使得普世真理的拥护者对那些批评普世性未考虑世界异质性的意见不感兴趣。特殊性的存在并不妨碍普世性。普世主义的要点就是从特殊实例走向更普遍的法则。抽象的普世性总是开放的;新的发现、原则和拥护者都受到欢迎。普世性的运作机制在第三章有进一步讨论。
9. Soroos (1997: 110–46)回顾了1980和1990年代各国在制定污染公约时的立场。Vogel (1993)提供了欧洲共同体环境政策的背景。
10. 在这一时期,跨国权利话语对印尼活动家来说似乎是必要的,用以驳斥威权国家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主张(Tsing 1997)。
11. 如果不关注其具体的提议和承诺,我们就无法评估一个关于普世性的命题。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重演普世性》(“Restaging the Universal”, 2000)中以哲学上的清晰度讨论了这一点。我的分析得益于她的讨论。
12. 杜波依斯(Dubois, 1997)描述了法属加勒比地区起义奴隶对普世主义的运用。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在发展普世权利观念方面紧密相连。(沿着这个思路,巴克-莫斯 [Buck-Morss, 2000] 认为,黑格尔的普世历史理想是在与海地革命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启蒙理想和普世真理也是亚洲反殖民主义传播的关键。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1991)以文学形式描述了启蒙理想对殖民时期爪哇新兴民族主义的启发。普世主义既激发了民族承诺,也激发了跨国承诺。杜赞奇(Duara, 2001)追溯了二十世纪初泛亚主义话语中,欧洲与北亚关于普世真理和文明的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13. 我在开头提到的作者——斯皮瓦克(1999)、查克拉巴蒂(2000)、谢永平(2003)、穆丁贝(1988)——都以不同方式讨论了这些问题。
14. 普世主义诉求的广泛性激发了政治哲学家们,就普世性与民主、世界主义和社会变革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的前沿,一些理论家提供了思考介入性普世性之实践困境的工具。朱迪斯·巴特勒评论说,即使是最进步的普世主义,其排斥性也源于“普世性言说的文化位置”(2000: 37)。她沿着这个语言学隐喻,主张翻译的重要性,认为翻译是被排斥群体为争取被纳入普世主义无标记主体所享有的特权而斗争的过程。由于语言的特殊性,翻译总是既是再现又是误现。巴特勒认为,所有普世主义都是在翻译的历史中形成的。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 2000)指出历史偶然性在将特殊诉求转变为普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拉克劳认为,一个阶级部分要进入政治进程,就必须将其目标呈现为实现社群的普世目标。正是这个过程的偶然性,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关键。
15. 关于全球化的左翼理论,例如,见哈特和奈格里(2000)、詹明信和三好将夫(1998)、萨森(1998)、阿帕杜莱(1996)、汉纳兹(1996)。
16. 见詹明信(1991);哈维(1989)。
17. Dowie (1996) 讨论了1990年代美国环保立场的混乱。Hager and Burton (1999) 描述了一场澳大利亚的反环保公关运动及其瓦解过程。
18. 关于环保主义的反科学研究论战,见Soule (1995)。
19. 科学研究学者在描述人与非人之间的协作方面尤其富有创新。例如,见哈拉维(2003);拉图尔(1996)。
20. 南希·佩卢索(Nancy Peluso, 1992)描述了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爪哇岛的柚木开采。
21. 多弗涅(Dauvergne, 1997; 2001)和罗斯(Ross, 2001)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我的叙述借鉴了他们的论述。
22. 来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投资者很活跃,那里的木材采伐已经适应了日本的需求。香港、美国、日本和韩国也在木材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23. 在木材热潮的最初阶段,军官和基金会占了很大份额。军方与外国公司和华裔印尼公司达成协议进行伐木,而军方提供特许权。在这方面,苏哈托总统延续了他通过让军方控制印尼石油来间接资助军队的做法。在后期,外国公司被挤出木材行业。特许权持有者的预算外捐款使得政权能够平衡和安抚不同的军方和文职精英(Ascher 1998; McCulloch 2000)。
24. 其他东南亚森林也参与了这一转变。综合商社最初接触菲律宾寻求龙脑香。当菲律宾森林枯竭后,贸易商转向沙巴、沙捞越的森林,然后才到印尼。这些在生物学上有些相似的森林的区域性广度,使得日本贸易商的野心得以增长。不可持续的采伐没关系,因为还有其他森林在等着。环境学者彼得·多弗涅(Peter Dauvergne, 1997)将日本贸易公司描述为在东南亚投下长长的“生态阴影”,因为它们在该地区穿梭,先后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摧毁森林。
25. 超过100家伐木公司破产,许多外国和军方投资者抛售了他们的股份(Ross 2001: 182–83;亦见Brown [1999],他认为军方投资仍然很重要)。新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到1985年,印尼有101家胶合板生产公司——而1978年只有19家——该行业的年产量为650万立方米。(1978年,产量仅为80万立方米。)到1990年,产量为1260万立方米(Barr 1998: 9)。1992年,禁令被出口税取代(Ascher 1998: 50)。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迫使“新秩序”政权取消了禁令(Barr 1998: 35)。
26. Barr (1998) 的描述非常详尽。他的分析指导了我的分析。
27. 引自Dauvergne (1997: 91)。
28. Barr (1998) 报告了哈桑的许多越轨行为。2000年,哈桑因腐败被调查,并于2001年入狱。关于哈桑兴衰的各种资料收录于Gallon (2001)。
29. 引自Barr (1998: 1)。
30. 1980年代,印尼大部分森林落入华裔印尼伐木公司之手(Ross 2001: 183–85)。事实上,哈桑开创了政权官员与华裔商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成为“新秩序”经济的标志。哈桑是苏哈托的商业伙伴,早在他们共同利用走私来资助一个军师的时代就开始了(Barr 1998: 2–4)。当苏哈托于1967年成为总统时,他的政权将这种关系作为一种模式。华裔印尼企业家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一个方便且可控的国内替代品。他们被剥夺了正式公民的特权,便提供资金和商业经验,以换取赚取巨额财富的权利——其中一些财富又回流到他们的政治靠山手中。与此同时,军方在推动合法和非法资源开采方面也保持着重要存在(McCulloch 2000)。
31. 关于非法伐木的描述见McCarthy (2000) 和Obidzinski (2003)。
32. 关于权力下放的规定繁多且相互矛盾。Colchester等人(2003: 249–51)回顾了相关法案,结论是“权力下放带来的困惑多于清晰,并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的‘拔河’”(2003: 251)。
33. 印尼的环保工作涉及政府官僚、外国组织和本国环保主义者。这三者的议程非常不同。在本书中,我只讨论这三者中的最后一个。Barber (1989) 对“新秩序”时期的国家林业做了很好的介绍。Lowe (1999) 对外国环保项目提供了基于民族志的批判。Stone and D’Andrea (2001) 讨论了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是一个在印尼有强大国内基础的跨国组织。“新秩序”时期,全国环保运动主要围绕总部设在雅加达的伞状机构组织起来。“印尼环境论坛”(WALHI)至今仍在协调数十个区域性和议题导向的团体,并在国内外论坛上为国家事业发声。1980年代,“印尼非政府组织热带雨林保护网络”(SKEPHI)也是一个全国性的伞状组织;1990年代它变成了一个议题团体。
34. 在此期间,反政府情绪也通过伊斯兰教表达出来。关于印尼全国性伊斯兰政治的兴起,见Hefner (2000)。
35. 普世自由权利的概念词汇之所以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其全球流通,也因为印尼的政治历史。“新秩序”是通过消灭印尼共产党上台的。在“新秩序”时期,共产主义的修辞工具会吓跑大多数公众。然而,“新秩序”一倒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充满了书店,并像被禁的糖果一样被抢购一空。
36. 我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印尼的环保运动。亦见Mayer (1996); Gordon (1998); Eldridge (1989); Belcher (1993); Aditjondro (1991a)。关于议题和运动的大量文献可从环保运动的资料中获得,包括英国的期刊《Down to Earth》和印尼环境论坛的英文刊物《Environesia》以及印尼语的《Tanah Air》。互联网邮件列表,如“WALHI updates”([email protected]...),提供了进一步的文献资料。
37. 语言能力并未被描述为一种天生的女性特质,而是女性在大学里倾向于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结果,与此相反,大学男性则主修技术领域。对于1980和1990年代那些面向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