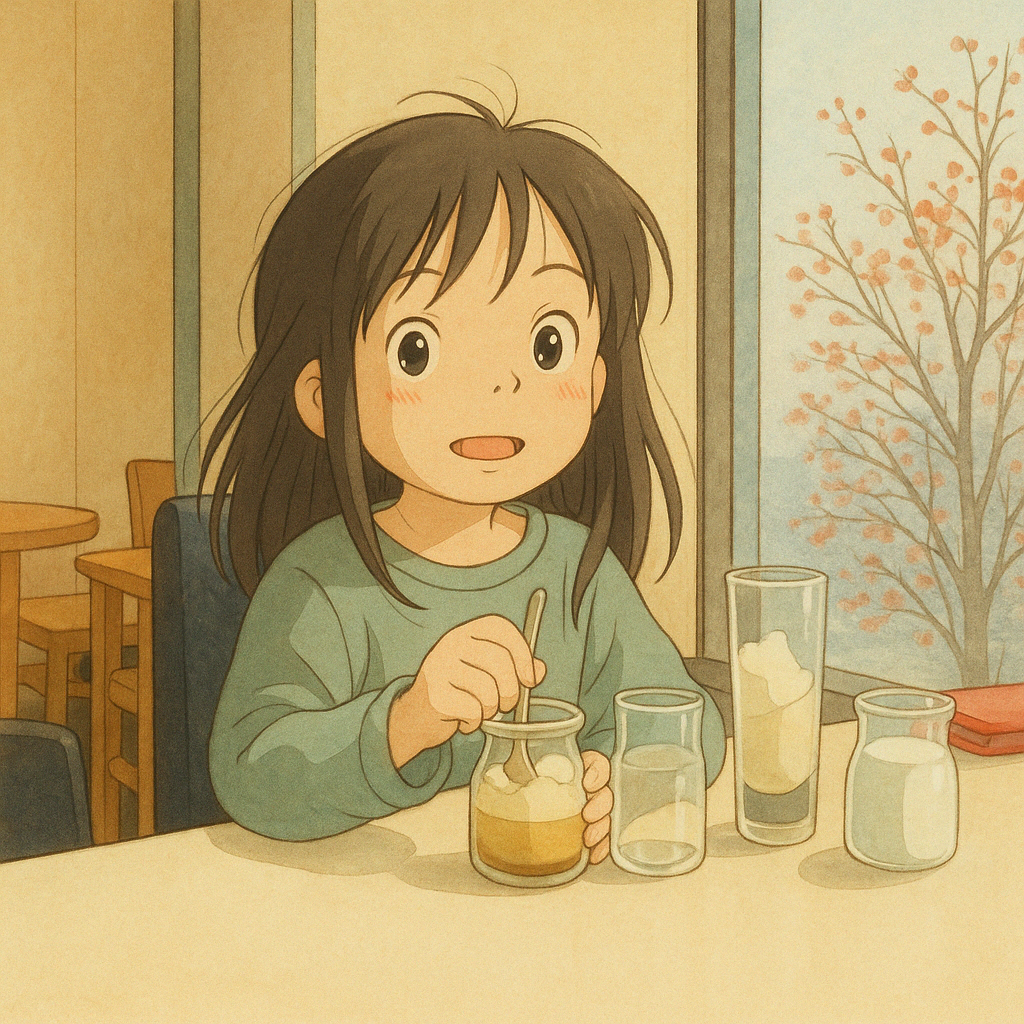救赎的幻觉:从排华法案到以色列建国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那是一部看似普通的移民法,却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一个族群不再被欢迎。那一年,旧金山的华工被要求离开,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修过铁路,开过洗衣铺,在加州淘金热时为当地经济贡献过青春。现在,他们必须重新上船,用一张写着“回国许可”的纸,证明自己曾经属于这里。
值得玩味的是,这一法案的颁布距离南北战争结束仅仅17年——那场战争刚刚以废除奴隶制的名义,为“平等”与“自由”确立了新的国家信条。但现实却为当初的理想主义抹上了讽刺的一笔。经济萧条、劳工失业、社会焦虑,让“外来者”成了最方便的解释对象。于是,一个刚刚宣称“人人平等”的国家,用排斥另一群人来重新确认了自身的秩序。
六十多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另一场道德修复正在展开。欧洲的战争结束了,集中营的影像让“文明社会”陷入集体的愧疚。为了补偿犹太人,西方支持他们在中东建立以色列。那被视作一种赎罪——让受害者拥有自己的家园。只是,在这个新家园上,原本的居民开始流亡,旧的灾难被新的悲剧取代。
这两段历史看似遥远,却有相似的逻辑:
当一个社会在道德上需要重建自我时,它往往会选择一个更弱的群体来承担那份代价。
历史从来不是单纯的善恶之争——那些看似出于正义的选择,往往在另一处,悄悄制造了新的伤口。
一、从废奴到排华:美国的道德幻觉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一个自我重建的时代。宪法修正案宣告奴隶制度终结,黑人第一次被写进“平等”的定义之中。城市里挂起了庆祝自由的横幅,教堂的讲坛上,牧师高声宣读《独立宣言》的段落,仿佛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然而,这种道德上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战争的废墟与经济的萧条,让“自由”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口号。工业化的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退伍士兵回到家乡,却发现没有工作等着他们。对许多人来说,“平等”成了一种威胁——如果每个人都平等,那么他们失去的特权又算什么?
就在这种焦虑中,新的替罪羊出现了。最初是欧洲的移民,接着是来自太平洋另一端的华工。十九世纪中期,大批中国劳工受雇修建横贯大陆铁路,他们吃得少、干得多、不抱怨。雇主称赞他们“勤勉可靠”,工会却把他们看作“冷血的机器”。经济下行时,他们被指责压低了工资,工人组织的标语写着:
“白人工人的工作应由白人完成。”
政治人物很快捕捉到了这种情绪。1870年代的选举演讲里,“排华”成了争取选票的口号。报纸漫画把华人画成长着辫子的怪物,议员们在国会辩论时公开说,中国人“不理解自由”,他们“不是公民材料”。于是,1882年,《排华法案》顺理成章地通过了。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那是一种“恢复秩序”的行为。国家的理想依旧存在,只是“某些人”不在理想的范围之内。一个曾以废奴为荣的社会,就这样重新划定了文明的边界。
但更深层的讽刺在于,这场排斥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恐惧——对动荡的恐惧,对失控的恐惧,对理想被证明无法兑现的恐惧。当一个社会无法面对自己的不平等,它就会寻找新的他者来维持平衡。
那些被赶出美国的华工,大多没有留下文字。他们只是消失在历史的空白里。留下的,是这个国家在自由叙事中的第一个裂缝。
二、从屠杀到建国:欧洲的虚伪赎罪
二战结束后,欧洲像一个从噩梦中醒来的病人。集中营的铁丝网被推倒,尸骨堆积在泥土下,历史在空气中留下了一种难以呼吸的味道。人们开始谈论“文明的重建”,谈论人性、信仰、道德。
在这场巨大的自我审判中,犹太人成了整个大陆的象征性受害者。对他们的补偿,是欧洲重新获得道德的必要步骤。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那一天在伦敦与纽约被描述为“人类的胜利”,在加沙与耶路撒冷郊外,却是另一种景象——被迫离开的农民拖着行李走在尘土路上,女人抱着孩子,不知道该往哪去。
他们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却在别人的赎罪中失去了家园。
他们的村庄被划入新的边界,他们的土地在国际公报里变成抽象的“领土调整”。
当报纸刊登欧洲政治家的演讲时,没有人采访这些离开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的哭声被归入“地区冲突”的背景音,仿佛那只是地理学问题。
西方媒体很快塑造了清晰的叙事:犹太民族回到了祖先的土地,历史终于得到补偿。这个故事干净、完整,也让人心安。只是,它要求人们忽视那些仍然站在原地的人——他们的语言、房屋、墓碑,都不再被承认为历史的一部分。
欧洲完成了自己的赎罪,而巴勒斯坦人被遗留在赎罪的阴影中。
三、两次事件的共同结构:救赎与支配的循环
纵观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美国的排华到欧洲的赎罪,表象不同,逻辑却惊人相似。“文明社会”在经历了自身的道德危机后,总要寻找一条通往“自我修复”的道路。而那条路,几乎从来不是回到平等本身,而是通过重新划定谁可以被同情、谁必须被牺牲来恢复秩序感。
在美国,这种逻辑体现为恐惧。废奴之后的白人社会既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又暗暗害怕失去控制。排华法案让他们重新找回安全感。只要仍有人被排除在外,“平等”就不会显得危险。
在欧洲,这种逻辑表现为赎罪。面对大屠杀的阴影,西方政治家选择用一种外向的方式重建道德:让另一片土地承担他们的负罪感。以色列的建立确实让欧洲社会获得了“人道的安宁”,但与此同时,它也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背负了他人的历史。
这种结构的共同点在于——“救赎”并没有解构伤害,而是让伤害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通过排斥“非我族类”来证明自己依旧是文明的中心;欧洲通过援建“受害者国家”来证明自己依旧是人道的典范。
两者都在说:我们懂得反思,我们依然是世界的道德坐标。
但他们的反思从未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坐标永远由他们来制定。
在旧金山的海风和耶路撒冷的尘土之间,有一种静默的相似——
自由与赎罪,都在被不断地讲述;
被迫沉默的人,却始终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那一部分。
结语:救赎的幻觉与文明的阴影
回望这段历史,人们常以为排华法案和以色列建国只是过去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误差。但如果仔细看,它们留下的并不是事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善意”包装权力的方式。它没有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消失,而是悄悄融入了当代文明的语言。
在今天的世界,国家不再以肤色为界划分优劣,却仍在以制度、价值与文明标准决定谁“成熟”、谁“落后”。
当西方国家谈论人权、民主与自由时,那种语气里仍带着熟悉的温度——对他人高高在上的评判。
他们依旧相信自己是世界的教师,只是教室变大了。
这种影响更深层的表现,并不是显性的压迫,而是一种心理的主导——非西方世界被动地在模仿、解释、辩护,在别人的坐标里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即便是反抗,也常常被迫以对方的语言表达。白人中心的权力结构,不再需要殖民军舰,它早已嵌入了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和道德秩序。
当一个文明相信自己是正义的源泉时,它就不再需要怀疑自己。它可以在同情中行使权力,在道德中实施排除。
历史没有终结,只是进入了更隐秘的阶段。
在这漫长的循环中,真正被忽视的,也许不是那些被驱逐、被流亡、被误解的人,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掌握话语权的文明是否愿意放下“中心”的位置,与他人平视。
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文明社会”就永远只是一个温柔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