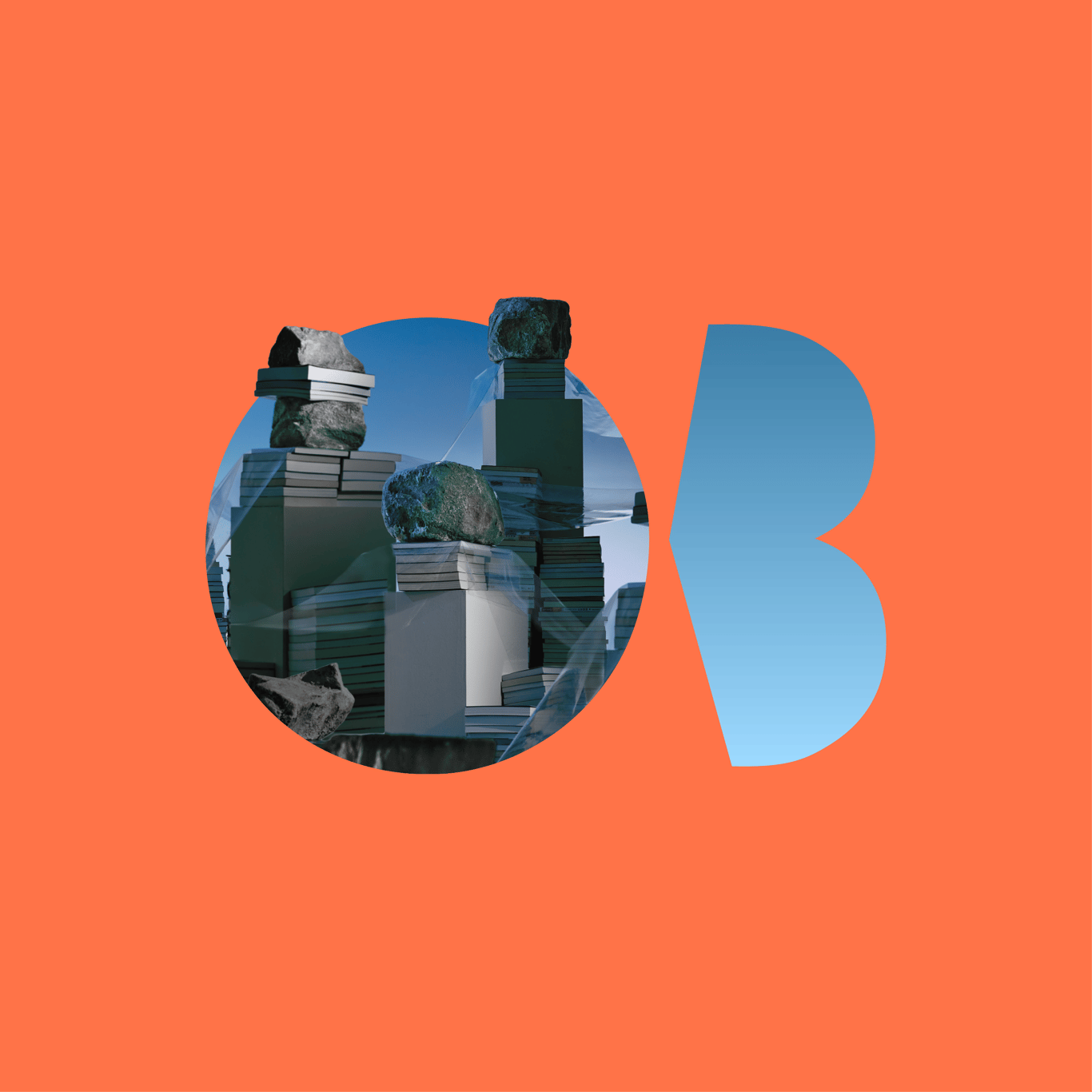編劇書簡S2EP8》這是我要的人生嗎?從短篇小說〈失明〉到電影《失明》
撰文|劉梓潔(作家)
本文有微量劇透,介意暴雷者,請看完電影再回來閱讀。(本文劇照取自電影《失明》Facebook專頁)

由編劇的眼光領略故事的編織,從作品細節欣賞影視的魔法,在戲劇中蔓延閱讀的支線。「編劇書簡」專欄,由編劇、作家劉梓潔執筆,是觀影筆記,也是影視與文學的對話,每月刊登。他嫌她乾的那個早上開始,她就感覺自己要失明了。
這是短篇小說〈失明〉的第一句。22年前,我以這篇8000字小說獲得了有「文壇入場券」之稱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最初要讀到它,只能去找那一期雜誌的文學獎專號。又過了10年,12年前,2013年,它才被收錄進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親愛的小孩》。應該也是那時,電影界掀起IP潮,對熟識的影視製片導演釋出合作善意,出版社、版權代理商也積極推動,但總只聞腳步聲與敲門聲,無人真正遞上合約。一直到2019年,伯樂出現了,是周子娛樂的周美豫導演與林依晨監製,她們一眼看上了〈失明〉,反而不是其他篇更近期創作、更有話題的小說。

我知道從原著小說到劇本,再從劇本到開機拍攝,從殺青到後製再到上映。這過程太漫長艱辛,能走完都已經值得一座最佳毅力獎。她們真的做到了,我真心佩服導演、監製與團隊的勇氣與決心。費時近6年,今年(2025)2月份終於在鹿特丹影展及各大影展亮相,而我也在台灣上映前夕看了最終完成版。
電影是另一個生命,小說在改編成劇本時,原著已投胎轉世,我不預期能夠「認」出它來。然而,一場床戲,重現了小說的第一句。自知自己性向是女同的主角書儀(李沐/林依晨飾),大學時硬找了個直男來做第一次,自然只能尷尬硬裝,還得到了「你怎麼這麼乾?」的回應。文學的「乾」只是隱喻,影像的「乾」需有因果,硬做硬裝、自作自受的乾,點出了書儀由裡到外的人生困境。
一乾各表。我開始覺得有趣。

➤恐懼如何改編?
事實上,美豫導演一開始極力邀請我親自改編,但我堅持不干預創作,我更期待它長成全新的作品。另一方面,售出電影版權時(2019),距離我創作這篇小說的時間(2002)已經太久,久到我自己重讀都會不好意思。然而,在電影製作期間,這本短篇小說集也出版了日文版,我與日本作家、《蛇信與舌環》原著作者金原瞳有過兩次對談,她說整本最喜歡〈失明〉,喜歡到已經把第一段背起來,每次見面她都會用日語讀上面那行第一句給我聽,我更是不好意思到想鑽進桌下。但也是從那時起,我才比較坦然面對「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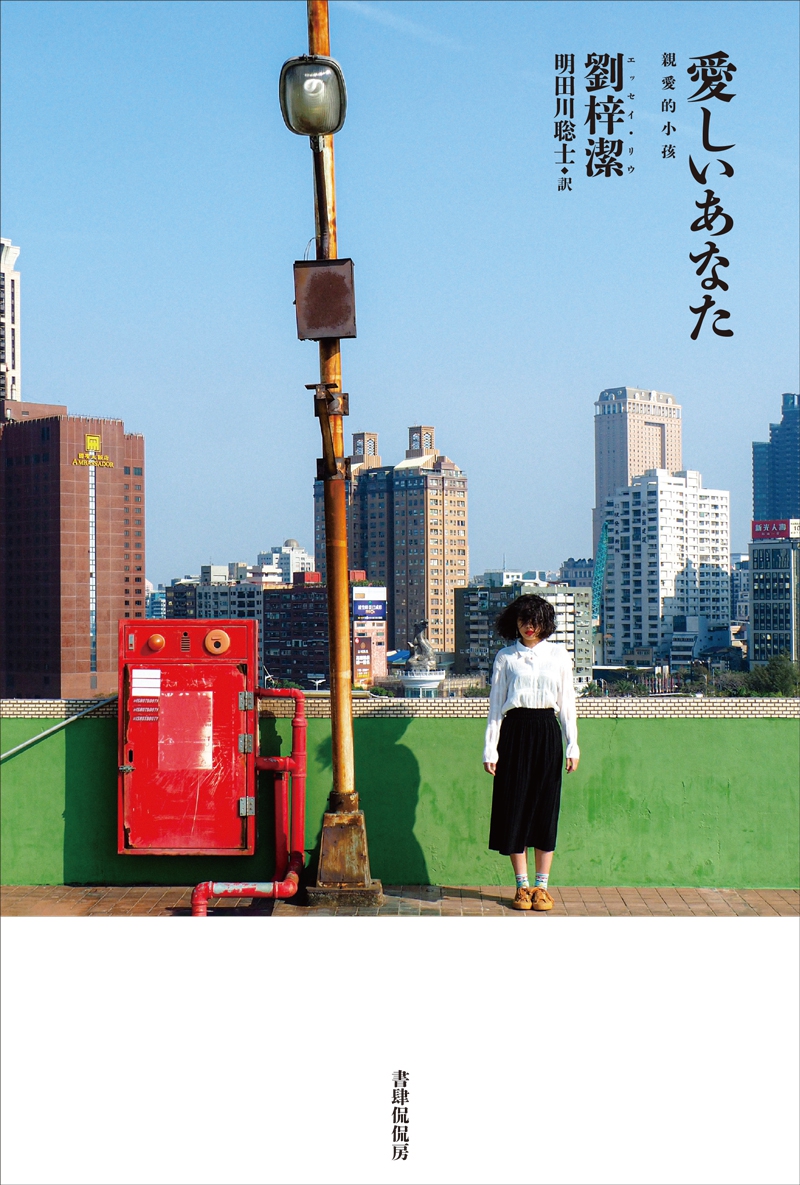
在對談中,金原與我談到,我們的處女作都以自己最熟悉的身體感官下手書寫,她寫裂舌,源自疼痛,而我寫失明,則源自恐懼。二十出頭歲的我,已經近視一千度、散光兩百度,還動不動就長針眼大膿包,我怕我還沒寫出第一篇作品就瞎掉了。真實版的人生有了Happy Ending:我用新人獎的獎金拿去做雷射手術,從此脫離眼疾之苦,還寫了續集〈雷射〉,在2014年由金馬學院學員改編成短片。
若小說的核心是「恐懼」兩字,那麼恐懼如何改編?小說裡的主角恐懼失明、恐懼被拋棄,那麼電影《失明》的主角書儀恐懼的,則是「不對」、「不正常」、「不一樣」,大學時硬裝硬做又乾又痛,成年後繼續裝,裝成了雍容華貴醫師娘,正要卯足力幫助丈夫當上院長。
這是電影《失明》大膽改編、且超越原著的設定。上流社會虛偽矯情,深櫃女主配合著演,幫加班晚歸的丈夫加熱鹹派當宵夜(注意不是鹹粥喔!),戰戰兢兢鋪好桌墊,林依晨演出的中年書儀眼明心盲,每日如踩鋼索,過了就是滿堂彩,失足就是深淵。初戀情人雪津(王渝萱/吳可熙飾)則是完全不演,性別流動,狂野率真,野獸性格陰錯陽差吸引到了書儀的叛逆兒子天瀚(劉敬飾),電影的一句話梗概(logline)明確吸睛:「兒子發現自己的情人是母親的初戀情人」。

原著小說是「女兒發現自己的情人是父親的往昔戀人」,性別改編翻轉,翻得好。在父權體制下壓抑陪襯、走入家庭、假裝正常的女同志,如何破繭而出?同志遊行、婚姻平權、看似百花齊放的台灣社會,到底還有多少人因恐懼而隱忍?大眾的目光與價值觀真的多元開放嗎?電影拋出更多議題與思考,觀眾等著看書儀縱身一躍。


➤性別顛倒,仍忠實還原小說
小說中另一句被一字不差地呈現在電影裡的對白,是「為什麼不開燈呢」。小說裡是主角對著清晨不開燈的節儉爺爺說,當我聽到在安養院失能狼狽、幾近失明的書儀母親(陳季霞飾)說出這句對白時,忍不住會心一笑,也感謝編劇與導演的用心。
書儀母親在電影版畫龍點睛。大學時書儀與雪津在電梯親密擁吻,被母親撞見,成為母女心結;而母親過世,書儀悲傷低落又找上雪津。另一個如母親般的角色,則是蘇明明演出的前院長夫人顧太太。她是書儀的模範版,一生演好演滿,也就是那樣,而書儀再跨一步就可以功德圓滿,成為到處行善拍照頒匾額的院長夫人——這是我要的人生嗎?我要在高級宴會廳陪笑陪酒,還是去情人的嬉皮公寓天台恣意跳舞?

然而,另一邊不見得就是幸福快樂。這是另一個「有認真」讀小說和看電影才會發現的電影裡的巧思。小說中有這段描述:
早上醒來她好快樂,幫他刷浴室,刷到鏡台才發現,有好多不同牌子的洗面霜,突然她知道了,他不只有一個女病人。她還是把一瓶一瓶整齊排好,蓋子沒旋緊的旋緊,擠太多糊在外面的也擦乾淨。
細心的劇組,在狂野情人羅雪津工作室的浴室鏡台上,陳設了雜亂擺放的女用保養品、男用刮鬍刀,而書儀和天瀚也以此為線索,發現雪津的多重關係。
但若要說,電影最「忠實」呈現原著的部分,我想是敘事結構。原著雙線並行,主角一邊與神秘情人發展戀情,一邊追溯家庭記憶,最後發現了父親的秘密。電影結構亦現在式與回憶交錯,層層揭開謎底,關於書儀為何且如何變成今天這樣。周美豫導演曾在訪談中說到:「整個小說的寫法很曖昧。閱讀的過程中,你會去猜。我覺得作者寫故事的方式,『讓你去猜』這個部分我很喜歡。」若要說,原著幫助了什麼,我想只有這小小的一點貢獻。
電影裡,我覺得最飽滿、我最喜歡的一場戲,也是我認為全片的高潮,是兒子天瀚與母親書儀在酒會上的共舞。天瀚理解了母親,希望母親快樂,而書儀也不再畏懼他人目光,醉酒失控,原形畢露,而這原形,才是那個不再偽裝的自己。接住她的,不是情人,而是自己的兒子。母子不再是母子,也不再是情敵,而只是單純地希望彼此自由快樂。這場戲當然不存在於原著,但當我重讀,我發現其實是編劇導演忠實地還原:「他(父親)要一種自由,這種快樂不是婚姻幸福家庭美滿的快樂可以借代的。」
至此,我可以說,小說〈失明〉與電影《失明》在問的,是同一件事:我快樂嗎?這是我要的人生嗎?●(全文於2025-09-22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