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季学期结束了: AI到来的恐惧

从八月中旬开学到下个星期三,十二月三号,十六个星期,2025年的秋季学期就要结束了。
明天是感恩节,到处都是节日的气氛,圣诞灯光已经在街区亮起来了,商店里的音乐已经是圣诞音乐了,一进去就喜气洋洋的,这种喜气洋洋的乐感让我想起张爱玲的小说《秧歌》里的过年的气氛,被杀的猪在被烫过和刮过猪毛后,猪头切下来,突然的白脸猪头大咧着嘴笑。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但节日的欢乐却是不变的,猪头还在笑,人也在忙碌。
我也忙忙碌碌地过了这个相对平静的学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学期,没有很多的打扰,学生似乎也不错,总是有好的或者基本好的学生赋予教书生涯以意义,其他的学生就是陪读,无论你怎么做,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们就是一般的学生,在人群里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人,作为老师我给他们天天喊加油,是弹冠自庆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美国的教育系统在AI的进入下,正在发生彻底变化,很多人文学科已经不再继续需要了了。2025年七月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系统宣布砍掉了19%的专业,400多个大学专业和研究生专业被砍掉或合并了,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我引用的资料之一是这个:(www.highereddive.com...).
关心大学教育的人哀伤一片,我却没有那种哀伤,因为于瓦尔·赫拉利的出版的书《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个课题》(中文翻译为《未来简史》)和他的新书《联结》早就准备了我对未来教育的变化。在他的书中,他多次说,我们现在教授的内容,根本是无用的,我们这些在高等教育里的工作的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传统教育的惯性的幻觉里,我们教的一切,在未来都基本无用,但我们也不知道教什么好,于是就靠惯性,教着在未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好像一列火车,在惯性的作用下,盲目地奔驰着。
我是非常赞同赫拉利的观点的。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了,越教越觉得自己在教什么东西啊,越来越困惑,我教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教中国文学吗?美国的中国文学课堂,大多都是通过文学学习中国的社会、政治与历史,跟文学是人类灵魂的表达差十万八千里。我们不分析人物的塑造,写作的方法,语言的妙处,我们分析社会的再现,分析时代话语的作用,分析性别与群体的身份认同,我甚至觉得只有自己读想读的书时,才能回归文学,如果是给学生上课,文学其实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简单的教书,可以很有趣,却也本质上没有什么用。我的学生就多次要我把问题的答案给他们,他们说,我们背一背,考试考好就行了,至于中国文学有什么用?他们连美国文学也学不了多少。
那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的“Critical Thinking”,动不动就自称自己在教“批判性思维”的人文学科教授们,就我接触的教授来说,真正有思考的人非常少,其实真正读广博的书的人都很少。大多数人无非是重复他们每日阅读的新闻,他们甚至很少阅读超出他们日常阅读的新闻之外的杂志或书。大部分教授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教书的。不久前我问一个研究中国大众传播的学者,你读了赫拉利最近的书《联结》(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了吗?她看着我, 一双灰蓝的眼睛里一片迷茫,没听说过,也没读过。我无语。
我在二十年前参加了一个暑期“批判性思维”训练班,至今我还保存着那个训练班发的小册子“批判性思维:概念与方法”(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 and Tools), 这个小册子是我多年上课和要求学生写作文的一个小指南,写作这个小册子的教授们还有一个网站:www.criticalthinking..., 我偶尔会上去看看,看有什么新的概念的出现。
二十年教授这个方式方法,我的感觉是失败的,我渐渐地意识到,大部分的学生不会成为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就如同人类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思考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就是能思考的人,其思考能力也不一样,我常常悲叹自己思考能力的局限,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深刻思考的人,虽然爱读书,但把书变成智慧和洞察力,我的能力不够。
大多数人就是传声筒,他们看《纽约时报》之后就是重复《纽约时报》的观点和立场。二十年前我在一个朋友家过感恩节,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父亲是爱因斯坦的学生,她的姑姑姑父是律师,叔叔和他的妻子是医生,我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过感恩节,听他们谈话,最终感到十分无聊,因为大家重复的都是《纽约时报》,那是我的第一次发现高级职业人士大家意见一致时的无聊。
今年夏天参加一个会议,欣喜地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博士生参与,听他们讨论他们的博士论文,听了他们的题目,我忍不住问:你的论文将怎样改变我们对非洲与中国的关系的认知?你的论文怎样成为我们努力要取得的不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在西方做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受他们的导师的限制——如果导师是西方人的话,学生的题目很小,如果有大眼光,小题目也能做好,从细节也可以看到更大的宏观的东西,但,很多博士论文就是小到最终没有意义。
今年五月我被邀请主持了一个讨论组,讨论的少数族裔在美国某个城市的历史,题目很政治正确,但说来说去,直到目前这个少数族裔在这个大城市的人口也不到百分之一,这个题目本身对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其实也就只有百分之一的意义。当然,并非没意义,但这样的知识生产意义到底何在呢?
我今年的两次经验都让我更深刻地感到人文学科的危机,现在的很多学术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在大的背景下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的命题或对未来有启发,我觉得阅读这些学术和没阅读简直没有区别,这种学术,不做也罢,免得在这个信息垃圾化的今天给世界增添垃圾。
赫拉利说,历史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变化,这才是学术的真谛吧。所以我对印第安纳大学系统的几乎是粗暴的大砍专业,不表示意见,我们不知道四百多个学科和项目的砍掉、合并对新知识生产的作用是否有促进或阻挠的作用,但我知道,那些用已故著名教授大卫·格瑞伯(David Graeber)创造的词“Bullshit Jobs” (狗屁工作)可以定义的工作被砍掉了,并非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格瑞伯教授在《罢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狗屁工作的现象》,论证了当代许多工作的无意义性,尤其是金融、法律、人力资源、公共关系和顧問等领域的工作。其受欢迎程度超过一百万次点击,造成激进杂志《罢工》的网站崩溃。2018年,格瑞伯根据自己的文章, 又采访了很多人,出版了书《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 2018)。这本书很好读,我觉得年轻人在选择大学专业前都要读一读,反思自己对未来的选择。“狗屁“工作被砍掉,”狗屁“知识不再生产,至少可以节约年轻人的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学期学校里开始训练我们关于AI, 很简单的讲座, AI的ABC。我还参加了一个AI读书小组。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在改变,比如外语教学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学外语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看到有的地方还在努力招人来教西班牙语、法语什么的,我甚至觉得奇怪,难道我们不是在外语教学失业的前夜吗?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系统把外语教学基本砍没了,外语已经不需要学了,有个手机就可以交流,将来只有少数人,比如外交官什么的,需要外语吧?
明天是感恩节,我正在准备感恩节的聚餐,却胡思乱想这个学期的事情。我年年都招待朋友,今年也不例外,只不过减少了人数,我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花大力气做饭,招待他人了。几年前的感恩节,我因为切菜切破了小手指,当天去急诊室把伤口缝上,以后,这个小手指的一部分就麻木了,神经被切断了,也没有接上,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现在呢,我就招待两三个朋友,不再花很大的力气,我现在其实真没力气招待他人了。
我需要感激的是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失过业,总是有工作可以做。将来的人没那么幸运了,还如赫拉利所说,年轻人的一生将都在工作的面试里,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地准备失业,在重新塑造自己,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是很难再塑造自己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重来,比如那个叫马静芬的老太太,褚时健的妻子,他们都在七十岁以后再创业而成为亿万富翁。虽然我对成为亿万富翁感兴趣却做不到,但我对他们的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更感兴趣,马静芬所说:“我就像一株仙人掌,随便丢在哪里都能活,这辈子不会在困难前倒下,活到100岁,还能撸起袖子加油干!”——有多少人可以在近七十岁时可以重来?
希望我们都有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来的精神,在AI将席卷而来的时刻,这就是2025年感恩节前夕我想到的。
2025/11/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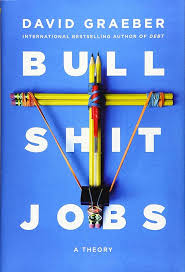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