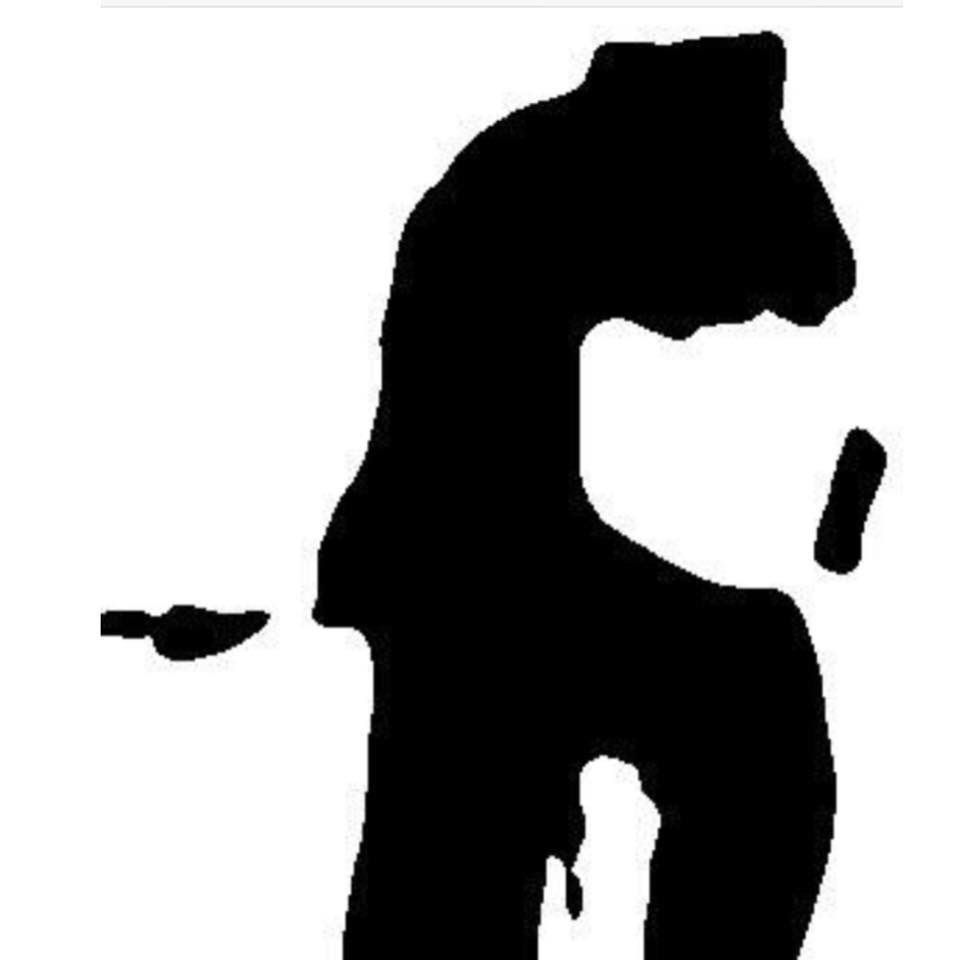無從定義的身世仍持續漂流:讀郭強生《惑鄉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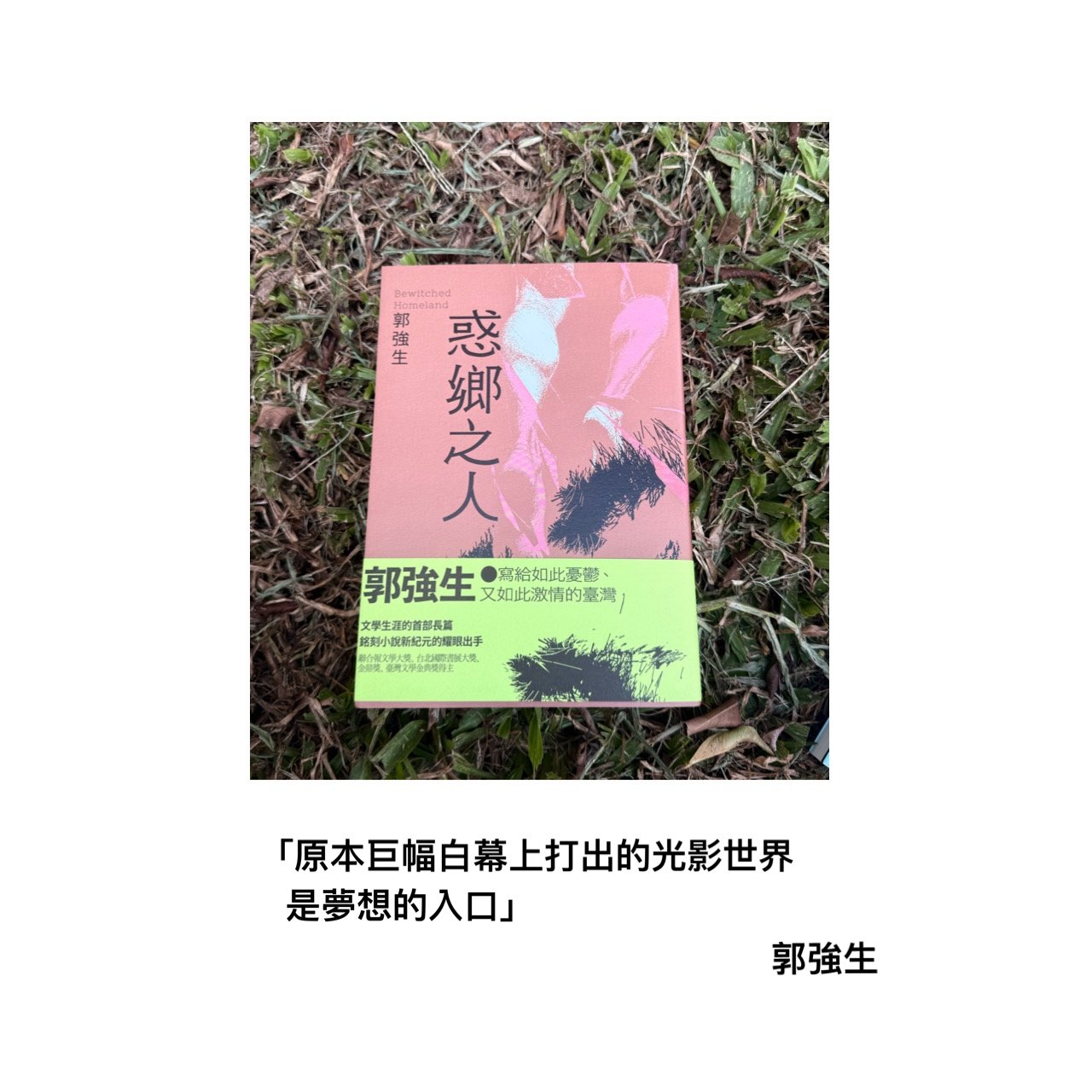
郭強生的《惑鄉之人》以一座即將拆除的老戲院為起點,編織出一個橫跨七十年、糾纏四代人命運的故事。
男孩與巨幅的白幕,恍若電影《新天堂樂園》的場景,跌唱著夢想與時代,而人與人都是過客。
小說開篇那個灼熱的深秋午後,吉祥戲院的父親與孩子,錯綜複雜的親情與愛情,一一在鐵榔頭的敲擊聲中逐漸瓦解。一寸一寸剝落的建築,彷彿也粉碎了某個時代的夢。
最觸動我的,是小羅與父親老羅之間的微妙關係。老羅為戲院畫了十幾年看板,卻認為電影是「不好的東西」,甚至將左派電影與國家淪陷連結。這種矛盾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夢與禁忌的雙生共相,也成為父子之間唯一的連結。
作者透過電影,將不同時空的人物串連起來。一部名為《多情多恨》的電影,成為貫穿全書的謎團。從日治時期的松尾、戰死的臺籍日本兵敏郎,到戰後的小羅、日裔美籍的健二,每個人都在追尋這部電影背後的真相,實際上卻是在追尋自己的身世與認同。
書名「惑鄉之人」精準地點出了主題——什麼是故鄉?對老羅這樣的外省老兵而言,臺灣不是故鄉,大陸已回不去;對松尾來說,臺灣是出生地,日本是祖國,兩者都讓他無所適從。這種「失根」的焦慮,在錄影帶時代來臨、老戲院即將拆除的時刻,更顯荒涼。
郭強生的文字細膩而節制,沒有過度煽情,卻在日常細節中透出深沉的哀傷。當巨幅銀幕上的光影世界被壓縮進錄影帶的黑匣子裡,當電影從儀式變成商品,某種屬於集體記憶的神聖性也隨之消逝。小羅說「在他心裡那樓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塌了」,塌的不只是建築,更是一整個時代的價值與信仰。
時序往後推演,今日我們仍重複著疑惑的步伐,試圖尋找腳下的定義。不斷被拆除的故鄉又在陌生的場域重建,當記憶不斷被覆蓋,遺忘與回憶之間,血脈躍動之餘,我們還能在哪裡安放自己?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