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ight on the Shore You Saw》
“...I know,” with all the unanswered questions.
早在人們被層層衣物給包覆住,被迫穿戴厚重面具與手持防身武器的那一天降臨前,晝日被染為永恆的赭紅,大地為塵土和風沙所困之前。
遙遠舊時代的夏日曾是茵綠與湛藍的顏色。
陽光順著繁茂枝葉斜斜的撒落,打碎了記憶中斑駁的光影,反射在一輛略顯年歲的舊式休旅車上。車身受盛夏的炙熱牢牢燒烤著,而車頭上的水瓶已空了一半,瓶底下滿是滴落的水漬。妳下意識地盯著那些滑落的水珠,沒打算擦拭額間的汗水,食指輕敲車身,思緒如沉入滾燙的水盆中。
妳已經幫她想好了所有理由:她可能還沒準備好,還要再幾天才會到,反正事情總是太多。
然後妳撥出了那通電話。
十位數字,是妳早已記熟的號碼。手機螢幕在夏日裡微微發燙,撥通的過程總讓人焦躁。嘟嘟聲緩緩順著被混凝土封住的綠蔭山路,一路延伸,等著另一端的回聲。
通話每每都從妳這頭先開始,而對面總會接通,妳想,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母女默契。
嗨,小熊。
耳際邊傳來了熟悉的女聲,帶著點小心翼翼的溫軟語氣。
妳那邊應該還是很熱吧,俄勒岡夏季一直都是這樣,乾熱得厲害——她這話十之八九是在冷氣房裡講的,聲音裡聽不出一絲汗氣。妳幾乎能想像她坐在公司會議室外的深藍色小沙發上,長腿交疊,妝容精緻無瑕,嘴唇塗著今年夏天最流行的冷杏仁色。
前幾天新聞才又再報林間大火,她說,這幾年真的太可怕了,山裡老是出事。講到這裡時,她大概抿了抿唇,指尖開始轉著手腕上的銀色手環,像繞著電話線一樣,一圈又一圈,這是她試圖避開某個話題時的預兆,某種改不掉的小習慣。
公司最近有些事——不久後她的話音果然壓得更低了,語速也加快了些。事情很多,會議擠成一團,真的不是不想去,只是抽不出時間。
當然、當然她沒忘記,她向妳保證。只是律師那邊還有幾份文件在跑,保險、帳戶、屋契……還有他所留下的那堆遺物,彷彿只要這些字眼一說出口,一切就還在掌控中。她繼續保證她會盡快處理完這些事,或許妳們可以再改約下週會面......
電話那頭罕見的停頓了一下。
「妳知道我不會把妳丟下不管的,我只是……需要再一點時間,妳能懂吧?」
那些關於死後人們留下的東西,生者總是過猶不及。
「我知道。」妳說。「那就下週見。」
妳掛斷電話,然而妳沒等她,正如十多年來妳母親缺席的每一刻,妳自有解決的辦法。
將疑問拋上搜尋引擎,大多時候都可以找到實際的解決方法:一個人搬家要怎麼做?和對象和平分手的解決辦法?該怎麼準備生涯的第一份實習工作?
同理,該如何處理一個死去之人的遺物——妳父親的遺物,理論上也不會是太艱難的事情,搜尋引擎還會貼心地附上殯葬業和律師事務所的廣告頁面。妳想妳母親應該早就做過一樣的事情,打電話,找人幫忙;花錢,處理遺憾;再花幾個月的時間,邀妳一同參加心靈諮商治療——從未真正問過妳是否需要,只是相信傷痛能代入一套公式來應對、安放、抹平。然後過往的篇章便如此翻頁了。
畢竟之後就只剩妳們兩個人了,妳能懂得吧?小熊。她會這麼說。妳知道她總是這麼說。
就如同妳無法阻止她如何回收、拍賣、無限期擱置那些舊家的遺物;她也無法阻止妳——挖出舊鑰匙,打開後車廂,先下手為強,把記憶一件件拖出來,翻出那些人們總習慣在人死後避而不談的東西,看看到底還留下了什麼。
看看在他死去的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妳的第一個線索,是這輛一九九零年出廠的雪佛蘭休旅車。墨綠色的車身貼著幾張早已褪色的國家公園通行貼紙,外型像出自某部復古動作電影,可能還被幾隻遠古時代的爬蟲類追殺過。那歷經磨損的外殼和略帶塵土的車胎,承載著某種個人品味無法割捨的舊年代的氣息。
妳順著燙手的後車廂邊緣找到鑰匙孔,打開後門的那一刻,一股混著潮濕與霉味的氣味鑽進鼻腔。妳像個採檢中的驗屍官一樣俯身進去,開始摸索每一處可疑的角落,當那個包裹著某物的巨大黑色塑膠袋映入眼簾時,妳不禁自嘲地想著:或許,這裡真的藏著另一具屍體,這樣一來,他的死就能被解釋得更有道理了。
拆開袋子,倒出回憶的屍塊,工具箱、收音機、帆布袋……理所當然的,還有必備的釣具套組,每一樣物件都還浸染著尚未乾透的濕意。這印證了妳掌握的第二個線索,妳父親哈倫·雷蒙開往湖岸的那個午後,顯然天氣並不是很好,下了點小雨,雨勢不會太大,否則湖岸釣魚場會在那天鎖上。
妳想起早些年總有年輕人喜歡在下暴雨時跑去湖邊,他們大多不是失蹤了,就是死透了,他還總喜歡拿這些事蹟告誡妳。可能他也沒預料到,山區的小雨也同樣危險,雨勢不大卻能吞人。陰鬱的灰色雲朵,人煙稀少的湖區,每一個都是造就無名兇案的絕佳要素。
你也是這麼想的嗎,哈倫·雷蒙?
妳知道他當然不可能回話,再也無法,而他所留下的物品和他本人一樣沉默。
……不想說也沒關係。
妳會找出答案的。
計劃是這樣的:扔掉不重要的垃圾,收拾剩餘的行李,最後開去湖岸探查一番。畢竟現在陽光正明媚,妳所要做的事情就這麼多,運氣好的話,今晚還能早點回來休息。
車內所遺留的大多數物品都非必需品。
就好比妳從工具箱翻到那支灰黑色、磨得發亮的手電筒時,有點驚訝它還在。
那是個早該壞透了的東西——開關鬆動,燈罩有裂痕,握把膠皮也脫落了一半。妳記得有一年車子拋錨,哈倫·雷蒙還是照例拿它出來用。
只是太久沒上工了。他當時邊敲著手電筒邊說,像在喚醒一個沉睡老兵,但這招並不總是都奏效。
換妳敲敲看,這邊。
如果手電筒不亮,他就會這麼說。隨著夜風吹過,四周的細葉沙沙作響,枝條被掃的微微蜷縮,妳隱約瞥見幾株野草貼著底盤顫抖——也許是泥土、蟲子、枯枝、野狗,或其他什麼——昏暗的樹叢裡,看什麼都不真切,只有他的聲音異常清晰。妳不害怕,倒不是因為妳多勇敢,而是這場景妳已經遇過太多次了,每一次妳都在內心嘀咕,怎麼他就不買個新的呢?
給它點時間,東西老了,反應都會比較慢。他說。
而這種事妳也不是第一次做了。那時的妳還很瘦小,便坐在車尾箱上搖晃著雙腿,專心替他拍打著手電筒。雖然老東西不太好使,但最終總會亮起一點微弱的光,勉強照亮他只存在記憶中的黝黑笑意。
在更久之後,妳已成年,也學會了更省事的辦法,修車對妳來說不再是難事。在他還在固執地敲著手電筒時,妳會二話不說地打開手機手電筒幫他照,有時妳甚至會直接搶過工具箱,也不想再看他在寒風裡慢慢地折騰。
如今妳試著再敲了一下,果真沒有亮。也有可能僅是電池完全沒電了。
妳把手電筒放回原位,關上工具箱的蓋子……改天再處理吧,妳對自己這麼說。
妳想,當年他大概也對自己這樣說過,無數次。
第二樣意料之外翻出的東西,是一張印著聖誕樹圖樣的紙卡。
它被夾在幾張泛黃的收據和加油單之間。就妳所知,現在哪還有人寫節日卡片——哈倫·雷蒙不可能有那種閒情,妳母親更不會。
妳翻開封面,紙張因歲月而略顯乾脆,纖維間滲著餅乾的甜香,伴隨一個久遠的名字一同浮現。
裡頭的字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今年準備了草莓蛋糕、巧克力脆片餅乾和大受好評的聖誕火鍋,希望雷蒙一家能來喔!尾端附註的「喬妮阿姨」旁還貼著一枚小巧可愛花朵圖案的貼紙——每年過節,妳們一家曾收過數十張相似的卡片,來自社區委員長的一貫問候,卻在妳滿二十歲那年忽然停下。
妳輕撫著那行圓潤的筆跡,卻幾乎記不清對方的臉了。
喬妮阿姨是那種典型有點囉嗦、略帶雞婆鄰居阿姨的存在——已婚,外表依舊顯得年輕。和孩子的關係說不上親密,也稱不上疏遠,總能看見她積極籌辦社區活動的身影。她把生活打理得體面又溫暖,笑聲宏亮,後花園永遠乾淨整齊,彷彿隨時能拍成雜誌專欄。或許她私下還經營著私人生活博客,從她不時向人炫耀餅乾與糕點的照片便可窺見一二。
妳對她印象最深的,是往年聖誕晚會上的草莓杯子蛋糕,新鮮又大顆的草莓,搭配香醇奶霜,分量慷慨得不像外頭賣的任何一款。那味道至今在妳的唇齒留存。
——可人為什麼會崩潰這麼快呢?
有天,她就突然病了,原因並非是她的愛貓寵物過世,也並非她的家暴前夫回來, 她沒有因經濟不景氣被資遣,家裡也沒有出天災或人禍。只是毫無預兆地,辭去工作,臉色發白,整個人開始潰敗:胃口不良、心情低落、所有興趣嗜好一時之間停擺,不想再見到人,也因此閉門不出,和周遭朋友漸漸地斷絕聯繫。
社區委員長換人後,往後的聖誕節活動變得單調而形式化,改成自助領取禮物,大部分年輕人也早已不再參加,再也沒有那些滑稽又過度熱情的聖誕卡片寄來。那時妳還在西雅圖念書,多年後妳回來最後一次見到喬妮阿姨,她正好要踏出家門,步伐因臃腫的身材而行動遲緩,手上拿著一疊凌亂的紙張和藥單,神情懨懨然地盯著遠處。
妳一時間沒認出她,她似乎也不認得妳,不想被任何人所認得。
她在這個社區待了二十多年歲,像這樣封閉的小鎮從來不乏傳言。有人說她和昔日朋友鬧翻了,有人說她落下了頑固的舊疾,還有人說她的孩子去了遙遠的都市工作杳無音信。喬妮至今仍住在這裡,她沒有死,她還活著,但從某一天開始,人們就不再提起她,而她也從妳的生活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妳重新挖掘到這張卡片的那刻。
妳不禁好奇,最後一次聖誕晚宴,妳父親是否有出席?為什麼他留著這張卡片?這些疑問雖不能幫助過去的喬妮阿姨回來,但下次若再經過她家門前,妳會試著打個招呼——也許妳可以帶些餅乾過去。
卡片被妳捏得有些發皺了,闔上後妳將它塞回那堆的凌亂的紙堆之間,與封塵的節日燈飾和香甜奶霜一併收起。那不是妳生活唯一遺留、所需面對的遺憾。
一九八零出產的小方收音機、過期的棒球票根、幾張皺掉的購物清單、陽春的夏威夷搖擺掛件、烙印整個俄勒岡公路的紙本地圖,還有妳遲遲不願拆封的釣魚工具套組——它們大多數被妳翻開後,先是放置一旁,過不久又歸回原位。到頭來,妳居然一個都沒丟。
車內所遺留的大多數物品都非必需品,但什麼才算生活的必需品?
妳果斷闔上後車廂,決心不再回顧那些東西,繞到駕駛座,車門一關上,裡頭的熱氣仿若誰未出口的嘆息,妳帶著一絲惱怒點火發動。不是說因為太陽即將落山,而是妳明白,一旦在這裡停留太久,一切就會開始原地打轉——越想挖掘每件留存物的意義,就越無法將車開往湖岸的那一頭。
是誰說處理遺物是件輕鬆的事?
妳將油門踩到底,那股悶意被一路縱橫交錯的樹影甩在身後。道路在前方展開,只有呼嘯的而過的引擎聲一時充斥妳的耳膜,車內的光景則在這份轟鳴中陷入了短暫的停滯。妳理應要對前往湖區的道路再熟悉不過,可沿途經過一間又一間荒廢或剛修繕的店面後,妳瞇起雙眼,將車速放慢了些。哈倫·雷蒙的車子從不裝導航,因此妳只能在幾處陌生的岔路間攤開那張老地圖,辨認自己身在何方。
妳記得,他過去不挑歌單,但會挑電台。他說 K-FX 以前比較好聽,現在的 DJ 太吵。妳轉過幾個熟悉的頻道,播的歌曲陌生又熟悉;大部分所謂的「經典」鄉村樂,已不是哈倫·雷蒙所認得的歌手。妳默默聽了一首又一首,最後將旋鈕轉回最初那位龐克歌手的嘶吼中。這次,妳沒有再改動電台,只讓它穩穩地伴著妳一路駛向湖岸,雖然大多數時候妳都沒搞懂他到底在唱什麼——等到妳意識回過神時,深藍色的湖水已在眼前漫開。
釣魚場的老普克還在,此刻正打著哈欠滑著手機。妳的車剛停下,他便抬起頭,表情裡多了幾分警覺。有時候,對一個地方太熟悉,不知道算好事還是壞事。
這不是……嗯,好久不見啊……這些天都還好吧?
他沒提雷蒙家的女兒,措辭略顯遲疑。妳當然知道原因,你們彼此認識很久了,從小到大,他一直是這座釣場的管理員,他看著妳長大,認識哈倫·雷蒙的時間幾乎和這座釣場一樣久。
環顧了一下四周,平日的釣場人並不多,湖面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爍著平靜的光芒,水波輕輕地在老舊的木板桅杆下蕩漾,景色看上去往昔依舊。
妳背著軍綠色的厚背包,舉起左手那堆配置齊全的釣具,只是淡淡地說道:還可以,有點忙,想來釣魚放鬆一下心情。
……你呢?釣場的生意還好嗎?
嗯——這兒可比城裡安靜多了。老普克像是有些不自在地挪了挪坐姿,抓著稀疏的頭毛瞥了眼東側湖岸的碼頭邊,數週前的封鎖線已然撤除,只留下幾片遺落的布條隨風飄盪。
還好,除了東區那裡還在整……理,沒有什麼改變,妳不用太擔心。
說到這,老普克的表情又閃過一抹警覺,鬍子微微翹起,但很快化作皺成一團的苦笑。泛黃的門牙仍舊少了那麼幾顆,給妳突然有種這裡好像什麼也沒變的錯覺。
總之,歡迎回來。有啥事,來找我就成。東西都有帶吧?妳要來點小點心嗎?我記得妳以前總愛喝橘子汽水——不用嗎?真的不用?行吧,當我請妳啦,妳這麼久沒釣,手感怕是生疏了,有東西配著也好。
他一邊碎念,一邊從櫃檯的提袋裡塞入一包又一包的垃圾食品,遞給妳的姿勢像妳是哪個暑假來度假的小毛孩。他嘴邊的鬍子翹得更明顯了,抖動的模樣彷彿在說:別說妳不喜歡,小鬼,還愛吃這牌薯片嗎?不愛我也塞進去了。
別客氣啊,諾,拿著。42號桌。
妳道謝的聲音肯定有些乾巴巴的,還是那句,有時在一個地方待太久,真不知道算好事還是壞事。直到妳走到那張印著編號42、靠近碼頭邊的陌生長桌旁,妳才勉強打開袋子一瞧,還真的什麼吃的都裝進去了,包括那瓶橘得太過鮮豔的橘子汽水。
而妳的背包還留有數罐莫爾森啤酒。
不是妳的,估計是他沒喝完的。日期還很新,瓶身卻被曝曬得灼燙,妳不確定喝下去會不會出事,妳從來就不愛那味道,可妳還是把它們都帶過來了。
因為他就是那樣的人,如果那天不是下雨,妳猜想他會把收音機照慣例擺在碼頭一角,轉到那台總是嗡嗡作響的地方棒球頻道。音量不能開太大,不然會嚇跑魚;但也不能關掉,否則魚上鉤時會太靜,會錯過第三棒擊打揮出去的歡呼聲。
一則不重要的小故事:有一回,妳曾問他為什麼鎮裡人普遍不支持道奇隊,卻老是收聽他們比賽。他那時神情專注地盯著釣竿,浮標紋絲不動,維持那姿勢已經好幾個小時了。沒有為什麼,他說。我從來沒在聽。
然後很快到第七局關鍵時刻,他便會把釣竿放一邊,嘴上說著「看樣子今天是釣不到更多了」,手卻默默把收音機的音量調高了兩格。
妳心裡想著:又來了,他大概則想著:誰在乎那群傻道奇。
就妳後來所知,大部分的人只是不想看他們贏得太輕鬆,與之敵對的球迷更是不想錯過他們輸球的時候,那種搭配莫爾森啤酒與最後一桿魚沒上鉤的不甘心,剛好配得上湖岸邊夏日傍晚的味道。
妳以前從來不理解那是什麼感覺,現在卻可能有點懂了,妳試著喝了口啤酒,發酵的酸味讓妳嘖了下舌——果然是妳討厭的味道。
落日的餘暉映照妳半側的臉頰,湖面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色澤,然而妳的舌尖是苦的,妳的指尖已經有些冷了,妳還在等待答案。
線索其實已經掌握了一些,比方說,釣具。
他若是獨自出門,總會帶上那套「誰碰都要被他碎念兩句」的裝備:捲線器包兩層,掛鉤收得像精密機械。可妳後來沒看到它,取而代之的,是 Ugly Stik——那支他總說「爛得很」,卻從沒真的丟過的竿子。
只和妳釣魚時才用得竿子。
妳靠在碼頭邊,盯著手中釣桿柄上裂開的握把、上頭兒時寫上的名字早已脫色,還有他為了防水而套上的膠布。奇妙的是,那天他偏偏搭配了 Shimano 的高端捲線器,讓人根本摸不清他的意圖。
你到底在想什麼,哈倫·雷蒙?
你希望我在這嗎?你希望一個人待在這嗎?或者說,你是故意這樣搭的?給我看?
當然,妳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那天他怎麼想的。就像妳找不到那把槍。或許找不到才是最合理的,警方他們通常會把那類物品收起來作為證物,家屬看不見,摸不著,也就比較不會受亡者的幽影所困。因為來自己身的死亡——那本來就不是能靠理解就能推知意圖的東西。
收音機的比賽早就播報完了,只剩下夏夜的晚風,喝不完的啤酒,妳滿心的疑惑,和已經不會上鉤的魚。釣場再過不久就要關閉,然而妳還待在原處,瞇著眼,固執地盯著即將落下的夕陽。
這一次,妳不會再說妳知道。
在即將吞沒湖岸粼波的夜色中,妳等待著一個永遠無法知曉的答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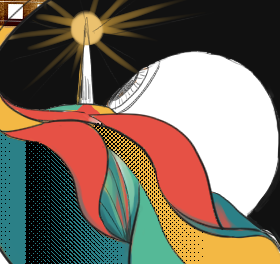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