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逃亡实录《人间蒸发株式会社》 揭隐世背后的千疮百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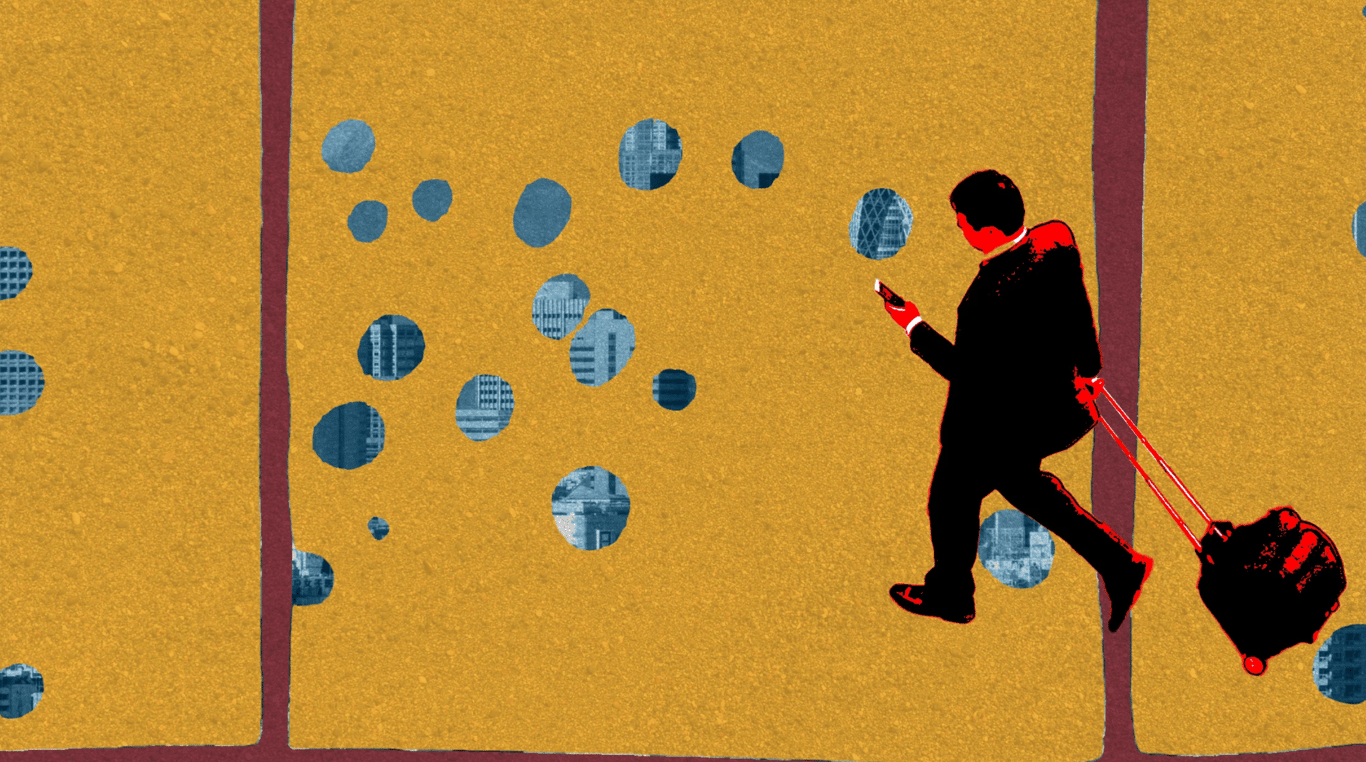
文|刘彦汶
原文发布时间|12/02/2024
1967年,日本名导今村昌平在失意之时拍摄伪纪录片《人间蒸发》,以访谈、跟踪的手法拍摄失踪者大岛的未婚妻早川寻夫之旅。当时,确有一名叫大岛的推销员无故失踪,今村昌平以虚构方式拍摄,虚实之间渗透出社会上耐人寻味的一面:好好的一个人,为何突然失踪?
日本每年约有8万人消失,“人间蒸发”这课题仍魂绕整个社会。德国导演Andreas作品《人间蒸发株式会社》拍摄西成区“自愿消失”的族群,他们“逃”非为了逃债,也不是畏罪僭逃,当中夹杂着外界不为人知的原委。
日人抱有“不想打扰别人”的逃逸心态,奇怪的是逃出生活圈的人们,一般很难被发现。“逃”就像魔咒,这种个人想法来得容易,在社会亦挥之不去,在日本天天上演。这些几乎只有日人才明瞭的隐士心态与光怪陆离,在《人间蒸发株式会社》一一呈现出来。
寻找“自愿消失”人们
亚洲话题作《人间蒸发株式会社》导演Andreas Hartmann热爱拍摄地下题材,以“外乡人”的视角寻找日本各种奇景。Andreas每天骑单车到驻留的学院,一天赫见一名年轻人在河边露宿。这名年轻人成为了纪录片《A Free Man》的主角,偶然之间Andreas发现了大阪的西成区。
一年八万人消失 大多与债务、罪行无关
Andreas得到日本导演Arata Mori协助,一同拍摄《人间蒸发株式会社》,他们在网上找到“深夜搬家”公司的广告,搬运公司美其名替客人搬家,实际上协助客人在深夜秘密搬离原来的居所,并觅得新地方让客人隐姓埋名生活,“除了听闻美国会有公司为明星退隐以外,这种职业在欧洲是闻所未闻。”
在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爆破,数以千计的人设法逃离债务。导演们后来联络到当时创立首间深夜搬家公司的社长羽胜鸟,他帮助了无数的人“消失”,成功逃离债务。他将自身经历着书,其后被改编为颇受欢迎的电影与电视剧《夜逃屋本铺》(日本名:《夜逃げ屋本舗》)。
平成年代的经济泡沫爆破已过去30多年,“人间蒸发”的课题仍然挥之不去。据日本资料显示,2022年便有8万人失踪,2万3千人、占3成与疾病有关,其中1万7千宗涉及认知障碍;1万2千宗失踪案件与家庭关系有关,8千宗与工作事业有关,因为犯罪而僭逃仅约400宗,占总数0.5%。数字显示失踪个案大部分与疾病、家庭与事业有关,失踪大多数并非畏罪僭逃。在8万的失踪人口当中,约3千5百宗在半年至2年间才能确认对方所在地。
除了上述逃离原因,《人间蒸发株式会社》抽丝剥茧探索日人自愿消失的复杂因由。
导演也在逃离的人群中
逃离的人不只是欠债的人,连日人导演Arata也是逃离一族之一员,“我也在名义上算是从日本消失的人,离开日本时我没有和很多人说过。”九十年代Arata刚从大学毕业,恰巧碰上就业的冰河时期(Ice age of employment)。他那时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离开日本前往欧洲发展。
Arata指出,日本社会就业阶梯非常系统化(Systematic),一般大学生在就学最后一年找到工作,然后随年月晋升为部门主管或公司高层。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受聘的人多数为终身雇用制;但如果像他这样,无法在大学时期受聘,以后在社会只能找到非正规雇用的工作。他又表示,非正规雇用意指以临时方式聘用,不但收入较低,也难以有一番事业。Arata慨叹,“日政府已在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但依然是社会很大的问题,正影响着我这个世代的人。”
他形容日本是个“老旧、保守”的社会,不能容纳他这种“异类”,只要与社会有点不一样,就很容易被忽略。他在这个社会感到很抑郁,也没太多朋友,所以毅然离开,“所以我的故事也跟《人间蒸发株式会社》很有关连,连系到日本‘消失’的现象。”
性别不平等、家暴迫使弱势社群“消失”
Andreas与Arata采访的对象均是有意“消失”的人,即便是深夜搬家公司的社长Saita,也因担忧失踪者的家属得知她的样貌会造成麻烦,而不愿意露面。后来,他们花了6年时间不停往返德国与日本制作这部纪录片,慢慢建立日本的人脉,也取得了受访者的信任。终于,受访者们均愿意在日本以外上映作为露面的条件。
Andreas 表示,《人间蒸发株式会社》的主角Saita替客人逃走,客人有各式各样“消失”的理由,“家庭暴力是‘人间蒸发’的最大成因,Saita一半的客人是家暴受害者,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依然是日本最大的问题。”Arata形容,日本对性别平等的意识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差,“有很多女性即使受到性暴力,也不会发声;也会有男性受女性家暴。”他续指,Saita的客人有一半是女性,当中有八至九成的人是因受家暴而选择“消失”。
《人间蒸发株式会社》团队在当地拍摄必须步步为营,因为西成区至今现时还是黑道活跃的地方,但Andreas却认为这些地方有存在的必要,“我很惊讶会有这些地方,这个地方是无家者的归处(Where they belong),有一个系统、一个社区让他们可以在这里生活。”
Andreas表示,电影中其中一名受访者Kanda因逃离黑道而到西成区生活, Kanda形容这个地方为世外桃源(Paradise), 因为他在那里不用再被人批判,可以自由地生活。他指出,这个地方同时是日本LGBT友善的社区,“有很多上年纪的同志,他们无法向家人出柜,而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活出自己。”
模糊的身份制度 给予逃逸空间
今年年初被日警通辑49年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份子桐岛聪患在病榻下自首,临终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日媒透露,这位1975年在银座韩国产业经济研究所引爆土制炸弹的青年,逃亡早期竟在新宿歌舞伎町一间人气餐厅打工,之后移居到神奈县,打工并结识女友,如此招摇,潜伏49年仍不为人知。
归根究底,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欠缺身份证制度,为日人提供“消失”的条件。Andreas指出,日本政府以前没有给国民派发身份证,不像香港或其他欧洲国家,国民没有持有身份证的义务,“没有身份证识别,人们可以随意到其他地方开展新生活。”My Number Card(个人编号卡)于2016年才正式于日本上线,政府会分发一个有12位数字的编号识别国民身份,然而到目前为止,取得My Number Card依然不是强制性的政策。
一旦有突发事,国民靠驾驶执照或国民保险证件证明身分,而日警除了在频繁出现罪行的地方如新宿歌舞伎町进行截查,在街上一般不会截查可疑人士。日本一直凭藉信任制度去维持治安,土生土长的日人对此不以为然,外国人却对这种模糊的身份证制度大惑不解。
2020年,日本东京歌舞伎町内,戴着防护口罩的警察正在巡逻 ( REUTERS / Issei Kato )
不论是《人间蒸发株式会社》记录西成区逃离人群的各种原因,还是官方提供的失踪数字,这也只是冰山一角。情愿离开生活圈的视线,隐世埋名的瑟缩在村落一隅继续生活,这种比躺平更躺平的避世心态,不仅折射出当地光怪陆离的社会,也延续了日本的隐士文化,这是城外人难以明瞭的心事。
歪脑网站
歪脑Instagram
歪脑Youtube
歪脑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