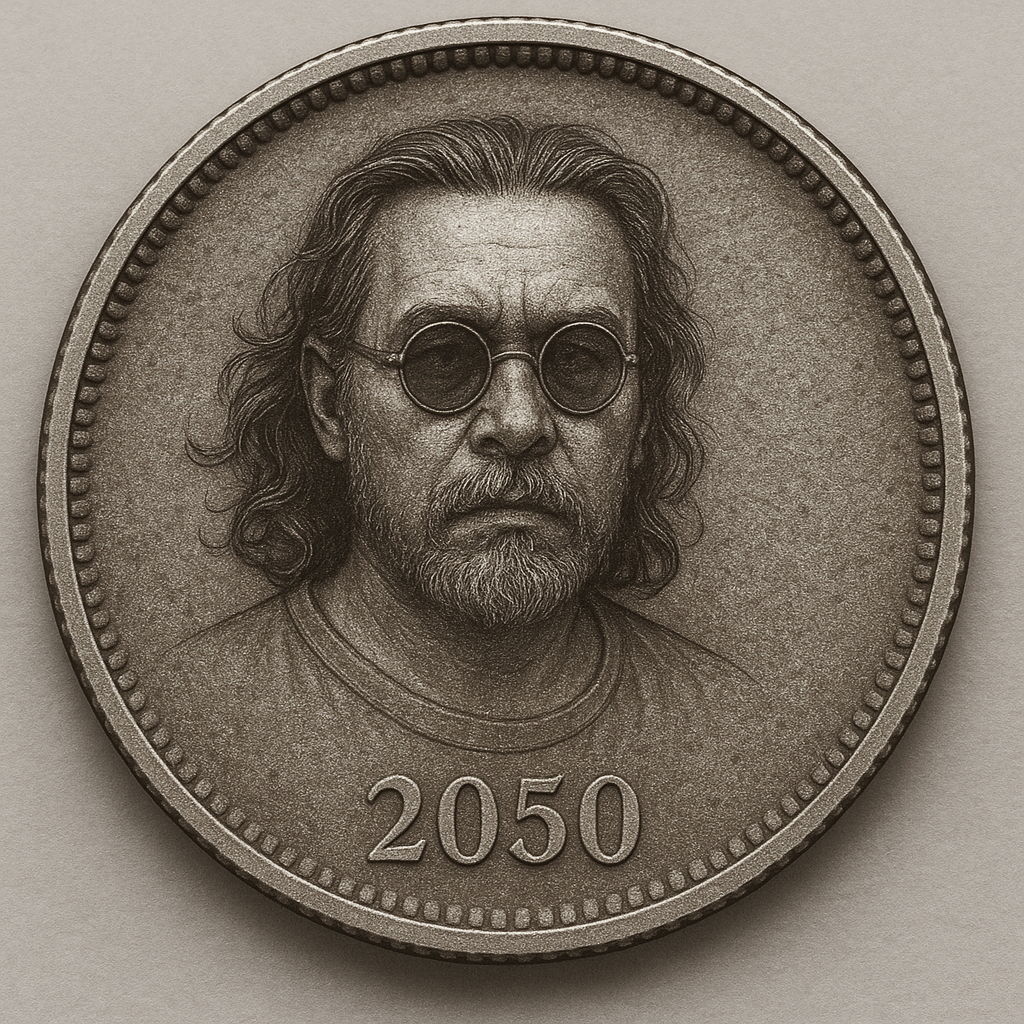咖啡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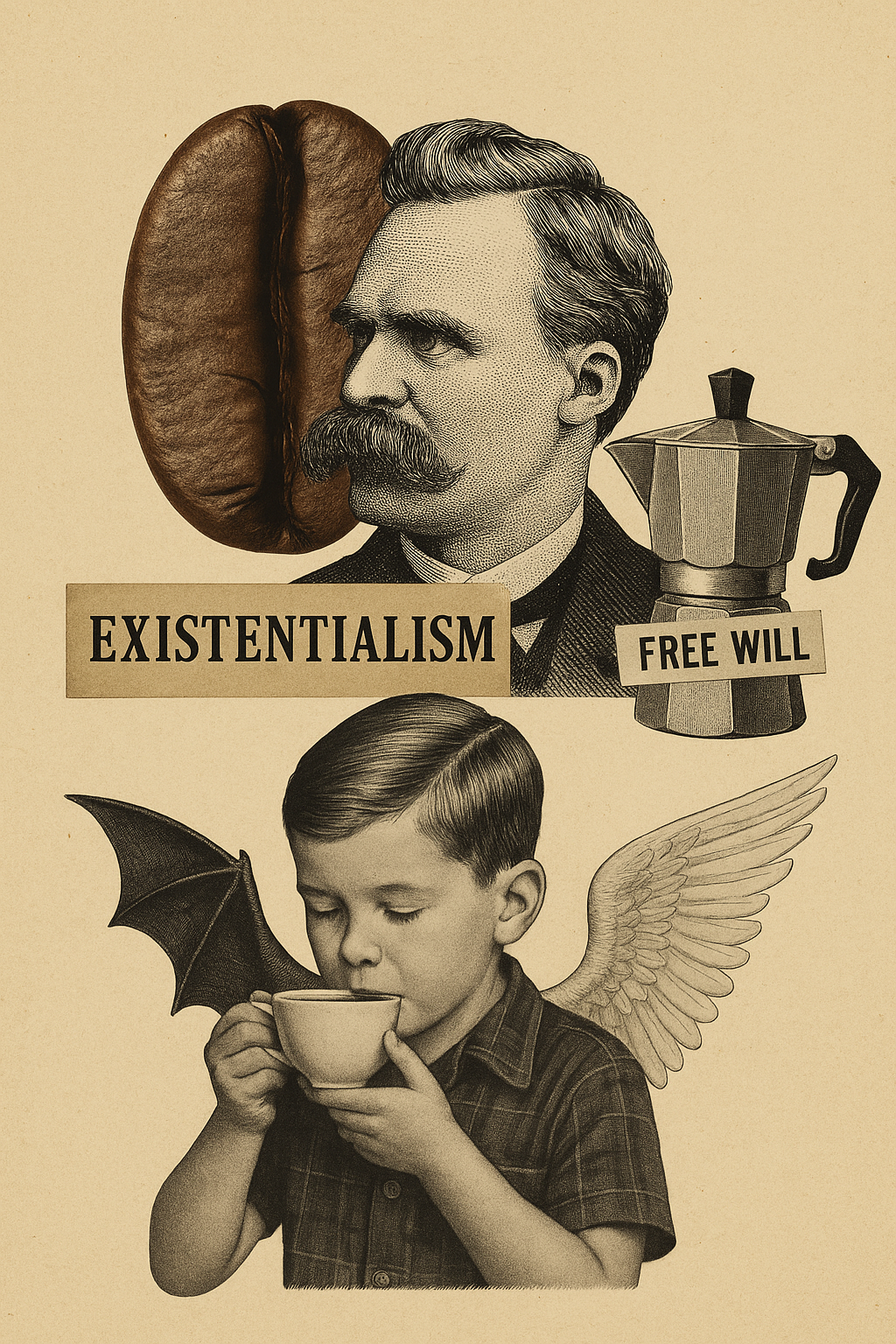
第一节】爆豆聲與尼采
我第一次买那家泰北农家的咖啡,是四年前的事。当时正逢一场“有机热”,什么都要有机,连花盆都得贴标签。我被“有机栽种、农家自烘”八个字迷住,脑海自动补上了一个身披麻布、满面皱纹的老人家,蹲在瓦罐前炒豆,背后还站着一只鸡。现在想想,那不是误会,是我自带的浪漫病。
包裹一到,快递员的喇叭急得像《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我却听成了炒豆子的爆裂声,神经条件反射般冲出去收货。撕开包装,一股熟悉的焦糖味扑面而来……以及一种隐隐的“糊感”。我倒了些进磨豆机,再烧水试喝。一口下去,只能说:太尼采了。苦是苦的,但苦得毫无意义,空洞得像是某种“超人”死后留下的气味。
于是我决定试试看中焙。豆子小,密度高,像个没睡饱的大学生。刚烘好那几天根本不能喝,青涩得像在家庭聚会上高谈理想的叛逆少年——味道情绪极不稳定,仿佛下一秒要吼出“我要自由”然后哭出来。
我把它放了一边,好几个星期不管。直到某天清早没豆喝了,才想着“炒都炒了,丢掉也浪费”,泡一杯来试试。结果意外惊喜:味道竟然变稳了,像少年经历了军训,变成一个会自己洗袜子的青年。我猜农家当初是想“驯服”它,才多烘了一会。果然,中焙才是它的归宿。第一周的锐利像发烧,七天之后,明亮的调性收了下来——就像一位突然懂事的少年,对你说:“叔,我不去柏林念哲学了,我想开间咖啡馆。”
从那天起,我决定长期观察它。每隔几个月就进几公斤,当作是追踪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最近,他们家推出“Whisky口味”咖啡豆,名字很唬人,我好奇又上当。结果是:依然烘过度,从尼采进化成了沙特——苦是更有哲学深度了,但还是不好喝。
奇怪的是,生豆味道却很迷人。发酵处理过,带着浓郁的酒香,像一杯你只敢闻不敢喝的单一麦芽。我尝试不同焙度,发现最香的时候,就是它还没完全发疯之前——像个喝醉后还保持礼貌的诗人。可惜,再下一单,它变成了“红酒口味”,整杯咖啡像刚被失恋的人哭过。
四年过去,他们家的豆子无论水洗还是发酵,都越来越有个性了。只要不是他们自己烘的,基本都值得一试。
【第二节】哲學家的杯測
〈哲學不是用來懂的,是用來活的〉
我喜歡哲學,雖然一直讀不太懂。這話聽起來像是對自己太寬容了,其實是事實。會開始讀,是因為一位同學。他不是哲學系的,但動不動就引用康德、海德格、維特根斯坦——我懷疑他有背過整本《哲學字典》。我一開始還佩服他口才好,後來覺得這人太囂張,決定買一整箱書準備與他決一死戰。
那箱書是我表哥從台灣幫我扛回來的。我讀了好幾年,一頁頁啃,像在爬一座聽說山頂有答案的山。爬到一半,那同學已經進入學術界,像仙人一樣消失了。我手裡握著那一堆尚未讀完的頁碼,彷彿手握尚方寶劍,卻已無仇人可斬。
後來我乾脆一個人跑去歐洲。想搞清楚那些哲學家為什麼寫得那麼難。結果到了那兒,我才發現:哦,原來他們是那麼活的。天氣陰鬱、人話少、公共交通準時得像一場儀式感;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是用公分量的,而是用存在主義來拉開的。他們寫的東西,不是用來懂的,是用來活的。
從那以後,我就比較少翻哲學書了。哲學,不僅僅是語言或學科,而是一種內在的結構。就像咖啡——它不只是一杯飲料,而是一種從童年就埋下的語言之外的記憶。
我不反對哲學,甚至尊敬每一位哲學家。只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抓緊的東西太多,時間有限,字太多了。尤其對於一個從小與文字有點隔閡的人來說,把這些需要高度抽象語言才能定形的東西給抓出來,有點不公平。我比較擅長抓的是語言以外的系統,例如味覺,例如結構感。
所以我後來喝咖啡,都用哲學家來形容豆子的味道:烘過頭的像尼采,年輕未穩的像沙特,發酵混亂的像福柯。有人覺得這太扯——誰會用哲學家來評估咖啡?但你要我說藍莓、葡萄乾、花香、柚子味什麼的,反而說不出口。那不是為了拼貼味覺成分,而是為了記住那一杯給你的感受。不是水果,是存在。
我的第一杯咖啡,出現在童年。家裡會泡一大壺黑咖啡,從早喝到晚,加糖——這就是今天人們說的「南洋咖啡」。當時只有兩種喝法:加糖或加煉奶。咖啡館裡會再進階一點,加淡奶加糖,但家裡嫌麻煩。
一開始全家一起喝。後來不知從哪兒聽來的傳說說小孩不能喝咖啡,大人便開始限制。可越是不讓,越想喝。為了不留證據,我不用杯子,直接從水壺咀吸,還會一邊喝一邊吐咖啡渣。現在回想起來,喝完洗個杯子不就沒事了嗎?可小孩當年不是這麼想。
後來大人發現我偷偷喝,於是又換回茶葉了。只有在下午茶時間,大人才會泡一小壺自己喝。我只好轉向偷吃咖啡粉,含在嘴裡像是黑暗中的儀式。這是我與咖啡最初的關係,一種偷來的,苦苦的,無以名狀的記憶。
【第三节】
〈烧焦轮胎与一口臭屁:本地咖啡界的真香定律〉
南洋咖啡与雀巢咖啡,听起来像是一个人情世故的老油条,另一个则是躲在角落的老实人。别看他们都用热水冲,冲出来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南洋咖啡,看似粗鲁,其实讲究得很。香不香,全靠几间“有手艺的”茶室。家里泡再多次,也泡不出那个味儿。你以为是咖啡粉的问题?不,问题在锅、在火、在那只几十年没洗干净的滤布。
至于雀巢,它有个优点——稳定。你在家冲,它就是那个味;在茶室冲,还是那个味,只是贵一毛钱而已。通常只有当你知道那茶室的师傅“手势不太行”,才会点雀巢,省得喝出一杯失望。至于我,当上漫画家之后,它就成了我赶稿的燃料——像汽车加油,只求能跑,不管排放。
但说实话,雀巢咖啡没办法像南洋咖啡粉那样可以“干啃”,咬下去像嚼煤渣。它的苦,是不能玩笑的苦,一口下去像是被人生教育了一番。
香气呢?刚开始我也觉得它多少还是有点香的,很多年都找不到那气味的形容词。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一场车祸现场,鼻子一皱——找到了:烧焦的轮胎味。就这样,它的灵魂被命名了。
后来本地开始流行三合一咖啡,把咖啡、糖和奶精塞进一个小包里,只要热水一冲,就有味道、有甜、有力气,连名字都不必多想了。雀巢也跟着推出了三合一,可惜打不回失去的江山——一如打工仔再努力也爬不上老板的空降儿子。
三合一的崛起不是偶然。那香气,不再是单靠Robusta豆的焦苦支撑,而是混了点什么神秘豆——后来才知道,是Liberica。
这个名字你可能陌生,但你喝过的每一杯南洋咖啡,八成都曾在他身上靠香气维生。他就是那种“背后默默努力”的角色,没露脸,却主导了一整个时代的味道。直到最近,才有一家来自柔佛的咖啡馆愿意给他正名。感谢他们,总算还Liberica一个江湖地位。
不过,要说Liberica的味道……真的不是谁都能接受。
浅焙的时候,有一种蟑螂味,不是玩笑,那是认真形容。深焙呢? 妙,简直就是一口自己的臭屁——浓、热、直冲脑门,关键是还挺满意的。
这话说出来不好听,但你要真喝过那种“臭得自带自信”的味道,就会懂了。
我个人偏好的是中深焙。甜感里藏着一丝微酸,滑过喉咙后就像灵魂飘上去了,脑门那一抹浓郁像天灵盖被敲了一下。那不是花香,不是柑橘调,也不是什么巧克力尾韵,而是一个词——存在。就像哲学不是拿来懂的,是拿来活的一样,Liberica的香,是喝进身体、叫你闭嘴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