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1《地狱图书馆》:独裁者的著作如何统治世界|徐賁
野獸按:進來讀了《波士頓書評》的幾篇徐賁先生的文章,開讀他的《暴政史》。試著在公號上推送,想分享給更多的內地書友。
《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美化专制独裁的心理机制与当代回声》竟然推送成功了,而《地狱图书馆:独裁者的著作如何统治世界》就沒法子了。在這裡做個備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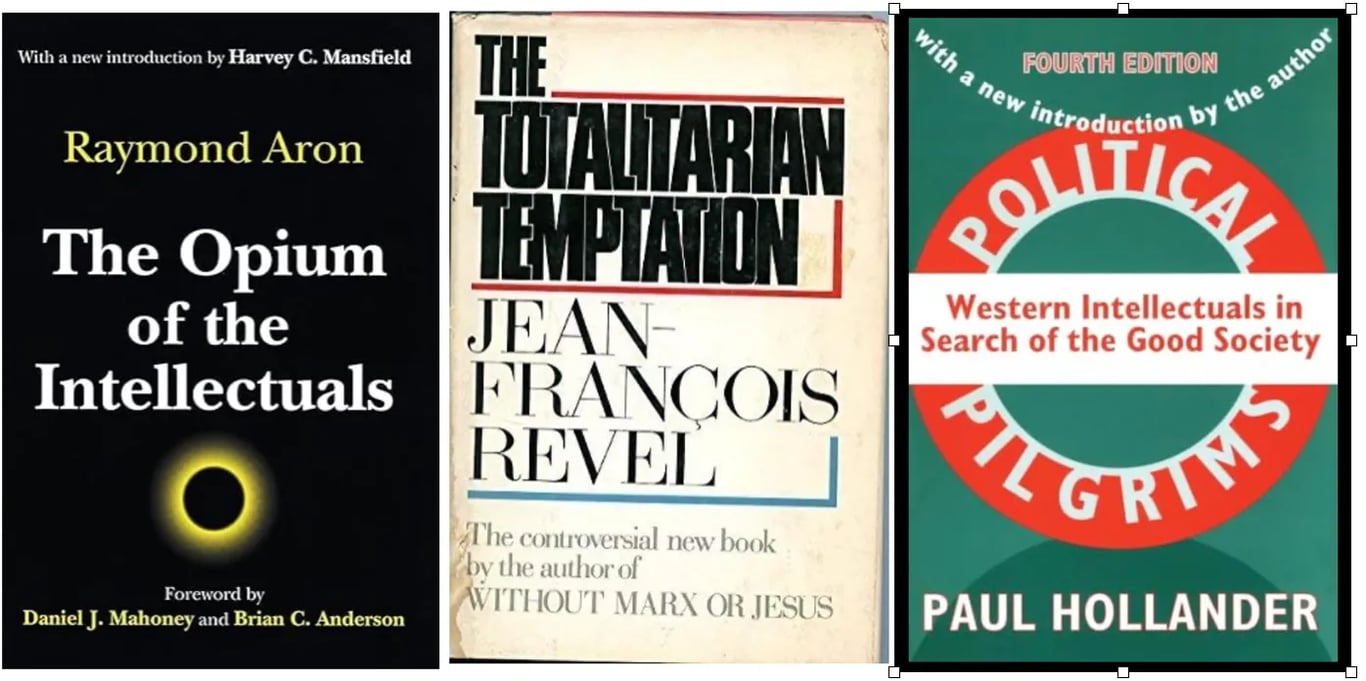
徐贲 | 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美化专制独裁的心理机制与当代回声
JUN 25, 2025
編者按: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價值似乎成為共識;曾經冷战的铁幕也早已崩塌,形式上的極權國家在數量上減少了,但是為什麼到了今天,環顧世界,俄羅斯、伊朗、哈馬斯等專制政權依然在世界上狼環虎視,甚至形成獨裁者聯盟與民主世界對峙,甚至得到了當代知識分子的辯護。
學者徐賁以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讓-弗朗索瓦·雷韋爾(Jean-François Revel)及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的思想為核心,分別從思想錯誤、道德偽善與心理病態三個維度揭示知識分子美化極權的根源。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批判知識分子以「歷史必然性」為極權暴力開脫,將其視為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並與薩特、梅洛-龐蒂的思想決裂,強調理性與現實責任。雷韋爾在《極權主義的誘惑》中揭露知識分子的選擇性道德憤怒,對民主社會不公過度批判,卻對蘇聯勞改營、毛澤東大躍進等暴行沉默,顯示其偽善的自我感動機制。霍蘭德在《政治朝聖者》中從匈牙利革命的親歷者視角,剖析知識分子對異域極權的理想化,視其為對西方社會不滿的心理投射,形成「投射性烏托邦」。徐賁還指出這一心理機制在21世紀的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及伊朗代理人戰爭等背景下依然延續,當代知識分子以「反帝」「反殖」等新話語為俄羅斯、伊朗、哈馬斯等專制政權辯護,重演歷史錯誤。
徐賁強調,知識分子的這種自我欺騙不僅是思想與道德的墮落,更是心理結構的病態,呼籲知識分子直面現實、拒絕謊言,重建批判理性與道德勇氣,以抵禦新形態的極權誘惑。
三、保罗·霍兰德与《政治朝圣者》:从匈牙利悲剧到西方伪善的心理剖析
如果说雷蒙·阿隆和让-弗朗索瓦·雷韦尔的批判,主要来自学术理性与道德良知的驱动,那么保罗·霍兰德的批判则带有一种亲历者的悲剧意识。阿隆与雷韦尔的知识背景均扎根于法国知识界,他们身处于那个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以“激进左翼”文化著称的巴黎思想圈,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更多来自理性反思与道德责任;而霍兰德,则带着一种从废墟与苦难中走出的幸存者意识,这种背景差异使他的批判具有更强烈的个人记忆与心理切肤感。
霍兰德出生于匈牙利,亲历了二战后东欧苏联式极权主义在匈牙利的全面扩张。他的青春岁月正是在谎言、镇压与恐惧的政治氛围中度过的。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被苏联坦克血腥镇压的场景,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精神创伤。在逃亡到西方之后,他亲眼目睹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中国、古巴等极权政权的理想化,这种认知落差成为促使他写作《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的直接动因。
正因如此,霍兰德对知识分子美化极权主义的批判,不再只是思想上的驳斥或道德上的愤怒,而是一种幸存者对旁观者冷漠与伪善的绝望控诉。对阿隆而言,极权主义是思想错误;对雷韦尔而言,是人格伪善;但对霍兰德而言,极权主义首先是一种切实发生的巨大灾难,而那些在巴黎咖啡馆里谈论“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对着真实的废墟与鲜血发表“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演说”。
更具洞察力的是,霍兰德敏锐捕捉到了这些知识分子心理活动中的投射机制(projection mechanism)。他在《政治朝圣者》中通过大量实例——从伯特兰·罗素、萧伯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一一揭示这些西方“进步人士”如何对异域极权政权抱有非理性的理想化期待。霍兰德指出,这种心理机制的本质,是一种心理补偿(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因为对自己所在社会感到不满、焦虑和羞愧,所以需要一个“纯洁的他者”,一个“他方乌托邦”,来填补内心的道德焦虑。
霍兰德特别强调,这些“政治朝圣者”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些谎言,不是因为被欺骗,而是因为他们主动需要这些谎言来构建自我心理的完整性。他甚至用一种带有精神病理学特征的语言,将这种行为视作一种集体性的自欺心理病态(collective self-deception psychopathology)。他们不是不知道极权的暴力与恐怖,而是下意识地选择不去知道,选择性失明,以便维持“我站在正义一边”的幻觉。
与阿隆和雷韦尔相比,霍兰德的语言更加冷静,带着一种近乎学术化的克制——但这份克制背后,恰恰隐藏着更深刻的愤怒与痛苦。阿隆和雷韦尔批判的是“错误”和“伪善”,霍兰德揭示的是心理结构的病态化倾向,是知识分子如何在认知结构中主动制造谎言来逃避内心冲突。他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进入了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维度。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因为霍兰德来自匈牙利这个极权制度的直接受害国,所以他的视角天然带有一种**“真实受害者的眼睛”。这种视角让他对西方知识分子“投射性乌托邦”(projective utopianism)的机制有着天然的敏感。他的愤怒不是来自意识形态争论的失败,而是来自对历史真实被践踏**的痛感。
因此,阿隆、雷韦尔与霍兰德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思想—经验对照结构:
阿隆代表着哲学理性,从逻辑错误入手,揭露极权主义神话背后的认识论骗局。雷韦尔代表着道德正义,从人格伪善入手,揭示知识分子如何用双重标准维护自己的道德虚伪感。霍兰德代表着历史记忆,以亲历者的愤怒,揭示心理机制中的自欺倾向与病态补偿结构。
三人之间的差异,正是思想批判的三个维度:思想之错、人格之伪、心理之病。阿隆为这一体系奠基,雷韦尔将它推进到道德结构层面,霍兰德则将其引向心理学与文化认知的深层。
对当代世界而言,霍兰德的贡献尤为重要。因为今天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往往更加柔性与符号化,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独裁统治”,而是披上“反帝”“反殖”“解放运动”的道德外衣,形成新的心理迷宫。而西方知识分子依然在寻找新的乌托邦对象,新的“纯洁他者”,以此对抗他们对本国不公的焦虑与羞愧。霍兰德揭示的投射性乌托邦心理结构,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哪怕极权的灾难一再重演,知识分子依然愿意为之辩护。
霍兰德的匈牙利背景与阿隆、雷韦尔的法国背景之间的张力,也反映出欧洲东西方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认知差异的本质。法国知识界固守在理性与道德优越感构筑的象牙塔之中,而来自东欧废墟的声音,则以亲历者的身份,撕裂了这一虚伪的道德叙事。霍兰德让西方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现实:当你们为乌托邦歌唱时,你们歌声的回音正好在废墟之间回荡。
四 专制独裁阵营与反专制独裁阵营中的知识分子姿态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与极权主义之间复杂的心理纠葛,阿隆、雷韦尔与霍兰德的批判性著作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一项未竟的启蒙工程。这一启蒙并非针对大众的“扫盲”,而是针对知识阶层自身的自我净化。他们揭示的,不仅是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本身的暴力结构,更是知识分子参与制造谎言、粉饰暴力、逃避真相的机制。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控诉,更是对未来的警告。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但专制独裁公然企图改变二战后世界民主价值共识的时代。形式上的极权国家在数量上减少了,曾经的冷战铁幕早已崩塌,但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意识形态逻辑和道德伪善却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在世界政治与舆论场中发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世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独裁阵营与反独裁阵营的全球性对峙,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斗争,更是一场涉及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道德选择的精神战争。
以俄乌战争为例,普京政权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打压异见、发动侵略战争的典型现代独裁体制。然而,在许多自诩“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话语中,俄罗斯却被描述为“反对北约霸权”的“反帝先锋”,乌克兰则反而成为“美帝走狗”的象征。这种选择性正义,正是霍兰德揭示的“投射性乌托邦”在新世纪的变体——那些对西方自身存在的不公义愤怒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抵抗者”的角色来安慰自己内心的道德焦虑。俄罗斯、伊朗,甚至哈马斯,便被包装成新的“纯洁他者”,成为他们心灵乌托邦的替身。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以哈冲突中。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选择性忽视哈马斯的暴力恐怖主义本质,将其包装成“反殖民”的解放力量。他们有时甚至不惜为屠杀平民的行为进行模糊化辩护,只因为这个行为发生在他们认定的“被压迫者阵营”。这种逻辑轨迹,与二十世纪为苏联古拉格、大清洗辩护的“历史宽恕论”高度相似,只是换上了新的词汇,披上了新的身份政治外衣。
这种心理结构的延续,恰恰验证了阿隆、雷韦尔、霍兰德三者批判的当代相关性。阿隆早已揭示,“历史必然性”的神话只是宗教信仰的世俗替代,今天的“反殖”“反帝”叙事本质上就是新的神话编织。雷韦尔尖锐指出,知识分子热衷谴责自己国家的不公,却甘愿忽视异域极权的暴行,原因只是为了维系虚假的道德优越感。而霍兰德则深刻揭示,这种行为的深层动因,不仅是思想懒惰或政治利益,更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他们需要一个纯洁的“他者”,来逃避面对自我社会困境的勇气与责任。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独裁阵营,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国际网络: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以及多个中东代理人武装,这些政权不仅在物质与军事层面结盟,更在话语体系与道德象征体系上进行联动。令人遗憾的是,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依然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些极权势力的“话语同谋”,用“反美帝”“反殖民”“全球南方”的旗帜,将这些残酷的独裁者塑造成“世界正义的新代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投射性乌托邦”的机制,往往发生在那些本国享受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政治权利保障最充分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正如霍兰德所指出:“那些拥有最多自由的人,反而最热衷于为不自由辩护。”这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政治的一大悲剧。
然而,另一方面,反独裁阵营同样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共识。乌克兰的抵抗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战争,更成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自决权的象征。伊朗国内反对神权极权的“女人,生命,自由”运动,同样是一场反极权与反父权结构合流的民主觉醒。这些现实正在不断提醒知识分子们,真正的“进步”,从来不在于虚构一个远方的纯洁乌托邦,而在于维护每一个现实中具体人的自由与尊严。
阿隆的怀疑主义、雷韦尔的道德愤怒与霍兰德的心理剖析,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立场时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同传递的最核心讯息就是:不要用远方虚构的正义,掩盖对身边真实暴力的视而不见;不要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为不自由的暴政提供道德辩护。知识分子的责任,首先是面对真实,面对事实,面对自身的认知结构,而不是用道德幻想为暴力镀金。
今天,新的极权主义正在以新的,尤其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幌子的专制独裁形式回归,新的“投射性乌托邦”仍在知识分子心中运作。但同样,新的反极权,反专制独裁的力量也在形成,新的启蒙任务也在召唤。阿隆、雷韦尔与霍兰德的遗产,不是过去思想的注脚,而是当下责任的起点。在独裁阵营与反独裁阵营的世界性对峙中,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启蒙,拒绝自欺,拒绝伪善,拒绝“美丽的谎言”,才有可能重新成为自由世界真正的道德先锋。
结语:
在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换上新的面具、旧有神话以新的语言卷土重来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回到反专制和反极权的思想遗产之中,重建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勇气与批判自觉。逃避复杂现实、投射虚假乌托邦,从来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只有直视真实世界的残酷与矛盾,才可能避免在“正义”的名义下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
美化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这从来不仅仅是独裁者的阴谋,它更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自我欺骗的共谋,是理性滑向神话、道德沦为姿态、真理让位于心理安慰的过程。阿隆的冷静怀疑、雷韦尔的愤怒揭露与霍兰德的悲剧见证,共同构成了一种至今仍未完成的精神启蒙。在独裁与反独裁阵营的全球性对峙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不仅是立场之争,更是人格尊严与精神诚实的试炼。
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才是专制独裁和极权幽灵真正的庇护所。而真正的启蒙,不是制造新的乌托邦,而是勇敢直视那个令人不适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的诱惑远未结束,而思想的责任,也才刚刚开始。
Aron, Raymond.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62.
Revel, Jean-François.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Paul Hollander.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原版出版: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Second Edit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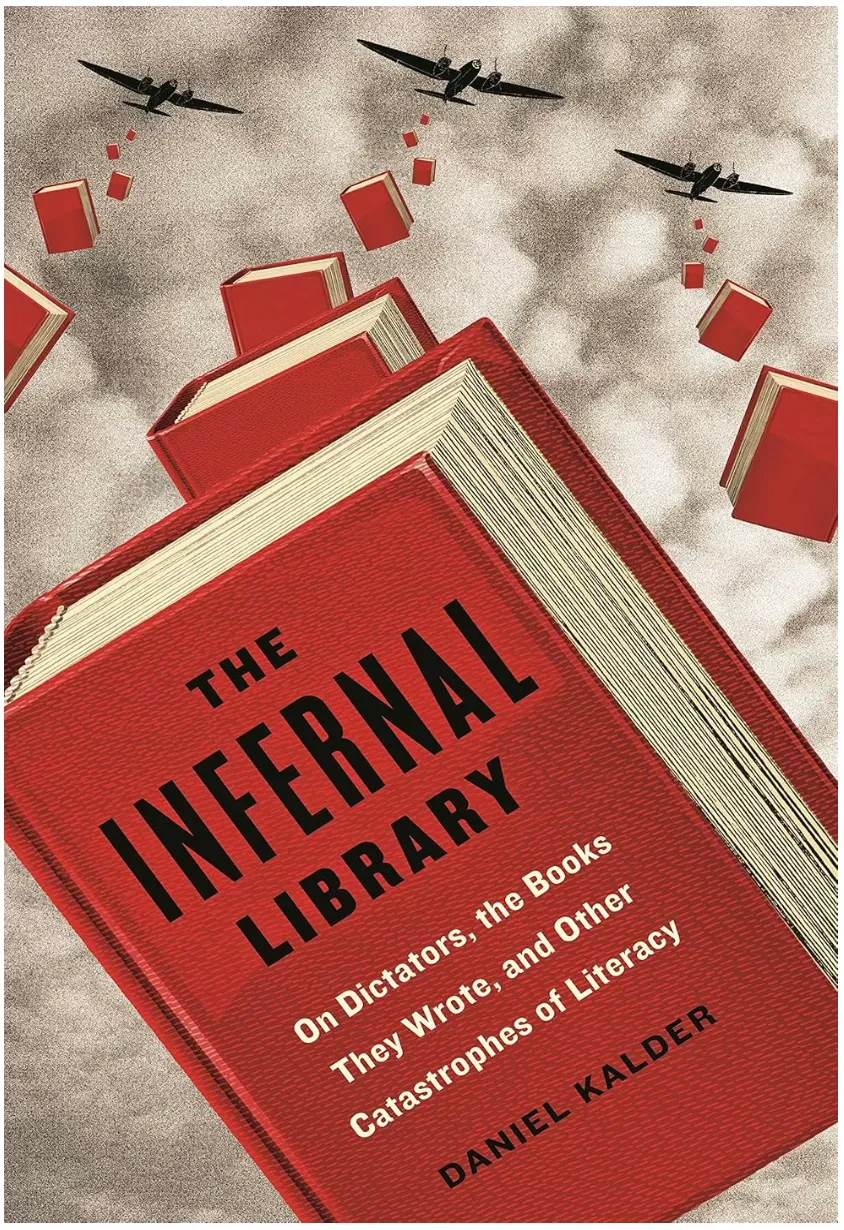
徐贲 | 《地狱图书馆》:独裁者的著作如何统治世界
JUL 10, 2025
編者按:丹尼爾·卡爾德的《地獄圖書館》以20世紀獨裁者(如列寧、希特勒、毛澤東)的著作為切入點,揭示語言如何在極權統治下異化為控制工具。卡爾德通過閱讀這些邏輯混亂、空洞冗長的「毒書」,分析其將閱讀從自由思辨扭曲為忠誠儀式,語言從溝通工具淪為權力延伸的機制,並探討獨裁者從「失敗作家」到強迫民眾接受其文本的心理轉變。學者徐賁強調該書不僅反思歷史上語言暴政的運作邏輯,還警示當代信息社會中算法、煽動性話語等新形式的語言控制,呼籲保持批判性閱讀與語言自由,以維護思想獨立與文明發展。
6月16日
《地狱图书馆》(The Infernal Library: On Dictators, the Books They Wrote, and Other Catastrophes of Literacy)是英国作家丹尼尔·卡尔德(Daniel Kalder)于2018年出版的一部独特非虚构作品,副标题为《论独裁者、他们写的书,以及其他文字灾难》。这部由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的著作,以一种既讽刺又严肃的笔调,深入剖析了20世纪那些臭名昭著的极权领导人——从列宁、斯大林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从毛泽东、卡斯特罗到卡扎菲、萨达姆——所留下的文字遗产。
卡尔德用"地狱图书馆"这一形象的隐喻,精准地概括了这些独裁者著作的本质特征。这些文本往往逻辑混乱、冗长乏味、重复空洞,然而正是因为其作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它们却成为了亿万民众必须学习、背诵甚至信仰的圣典。在这种扭曲的现实中,阅读——本应是通向自由与思辨的桥梁——被彻底异化为灌输与压迫的工具。
更为可贵的是,卡尔德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嘲讽。作为一名自称的"异议读者",他花费数年时间强迫自己通读这些"毒书",试图从内部理解它们的结构逻辑、修辞模式与影响机制。这种近乎自虐的阅读体验,让他得以从读者的切身感受出发,深刻反思文字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暴力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地狱图书馆》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它揭示了在意识形态的绝对支配下,语言如何失去其本真的意义,却反过来制造出一种虚假而强烈的意义感。更令人深思的是,在那些权力结构尚未完全崩解、民众意识尚未彻底觉醒的灰色地带中,阅读行为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它不再是个体的自主选择,而沦为集体顺从的仪式。这种语言、权力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共谋关系,恰恰构成了极权专制的核心特征。
因此,《地狱图书馆》不仅仅是一部政治文学评论,更是一部深具思想史价值的著作。它不但为我们理解20世纪极权专制的文化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更为当下关于后极权写作、身份漂移与语言失效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在一个信息泛滥而意义稀薄的时代,重新审视文字与权力的关系,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必要。
一 文字的蜕变与语言的专制
卡尔德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指出这些独裁者的著作并非"思想"之作,而是"统治"之书。这一洞察揭示了极权主义文化生产的根本特征:文字不再承载思辨的功能,而是沦为权力意志的直接延伸。这些著作往往充满冗长的空话、重复的口号、逻辑的混乱,缺乏真正的分析和怀疑,却被精心包装成不可质疑的"真理文本"。
在这种语言的专制化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词汇的内容被掏空,语言的指称功能被彻底颠覆。独裁者的文字不是为了描述现实,而是为了重新定义现实。"人民"不再指向具体的个体,而成为抽象的政治符号;"自由"不再意味着选择的权利,而被重新阐释为服从的义务;"真理"不再需要验证,而成为权威的同义词。这种语言的异化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系统性破坏。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文字的蜕变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认知结构的根本性扭曲。当语言失去了其沟通和思考的本质功能,转而成为灌输、命令和控制的工具时,阅读者的主体性也随之消解。读者不再是文本的对话者,而成为文本的接受器;不再是意义的创造者,而成为意义的被动消费者。在这种语境下,文字从通向自由的手段堕落为强化奴役的机制,这种转变的彻底性和隐蔽性,正是极权主义文化统治的精妙之处。
然而,这种语言的专制化并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它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更为隐蔽的形式。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语言的碎片化、标签化和情绪化,同样可能导致思辨能力的退化。当复杂的社会现象被简化为简单的标签,当深度的思考被快速的反应所取代,当多元的声音被单一的话语所覆盖时,我们或许正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语言专制化。
因此,重新审视文字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对当下的警醒。在一个信息传播日益便捷而意义生产日益稀薄的时代,保持语言的批判性和思辨性,或许是抵抗各种形式的文字专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批判性的对话,而非被动的接受;真正的写作应该是对现实的质疑,而非对权威的复述。
二 作为服从仪式和驯服行为的“阅读”
卡尔德敏锐地指出,在极权和专制独裁政体中,阅读这些独裁者文本并非出于真正的兴趣或求知欲,而是一种政治义务的履行。斯大林全集、毛泽东语录、金日成著作、卡扎菲《绿皮书》或希特勒《我的奋斗》被强制学习与背诵,形成了一种深刻的"阅读的虚假性"。这种阅读不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而是为了在公共空间中展现忠诚与顺从,从而彻底消解了阅读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与个体化特质。
这种阅读仪式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最基本认知活动的系统性扭曲。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对话性行为——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与自身经验进行多重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理解和批判性思考。然而,在极权语境下,这种对话性被彻底切断。读者不再是文本的质疑者和阐释者,而成为文本的复述者和传播者。阅读从一种主动的智识活动,退化为一种被动的模仿行为。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仪式化的阅读创造了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想象。当千万人同时诵读同一段文字、背诵同一套话语时,表面上形成了思想的统一,实际上却是个体思维的集体消失。这种看似壮观的集体阅读场景,掩盖了思想多样性的彻底丧失。每个人都在"阅读",却没有人在真正思考;每个人都在"学习",却没有人在真正质疑。
这种阅读方式的危险性在于它的自我强化机制。一旦阅读成为展示忠诚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就会被视为危险的异端。那些试图在文本中寻找矛盾、提出疑问的读者,不仅会面临政治风险,更会在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道德压力。久而久之,自我审查成为一种内化的习惯,批判性阅读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萎缩消失。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阅读的仪式化现象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极权社会。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某些文本因为其权威性或社会压力而被强制性地"必读",读者往往更关注是否读过、是否能够引用,而非是否真正理解和批判。社交媒体时代的"打卡式阅读"、学术界的"经典崇拜"、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学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这种仪式化阅读的模式。
因此,重新激活阅读的批判性功能,成为抵抗各种形式文化专制的关键所在。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它要求读者有勇气质疑文本的权威,有能力识别话语的陷阱,有智慧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判断。只有当阅读重新成为一种个体化的、批判性的、对话性的活动时,文字才能重新获得其解放的力量,而不是沦为奴役的工具。
这或许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警示:在任何时代,保持阅读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是维护思想自由的最后防线。当我们面对任何声称不容质疑的文本时,最好的回应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勇敢的提问。
三 权力与文本的共谋结构
卡尔德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恰恰是这些书的糟糕程度——它们的极端、虚假、荒谬、暴力、伪善、空洞、难以忍受——最直接地展现了权力的全能性。这些文本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大量出版、被奉为不朽的"圣典",并非因为其思想价值或文学成就,而完全是因为权力意志的强制推动,使它们得以凌驾于一切质量标准和理性判断之上。在这种机制下,"写作"不再是个体创造性的表达,而成为极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语言的生产直接服从于权力的再生产逻辑。
这种权力与文本的共谋结构,揭示了极权主义文化生产的深层机制。在正常的文化生态中,文本的价值通过读者的自由选择、批评家的专业评判、时间的历史检验等多重机制来确立。然而,在极权体制下,这些自然的筛选机制被人为地中断或扭曲。权力直接介入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创造出一套完全脱离质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文本的"伟大"和"英明"不取决于其思想深度或艺术成就,而取决于作者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意志的需要。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共谋结构具有自我证明的循环逻辑。糟糕文本的广泛传播本身就成为权力威慑的一种展示:既然连这样明显缺乏价值的作品都能被强制推广,那么权力的触角究竟能延伸到何种程度?这种"以糟糕证明全能"的逻辑,实际上是对理性评判体系的公然挑战。它向民众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客观标准都是无效的,任何个人判断都是多余的。
这种权力与文本的共谋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写作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思想或情感,而是为了服务于权力的政治需要。作者——无论是独裁者本人还是其他被指派的写作者——都成为权力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创作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生产而非文化生产。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使文化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谋结构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新的表现形式。在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中,某些文本的成功同样可能与其内在价值无关,而更多地依赖于权力资本的推动、媒体的炒作、网络效应的放大。虽然这种商业化的文本生产机制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化生产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差异,但其背后都存在着权力(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对文本价值判断的直接干预。
此外,数字时代的算法推荐机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应。当文本的传播不再主要依赖于读者的主动选择,而是由算法根据某种预设逻辑进行分发时,我们同样面临着"权力意志"(此时是技术权力)介入文本流通的问题。虽然这种技术性介入在表面上显得中性和客观,但其背后同样隐藏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考量。
因此,理解权力与文本之间的共谋结构,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当代文化生产机制的深度反思。在任何时代,当文本的价值不再由其内在品质决定,而是由外在权力确定时,我们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真正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是一个文本价值能够通过多元化、开放性的评判机制得到公正确立的生态。只有在这样的生态中,写作才能重新成为自由表达的行为,阅读才能重新成为独立思考的过程,而文字也才能重新获得其启蒙和解放的本源力量。
四 历史记忆与阅读“毒书”的必要
尽管这些文本令人深感不适,卡尔德坚持认为"必须阅读它们",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极权主义是如何通过语言这一看似无害的工具来构建和操控现实的。他以"异议阅读者"自居,以一种既反讽又严肃的姿态勇敢地进入这些"地狱文库",试图从中解剖语言暴政的深层机制。他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文字历史,不去理解它们运作的逻辑,那么它们的幽灵很可能会借尸还魂,以更加隐蔽和狡猾的新形式重返当代政治舞台。
这种"毒书"阅读的必要性,实际上触及了历史记忆保存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事实的记述——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件。然而,卡尔德的工作提醒我们,仅仅记录外在的历史事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深入理解那些推动历史事件发生的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和意识形态机制。这些"毒书"虽然在思想上贫瘠,在逻辑上混乱,但它们却是理解极权主义内在运作逻辑的珍贵"化石"。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修辞策略、论证方式、情绪动员手段,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极权统治者是如何一步步瓦解理性思维、操控民众情感、重塑社会现实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毒书"阅读具有强烈的预警功能。历史的悲剧往往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以变异的形式螺旋式地回归。当代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话语、极化的意识形态对立、简化的敌我二分法、情绪化的政治动员,都可能在这些历史文本中找到相似的修辞模式和操作手法。通过深入研读这些"毒书",我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免疫力"——当类似的话语模式在当代政治中出现时,我们能够迅速识别其危险性,而不会被其表面的合理性或情感的煽动性所迷惑。
然而,这种"毒书"阅读也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和心理挑战。正如卡尔德在书中坦言的那样,长期浸润在这些充满仇恨、谎言和暴力的文本中,对读者的心理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阅读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挑战,更是道德勇气的考验。它要求读者既要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进行客观分析,又要承受这些文本所传递的负面情绪和扭曲价值观的冲击。这种矛盾的阅读体验,恰恰体现了历史记忆保存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毒书"阅读的必要性变得愈加迫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用于洗脑的APP程序、各种极端思想和煽动性言论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培养民众识别和抵抗有害话语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和方便。通过研读历史上的"毒书",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病理学"知识体系,为识别当代政治话语中的危险因素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这种阅读还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许多国家,对极权主义历史的教育往往停留在事实层面,很少深入到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和分析这些历史文本(当然需要在适当的指导和保护措施下),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极权主义的本质,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历史敏感性。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仇恨,而是为了培养智慧;不是为了延续分裂,而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因此,卡尔德倡导的"毒书"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勇敢的历史担当。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记住历史的光明面,也要直面历史的黑暗面;不仅要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也要深入理解人类堕落的深刻教训。只有通过这种痛苦而必要的阅读,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这或许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它教会我们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如何在面对人性之恶时依然坚守人性之善。
五 失败的作家与成功的独裁者
卡尔德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许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都曾怀抱着成为作家和诗人的梦想,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失败,恰恰促使他们通过获取政治权力来强行实现"写作的胜利"。希特勒、毛泽东、卡扎菲等人在青少年或青年时期都曾试图成为艺术家或诗人,当这些梦想在正常的文学竞争中破灭后,他们最终将整个国家变成了被迫的"读者"。这种现象揭示了创作欲与控制欲之间深层而危险的心理关系,也反映了语言在现代政治中所呈现的"变态性"特征。
这种从"失败的作家"到"成功的独裁者"的转变,实际上暴露了一种扭曲的补偿心理机制。在正常的文学生态中,作家必须通过作品的内在价值来赢得读者的认可,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精湛的技巧、真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自由选择。然而,对于那些在这种自然竞争中失败的人来说,政治权力提供了一条"捷径"——通过强制手段获得本应通过才华赢得的关注和"崇拜"。
这种心理机制的危险性在于它将文学创作的失败转化为政治控制的动机。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文学上的成功时,他可能会试图通过控制整个话语体系来实现这种成功。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中,如果读者不愿意主动阅读他的作品,那就强迫他们阅读;如果批评家不认可他的才华,那就消灭批评家;如果文学史不收录他的作品,那就重写文学史。这种从说服转向强制、从竞争转向垄断的心理转变,恰恰体现了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
更深层次上,这种现象反映了现代政治中"表演性"和"叙事性"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主要通过暴力、血缘或宗教来合法化,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越来越依赖于话语的构建和叙事的塑造。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强烈表达欲望但缺乏真正才华的人,往往会被政治舞台的巨大诱惑所吸引。政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将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作品",将全体民众当作自己的"读者"。
这种错位还揭示了艺术冲动与权力冲动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表面上看,艺术追求的是美和真理,权力追求的是控制和支配,两者似乎截然不同。但在某些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冲动可能共享着相同的根源:对关注的渴望、对影响力的追求、对不朽的向往。当艺术冲动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得到满足时,它可能会寻找其他的出口,而政治权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有效的替代性满足途径。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失败作家"现象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新的表现形式。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了表达和"出版"的机会,但这种机会的普及也加剧了注意力的竞争。那些无法在正常的内容竞争中获得关注的人,可能会转向更加极端、更加煽动性的表达方式。虽然他们可能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但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暴力、仇恨言论、极端观点来强制获得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失败作家转向独裁者"的心理机制。
此外,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成功"的定义和实现路径。当社会过度强调竞争和成功,却缺乏对失败的包容和理解时,那些在某一领域失败的人可能会寻找其他更加危险的补偿方式。因此,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社会评价体系,为不同类型的才能提供不同的发展空间,或许是防止"失败作家"转向"成功独裁者"的重要途径。
最终,卡尔德揭示的这种错位现象,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的一个深刻警示:当文字的自由竞争被政治的强制垄断所替代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多样性,更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尊严。真正的文学成功应该建立在才华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是权力和强制;真正的政治领导应该服务于民众的福祉,而不是个人的虚荣和补偿。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错位的危险性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文学的纯洁性和政治的正当性。
结语:
《地狱图书馆》揭示了文字与权力结合时的毁灭性力量。卡尔德的敏锐阅读向我们展示,极权主义如何将人类最基本的智识活动——阅读与写作——转化为心灵控制的工具。这部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揭露了语言暴政的完整机制:词汇被掏空意义,阅读沦为政治仪式,权力直接操控文本生产。当"人民"、"自由"、"革命"、"真理"等词汇失去真实内涵,成为权力操控现实的符号时,个体的主体性和批判能力便彻底瓦解。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语言专制化并未随历史终结。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算法推荐、回音室效应等新现象正以不同形式复制着历史上的语言控制模式。"失败作家转向独裁者"的心理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有了新的表现——那些无法在正常竞争中获得关注的人,转向极端煽动性表达来满足虚荣心。
因此,《地狱图书馆》不仅是历史反思,更是现实警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阅读应该是冒险行为,要求我们质疑文本权威,识别话语陷阱,在多元观点中独立判断。只有保持这种批判性阅读姿态,文字才能重获启蒙和解放的本源力量,而非沦为新的奴役工具。
在信息传播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广泛的今天,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维护语言多样性,建构健康文化生态,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责任。这部"地狱图书馆"的最珍贵启示是:保持思想独立和语言自由,始终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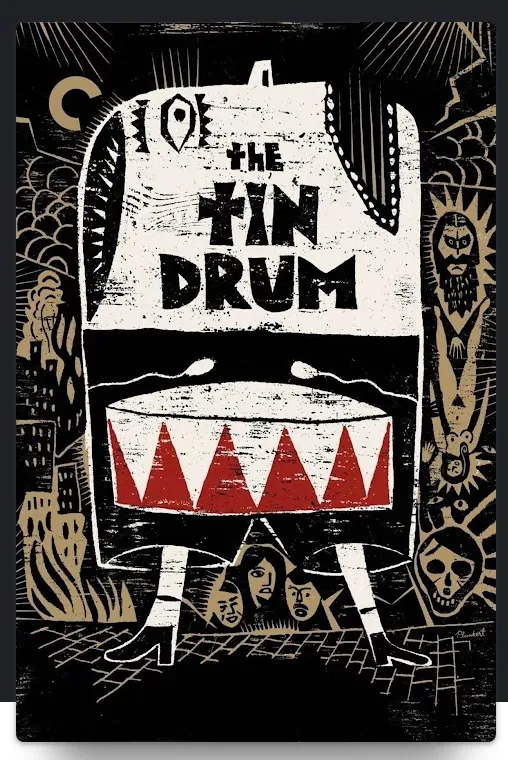
徐贲 | 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
DEC 16, 2024
编者按:“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本文为徐贲专栏最新文章。
文学的公共性与作为社会中人的作家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作为公共人物的作家便无法有效地讨论文学的公共性或公众影响。文学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思想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
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作了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各自代表人的三种存在方式,作为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us),作为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和作为行动者(Actor)。文学和艺术创作属于行动的范畴。行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行动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唯有通过行动,一个人才有可能在公共生活中显示“我是谁”。行动是在多元的人的世界中发生的,行动总是“处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际网络之中,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意向。” 行动往往并不按照人原先的意向发展。希望会落空,后果会有不测,这是行动的重负,也是人生的重负。
只有当在现实公共生活中有真话要说,而且确实能把真话公开地说出来的时候,文学才成为一种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社会行动。在不允许说真话的环境中,文学的这种行动变得困难而且危险,作家为之承担的重负也不相同。在自由环境下文学承担重负的方式(思想、讨论、辩论、批判)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会具有更鲜明的政治特色(揭露、异见、抵抗、不服从)。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公共性的变化是一种作家不可能充分预期的发展,也更可能为作家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一.在公共生活中有话要说的作家
雅典的公共生活很能说明个人行动的重负。柏拉图曾试想用哲学理性去消除多元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重负,阿伦特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她认为,雅典公民没有因公共事务的重负而放弃行动,他们勇于接受政治自由和它的真实的重负。同纯理性哲学一样,纯审美的或纯艺术的文学也常常被设想为一种对公民参与和公共事务的逃避。当公共事务的重负变得不堪承担,甚至危险的时候,文学变成了一种自我消遣。但是,承担公共事务重负的文学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对现实生活世界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并且坚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提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阿伦特指出,积极生活的雅典公民,他们接受真实重负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悲剧”的形式来说故事。由于同样的理由,阿伦特对非戏剧形式的文学也极为关注,因为文学最重要得社会作用就是承担行动重负意义上的“说故事”。“说故事”帮助人在公共事务承担重负,那是因为,“说故事……使人能够按事情的真实摸样去接受事情。” 一旦你把事情用故事叙述出来,不管你觉得它是好是坏,你都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事情是已经真实地发生了,你必须面对它,你不能回避它,假装它没有发生。接受事情的真实,也就是接受这个基本事实。当不准对历史事件真实地说故事的时候,压迫和谎言也就开始了,真实必然成为牺牲品。
正是着眼于“说故事”具有“道出真实”的政治作用,阿伦特写道,“讲述事实真相者也一定是说故事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促使‘接受真实’的人。黑格尔把‘接受真实’……理解为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我们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一起,在诗人的政治作用中看到一种净化,它清除一切阻碍我们行动的杂情。说故事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政治作用就是教我们如何按事情真实的样子去接受事情。”
阿伦特从人际关系的多元性和政治性来理解叙事,把叙事本身理解为一种行动,一种在公共生活舞台上的表演和展示。这样看待叙事,重点不是放在一般文艺叙述学所关注的形式或审美特征,而是放在叙述中那些最具揭示作用和典范意义的时刻、主题,以及在叙述中展示出来的那个行动者。如果文学有公共性,那么文学的创作者一定首先就是在公共世界中有所行动的积极生活者。
体现作者个人看法和想法的文学,它的公共性和政治性是一致的。文学是一种言论,言论的目的是“说服”(peithein),不是暴力压制。说服是一种“特别具有政治性质的言论,”用以说服的应该是个人自由而独立的想法(doxa)。 阿伦特强调,doxa指的“不仅是看法,而且还是精彩和声誉。”doxa要求民众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看法也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公开地让他人能够看到和听到自己。雅典人把在公共事务中展现自己当作是公民的职责和光荣,在私人领域中人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在公共的地方不只是对多个别人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是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表示自己的想法。
作家是通过文学写作在公共领域中获得了认可、取得了声誉的公民。文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被公众注意、重视,是因为他有过文学的成就、有知名度、证明有思考能力、展现过阿伦特所说的“我是谁”。他的意见不见得比别人高明,但比别人更具可见性,因为他这个人更具可见性。而且,作家具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擅长与他人沟通,也更有可能说服他人。作家可以直接通过文学的文字,也可以运用非文学的文字(评论、杂文、论述、时论、辩论等等)来传达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在公共领域中,作家个人身份的“文学家”与“公民”是可以区分的。以公民为主要身份的作家与其他公民具有平等的身份,作家不是精神导师,只是思考、表达、写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公民。
二.自由的和强制的公共空间
柏拉图因为苏格拉底被判罪,对个人能否有效说服他人,对个人想法是否能在公共事务中发生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被处死证明“苏格拉底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全然无效。”多兰把哲学家对城邦政治的恐惧、厌恶、疏远称作为“柏拉图的精神创伤”。 同样,许多文学作者会由于他们自己的类似柏拉图精神创伤而对政治和文学的公共性抱有怀疑、厌恶、疏远的态度。造成这种精神创伤的往往是某种特别残酷,特别具有强制性的政治经验和记忆。以政治压制、思想钳制为特征的“公共性”与阿伦特所说的自由公共性是完全不同的。
强制性的公共空间是单一的、排斥异己的。自由的公共空间是宽容的、包纳多元的。强制性的公共空间以大众的蒙昧为条件,思想控制和审查是它运作的特征。自由的公共空间以启蒙为条件,独立思想和自由交流是这个公共空间的生命源流。在强制性的公共空间里,文学被迫或者自愿成为某种权力意志的宣传工具。这类文学帮助强化强制性的公共秩序,压制不同的声音。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使得许多人对文学公共性彻底丧失了信心,以怀疑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可能具有的任何独立、自由公共意义。
从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公共”秩序,它和我们现在追求的自由公共秩序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纳粹时代,野蛮强制、排斥异己、思想钳制的公共秩序却恰恰是无数的德国人所接受甚至认同的。诗歌在德国文学传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纳粹的公共秩序中也起过很大的公共鼓动作用。然而,正如文学史家里奇(J. M. Ritche)所指出的,“在纳粹时代的恐怖过去之后,要找出真正的纳粹诗歌的样板很不容易,要获得对纳粹诗歌的总体印象也很困难。可以合理地推断,纳粹文学都是些哗众取宠的货色;纳粹诗歌是对传统民谣和自然派诗歌的粗劣模仿,又融合了‘血与土’文学那种带着粗野和伤感的渴望。”
这样的诗歌中有德国传统文学的成分,就像文革样板戏运用传统戏剧的原素一样。它的公共性是这样定位的,“抒情诗被看作建立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文化武器。这类诗的功能与其说是吸引人,不如说是胁迫人。” 即使那些并不是在纳粹期间创作的诗歌,也同样可以发挥这样的公共性。例如,戈林在向国会提交《授权法案》(要求国会将控制全德国之权授予纳粹党)时背诵德国诗人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的诗篇《德意志醒来吧!》(1928)。所有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听到这种严肃的发言等于被邀请参加一次大运动,也要求每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去与民族整体融合到一起。” 在这个整体中,个人和他的看法是渺小、微不足道的,随时可以牺牲掉,更不要说是被压制、被排斥了。
这种强制的公共性与以政治自由为基础的公共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强制的公共性中,公共责任意味着绝对服从,但是,在自由的公共性中,公共责任是政治自由的一部分。政治自由的要义在于,正当的政治关系是在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平等个体公民之间形成的,不是自上而下地贯彻某种绝对的权力意志。自由公共性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公众的批判理性,这恰恰是强制性权力和思想统治所不能允许的。在专制国家的社会中存在着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专门知识有余,批判性知识匮缺的弊病。米尔斯把批判性知识看作是民主公共性的要素,他认为,“只有在公众(publics)和(社会)领导变得更敏感、更负责任的地方,才能建立民主秩序。而且,只有当知识具有公共相关性时,民主秩序才可能建立。”霍罗威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就此写道,“米尔斯呼吁回归‘古典传统’,这是一种理性、启蒙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人的思想是自我完足、独立于权力的。这样的思想与社会成熟之间有着道德的联系。”霍罗威兹称米尔斯为“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因为在米尔斯那里,研究社会永远与关注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
米尔斯关注的“公众”是复数的publics,也就是具体的、多元的小公众。这是文学和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那种公众。有的公众对文学有兴趣,有的公众对文学未必有兴趣,但对作为公共人物的或个人的作家有兴趣,还有的公众对这些都缺乏兴趣。文学和作家的影响力不是单方面的,必须以公众的接受意愿为条件,而这个意愿是不能强迫的。在自由公共空间中,文学的公共性是在作者与不同公众的多样、多元互动中形成的。在强制性的公众空间里,具体的多元“公众”被抽象的“民众”所代替。“民众”既是大写的、单一的Public,又是实际上原子聚合的Mass(“群众”),不管对文学有没有兴趣,这样的民众被无一例外地当作是宣传式文学的思想灌输对象。
自由公众和受制群众是有区别的。法国社会文化学者戴扬(D. Dayan)将自由“公众”归纳为这样一些特征:公众是具有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的社会群体、公众永远是复数的publics中的一个“小公众”、公民社会由许许多多的小公众组成的、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每个具体的公众都在公开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确立与其它公众的关系、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价值认同、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总而言之,没有个人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公共交往就没有公众。与“公众”相比,“群众”只是零散分离的个体,他们彼此缺乏社会交往和稳定联系,既不必作公开的自我表现,也无须持有某种共好的理念。群众对外界的反应是被动、顺从的, 群众是一个被专制统治权力所动员、控制、蛊惑的群体。
具有独立自我意识和自由要求的公众只能存在于民主政体之中,而聚合型的群众则总是与专制政体共生。公众或群众都是政体生活秩序中的人际关系形式,正如政治学者潘格尔(T. Pangle)所说, “除了人性之外,没有什么比政体更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形成了。” 可以说,政体形式决定了人,也决定文学在社会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与文学特定的审美或艺术品质可能有一些联系,但也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指出,纳粹时期的诗作可以是平庸无奇的,但在现实中却能起很大的作用,“它们也的确在国社党组织的无数次示威游行中发挥了作用。千万面旗帜被高高举起,千万人拥在一起前进,像冲锋队一样安静平稳地前进,透露出纪律和约束力,也透露出平静的信心。这是在呼吁懦夫加入到群众运动中来。”
与专制政体中鼓动千万群众的文学相比,民主政体中诉诸公众独立理解和理性判断的文学,它的公共作用则往往平淡无奇。这不是说,民主政体中的文学公共性不如在专制政体中来得重要,而是说,民主政体中的文学公共性应当从完全不同于专制政体经验的角度去加以理解。这是因为,文学不再被用作为“鼓舞”、“号召”、“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在平等群体中表述自己“看法”(doxa)的一种方式。专制和自由政体中的公共性的对比清楚地表现在1933-1945年和二战后德国的对比。从纳粹的政治文学到二战后的反思文学,德国文学公共性的变化是发生在变化了的政体公共空间中的,许多作家对文学公共性和公共角色的重新认识也是发生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转变中的。
三.作为公共性作家的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是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深深介入战后的德国政治文化重建,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义德国作家的公共角色。从事战后德国思想史的学者米勒(Jan-Werner Mueller)就此写道,“(格拉斯)对这一角色的定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充分知情的、对时事抱有立场的公民,并且敦促他的同胞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他拒绝了‘精神’和‘权力’这一对传统的德国式区分,转而把作家的位置摆在‘社会的中间’。冷静的、反乌托邦的怀疑主义和本身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是这一类型的公民特征。格拉斯认为,这类公民的人数越多,最后就能让德国越接近启蒙运动的传统,而后者是他一贯公开支持的。”
格拉斯出生于1927年,1933年纳粹上台时他才6岁,对纳粹上台前的魏玛共和国不可能拥有像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或者阿伦特(1906-1975)那一代人的个人经验记忆。格拉斯和哲学、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出生于1929年)同属于1945年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德国战后的民主宪政和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宪政有所不同,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的知识行动具有鲜明的德国战后民主宪政公共性特征。格拉斯是文学家,哈贝马斯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那里,文学和哲学、社会学具有相同的公共性。战后德国公共性由民主宪政重新开启。这一民主公共性所反对的,正是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格拉斯、哈贝马斯这两代德国知识分子都予以谴责和保持警惕的纳粹极权。
格拉斯于1959年32岁时发表小说《铁皮鼓》,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这部小说与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的年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都以但泽(Danzig)和维斯瓦河(Vistula)三角洲民族混居和复杂的多民族历史为文化背景,描述了纳粹的兴起和二战时的德国人经历。格拉斯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但仅仅文学风格并不足以使一个作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人物。
格拉斯一直是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他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勃兰特(Willy Brandt, 1969-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在华沙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悔罪下跪,引起全球瞩目,于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活动,公开表示反对左翼激进。 格拉斯赞同社会民主的妥协和点滴进步的理念,将之同情地称作蜗牛的缓慢前行。他在1969年明确宣告,“我是革命的反对者。”他站在社会民主的立场,拒绝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激进左派主张。每当大选临近,他总是有参与的冲动,想“甩开他的书桌,”参与“民主的鸡毛蒜皮”,那些常常是为达成妥协所做的艰难工作。
格拉斯并不认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现代民主已经十全十美,但他拒绝对这样的民主扮演1933年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对魏玛民主扮演的那种祸事预言者的角色。在专制政治传统强大的德国,魏玛共和代表的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共和民主制度。由于它的脆弱和缺乏权威,它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各种批判、诅骂和祸事预言。最终,魏玛自由民主因不完善而遭舍弃,代之而起的是强势、有权威、有效率,但却残暴、邪恶的纳粹政权。格拉斯对社会民主抱有虽不完善,但必须坚持到底的信念。1965年勃兰特竞选失败,格拉斯拒绝投降,以文学家的想象,他把西绪福斯奉为“自己的圣人”,并把乔治·奥维尔和阿尔伯特·加缪引为知识楷模。
在坚持社会民主理念这一点上,格拉斯与哈贝玛斯坚持现代性和启蒙有相似之处。1933年以前,许多右翼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把魏玛共和的自由民主政治当作一个必然走向反面的现代性和启蒙案例来批判。这种批判在20世纪后叶的后现代理论中得到了延续。哈贝玛斯坚定地捍卫现代性、启蒙和公民社会的意义。他认为,启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应当对它进行纠偏和补充,而不是排斥和抛弃。哈贝玛斯对现代理性和启蒙同样拒绝扮演祸事预言者的角色。他和格拉斯一起代表着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德国纳粹极权经验教训,拒绝重蹈魏玛时期知识分子覆辙的公共政治选择。
格拉斯把帮助德国人记住奥斯威辛当作自己的公共责任。他常常嘲笑文学和作家以为个人介入就能够担当民族良心的想法。他认为,作家自命为良心代表,会让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们自己的良心。德国人必须记住奥斯威辛,因为奥斯威辛能让德国人认识自身。 格拉斯并不是奥斯威辛的局外人,他10岁时曾是少年团的一员,14岁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5岁成为了一名高炮团助手,到了17岁便正式加入了陆军,直到被美国人俘虏为止。换言之,他“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一直到了19岁,他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得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奥斯威辛的意义在格拉斯思想中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议题。他自己就曾卷入在纳粹的恐怖罪行之中,他对纳粹“魔鬼般的”世界作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滞后反应”。格拉斯说,每当他写作的时候,死者都在看着他。他对纳粹主义的反应一直是个不完整的过程,随着那段历史渐渐远去,他就越是努力地要帮助德国公众把这一段历史保持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格拉斯对战后德国公共生活的介入不只是把自己投入到一个现成的公共群体中去,而且还努力帮助改变、重塑、更新这个公共群体。作为一个公民,他要帮助战后德国摆脱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而代之以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宪法爱国主义”。格拉斯所警惕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政权灭亡后,国家主义继续有可能把人们带向灾难。他采纳了雅斯贝尔斯在反思纳粹极权中提出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德国人能够给全人类提供一个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毁灭公共生活的教训。雅斯贝尔斯曾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一件事: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它大陆意味着灾难。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绝对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可以着手揭示其根源,促进其否定。”
警惕狭隘的民族国家的危险,使得格拉斯坚持民主宪法在国民身份意识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他坚定地支持西德宪法的基本原则,成为实际最早推动形成“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者之一。格拉斯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从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自由价值观出发的。早在1961年,他就明确同意雅斯贝尔斯的主张,认为自由优先于统一,因而东德人民争取自由必须成为统一的关键要素。他觉得在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那就是“自由联邦”。格拉斯在1967年时警告说,如果德国人达不到这种自我理解,那么西德的民族保守派和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右派”将会联手牺牲掉社会民主和“自由联邦主义”,而可能在德国重新建造一个“恶魔般的”民族体。
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为建立一个后民族国家主义的德国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格拉斯坚持宪法爱国主义与索尔仁尼琴坚持俄国文化民族主义完全不同。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作家,他们最值得炫耀的都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政治介入。索尔仁尼琴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丧失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双重称号,但却因此成为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和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
从文学上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都为重新构塑他们各自国家社会群体以及人类社会群体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文学都帮助读者公众变得更有同情心、对苦难更理解、对邪恶更警觉、对人性的复杂更了解、对多元的生活更珍惜。经受了这样的人性熏陶,公众便再也难以漠视那种极权生活的虚伪欺骗、阴狠毒辣、冷酷无情和仇视他人,也变得更加向往新的、更真实、更人性的公共群体。 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理念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所起的公共作用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格拉斯坚持的是一种以人的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而索尔仁尼琴奉行的则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沙文主义。索尔仁尼琴在反对专制权力时嫉恶如仇,但涉及国家民族时,则却又把国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严更重要。出于坚持自由公共性的立场,格拉斯和战后德国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所警惕和反对的正是这样一种与专制国家主义的妥协。
文学作为一个思想领域,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是平行的。在每个思想领域中,一个人有所成就,包括作为作家的成就,都是在公共领域中成为角色的条件。但是,一个人在专门领域中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他作为公民在公共社会中的作用,更不要说转化为在公共社会中的实际积极影响。作家要起到积极的公共作用,必须对公共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当然不是所有的)有所关注和参与,这种关注和参与反过来也能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更大兴趣和重视。作家不仅仅是以文学作品介入公共生活。文学创作往往会因为特定语言和表达方式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全面地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社会价值、文化观点。作家因此在介入公共事务时需要运用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当公民有文学家的背景、当文学家却并不囿于文学,这正是文学公共性研究应当重视的作家社会行动特征。

徐贲 | 集中营的囚犯人格和专制极权的臣民人格
NOV 04, 2024
編者按:本文为徐贲最新专栏文章,原发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是两位亲身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他们分别留下了关于集中营囚犯心理的见证著作:《知情的心》和《活出意义来》。可以通过讨论这两部著作来探讨集中营对囚犯的非人格化摧残及其严重后果:受害者失去了尊严感和自主意识。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都认为,自由、意志自主和尊严等术语或多或少是同义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剥夺个人行为的最终选择,也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定义了每个人的人性。任何对人的绝对限制,即使是在集中营或极权国家里,最终都不可能彻底有效地消除人性。但是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对集中营中的人性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角度,形成了他们在理解人在极端环境下的个体意识、生存意义和抵抗可能等方面的差异。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以更好地获得关于非人化人格的完整理解。
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的囚犯人格心理学阐述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特殊的,这是因为他们两位虽然在集中营里的时间不长,但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在众多研究中,阿德勒(H G Adler)探讨了对集中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格雷吉尔(Tadeusz Grygier)研究了压迫造成的多种心理影响,迪姆斯代尔(Joel E Dimsdale)研究了囚犯的应对行为;德普雷斯(Des Pres)对集中营生存提出了另类的“苟活英雄主义”,等等。在诸多著作中,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的作品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些后来的研究也都以他们的著作作为参照和商榷的对象。
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都是对集中营有亲身体验的心理学家,这是后来研究者不能与他们相比的。他们在集中营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术训练、洞察力进行了大量实地观察,这种特殊的综合条件所产生的作品,自然有着特殊的分量。凯瑟琳·利奇(Catherine Leach)评论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知情的心》提出的理论在解释集中营的行为方面也许是分量最重的。”1984年,弗兰克的《人对意义的探索》——我这里用中文版《活出意义来》的译法——的英文版本已经印刷了73次,英文版本已经售出250万册,并以其他19种语言出版,可见其在读者那里的分量。相比之下,贝特尔海姆死后名誉受损,就要显得相对暗淡。
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都曾经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但时间长度并不相同,而且不同的集中营生存环境的残酷程度也不相同,这可能影响了他们的不同幸存叙述和理论思考。贝特尔海姆在获准移民美国之前,在集中营中被关押了大约一年(1938—1939);弗兰克在获得解放之前,从1941至1945年,在集中营和工作营中度过了4年。此外,弗兰克的兴趣主要在于集中营中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在普通囚犯的头脑中,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集中营处境。他发现,那些面向未来的囚犯,无论是未来有要做的事,还是未来与心爱的人团聚,都最有可能在集中营的恐怖中幸存下来。他记述道:“有名俘虏曾告诉我,他抵达车站后,随着长长的队伍步行到集中营,当时只觉得好像是走在自己的出殡行列里似地。他的生命仿佛早已死去,有如过眼云烟,毫无未来可言。”相比之下,贝特尔海姆关注的主要是“集中营如何在囚犯身上产生变化,使他们成为纳粹国家更有用的受支配者”。他发现,囚犯在集中营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有可能倒退到婴儿期的行为,这将最终导致人格的退化,囚犯因此接受盖世太保的价值观,并将之作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由于弗兰克在纳粹政权下忍受了很长的时间,作为受迫害的犹太人和集中营中的老囚犯,他可能更倾向于寻找并强化那种能给他带来生存希望的东西。但对于人们今天认识他的主要理论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经历作为他著名“意义疗法”(logo therapy)的基础。其基本原理是:意义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我们对意义的意愿是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基本动力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用的个人心理疗法。相比之下,贝特尔海姆的理论更具有集体心理分析的价值,在社会学中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尽管贝特尔海姆在进入集中营时没有发表任何心理学成果,但他后来扩大了他在集中营中获得的关于囚犯再社会化过程的理解,发展出关于极端环境下人类行为普遍特征的理论,如现代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里“大众”(群众)状态对个人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他在《知情的心》中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在集中营里的初步囚犯心理理论对他后来的社会学理论观点有明显的影响,后来许多人也接受了他的理论框架并将他的观点做了扩展。例如,埃尔金斯用贝特尔海姆的分析来理解非洲奴隶的行为。他引用贝特尔海姆的观念来解释奴隶婴儿化的人格特征,并指出, 为了心理安全,奴隶“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他的主人想象成‘好父亲’,虽然这在集中营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对“慈父”般的领袖和政府的期盼在极权国家也非常普遍。又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他对极端情况的解释中发展了对“再社会”(resocialization)的理解,所谓“再社会化”,指的是人由于极端经历(或“危急情况”),其常规行为模式被改变,因而重新创造出一个不同的自我,这种改变是人在粗暴的外力驱使下作出的自我调适,也就是环境适应。极权社会里普遍的人格变形和人性沦丧,都是这种再社会化的结果。吉登斯的这部分论述几乎完全由贝特尔海姆的引文来支持,特别是贝特尔海姆对“老囚犯”的描述以及他在他们身上观察到的具体行为。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提出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再次回到了贝特尔海姆对集中营中囚犯人格退化的分析。他认为, “贝特尔海姆所描述的人格变化”是 “所有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在数年内所经历的”,这些变化 “遵循一定的阶段顺序”,“很明显是一种倒退”。集中营里“老囚犯”的情况与长期生活并适应于极权社会环境的“老顺民”一样,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外面世界的定位,他们通过将自己完全被动地融入极端环境,成为集体素质退化的参与者。他们用退化的人格重新构建了自己的身份,作为被压迫者,他们模仿压迫者的行为模式,不仅仅是为了讨好压迫者,而且是真的在观念中引入了压迫者的规范性价值。
二、囚犯心理学的不同观察和解释
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的分析性理论基础是由他们自己所观察到的集中营事物和现象所提供的。经常是,他们观察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将其归结为囚犯性格中不同型类的变化,这是他们的理论多有分歧的一个原因。他们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又引导他们在集中营里观察到了不同的现象,这是理论对观察的导向作用,因为现象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构建而成的。简·弗莱克斯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叙事都有建构性,保罗·马库斯和阿兰·罗森伯格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有在理论上中立的、无争议的方法可以用来确定哪种叙事是‘真实的’”。
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囚犯在集中营里“观念变化”(opinion change)的性质和过程有不同的理解。囚犯在集中营里发生观念变化,这是他们都观察到的现象,但他们对这样的现象却有不同的理解。心理学家赫伯特·凯尔曼曾指出,观念的改变和形成始于这样的假设:“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影响条件下被采纳,由于不同的动机,观念的本质特征和随后的变化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他概述了“观念变化”的三种类型:顺从、认同和内化。一个人希望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好处,于是接受那人的影响,并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这种观念改变就是“顺从”(compliance)。一个人仿照他人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对自己有利或能提高自己的身份,这时候的观念改变就是“认同”(identification)。一个人平时并不喜欢穿军装,但因为军装是高等身份的象征而穿上军装,这种观念变化就是贝特尔海姆所说的认同。还有一种观念变化:一个人受他人的诱导,被诱导的行为与诱导者的价值观一致,这就是“内化”(internalization)。正如凯尔曼所解释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观念改变过程一般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但会出现一种类型起主导作用的情况,这又决定了在类型互动时什么会被当作是核心特征。
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都关注囚犯观念变化的现象,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不同解释的区别源于他们各自认为什么是主导的占优势的东西。例如,为了生存,大多数囚犯必须表现出对党卫军的顺从(或服从)。弗兰克认为,囚犯对未来还有所希望,所以会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大多数囚犯是为保住性命才服从党卫军,向他们表示顺从的,他们并非是认同党卫军。相反,贝特尔海姆认为,为了能在集中营里长久地活下去,许多囚犯早已在认知和思想方式上完全适应了集中营里党卫军的那一套规矩,学会了想党卫军所想,把党卫军的要求化为自己的行动,他们的领会程度之深与接受党卫军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贝特尔海姆认为,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认同”和“内化”。但是,由于纳粹集中营的目标并不是让党卫军的价值观成为囚犯的价值观,所以不同意贝特尔海姆的人也可以认为“认同”和“内化”即使发生,也是非常次要的。倒是在古拉格劳改营里,由于监管人员的目标是改造犯人的思想,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会要求犯人有脱胎换骨的认同和内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纳粹集中营有这样的目的或要求,这是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的一个重要区别。
贝特尔海姆认为,囚犯开始认同党卫军的迹象之一,是他们彼此对待的方式开始模仿党卫军的暴力和攻击性。这种情况被莱维称为囚犯“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且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他还指出,“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起研究者们从多种角度的关注和讨论。弗兰克也谈到一些囚犯用凶狠的暴力手段对待其他囚犯,但行凶的通常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卡波”(囚犯工头或管事)。卡波们经常比看守更严厉地对待囚犯。弗兰克并不认为卡波凶狠是因为认同或内化了纳粹的暴力价值,他似乎认为,卡波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他们是奉命干脏活的人,在看守的胁迫下,为了保住自己的优越地位,只能特别卖力地表现对其他囚犯的严厉;有的时候则是因为与别的囚犯有私怨,有了机会就挟私报复,恶意整人。弗兰克解释说,这些卡波都是从那些性格适合这种“脏手”工作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有负所托,立刻就会被刷下来。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卖力表现,俨若纳粹挺进队员和营中警卫”。但是,我们知道,奉命干脏活很可能就爱上了干脏活,服从也就转化为认同,因此弗兰克对囚徒行为的解释与贝特尔海姆的解释并不一定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
贝特尔海姆对囚犯个性解释中最有争议的是“囚犯认同看守的价值观”。尽管集中营环境对一些囚犯的人格和个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的相应行为是否就能表明他们认同了党卫军的价值观呢?这涉及对行为意义的解释,行为是可见的,意义则不是。对于意义,不同的人们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应该看到,这是关于“解释”(也就是“看法”)而非“事实”的争议。“认同”是很难确定的,可能是一个过程或结果,也可能是指其他行为反应。例如,1938年,有的囚犯穿上了看守的废旧制服,贝特尔海姆认为,集中营里的老囚犯搜罗党卫军的旧军装,并穿得像党卫军一样,表现出一种价值观的内化和认同。但不同意他的人却有不同的解释。贝特尔海姆的一个同伴保罗·诺伊拉斯(Paul Neurath)就说,许多囚犯愿意穿这种旧制服,是因为它们比囚徒制服更暖和。到底是不是认同,恐怕得看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如果这么穿着的囚犯在内心感觉良好,完全没有心理不适或障碍,那么贝特尔海姆关于身份识别的解释也还是合适和可信的。
但是,确实也有囚犯把穿制服这件事当玩笑来对待的。幸存者大卫·魏斯(David Weiss)所在的集中营被解放的那天晚上,所有的看守都已经跑得无影无踪,美国人进来了,仓库被砸开了。他描述道:“当囚犯们打开仓库时,除了食物,他们还开始寻找衣服,我们的衣服上都是虱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换了衣服,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换了。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笑]穿上了德国的制服,看起来像将军[笑]。他们穿上了将军的制服,不管他们找到什么,上尉的制服,但你一眼就能瞧出他们是谁。只要看看他们,你就知道他们是囚犯[笑]。他们几乎不能动,但[笑]他们穿着德国制服。”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穿上卫兵制服并不是因为这是他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的衣服,他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衣服,但是他们选择了德国人的制服。怎么解释这个真实的现象呢?因为好玩和幽默?还是因为这些制服的权力象征?他们穿上这些衣服似乎是一种玩笑,但也可以以此表明他们现在已经从无权变成了有权的一方。穿上制服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它展示了纳粹的失败。服装有隐秘的权力涵义,不只是军服,其他衣着也是如此,贝特尔海姆的解释符合这种对衣着政治复杂含义的理解。
三、集中营极端环境中的生存适应
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都观察到了囚犯在集中营极端环境中的生存适应,但对程度和性质的理解并不相同。与贝特尔海姆强调老囚犯的认同和内化不同,弗兰克坚持认为,那些最有可能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囚犯——许多是老囚犯——是那些面向未来的人,无论是未来有要做的事情,还是未来要与家人或爱人团聚。对弗兰克来说,即使是长期关押的老囚犯,也有现实的梦想,而不是像贝特尔海姆说的那样,放弃了与家人相聚或重新开始原先生活方式的希望。事实上,有的老囚犯在解放的时候确实谈到了自己的梦想:“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有多少次为梦境所骗啊!我们梦到获释的日子来到了,我们重获自由,并且重返故乡,会见朋友,拥抱妻子,还坐在餐桌旁边,畅谈营中的一切经历——还说我们常梦到获释的光景。”
与弗兰克相反,贝特尔海姆认为,囚犯在集中营的时间越长,他们对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期待就越低。他还发现,长期的囚犯有宏大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成为国家元首,他们在做白日梦时排除了与家人的团聚或延续战前的生活。贝特尔海姆解释说,这些白日梦可以部分理解为,许多囚犯认为,权势是他们的痛苦所能带来的一种回报或安慰,只有高级的公共职位才能帮助他们体面地与家人相聚。这就像在外闯荡多年,混得落魄的人会梦想大富大贵地衣锦还乡一样,白日梦其实是一种心理补偿。尽管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都认为囚犯们喜欢幻想,但对弗兰克来说,这些梦想是以过去为中心的,而对贝特尔海姆来说,长期囚犯的白日梦却更多是面向虚妄的未来,“老囚犯似乎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沮丧状态;与他们以前的辉煌相比……可能太令人沮丧了”。
可见,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叙述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如何解释囚犯对长期禁闭的反应。这种解释也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长期在极权统治下当顺民和奴民的人们。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囚犯会对他们周围的恐怖变得麻木。但贝特尔海姆认为,他们会开始认同党卫军。他认为,老囚犯会从党卫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会模仿党卫军的做派,像党卫军那样行使语言或身体暴力,渴望得到党卫军的旧制服或将自己的衣服按党卫军制服的样式来修改,只不过是模仿的一种。比认同衣着更严重的是认同纳粹的种族优越论和纳粹的宣传说辞:西方批评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对德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所有囚犯身上,然而,在“愿意并能够接受党卫军的价值观和行为作为自己的人格结构”的囚犯们那里,“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似乎最容易被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犯在这种认同方面也走得很远。例如,美国和英国的报纸曾一度充斥着关于集中营中残酷行为的报道。党卫军因为这些故事的出现而惩罚了囚犯,……因为这些故事一定是源自于前囚犯的报告。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老囚犯们坚持认为,外国报纸没有资格评论德国内部机构的所作所为,并对试图帮助他们的记者表示憎恶”。1938年,贝特尔海姆询问了一百多名老政治犯,问他们外国报纸是否应该报道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许多人犹豫不决,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当被问及他们是否会加入外国势力以打败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时,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表示,逃离德国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地与纳粹作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的非犹太囚犯都相信德国种族的优越性。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成就感到非常自豪,特别是通过吞并进行扩张的政策。为了配合他们对新意识形态的接受,大多数(非犹太人)老囚犯认同盖世太保对所谓‘不合格囚犯’(the unfit prisoner被纳粹处决的老弱病残囚犯)的态度。……认为盖世太保清理的是‘不适合的人’”。不得不说,在观察和分析有些囚犯认同纳粹价值的问题上,贝特尔海姆看得要比弗兰克清楚得多,因为弗兰克只是认为,囚犯在集中营里呆长了,会学会钝化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与是否认同党卫军的价值无关。这两位心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都是真实的,但对现象的意义的解释并不相同,深度也不同,尤其是,贝特尔海姆的解释对认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和认同方式,对认识他们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更有现实意义。
对囚犯之间的暴力行为,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的解释也不同。贝特尔海姆认为,这是对党卫军随意打骂和动粗作风的认同;而弗兰克则认为,这是囚犯所处的攻击性环境的情绪升级。然而,弗兰克的观察很容易符合贝特尔海姆的解释。弗兰克解释道:“囚犯由于经常目睹殴打的场面,暴力冲动自然会跟着增强。我在又饿又累时一旦怒火攻心,就常发觉自己双拳紧握。”弗兰克认为这种行为是营地环境的后果。鉴于此,我们可以按照吉登斯的解释,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一种 “再社会化”的表现,是指在极端经历期间或之后获得的,已经改变了的行为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或创造的自我。囚犯们倾向于暴力,那是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学会了在那里处理各种情况的唯一有效方式:凡事都凭拳头大、胳膊粗,决不妄想以理服人。贝特尔海姆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对看守的暴力价值的一种认同——集中营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暴力,而不是理性协商或说理。贝特尔海姆和弗兰克都观察到,即使党卫军不在场,囚犯们也是同样粗暴,互相口出恶言,打架斗殴。这种暴力倾向在极权社会里也很常见,行为的粗野和不文明相当普遍。解释的原因可能相当复杂,但归结为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应该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
由于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都有亲身的集中营经历,他们的不同解释经常无法通过分析各自的经验观察本身来澄清。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察和解释,有时候需要将他们的经验叙述与其他目击者的证词进行对比。虽然现在有许多可以用来理解囚犯人格心理变化的见证材料,但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却一直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虽然可以用这类见证材料对比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的陈述,但仍然难以对他们的心理学理论得出证实或证伪的结论。相比起他们提供的见证和问题来说,有没有最后的结论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四、幸存者口述证词的局限
集中营幸存者们的见证和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受到公众重视的。二战后,大约有50万犹太人在欧洲幸存下来,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以色列,而大约有5万人去了美国。开始的时候,公众对幸存者见证的意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兴趣听取大屠杀的证词。即使有的幸存者想讲述自己故事,但由于没有听众,他们并没有强烈的讲述冲动。一些幸存者写的作品也是主要被当作“文学”来阅读。至于搜集和出版幸存者的文字或口述见证,那是没有听说过的。仅仅限于“文学”的大屠杀记忆并没有广泛的公众基础。美国、德国或奥地利的许多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到大屠杀,《大英百科全书》中可以查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没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产生好奇心,之后公众的兴趣逐渐变得更加浓厚。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于1994年制作了《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纳粹浩劫幸存者视听历史基金会成立,目的是尽量搜集所有幸存者、解放者、救援者和其他大屠杀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
搜集和收藏幸存者的口述证词是一项庞大的长期工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口述历史收藏馆的档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该收藏馆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莱诺克斯和蒂尔登基金会的多罗特犹太人分部的一部分。1974年至1975年期间,口述历史图书馆对居住在美国62个城市的大屠杀幸存者和家庭成员做了约250次采访,并做了记录。所有幸存者的证词长度从10页到250页不等,涉及二战后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的生活。资料的重点是幸存者的战时经历、适应美国生活的情况,以及大屠杀对其子女的影响。虽然不完全清楚这些幸存者是如何被招募的,但他们的证词似乎是根据口口相传以及从那些已经或正在通过演讲和出版物公开其经历的人们那里收集的。根据项目的回忆录,西尔维娅-罗斯柴尔德编辑了《来自大屠杀的声音》。
由于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曾被囚禁在奥斯威辛、达豪和布痕瓦尔德,他们的囚犯心理和人格变化理论可以与这些集中营的见证材料进行对比。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这些见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毫无疑问,采访过程会勾起许多痛苦的回忆,见证者在记忆中唤回和叙述什么,压抑和排除什么,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一些幸存者对采访问题的回答就像他们已经排练了多年的答案一样。许多幸存者只涉及公众熟知的事件信息,而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则避免提及或缺乏深度思考。这是各种“见证”的通病,也限制了见证的事件判断和历史理解价值。
例如,由于幸存者知道他们的证词会被公开,他们更多提及抵抗而非服从的行为,并淡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与看守合作这一类不光彩的行为。因此,很难找到与贝特尔海姆的囚犯人格退化理论可以对照的材料。没有人提到贝特尔海姆所观察到的那种囚犯殴打囚犯,或犯人穿党卫军制服的事情。就算有人确实提到了囚犯打囚犯的事情,那也都是别的囚犯打他们,而不是他们自己打别人。见证者都特别强调地叙述他们如何在集中营里怀念家人,梦见过去的生活场景,希望解放并与家人团聚,而且还表示,这样的记忆和希望给了他们在集中营里存活的意义和力量。这样的叙述显然证实了弗兰克关于“活出意义来”“生存的意义提高了生存的可能”的论断。但这很可能是幸存者后来对集中营经验的理解,而不是他们能坚持到最后的真正原因。因为集中营里的幸存和被解放往往是纯粹偶然的结果,并不是某种特定心理因素的必然结果。这一类记忆偏差和重构在其他后灾难或后暴行记忆中也很常见。
了解了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对集中营人格变化的叙述,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贝特尔海姆受到远比弗兰克要多的非议呢?这恐怕是因为,弗兰克的理论主要是描述和解释性的,而贝特尔海姆的理论则是批评和指责性的。由于批评的对象是犹太人,这会被看作是对犹太人的遭遇缺乏同情,犯了“责备受害者”的忌讳。阿伦特因为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里批评了一些犹太人与纳粹的妥协性交易,也受到了与贝特尔海姆相似的非议。德普雷斯对贝特尔海姆的非议和指责是最有代表性的(下文还要讨论)。有意思的是,他攻击贝特尔海姆,连带攻击了囚犯研究的整个心理学取向,他认为是心理学的传统观念导致了贝特尔海姆对集中营中囚犯人格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他在《幸存者》一书里写道:“迄今为止,对集中营经历的认真研究几乎完全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的。埃尔金斯(Stanley M. Elkins)从埃利-科恩(Elie Cohen)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那里获得了大部分证据,他们都采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最后都被他们的方法引向了错误的结论。精神分析的方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基本上是关于文化和文明国家中人的理论。”它不适用于集中营的野蛮世界。
德普雷斯认为,不能用“文化和文明国家中人”的道德概念去理解集中营受害者的道德,甚至在讨论的时候运用这样的文明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集中营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文化或讲文明的地方。例如,人们在文明环境中运用的“苟活”概念就完全不适用于集中营环境和幸存者的生存努力,他们那种在屈辱和无助中能坚持“活着”,其本质不是苟活,而是“生存的英雄主义”。德普雷斯解释道:“在极端情况下,(幸存者)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命;赋予文明行为以深度和复杂性的动机的多样性已经丧失。”但是,弗兰克和贝特尔海姆认为,即使是在集中营里,文明的标准也并未丧失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被强制抛弃了而已。如果就此否认文明的标准,就不再有任何其他标准可以判断集中营是一个残忍和野蛮的地方。
五、极端状况与人格退化
对囚犯在集中营里的不同变化期的解释,也显示心理学理论是有不同层次考量的。
对集中营囚犯来说,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突然发生的。从文明社会到集中营是一个突然的环境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囚犯在认知、情感、道德上不可能把他在文明的正常社会中所习惯的一下子全都抛弃或忘却,尽管他在集中营里经过自我调适,行为规范发生了突变,但一旦被解放出来,必然又会回归正常社会,重新用文明的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也许并不是像德普雷斯所认为的那样,集中营里的犯人行为已经完全不再能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去理解和批评。
环境的突然改变造成人格的改变,其实古人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三卷第5章《科西拉的革命》里就已经讨论了因为突然的革命和内战,科西拉人的人格和行为如何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本来都是同一城邦的邻居、朋友和熟人,但却因为内战而分裂成敌对的党派,互相仇恨,互相杀害。修昔底德说:“科西拉人继续屠杀他们自己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人是因为个人私仇而被杀害,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有各种不同的死法。正如在这种形势之下所常发生的,人们往往趋于各种极端,甚至还要坏些。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被从神庙中拖出,或者就在神坛上被屠杀的;有些实际上是被围墙封闭在道尼修斯(狄奥尼修斯)神庙中,因而死在神庙里面的。”
修昔底德关注的不光是发生在科西拉城里的暴行和杀戮,而且是革命给希腊世界带来的动乱。他忧心忡忡地写道:“这次革命是这样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引起许多革命热忱的新的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
修昔底德认为,造成人性如此堕落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某种恶的极端环境,在这类极端环境里,人性中最黑暗的仇恨和暴力会暴露出来,并且无限膨胀,最后人们完全丧失了良心和怜悯。他在描述雅典发生的瘟疫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内战更是如此。修昔底德认为,“在和平时期,没有求助于(外来势力)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每个党派总能够信赖一个同盟,伤害它的敌人,同时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修昔底德还认为,“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术士……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性退化,人格变质,心灵沉沦,首先表现在人们用词语来表现的道德观念上,“常用词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软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狂热的冲动是真正大丈夫的标志,阴谋对付敌人是完全合法的自卫。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这正是我们在德普雷斯对“幸存”的解释里看到的:通过常用词句意义的改变,“苟活”成为“生存英雄主义”——一种极端环境下的另类美德。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他的《革命心理学》里讨论了在“革命”的特殊境遇中常见的人格变化:“一旦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原来的人格要素)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些分崩离析的要素将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这一全新的人格将由其思想、感觉以及行为表现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惊人变化,简直就是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诚实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以友善著称的温文尔雅的政府官员们竟然变得嗜血成性,残忍好杀。”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法国革命时期,在其他极端情境下也同样会发生。
勒庞列举了大革命极端环境下的一些突出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都不能视为德普雷斯所说的那种极端环境中的另类美德。首先是“仇恨”,对人的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憎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党,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要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的话,那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叛国者,他们夸夸其谈,既腐败又无能,干尽了暗杀的勾当,骨子里与暴君无异。”“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人们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等等派别概莫能外。”
紧随仇恨之后的是“恐惧”。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个人所表现的勇敢无畏与集体所暴露的胆小懦弱并行不悖,“各种形式的恐惧比比皆是:最流行的恐惧就是惟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等,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比对手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根源之一”。
野心、嫉妒、虚荣等等也是大革命极端状况下突出的人格特征,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情感因素的影响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发展到极度膨胀的地步。比如说野心,“它必然会受到一种社会等级形式的限制。尽管士兵有时候确实能成为一名将军,但这只能是在长期的服役之后。而在革命时期,情况则大为不同,士兵想成为将军根本不需要等待。每一个人几乎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所以个人的野心极度膨胀,连最卑微的人也都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最高的职位,……所以,每个人的虚荣心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这种人格变异在其他革命中也同样发生,人人都想通过不凡的表现得到快速提升,又都嫉妒别人的提升,唯恐被他人超过,所以会格外激进,结果演变为一场看谁能更暴力,更残忍的恶魔表演竞赛。
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看到,社会的约束被打破,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一些人格特征开始滋长,有了可以发泄、膨胀和变异的机会。这些社会约束包括法律、道德以及传统,但是,它们不可能完全被解除。它们可能被废止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被不可逆转地永远代替和彻底重建,进而产生一套全新的社会规范。一般来说,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残存下来的那些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得到恢复,缓和了危险人格的长期恶性影响。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革命的人格蜕变被随之而建立的专政独裁或极权制度延续和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时期的人格理论也就被研究者们发展成为关于专制时期的臣民人格理论,并归纳出这种臣民人格的突出特征,如奴性、盲从、随众、冷漠、懦弱、虚假、愚蠢、善于伪装、急功近利、欺软怕硬、愤世嫉俗,一句话,这些人格特征和说假话一样,正如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在《专政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里所说:“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是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制度问题。”这些人格特征都有在极端状况下的自我保护和适应环境作用,但都不会因此而成为德普雷斯所说的另类美德。
集中营里的囚犯心理理论可以是一种浓缩的专制主义臣民心理理论,就像专制主义臣民心理理论可以是浓缩的大众或群众心理理论一样。越是浓缩的心理理论,它的运用范围就会越狭隘,越专门,越特殊,因为它是产生在更加极端的环境中的。不同范围的心理理论不能简单地直接照搬或移植,但可以互相参照。囚犯心理有许多洞见可以用来说明极权社会的臣民心理,但是,极权社会的臣民心理也有很大部分是不能用囚犯心理来解释的。不同集中营的囚犯群体心理中还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不同专制国家的臣民心理也是一样。与这些不同的心理研究途径一起,另外一些着重于人文素质的研究——文化心理、民族心态、国民思维方式的研究——也可以告诉我们在极端的环境中,我们的人格会发生怎样的退化。这些理论还能帮助我们思考,为了抵抗这样的退化,我们需要有怎样的个人和集体坚持,而且,为了保护人应有的健康心灵和精神,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抵抗和改变那种摧残人性和人格的极端环境时,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徐賁 | 邂逅口述史 发掘口述史:前苏联的人民记忆
AUG 29, 2024
編者按: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维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纪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本文徐賁教授專欄。
发掘口述史材料、做口述史研究是要有一点运气的。有两个比喻可以说明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运气”。一个是刻舟求剑,另一个是灯下寻物。一个人在船上把剑掉到河里,在船上划了一道印子,希望能在船停下的时候,按照这道印子在河里捞回失剑。另一个人在黑夜里丢了物件,在有路灯光的地方来回寻找。有人问,你为什么老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他说,因为这里是唯一有光亮可能看见遗物的地方。刻舟求剑和灯下寻物的二位,一位肯定找不到失剑,另一位极可能找不到遗物。但是,如果他们运气好,正因为他们留意去找了,他们也许能找到失物之外的东西,比失剑或遗物更有价值也说不定。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挡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一.费格斯的“运气”
1980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1920和1930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们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寻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1991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1989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事后找他们秋后算帐。现在回想起来,1990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前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1990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10年,2002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一代人的陆续逝去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0岁。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27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挡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循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挡案馆的人们。他不仅自己找,还雇请了一些助手帮他一起找。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挡案上,挡案馆就像黑夜中路灯下那一块有光亮的地方,不在这里找,还有办法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找吗?费格斯的寻找非常令他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挡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就在费格斯和他的助手在挡案馆寻找资料的时候,他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在他们家里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它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而且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1999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是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挡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来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2005年10月,监管此挡案的委员会决定在2025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挡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泽尼娅.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是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泽尼娅,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Serova Valentina,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1946-1953)对拉金斯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1992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金斯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二.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调节,在这个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个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中,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种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改变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在保存完好的斯大林制度中,勃列日涅夫很容易就完成了苏联社会的再斯大林化,并维持一种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式统治。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维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纪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主义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研究总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群众”运动或集体经历等“公共”方面。这样的历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个人,往往也是作为公共领域中人,而不是作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这一局限与历史学家所能接触的历史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在前苏联和共产党的挡案馆里,大多数的“个人材料”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把个人材料放进公家档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这些材料说的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的则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费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挡案馆里翻阅的几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够对了解家庭和个人内心世界有用的寥寥无几。
三. 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1991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挡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1985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1980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1991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回忆录的叙述结构还决定了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连贯性,而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则有一个可以确定,至少是一个大致可以确定的方向。读者从回忆录中读出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连贯性和方向的构建(尤其是回忆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日记形式则不相同。日记的叙述比回忆录松散、零乱得多。它是即刻记录的,并不知道所记的事件以后会如何发展,甚至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可接续的下文。因此,历史研究者往往觉得日记具有较大的“原始真实性”。当然,这是就最佳状况下的日记而言的。在斯大林的苏联环境中产生的日记,它的原始真实性往往不在于表述自然真实的思想,而在于隐藏这样的思想,所以它的不真实成了它最有特色的原始真实。
1930和1940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致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帐。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1991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挡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挡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Soviet-speak)。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作出解释。”
四.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Soviet subjectivity)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作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她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了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切切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这部口述史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挡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对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挡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