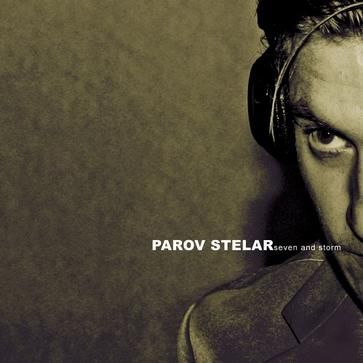《書寫歷史,書寫創傷》——在廢墟之上,寫字
這本書的名字,像是一聲低低的回響:書寫歷史,書寫創傷。彷彿兩件不同的事,被同一支筆捆綁在一起,注定要在同一張紙上掙扎。歷史學家如何面對創傷?如何把那些無法言說的痛,記在字裡行間?事件本身不是創傷,創傷是事件在靈魂里留下的裂痕,是一段不斷回返的回聲。大屠殺、戰爭、滅絕,這些極端的黑暗超出了語言的負荷。邏輯與敘事在此都顯得力不從心。幸存者無法只靠復述走出記憶的牢獄,因為創傷總是斷裂、破碎,像碎玻璃般閃爍又割人,像幽靈般徘徊不散。它困擾著活下來的個體,也困擾著後來所有的時代。
Dominick LaCapra 在書中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分野:acting out 與 working through。前者是重演,是陷入循環;後者是試圖轉化,是在承認傷口之後,借由寫作、研究或社會行動與之搏鬥。這個區分,不僅是學術的框架,更是一種倫理的選擇。他批評了幾種歧途:有的寫作把苦難轉化為救贖,好像犧牲天生應當換來光明;有的寫作冷漠如鐵,把人命化為數字,把血肉化為表格;也有的寫作自以為是,研究者代替了幸存者的聲音,卻丟掉了學者應有的距離與自省。這些寫法,無一真正承擔起對創傷的政治與道德責任。
與此同時,LaCapra 還提醒我們另一條危險的混淆:absence 與 loss 的界限。absence 指的是一種超歷史的缺席,比如“絕對的根基”從未存在過;loss 則是具體歷史中的喪失,比如親人的死亡、家園的毀滅。如果把這兩者混為一談,要麼讓具體的歷史痛苦被抽象成形而上的空洞玄談,要麼把人類反復的存在性困境縮減為單一事件的悲劇。前者抹去歷史的質地,後者喪失思想的縱深。LaCapra 的貢獻正在於,他要求我們在寫作中分辨這兩層,把缺席與喪失區隔開來,讓歷史保持重量,讓思考保有鋒刃。
書中同樣貫穿著一個核心緊張:文學與歷史的張力。歷史必須追求 referential truth——要對事實負責,要對“發生過什麼”給出檢驗與判斷。但文學,則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借虛構、隱喻與間接的敘述,觸碰創傷那不可直視的核心。LaCapra 並不是要把歷史變成小說,而是要指出:在極端事件的書寫中,歷史與文學往往彼此挑釁、互相借力。文學讓歷史學家明白單一敘事的局限,而歷史提醒文學不要陷入虛構的任意妄為。二者之間的張力,正是面對創傷時不可回避的火場。
在 LaCapra 筆下,歷史學家無法也不該假裝成冷眼旁觀的神明。進入史料的那一刻,情感與偏向便已在場,這就是精神分析所謂的“移情”。問題不在於消除移情,而在於如何處理:既不沈溺,也不否認。書寫歷史不僅是學術的技藝,更是倫理與政治的實踐。每一個字都可能是為死者作證,每一個段落都可能是向後來人交代。面對創傷,真正值得提倡的不是替代性的認同,而是帶著邊界的共情。既要靠近,又要保持清醒;既要傾聽,又要不斷反思。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讓我們理解,歷史寫作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而是被廢墟絆腳、被幽靈糾纏的行旅。它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寫下幾行字便完成了安魂。創傷不會輕易安眠,它逼迫我們一再追問:如何書寫?如何記憶?如何不讓歷史變成麻木的標本?
在當下,我們仍然被各式各樣的創傷環繞:殖民的餘燼、戰爭的廢墟、威權的陰影、疫情的裂痕。創傷不是過去,它仍在場。於是,這本書的意義不只是研究方法,而是一種姿態:在創傷面前,不要急著救贖,不要假裝冷靜,不要代替受害者說話。要寫下去,要不斷寫。寫得斷裂,寫得猶疑,寫得心驚膽顫,但寫下去。因為書寫歷史,就是書寫責任。
這是一部沈重的書,也是一部必要的書。它沒有給我們現成的答案,只留下一個艱難的命題:在創傷的陰影下,怎樣繼續寫作?怎樣既尊重死者,也對生者負責?怎樣讓文字不只是記錄,更是抵抗遺忘的火種?這是一本寫在廢墟上的書,也是一本逼迫我們凝視廢墟的書。